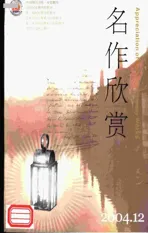对比与融合——析曼斯菲尔德《海上旅行》中的象征意义
2010-08-15赵文兰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赵文兰(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海上旅行》(The Voyage)①是20世纪初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后期优秀作品之一,写于1921年。在该作品中,女作家巧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暗示人物的潜意识暗流,展现人物心路历程的变化,可谓是不可忽视的一大亮点。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小说很少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关注。笔者认为,这个短篇无论从主题内涵,还是从艺术表现手法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尤其小说中诸如“黑暗”和“光明”等大量对比性结构构成了小说整体性的中心结构,并赋予了象征性含义。然而这种对立关系有时也并不那么绝对;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对照,而是相互依存、并融一体,旨在表现人物主体感受过程中的瞬间体验,烘托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并非偶合,而是充分表明了女作家的独具匠心。
一
像曼斯菲尔德许多其他作品一样,《海上旅行》这部小说的情节也非常简单。它讲述了一个新近丧母的小女孩儿芬内拉随祖母坐船到海对面的祖母家的故事。正如亚历克斯·考尔德(Alex Calder)所说:“《海上旅行》代表着一种恢复。它意味着接受死亡的现实,从而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慰藉……”②小说中最明显的对比存在于这次海上航行的两端:作为起点的惠灵顿码头是一片黑暗,到处充满着危险,而作为终点的芬内拉祖父母居住的小镇却明亮又温暖。故事开头对“黑暗”场景的描写似乎预示着这次海上旅行的原因,那就是芬内拉母亲的死,随后许多“黑暗”场景和“黑色”物象的描述则一直暗示着小女主人公正承受着丧母之痛。旅程结束于第二天的清晨,各种与“光亮”和“白色”相关的景色和物象则象征着芬内拉和她祖父母新生活的开始。所以说,故事前半部分的基调是阴暗而沉重的,后半部分则是明朗而欢快的。
小说是从芬内拉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小说开头的场景是在惠灵顿码头,那里皮克顿号轮船正在黑暗中等待起航。在此曼斯菲尔德用了一系列与黑暗相关的物象来开始对故事的讲述:“老码头上一片漆黑。羊毛打包房、运牛卡车、高高竖起的吊运机、微型蹲式铁路发电机,所有这一切好像是在严实的黑暗中雕刻出来的……祖母穿着咔嗒响的黑大衣,在他旁边也忙着赶路。”在芬内拉的眼中,这里的气氛似乎充斥着死亡、贫瘠和腐烂的因素:“到处是成堆的圆木,仿佛大捆黑色的蘑菇……”那个夹在父母中间边走边跳的小男孩“好像一只落在奶油上的小苍蝇”。这样,通过大量黑色场景的描写,女作家暗示出芬内拉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她失去了母亲,准备远离父亲去和祖父母居住,她的世界是一片黑暗。
在码头,芬内拉跟着父亲急忙赶着去上船,她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害怕,这里她的心绪通过码头上的灯象征性地暗示出来。“那里挂着一盏灯,但好像害怕黑暗似的,它胆怯而颤抖地闪烁着亮光。灯光好像只是为自己默默地亮着。”大人们的匆忙、父亲的沉默、祖母的焦急,所有这一切都使芬内拉的恐惧感加大。当祖母哽咽着和父亲道别时,芬内拉对大人们之间情感的表露感到有些害怕。“这场面很吓人,芬内拉马上背过身去,极力压制着没哭出声来。”另外,母亲躺在棺材里的场景一直萦绕在芬内拉心头,即使上了船,那种幽闭恐怖的感觉也一直挥之不去:“这个舱位太小了!好像跟祖母被关在一只盒子里似的。”“死亡”的阴影仍然一直伴随着她。
不过,当皮克顿号船起航后,祖孙俩显然有些安心了。“祖母不再那么伤心了,她觉得有些安慰”,芬内拉的心里也渐渐明朗起来。她们找到自己的舱位,开始了这段海上旅行,芬内拉的心路历程也进入了一个逐渐安全的境界。与黑暗、寒冷的惠灵顿码头不同,黎明中船将要驶进的港口却是那么明亮而温暖:“快要靠近码头了,它慢慢向皮克顿号船游靠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盘绳索,一匹无精打采的小马拉着一辆马车,还有一个人坐在台阶上,这些都靠了过来。”芬内拉看到了一些“小”房子,她们坐上了“小”马车,走上了通往祖母家的“小”鹅卵石路。至此,芬内拉的这次旅行把她从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的成人世界带到了她祖父母家僻静的小世界,它是一次从恐惧到安全的旅程。③
小镇上的一切在芬内拉眼中都充满着生命气息。她看到一只红色水桶,白色荷兰石竹“在清晨的空气中仍然弥漫着那种甜丝丝的味道”。这些石竹花使小女孩忘却了自身的不幸和忧伤,并暗示了她的心情已逐渐好转,重新对生活扬起了希望之帆。④一只白猫跳了下来,“芬内拉那只冰凉的小手藏在温暖的白色猫毛里……怯生生地微笑着”。祖父躺在床上,“他的头顶还剩一丛白发,一张红脸和长长的白胡子露在被子外面”。这里,“白色”给小主人公的印象不再是恐怖,而是让人愿意接近,甚至能联想到用玫瑰花和“银光闪闪”来形容。芬内拉仍然是只受保护的“小羔羊”;但是“芬内拉又笑了”。在这里小姑娘彻底完成了转变:从黑暗怪异的大城市来到了明亮温馨的小镇,从黑夜走到了白昼,她的心灵之舟也就从孤寂、荒芜的大海驶到了温馨、安全的港湾。
二
除了大量象征着“死亡”和“生命”的“黑暗”和“光明”之间的对比外,小说里还有其他的对比性描写——青春与暮年、男人与女人、手和脚、大和小、陆地和海洋、静止和运动、上船和下船等。另外,祖孙俩的这次海上旅行代表着一种危险和保护之间的对照:汹涌起伏的海水的强破坏力,以及乘客上下船等活动所具有的危险性,这一切都被起支撑和保护作用的各种物象所抵消:船上的栏杆、楼梯框、橡皮垫,还有羊毛打包房、运牛卡车、吊运机、房屋、贝壳、长沙发、床上的护栏等。这些物象似乎象征着经受丧母之痛的芬内拉在这次旅行中享受到了因为有了祖母的陪伴而带来的被保护感和安全感。⑤
尤其是,文中几次提到祖母的那把“伞把是一只天鹅头”的雨伞更具有象征性含义,构成了芬内拉从黑暗的惠灵顿海港到安全的祖父母家所经由的心路历程的不同阶段。当芬内拉背着雨伞急急忙忙赶着上船时,它“老是轻轻地触碰着她的肩膀,好像在催她快点走似的”。她们终于上了船,在这一路航程中,祖母叮嘱她“小心别让伞碰着楼梯框”。后来到了祖母家,她终于可以把伞放下让它歇一歇了,文中说到:“芬内拉又笑了,把天鹅颈的伞挂在床栏上方。”这里似乎回答了芬内拉在船上睡醒后的疑问:“哦,到头来却这么让人沮丧,要变天了吗?”就像天鹅颈的伞一样,芬内拉这艘在海上漂泊的小船也终于安全而自信地驶进了温暖的港湾。另外,故事中对人物“手”的描写也体现了“保护”性含义。比如,小说开头,一名水手向芬内拉伸出“干硬的手”把她拉上了船。后来祖孙俩上了船以后,祖母“抱着手”,祈祷着;在她的祷告结束时,她“松开手叹了口气,然后又叉在一起”,仿佛通过这些手势,就能受到上帝的庇护一样。
如果说《海上旅行》这个短篇的确包含大量的对比性描写和双重含义的话,那么特征最明显的莫过于小说的结构安排了。故事开头的两段话最具说服力。第一段主要是对惠灵顿港口一些设施的静态描写:羊毛打包房、高高竖起的吊运机、微型蹲式铁路发电机、成堆的圆木,还有一盏灯等等;而第二段则主要讲述了乘客们急忙赶着去上船的情景,显然是动态的。这样这两段话的氛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就小说整个大结构而言,小说前后两部分情节发展的几个阶段是完全吻合的,只是方向正好相反:芬内拉到达港口,从出租车下来,和祖母急忙赶着去码头,挤上舷梯,走上甲板,看到绳索落在码头上,当船起航时凝望着渐渐远去的港口,然后找到她们的舱位,将就着睡了一夜;在小说发展的后半部分:第二天早晨芬内拉醒来后,和祖母走上甲板,观察着即将接近的港口周围的风景,随着船的缓缓靠近,码头也进入了她的视线,她看到绳索抛了过来,落在甲板上,她和祖母从舷梯走下来,坐上一辆小马车,最后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祖母家。
三
那么,这个短篇小说中的对比性结构只是为了单纯地把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进行对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例如,文中是这样描绘祖母的:“她的白发像丝绸一样闪着光,背后的小髻子上包着黑色网帽。”祖母年事已高,但是芬内拉母亲的死使得这位老人不得不再担负起照顾小孙女的责任,这里“黑色”和“白色”这对相对立的物象反而在表达作者对祖母的怜悯之情方面统一了起来。另外,在船舱里,老祖母爬到上铺,而把下铺让给小孙女睡;后来睡醒后,她又触摸着从梯子上爬下来。这一“上”一“下”都暗示出祖母对芬内拉的爱。后来,船要进港了,芬内拉“单腿站着,一只脚趾头搓着另一只脚”,似乎通过两只脚的相互依存,她就能获得力量并驱走这份悲伤。另外在皮克顿号船准备起航时,芬内拉看到:“默默中漆黑的码头开始滑行,离她们渐渐远去。”船到达终点时,在芬内拉眼中,“快要靠近码头了,它慢慢向皮克顿号船游靠过来。”这两个场景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都是对立的,共同烘托了小主人公的沉重心情和茫然若失、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现实状况,无疑又是并融一体的。
正如帕特里克·D·莫罗(Patrick D.Morrow)所说,“《海上旅行》中的冲突似乎存在于芬内拉和祖母之间”⑥。不满的情绪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芬内拉不满的是母亲的位置即将被祖母所取代;而祖母怨恨的是在伺候卧病在床的丈夫的同时还得扛起养育孙女儿的重担。然而两人在那把“天鹅颈”的雨伞上达到了统一。那只小天鹅其实就象征着芬内拉;就像小天鹅没有保护者一样,芬内拉也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可以保护的人——母亲。而那把雨伞则是祖母的象征,总是时刻保护着芬内拉免受外来的伤害。如同雨伞需要支撑才能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一样,祖母也需要与芬内拉相互依靠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祖孙俩的关系是相互扶持、共同受益的。
故事结尾,芬内拉终于来到祖父母家,她欣慰地笑了。小芬内拉的到来使祖母有机会再次体验年轻时代的“金色时光”;而在这样一位走过了人生大部分旅程的“母亲”的陪伴下,芬内拉将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受祖父母乐观生活态度的感染,芬内拉不再有面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和惶惑,母亲死亡的阴影也在她心里烟消云散,她彻底从心理上接受了现在这一刻,她和祖父母之间达到了心灵的沟通和融合。
综观整个小说,对比结构构成了《海上旅行》整体性的中心结构。曼斯菲尔德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层面,对自然环境、各种物象和小说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性描述,赋予了其相应的象征性含义,揭示了小主人公芬内拉的心路历程和瞬间感受。然而,对立并非绝对,对立双方既存在于相互的比较中,又独立于其他的对照物而并存一体。这并非女作家的随意之作,而是她的精心构思,表达了女作家对和谐生活的向往。能从如此平淡琐碎的小事中给读者呈现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其精湛的短篇小说写作艺术尽显无疑。
①本文中《海上旅行》的译文引自《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杨向荣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第209页。不再另注。
②Calder,Alex.My Katherine Mansfield[A].In Roger Robinson(Ed.)Katherine Mansfield—in from the Margin[C].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Press,1994,135.
③Hanson,Clare and Gurr,Andrew.Katherine Mansfield[M].London:Macmillan,1981,97.
④赵文兰.析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意象的艺术性[J].聊城大学学报,2005,(2):112.
⑤Tytler,Graeme.Mansfield’s The Voyage[J].Explicater,Fall1991,Vol.50 Issue 1,43.
⑥Morrow,Patrick D.Katherine Mansfield’s Fiction[M].Bowling Green,OH: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19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