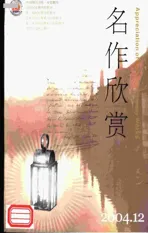哈姆莱特形象的存在主义解读
2010-08-15李小驹三峡大学文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李小驹(三峡大学文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以深刻的哲理和积极的介入意识,紧紧地把握住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脉搏,给处于荒诞世界中的人们指明了出路,因而成为当时西方几代知识分子唯一能够看到的哲学之光,对许多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存在主义文学不仅对当代和后世影响深远,而且与西方传统文学一脉相承。萨特文学作品的存在主义意识与莎士比亚戏剧反映的人类精神息息相通,前后辉映。这两个都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伟大作家,超越了时空,达到了心灵相通,共同表现了人面对着荒诞的存在,不屈服,不投降,奋起抗争,在与荒诞世界的斗争中捍卫人的尊严,实现自己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崇高主题。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无神论存在主义,它告诫世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先于本质”,要通过“自由选择”来确定人之在世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他把世界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指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它是非理性的、杂乱无章的、与人敌对疏远的、令人畏惧厌恶的世界;“自为的存在”是指人的内部世界或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它是非理性的、混沌无序的、与他人敌对隔膜的、令人憎恶的世界。“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二元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现象世界,呈现出一致性状态,萨特认为这种存在状况的本质就是荒诞。人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是孤独无助的。然而,人面对令人恶心的现实和荒诞的生存环境不能听任摆布,要通过积极的行动介入和干预生活,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确立自己的本质。“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在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他自身。”萨特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天生的英雄或懦夫,他们初来人世时都是赤条条一身清白,只是在后来成长过程中,在各种情境下,他们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行动,从而决定了自己在世为人的本质。萨特进一步说:“我们在争取自由时发现,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我不得不在争取我的自由的同时,争取别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不仅是为自己选择,而且也是为人类选择,对自己负责,也意味着要对所有人负责。选择有善恶之分,萨特主张的是“善的自由选择”,并积极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他的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萨特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意义和价值归结为人的自由和创造,这便给挣扎在荒诞中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出路——虽然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选择是自由的,那些敢于反抗黑暗现实,积极自由选择,从而创造自我本质的人,就是存在主义式英雄。①哈姆莱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式英雄。
《哈姆莱特》②(1601)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莎士比亚推陈出新,将一个中世纪流血复仇的故事,写成了一部深刻反映社会和人生的杰作。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早年在人文中心威登堡大学读书,年轻有为,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三幕一场,66页)。他有英武贤明的父王,美丽贞淑的母后,有霍拉旭这样忠诚的朋友,有奥菲利娅这样美丽的情人,他自己将来也要践登王位,可以说他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整个世界在他的眼中是美好和谐的,他对未来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然而,青天霹雳,灾祸连踵:父王暴卒,死因蹊跷;母亲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一幕二场,15页)改嫁新王小叔子了,以至“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一幕二场,11页);叔父克劳狄斯不仅篡夺了哈姆莱特应继承的王位,而且乱伦娶嫂,秽乱宫廷。这一切都给涉世未深,空怀理想的哈姆莱特以巨大的打击。在新王的统治下,整个王朝醉生梦死,纵欲贪欢,君臣经常作通宵的醉舞,国王每饮一杯美酒,便要鼓炮齐鸣,欢祝万寿;朝臣们阿谀逢迎,争向新王献媚邀宠;国内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邻国挪威蠢蠢欲动,准备对丹麦发动战争。整个国家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荒诞而丑恶的现实使哈姆莱特感到理想的幻灭,导致了他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以前“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现在在王子眼中变成“不毛的荒岬”;那“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也变成“一大堆污浊瘴气的集合”;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也不过是“泥土塑成的生命”(二幕二场,49页),整个世界成了“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一幕二场,14-15页)。“荒原”景象,触目惊心。此时,父王的鬼魂显现,向哈姆莱特揭发了奸王克劳狄斯弑兄篡位的罪行,嘱王子为其报仇。鬼魂的揭发可谓雪上加霜,给王子以更重的一击。哈姆莱特终于了解到罪恶的制造者,立志复仇。但宫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奸王的耳目和帮凶,他深深感到面对黑暗现实和所负重任的力不从心的悲愁和无奈,陷入了更深的精神痛苦之中,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一幕五场,33页)的浩叹。王子复仇的选择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道德的选择,他不仅要为自己报杀父之仇,而且要为世人“重整乾坤”。选择了目标,同时就承担了责任,而承担责任的同时,就产生了焦虑和烦恼。同时,哈姆莱特的忧愁和痛苦,是时代的忧愁和痛苦,“颠倒混乱”的12世纪的丹麦,其实就是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真实反映。
莎士比亚(1564-1616)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处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他主要经历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期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前期。为了加快资本原始积累,英国一方面利用海外贸易,大搞海盗、走私,建立海外殖民地,大肆掠夺海外财富,正如莎剧所说的“你(金钱)驱使船只在海上航行”③。与此同时,为了追逐暴利,在国内继续推行圈地运动,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致使千村辟荔,万户萧疏。莎士比亚面对这种凄惨的景象不由悲愤地喊道:“天哪!难道一个不幸的人,连一块安身之地都不能得到吗?我想他所到之处,就是地面也会从他的脚下逃走的”④。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大批农民,并不能立即变为工场或农村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四处流浪,挣扎在饥饿线上。马克思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削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⑤。为了强迫农民接受雇佣剥削,统治者借口整顿社会秩序,制定了一系列血腥立法,用鞭笞、割耳、烙印,甚至绞刑等严刑峻法惩治所谓“游民”,由于生活所迫,有些人沦为盗匪,被送上绞架。在伊丽莎白时代,每年都有三四百这样的“无赖汉”被吊死。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形象地把英国的圈地运动的这种惨状称为“羊吃人”——“羊通常是驯善的,易于满足的,但现在也变得如此贪婪和凶暴了,它们甚至吞食生人,破坏田园、房舍和城市,弄得一片荒凉”⑥。“羊”“吃人”,世界之荒诞,莫此为甚。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是一个很特殊也很复杂的时代,一方面,旧的封建势力还在为所欲为,同时,新兴的剥削阶级已经横行无忌。而克劳狄斯所代表的,正是这两种社会罪恶力量的联合体。而哈姆莱特单枪匹马地与之斗争,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⑦。在这样的时代,马基雅维里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盛行,克劳狄斯、伊阿古(《奥瑟罗》)、爱德蒙(《李尔王》)一类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野心家大显身手,一切契约、法律、道义、家庭、秩序都被破坏得荡然无存,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荒诞之中。
作为伟大艺术家的莎士比亚,他深刻体验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罪恶与荒诞,并以伟大的天才,敏锐的观察,睿智的洞见,高度的概括,在其悲剧中把世界的这种荒诞性表现出来。哈姆莱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就是“一座很大的牢狱”,而“丹麦就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二幕二场,47页)。面对荒诞的世界,哈姆莱特孤独彷徨,一时找不到为父复仇的机会和“重整乾坤”的良方,忧心忡忡,悲从中来。为了麻痹敌人,他故意装疯,用胡言乱语、嬉笑怒骂的“疯话”,来宣泄他对这个荒诞世界的仇视和恶心。恶心本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萨特曾用这种反应来表达人对环境的陌生感、恐惧感、厌恶感、孤独感等复杂的、难以名状的、不可驱遣的内心感受。哈姆莱特在经历父亲惨遭谋害,母亲投入凶手的怀抱,同学变成奸王的帮凶,恋人也成了敌人刺探自己的工具——这一切之后,不由得使他对现存世界感到憎恨和绝望:“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一幕二场,14-15页),恶心之感,油然而生。
在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等人文主义的神话破灭之后,王子面对荒诞现实,一时找不到出路,拔剑四顾心茫然,于是转向对自我深层意识的探究,开始深入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三幕一场,63页)
哈姆莱特面对着荒诞的世界,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伟大命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哈姆莱特对荒诞世界,态度鲜明,坚决拒绝。面对邪恶,他甚至想到了“以死抗争”。生有何欢,死有何惧。死亡如“睡眠”,只要能以牺牲为代价,通过斗争扫清人世无涯的苦难,就死得其所。然而,即使以死相拼就能彻底扫清社会罪恶吗?于是,便又忧郁、彷徨起来。此时,哈姆莱特尚处于“自由选择”前的焦虑期,思考多于行动,造成了行动的延宕。哈姆莱特之所以思考多于行动,是虽有行动的决心,但不知如何行动。同时,哈姆莱特对鬼魂的话也还半信半疑,“我所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加切实的证据”(二幕二场,60页)。哈姆莱特不仅要为父复仇,而且要公正地复仇。戏班子的到来,使哈姆莱特终于有了行动的机会,他巧妙地安排戏班子在宫中演出“贡扎古之死”以刺探克劳狄斯,终于验证了鬼魂的话,锁定了复仇的目标,两个敌手从此转入面对面的斗争,短兵相接,高潮迭起。先是哈姆莱特在母后寝宫误杀偷听的首相波洛涅斯,接着克劳狄斯以此为由让哈姆莱特出使英国,密诏让英王杀掉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机智地中途矫诏返国,适逢奥菲利娅的葬礼,哈姆莱特伤心欲绝,与冲动的雷欧提斯在坟场扭打,然后是全剧的高潮——宫中比剑。克劳狄斯利用鲁莽的雷欧提斯急于复仇的心理,借刀杀人,花言巧语诱骗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比试剑法,同时设下了利剑、剑刃上毒、毒酒等三重杀着,必欲置王子于死地。在此之前,哈姆莱特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逐渐摆脱了犹豫与彷徨,超越了死亡,树立了向死而生积极斗争的决心。面对奸王的一次次杀机,哈姆莱特也在一次次磨砺自己复仇的决心:“他杀死了我的父王,奸污了我的母亲,篡夺了我嗣位的权利,用这种诡计谋害我的生命,——如果我不去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五幕二场,132页)在比剑中,刀光剑影,杀机四起,王后代哈姆莱特饮毒酒而死,王子也中了雷欧提斯的毒剑命在须臾,雷欧提斯自己也中了毒剑,临死前揭发了克劳狄斯的阴谋。哈姆莱特旧恨新仇凝于剑端,终于一剑刺死了这个“败坏伦常、嗜杀贪淫、万恶不赦”的奸王,最终在临死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王子哈姆莱特的选择,是存在主义的选择,他面对荒诞的世界,不是退而逃避,而是起而斗争。尽管在斗争的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有过蹉跎和延宕,但他最终通过积极的自由选择,采取了果敢的行动,除掉了克劳狄斯——这个罪恶的渊薮,为自己确立了本质。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对存在主义哲理进行了精彩的演绎,所以哈姆莱特是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英雄。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以宣扬存在主义哲学为己任的,存在主义哲理就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核心和精华。所以,存在主义文学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观照人生,从而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哲理,是所有伟大文学的灵魂。
莎士比亚的伟大,也在于他不仅艺术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还在于他的剧作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哲理这一“高贵的养汁”(雨果语)。由于他对生活非凡的洞察和体悟,以及新时代的新思想——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深刻的哲学思想,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从而使他的剧作完成了从真实到哲学的概括,达到了在更高的境界上“反映人生”的目的。因而,他才不愧为“时代的灵魂”(本·琼生语),他塑造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才成为存在主义英雄的始祖之一,才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表达了‘世界的悲哀’的人”⑧。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辨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第9集),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③ [英]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五幕一场),《莎士比亚全集》第8集,第196页。
④ [英]莎士比亚:《辛白林》,(三幕六场),《莎士比亚全集》第10集,第205页。
⑤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4页。
⑥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6页。
⑦ [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46页。
⑧ 苏联大百科全书:《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戏剧理论论文集》(第8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