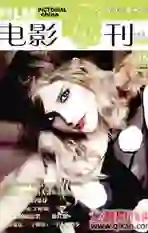暖暖夏阳里的葵花
2009-09-02肖雅
肖 雅
“我以摄影为生,家里有个宽敞的阳台。黄昏时分,斜晖映地,外头风景如水彩画般鲜艳夺目。那一年,阳子还在世。阳子是我的妻子,我很爱她。因为内分泌失调,阳子经常会歇斯底里发疯,终日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朋友们有意疏远她,我很难过,但能做的也只是极力避免触怒阳子,全心全力保护她,不受外界伤害。”
——荒木经惟《东京日和》

一
荒木经惟,日本知名写真大师,相片上小小的怪老头,两鬓怒发,带着圆圆墨镜,胸前拥抱一只细长蜥蜴。熟悉摄影的人,或者说异常迷恋声色的人,称赞他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把荒木的作品当作生活的慰藉:女体、都市、荆棘抑或捆绑中的焦虑与畅快,催生为艳丽颓靡的花朵,把白日喧闹嘈杂的东京锻造如同一座巨大欢场,夜夜纸醉金迷,笙歌无边;责备他的人,则会激烈地批判他“视奸”,用镜头任意强奸女性,并且广泛发布,引起一场群体意淫。
唯有两张简简单单的照片,躺在河边船上酣睡的女子与一双紧握在一起的手,征服了所有爱慕与唾弃荒木的人。照片一贯延续荒木的精致构图,黑白影像,宁静饱满,主角是荒木一生的爱人:青木阳子。年轻时的荒木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电通”就职,与同社女职员青木阳子恋爱,三年后,两人结婚。荒木辞去工作,成为摄影师,并自费出版了第一本摄影集《感伤之旅》。
此后的生活,阳子相伴在荒木左右,他们每日在东京吃喝玩乐与拍摄,欢愉之情,难以言表。本以为会一直这么放纵下去,但是1990年的1月27日,阳子因病离开人世。荒木在追忆阳子的《东京日和》一书中写到:“我的摄影生涯,是从遇见阳子开始的。63年入电通社,拍摄的第一幅作品就是阳子的写真。”然而伊人早逝,荒木在书本的最后伤感地记下:“至于以后,嗯,暂且打算去河边呆一阵,望碧空万里,任脚下河水安静流淌,随波飘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二
导演竹中直人为荒木的散文集《东京日和》所打动,拍摄了这部同名电影《东京日和》,影片故事尽管和书中具体内容关联不大,但仍然保留了男主人公摄影师的身份与其妻阳子的名字,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如同暖阳一般清新温柔的婚姻生活。

岛津巳喜男是一位自由摄影人,整日穿着风衣挂着相机在街道的四处游荡拍照,静止的风物、陌生人的面孔、抑或四季里细微的变幻,都是他胶卷里的常客。岛津最爱的,还是为妻子阳子拍照,美丽的阳子在镜头前手足无措地变化姿势,甜美的笑靥,深深打动岛津的心。然而和谐的生活总是难以长久,阳子在结婚的第七个年头患上歇斯底里的症状,整日焦躁不安,会与岛津的朋友发生龃龉,妄想逃离家庭,甚而把邻家的小男孩拐走并打扮成女孩子。面对阳子的怪异行为,岛津总会默默守候在她身旁,不动声色地追逐,为她解决困难,为她圆满善后,为她流泪哭泣。
看似分崩离析的家庭,若有似无的夫妻感情,随时可见的争吵与欺骗,却隐藏着不可思议的爱情。阳子介意叫错客人水谷的名字,岛津的不在意更让阳子觉得受到忽视,于是任性地离家出走并向上司撒谎岛津遭遇车祸,以小小的自尊和乖戾来报复岛津,为妻子担忧的岛津面对阳子幼稚恶意的谎言,没有去拆穿或反击,反而叮嘱阳子的上司为妻子保密,阳子归来的若无其事,令岛津愤怒却又欢欣雀跃。大雨中,阳子发现一块很像钢琴的巨石,两人快快乐乐地在上面弹奏起《土耳其进行曲》,轻松悦耳的音乐,两双洁白修长的手,像蝴蝶一样在雨中翻飞,无名指上一对闪亮的戒指,亲切地相依相偎,阳子笑得非常开心,像个骄傲的指挥家一般对世界发出号令,岛津微笑着仰望他心爱的阳子,满眼都是宠溺。
深夜里,阳子拐了邻居家的小孩去夜游,引起恐慌与动荡,岛津望着客厅桌上《土耳其进行曲》的碟片,狂奔至他们曾经嬉笑玩乐的地方,果然在曾经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找到阳子,面对发狂哭泣的妻子,岛津没有一句责备,反而是以深深的拥抱给予安慰,因为他知道阳子只是想要个孩子而已,而如果他们拥有一个孩子,阳子一定会把孩子带来这里玩耍,因为这是她和岛津之间的秘密,岛津想到这些,就觉得非常幸福。路上偶遇阳子的岛津发现一位读书的少年对阳子似乎有所倾慕,还送花给了阳子,不动声色的岛津坐在少年身旁,见他读的是国木田独步的《命运》,于是也买了这本书,在阳子面前仔细阅读,期望能引起妻子的注意或问询,岂料阳子毫无反应,岛津对此又爱又恨。在柳川,岛津去一家理发店修剪头发,竟然和年老的理发师一起睡着,醒来时,他发现不见了阳子,焦灼的岛津狂奔在乡间的小路上,峰回路转,在一处河边的小船上看到疲惫的阳子正在午睡,如同婴儿般安宁,岛津这才放任自己发泄似地大声痛哭。
风、阳光灿烂的和室、无言的藤椅、柔软行走于地的猫,还有远方电车的滴答声,在影片出现于首尾,或许还有房屋周围四处盛开的樱花,唯一不同的是,在生活最幸福的开始,岛津有阳子的陪伴,而几年之后,物是人非事事休,春日依旧,阳子不在。
想起高中时念书,正值青春年少,生活过得懵懂不知,却始终对苏轼的那首悼念亡妻王弗的词念念不忘,有时夜深人静,默诵课文,一不小心就轻轻念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句子,突觉天大地大,满心满眼都是难以自抑的伤感。后又遇到一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见他认真却又淡漠地写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几许凄恻,几许怀念,都掩映在看似平淡实则情深的句子里,中年丧妻的无措,被时光遗弃的落寞,如今,我又在《东京日和》里看到,我看到岛津和阳子在一起时疲惫却幸福的神情,我看到阳子离开后岛津茕茕孑立的身影,在微风中静静站立。
《东京日和》是一部追忆性的作品,竹中直人追忆的不是热恋时期令人心潮澎湃的激情,而是夫妻生活中含蓄到极致的爱意,无论是荒木与阳子,还是岛津与阳子,中年人的内敛与悠长,已婚夫妇的举案齐眉相濡以沫,在时间的无涯生命的仓促中,显得那么珍贵那么难得。岛津在柳川的时候,曾经很慎重很严肃地问阳子说:“别人都说我们感情好,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为何要隐瞒应该谈的东西呢,也许是太珍惜对方了吧,阳子,你快乐吗?跟我在一起快乐吗?”阳子转过头来,默默望着岛津,哀哀叹道:“别问我,我要哭了。”这是本片唯一直面情感的段落,我们却始终没有从话语或者行动上明白,岛津和阳子是否相爱,相爱有多深,这或许就是许多人的惯有思维,对于爱情,非要以文字、以数字或者物质来丈量。在《东京日和》里,岛津爱阳子的方式,是以照相机快门的次数来计算,是以沉默的关怀与无言的怜惜,来对待他一生的最爱。
有一天,岛津在街上闲逛,无意中见到下班回家的阳子,一个人款款而行在人潮中,岛津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妻子独行的美丽身影,想起:“婚后,头一次见到阳子一个人的样子,觉察到没有我,仍可生存,虽然是理所当然,仍令我血腾。”许多人不理解为何相爱的两人还要分出彼此,这显然与爱这个字眼相矛盾,而这却正是岛津尊重阳子个人自由和自尊的体现,他承认妻子拥有自我世界,允许阳子沉浸在她一个人的孤单和欢乐中。如果阳子幸福生活,岛津会乐意与她分享一切,陪伴她,和她说话、游戏或者做爱;如果阳子甘愿寂寞,岛津会为她筑起一道坚实的围墙,保护阳子脆弱的心灵,让她自我疗伤,这就是岛津爱的方式,或许只有“罐太郎”知晓呢。

荒木与阳子的一生,始终是与影像定格在一起,就像岛津与阳子的爱也是起始于摄影,现实与虚幻的两种人生重合,后者对前者的再次演绎,孰是孰非,孰好孰坏,恐怕只有当事人当时事才能辨得清说得明,但有三处惊喜,却能把现实与虚幻重合在一起,叫人久久不能忘怀。
第一处在岛津和阳子排队去看话剧的途中,有位影迷走上前来索取岛津的签名,夫妻两人既荣幸又惶恐,相视微笑,之后,影迷想与阳子握手,看似简单的情节却含蕴万千:现实中病危的阳子与荒木最感人的留念,就是荒木紧握住病床上阳子右手的那张照片。影迷与阳子的轻轻一握,既隐含世人对阳子的怜惜与尊重,对她与荒木爱情的祝福,却又暗示阳子即将会慢慢走向生命的终结。第二处是阳子安静甜美地睡在飘荡在河边的小船,蜷缩着细小的身子,面容在树阴里若隐若现,无论是荒木还是岛津,同为这美好的一刻感动,于是举起手中的摄影机,把阳子乖巧温驯恬然自得的一幕,留在最完美的风景之间。而第三处,经过导演竹中直人的巧妙安排,由荒木经惟扮演的列车员出现在影片画面之中,他站在岛津身后,微笑地看着远处阳子笑得极其开心地朝岛津奔跑过来,直到岛津能稳稳接住阳子,他才放心离去。我们在恍惚中,竟不能分辨这到底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戏庄生”,荒木、阳子、岛津三人在时间的无涯里相逢,暖暖夏阳,他们的笑容竟如葵花般充满期待和向往。
是的,如葵花一样啊,并肩而立的葵花在影片中不失时机地显露它们的微笑,在简单和室的桌上、在户外艳阳下、在阳子的双手里、在最后的镜头摇曳的微风之间笑得那样甜美,充满生机。葵花,夏日普遍的笑脸,宙斯忠贞的情人,花语为幸福就在你身边。梵高笔下浓烈的向日葵幸福地盛开在小镇腥香的泥土之上,吐着氧气泡泡,张扬旺盛的生命力,屋子里镜框中,岛津与阳子的结婚照,两人相依偎,面朝远方,就如同两朵幸福向阳的葵花。
然而有一天你把我丢了,再也找不到我,那一定是我走累了,想一个人静静,只是你还要微笑,像葵花那样,继续幸福生活。
日和,日本的一个节气,为好天气。
东京日和,是说飞蓬正茂盛,适远行,宜相爱。 [责编/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