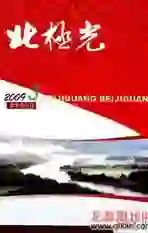作家自语
2009-06-30张连荣
张连荣
朋友要搞一个网络的文学活动,让我说一下自己的创作经历。
我是个文学的偶然涉猎者,全无成绩可言,羞于启齿。但朋友之托,难以辞命,只得就范。
小学三年级,偶然得到一本掉了皮的《说岳全传》,如获至宝,磕磕绊绊,连蒙带猜地读了好几遍。那算是最早的文学启蒙。那一年我家买了一匹白马,白马下了一头骡驹。隔年,卖了个好价钱,家里破例同意我订了一份《少年文艺》,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份杂志。
上初中,住校,学校有个阅览室,感到极大的惊喜。报纸、杂志、画报,应有尽有。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阅览室。假期则在图书馆借几本名著,读得很贪婪。那时觉得当作家十分神圣。首次见诸铅字的文字是1958年,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年代,大街小巷,穷乡僻壤的墙上都是宣传画、墙头诗,极端浪漫主义。花生之大:“剥个花生当船划”;粮垛之高:“撕片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抽袋烟”。班里有墙报,学校有壁报,我也凑着热闹。没想到市里宣传部门编的一个纸张极低劣的集子,把我的几首顺品溜也收了进去。
1960年开始,向本地报纸投稿,有时每周能发两篇,每篇能得3元稿费。自由市场窝窝头5角钱一个,在饥饿的年代,解决了大问题。
到了大学,我们的老校长,当年“创造社”三杰之一,被鲁迅先生称作“手持板斧”的成仿吾先生公开宣示:“中文系是培养专家教授,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我便觉得当专家教授比当作家更有出息,便拼命读古今中外的美学著作,读黑格尔、克罗齐、朱光潜、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卡片做了大半箱子。第一次在省报刊物露面是1966年上半年《山东文艺》,一篇批判三家村的评论文章。之后二十年做足了官样文章。
八十年代中期,因文革中受牵连,经历了一段情绪低潮。失意弄文章,认认真真写了两年中短篇小说,在《北方文学》、《小说林》、《十月》、《芙蓉》等杂志发表。累积数十万字,结成一个集子。那一段时间创作热情很高,不少报刊约稿。当时的感受是终于悟到“文无定法”,以及鲁迅说的“不要相信小说做法”之类。当完全按着情绪逻辑,完全突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羁绊写出来的东西,并得到认同,自己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如果按照当时的状况写下去,也许真的会取得点什么“成绩”,因为不乏生活积累,不乏阵地。可惜吾乃性情中人,写着写着就厌倦了,产生一种“不过如此”的想法,于是便尝试另一种生活。
有一次迟子建与我闲聊,问我退休后的打算。我说:长期受腰疾所累,趁退休前先看病。如果康复,退休后干点儿实事。如腰疾不能痊愈,也可能再写点儿东西。迟子建开玩笑:“最好治不好。”结果是经手术,腰疾有好转,但未根治。便给了我借口,不再想干实事,也不想再苦巴巴地爬格子。
现在是看NBA,搓搓麻,以免过早得老年痴呆。也有劳老伴儿这个“打手”写写博客,把值得回忆的亲身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事写下来。每个人的真实经历都是一部小说,而这些经历一定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等哪一天写个差不多了,把它们穿起来,说不定能收获点儿什么,只是别把它功利化了。
每个有点儿文化的青年都曾经是诗人。这话有一定道理。很少有在青年时代不写几首诗的。我也是。但从来未敢想做个诗人,是因为与真正的诗人距离太大。也怕,怕变不成诗圣而成为诗魔。不乏心智发育尚不成熟的年轻人,进入创作状态,陷入自造的幻影中不能自拔,抑郁者有之,自杀者有之,虽为数甚少,却也不是个案。
也是八十年代,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不少诗人。有老一代的如曾卓、邵燕祥;有中年的如周刚、王燕生、刘畅园;有苦吟派如梁南;也有田园派如傅天琳;也有被称作另类的如王家辛等等。他们先后来采风,都由我作陪。朝夕相处少则三五天,多则数周。不光谈诗,也每天将新作拿来交流,我也难免沾了几分“仙气”。
说到这里想起两件巧事。
一是文革中,我长征串连到武汉,在文联礼堂看大字报,很多是批文联主席曾卓的,其中一份长长的大字报公布了曾夫人的日记。记录在枕边曾卓向她坦陈与别人私情。我问曾卓是否确有其事?他惊奇于事情这么巧,即使武汉人也未见得看过这些大字报。即使我看了,也想不到竟能在这里遇上当事人。这是个侃快率真的老人,要不,也不会被打到胡风集团里去。
另一件事。一天下午,游船在黑龙江里缓缓而行。我和邵燕祥倚在甲板上闲聊,谈到我在北京的亲戚。邵突然拍了我一下,说:“世界并不大!”原来他竟然和我爱人的大姐,同在广播事业局同一个办公室共事过一段时间。
在一起处长了,便无话不谈。关于诗,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解读,谈的都是亲身体会。不过我记忆最深的是,我问当时刚刚在《诗刊》发表《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长篇抒情诗而引起轰动的青年诗人张学梦:“你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说写诗的诀窍。”他随即摸着自己胸前佩戴的一枚像章:“看到这枚像章了吗?看它的反面!”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很有味道,或许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感知所要表现的对象,或许还有别的含义,局外人很难确切诠释这种体会。但我觉得这么通俗的比喻比许多诗论还要经典。
张学梦很幽默。他出身不好,在一家工厂学过木匠,常常受到冷遇。他最怕的是别人冲他笑,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事求他,特别是怕别人求他做搓板,这一笑,得费他半天的休息时间。
他们每天都交流诗作,我也禁不住技痒,写了几首,分别拿给他们看,竟得到他们的首肯。有两首发表在《诗刊》上。
其后不久,本地为林业诗人出版一组诗集。我也滥竽充数,凑了几十首混在那些笔耕多年、辛勤半生的诗人朋友堆里,出了一个集子,名曰《流浪在远方》。聊以自慰的是有大半是真情,之后,再没有写诗。
我说一个真理。本地报纸、杂志及网络里一些年轻人的诗,排到《诗刊》、《人民文学》名人行列里,别人难识其劣。同理,那些名人的诗排到咱们的报刊中,也难说其优。愤青们别怨天尤人,怪只怪你还不是名人。等哪一天,一夜之间成名,把多年的退稿一古脑儿捅出去,评论家们都会说:“好诗!好诗!”
责任编辑 周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