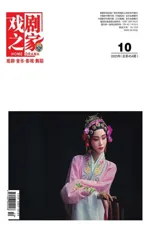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浙商创业题材影视创作
2023-09-19吴单旎
王 姝,吴单旎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4)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这一政策代表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开放。“经济上的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国际地位的回升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直接结果,经济因此成为具有某种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含义的词汇,获得了无限的豁免权,通行无阻,经济成为当代中国最大也是最具有力量的意识形态话语。”[1]改革发展背景下的创业剧正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回应,它既是对改革开放历史来路的一种回望与总结,更是对其身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艺术概括与理想依托。作为创业热土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先行示范,浙江创业题材影视作品围绕“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切片”叙事铺展开“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浙江创业史实,并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对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艺术思辨。
一、农村与城市
在电视剧《青恋》中,都市不再作为丑恶和堕落的代表,都市与农村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都市成为农村创业的精神基石,农村与城市在一体化关系中成为新的创业共同体。《青恋》展现了主人公林深的革命精神与理想,将青年创业梦、乡村振兴梦以及中国梦三者进行了融合,围绕着“两山理论”,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诉求。林深在都市创业受骗,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糟糕的生态环境和得了尘肺病的村民,遂决定争取关停村里的矿厂并留在家乡创业,寻求新的道路。都市经历让林深看到了绿色有机蔬菜的商机,也意识到了只靠采矿发展的农村经济不会长久。放弃了城市优渥的生活,林深的选择一开始受到了家人以及女朋友的不理解。断绝村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采矿,更是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使得林深的抗争多少带有踽踽独行的孤独英雄色彩。
剧中的沈聆作为投资行业的金领,也是林深的精神导师和伯乐。沈聆以她的现代都市眼光看到了林深的潜力,投资并帮助林深开展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创业项目。作为乡村的外来者,沈聆为林深带来了现代化的设备以及思想,也是林深奋斗的推动力。
如果说林深试图关掉矿场的抗争带有理想色彩,那么姚新海在剧中则是资本和经济发展下工具理性的代表。“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虽然带来了一定的自由,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1]姚新海作为村里依靠矿产发家的第一人,也是他的矿产让村里人有了收入来源,在姚新海看来,赚钱是第一目的。姚新海开办的农家乐项目由于排污超标被查封,所承包的沈聆的民宿工程项目也因擅自偷工减料、违背合同而被扣押工程款。遗憾的是,剧中对于姚新海这一人物的塑造并不饱满立体,更像是为了衬托林深这一主角的“工具人”。
二、传统与现代
更多的浙江创业题材影视剧展现了传统观念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摩擦碰撞,书写了现代商业变革的史诗。创业剧中的浙商形象往往具有积极奋进的特点,在继承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同时,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观众对于浙商形象的认同,一方面是“对于旧有的阶级叙事的一种心理反弹和对于暴富的‘成功人士’的一种心理认同……把富人阶级富有的原因归结于个人奋斗和个人才能”[2],另一方面,浙商的从商之道带有儒家思想,所传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仁、义、利的价值观念与我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心理达成了共鸣。影视剧《在远方》中的主人公姚远以及《鸡毛飞上天》中的主人公陈江河就体现了这一价值观。
《在远方》以改革开放之际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互联网以及快递业为叙事的突破口。“物流经济和电商模式,将商业模式扁平化,每个人都可以经商、都可以让自己有特长的产品迅速到达有需要的客户手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创业的人生梦想。”[3]在快递被国有管控的历史背景下,姚远作为一个快递员,结识了国营邮政稽查负责人的女儿路晓鸥,在针锋相对中两人暗生情愫,但因姚远的自卑以及路晓鸥父亲的不看好而分离。多年后两人重逢,路晓鸥帮助姚远打理公司,两人因理念不合多次争吵,路晓鸥最终离开。在创业的过程中,姚远已经初具规模的“在远方”快递公司被刘云天吞并,后来姚远振作起来再次踏上了创业的道路。
《在远方》将个人发展与时代脉搏相结合,姚远在剧中的处事方式带有传统文化色彩。“在叙述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创业史的同时,还将人物故事与时代洪流融合兼顾,把个人的创业传奇升华为时代精神的象征。”[3]剧中“非典”“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刘翔夺冠”等历史事件的穿插,既唤起观众的时代记忆,也契合了姚远命运的波折。历史事件将无数小人物的努力与奉献融汇成了时代精神。“每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实质,被称作时代精神,它是一种超脱于个人的集体意识,也是一个时代的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精神风貌。”[4]
姚远对于企业的管理也以人情和伦理为中心,带有强烈的家族色彩,曾在金融危机时死撑着不裁员。在姚远赢得人心的同时,他与路晓鸥的分歧也逐渐拉大。姚远以人情为主的家族式管理理念与路晓鸥所接受的现代管理理念不相符,同时,路晓鸥意识到姚远太过自卑,两人有着心理上的天然距离。最终路晓鸥选择离开姚远,投身心驰神往的大数据行业。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义乌人的生意经就是以传统伦理为基础,即“义”字当头。主人公陈江河是“义乌商人”白手起家的历史缩影,在个人意识背后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记忆。“鸡毛换糖”代表的“进四出六,开四门”的生意经(出门靠朋友,利润大家赚)代代相传,也是义乌经商的传统。义乌精神的背后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支撑,讲求的并非绝对利益而是人情世故。这种“和谐”以及以传统伦理观念为根基呈现的历史叙事是重构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
《鸡毛飞上天》以浙江义乌发展史为背景,讲述了陈江河从义乌传统的“鸡毛换糖”做起,学会最大利益的估价交换,在走南闯北谋求生计时遇到了一生挚爱骆玉珠,两人经过多次波折,最终走到了一起并联手创业,成立了玉珠集团。改革创业剧中的主角通常有着先见之明,并有着在尚未明朗的政策下与传统思想抗争的勇气,具有鲜明的个人意识和个人英雄色彩,甚至带上了些许未卜先知的奇异色彩。陈江河后期试图布置海外仓,打通国际市场,其海外仓的位置与今天的“一带一路”规划路线相重合。剧中每当有人询问陈江河“你是哪里人”时,陈江河每每回答“我是义乌人”,有效激发起受众的地域自豪感。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践行也带来了对现代性下工具理性的批判。《在远方》中,姚远的竞争对手刘云天作为从小生活在西方的人,显示出了极度的理性以及控制欲,甚至在与人相处中自有一套公式,在公司管理方面追求的是现代化管理制度。这种极度的理性在遇到传统人情世故后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因为疫情,刘云天、姚远、刘爱莲以及路晓鸥困于远方快递的厂房内,正是在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日常生活琐屑小事的互动逐渐瓦解了刘云天的绝对理性。解除隔离的最后一晚,刘云天与姚远喝得半醉,刘云天点明了网络普及以及全球化发展,认为物流的未来是电子商务,给姚远展现了一个广阔的未来物流市场。可以说在这一晚他们实现了朋友之间的交心,而不是对手之间的相处。
如果是路晓鸥和刘爱莲在姚远实现梦想的途中起到的是“贤内助”的作用,是情感上的寄托,那么刘云天可以说指明了姚远梦想的方向,既是导师,又是朋友,同时也是对手。在姚远重新开始并创立“新远方”之后,两人甚至是背地里的合作关系。刘云天与姚远相互成就,刘云天从一开始的全然理性到后期呈现出的人情与义气,与姚远的关系从对手到亦敌亦友。可以说,影视剧通过两人关系的变化表现了对于工具理性以及现代性的思辨探讨。“企业管理并不单纯依靠板上钉钉的制度和规则,特别是在‘东亚发展模式’中,领导人的表率作用与人情义气是企业管理、人际沟通中的重要黏合剂,这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有紧密联系,也是偏重规则与工具理性的欧美现代性之外的‘多元现代性’的有力证明。”[5]
浙江创业剧依托真实的历史背景,通过现实叙事,以积极的入世精神,书写带有儒家文化底色、以“信、义、利”为核心的从商之道,对现代理性商业准则进行了必要调整,为现代性下的地域文化重构提供了新的认同模式。
三、本土与国际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上的转折,在开放市场并加入全球化的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物欲替代不了精神家园的失落,人们在巨大的认知落差中,亟需重构民族以及地域身份的认同,这一重构是对精神文化根基的寻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原有的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经过全球化的全方位冲击,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被放大,人们需要一种方式来指认自身、回望历史并重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史’的想象,当下中国老百姓在民族国家和文化身份的认同焦虑中期待着被‘询唤’(阿尔都塞语),而询唤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功能,为当代社会每一个成员提供所能共享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和最核心的政治认同,是主流意识形态责无旁贷的使命。”[6]浙江创业剧在回顾时代故事时,其中的浙商文化以及浙江精神使受众在回望历史时能够寻求地域归属感,重建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体认同。“现代化的解放叙事和未来承诺阻挡不了人们对自己精神文化根基的回望和追寻,这种‘怀旧’式的精神文化消费,正是现代性的一种典型表现。”[1]
书写浙商的“创业史”,以平民化的底层人物为叙事中心,对应了利奥塔所说的“人们不再相信伟大、‘推动者’、伟大‘主题’,人们只运用‘小型叙事’,只相信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7]这与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中提及的地域政治问题也有着微妙的呼应。“‘地域’不仅指被排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外的边缘国家和地区,也指向生活资本主义环境下的边缘族群。”[8]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商与北方城市的国企改革、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相比,更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特点。“四个千万”精神,即“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是浙江精神的集中代表。“浙江精神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浙江人民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浙江特色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在浙商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9]在艰苦创业下形成的浙商群体是浙江精神的鲜明代表,沟通与互帮互助也成为浙江精神的注解。而浙江创作题材影视作品也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讲求实效、敢于创新”的浙江精神融于其中。浙商创业剧由此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一种象征符号”,是“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所共享的东西”。[10]浙商创业题材影视作品通过主流价值观与观众形成情感共鸣,构成了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1],立足于地域多元文化,也为浙江精神与浙江形象进行时代建构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