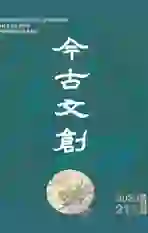反叛与归顺:浅析《西厢记》的女性意识
2023-06-15岳宏梅
【摘要】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历来被视为中国古典戏剧中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经典著作。但是在父系家族和儒教家族中,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权色彩。本文旨在以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分析《西厢记》中女性意识觉醒的局限性,揭露父权制社会下女性被压抑的历史真相和历史根源。从而探寻《西厢记》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另一种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西厢记》;女性意识;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1-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1.016
《西厢记》中崔莺莺挣脱封建礼教约束、勇敢追求婚恋自由的大胆行径历来被视为中国古典戏剧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不可否认,这确是《西厢记》反映女性意识觉醒方面的超前之处。但是多数读者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又常被它“大团圆”的结局所迷惑,忽视了崔莺莺作为女性对于父权制社会的妥协和归顺。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掌握话语权,他们往往以男性的视角和经验来评价女性的价值,将她们主要分为“红颜祸水”和“巾帼英雄”两类。无论是祸水,还是巾帼,女性都处于被动的境地。在此意义上,以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西厢记》,揭示那些被忽视的历史无意识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西厢记》中的女性境遇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颗明珠,其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批判和对女性追求婚恋自由的肯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文学史常执着于肯定其进步意义,而对其中女性意识觉醒背后的男权面孔有所忽视,从而使得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性别统治的真相被掩盖在历史叙事中。
(一)处于被看地位的崔莺莺
在男性叙事立场中,作者常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寄托在完美的女性形象上,让她们满足男性的所有期待。例如《孔雀东南飞》里美丽能干、外柔内刚的刘兰芝。《窦娥冤》中善良孝顺,勇敢刚毅的窦娥。她们的外貌形象、内在品质均符合父权社会下男性的审美标准。《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不例外,她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知书达理的品质,满足了像张生一样的风流书生对女性的审美理想。
当崔莺莺以完美的形象出现在人前时,也使得她处于被看的境遇。《惊艳》一折写莺莺,“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1]9金圣叹评:“圣叹遂于纸上亲见其翩若惊鸿,即日我将以此妙文持赠普天下才子,亦愿一齐于纸上同见双文之翩若惊鸿也”[2]41。从男性的视角来看,他们将莺莺视作一件观赏性的物品,可“尽人调戏”。文中对莺莺外貌的描写多是采用物化的方法,例如写她“檀口点樱桃,粉鼻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1]56。“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3]14-15显然,崔莺莺也是被物化的女性,时常处于被看的境遇。
(二)以“大团圆”结局掩盖女性悲剧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4]这里的“互相骗骗”大有深意。《西厢记》取材于唐代传奇《莺莺传》,两者情节大致相同,但是结局各异,《莺莺传》中的莺莺最终被张生抛弃,而《西厢记》中的莺莺得了圆满的结局。正是“大团圆”结局让部分读者认为莺莺反抗封建礼教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并非如此。王季思先生曾说:“第五本是对前四本提出的问题的解决,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要圆满解决这样的问题还缺乏现实的根据。”[5]3所以为了满足现实条件,作者在后面设置了张生高中的情节,让崔张结合变得合理。因此“作者最后表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进步思想的同时,也流露了他对封建家长的妥协。”[5]3由此可见,《西厢记》虽以“大团圆”结局收场,但是这种所谓的美好结局无非是为了掩盖父权社会对女性压抑的真相,掩盖剧中女性的悲剧命运,让反叛的女性最终归顺于父权。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来看,《西厢记》中的大团圆结局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性别谋划,即两性关系的对抗性消解,它用女性获得圆满结局来掩盖其被父权社会奴役、支配的真相。总的来说,就是将父权制社会下性别针对的暴力本质完全隐藏起来,让女性去自动扮演预定角色,自愿套入其中,听凭安排,这是那个历史时代内在化的男权文化结构的表现形式。
二、《西厢记》中女性的形象类型
“天使”与“妖妇”是西方1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所谓“天使”形象即指男性作家塑造的符合男权社会审美要求的女性;“妖妇”形象则指挑战男权社会权威的女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一种“他者”形象,这种形象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女性的独立自主性,完全臣服于男权社会,服务于男权社会,以男性制定的种种规则要求自己和其他女性。《西厢记》中崔莺莺就是典型的“天使”形象,而崔母则是典型的“绝对他者”形象。
(一)崔鶯莺的“天使”形象
崔莺莺是父权制社会塑造出的“天使”形象,她历来所受的教育让她成为了一个父权社会的合格女性。她出身名门、年轻貌美、才学出众,秉礼孝顺。遇见张生前,她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要求。遇见张生后,她虽春心荡漾,却还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直到张生用计解围,老夫人赖婚,莺莺在“情”与“礼”的矛盾斗争中,选择用儒家的“仁义”思想说服自己,与张生私下结合,以报活命之恩。她的这一举动确实是对礼教的一次挑战,展现了她不甘压抑的内心,但是她的这次挑战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崔母的严威下,她最终还是回到了父权制所秉信的礼教正轨上。崔莺莺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次勇敢的突破,也是她“天使”形象的一次蜕变,但这种蜕变并不标志着她反叛的成功。因为她与张生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父权制社会的宗法制度所认可。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6]由此可知,若张生中举,按照唐时惯例,迎娶高门之女才是他的正确的选择。崔莺莺虽为相国小姐,但是其父已亡故,家道中落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她并不是张生的唯一选择。因此长亭送别时,她对张生言:“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1]193,充分表露了她对张生变心另娶的担忧,也表现了其不得不将自己命运交予张生的无奈。崔莺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但是还是没有为自己争取到婚姻自主权,她的女性意识并没有完全觉醒,仍然充当着父权社会的“天使”形象。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父权制世界里,女性的反抗无非只有两种结局,一是死亡,二是归顺。她选择了归顺,依附于张生,靠着男性的责任感来解救自己。张生高中归来与莺莺成婚,二人结局看似是反抗的成功,实则是女性挑战父权制社会的失败。
(二)老夫人的“绝对他者”形象
此处的“绝对他者”形象,是指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女性,文中崔母就是一个典型,她是封建父权制的坚定维护者。剧中她“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1]30因此,莺莺在张生之前从未见过外男,致使她一见张生便春心萌动。当孙飞虎围寺欲强娶莺莺时,崔母称“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1]67。虽有怜惜女儿之心,但她更怕女儿被强掳去,辱没家族名声。在权衡利弊后她才接受了女儿的建议,因为许婚恩人保全名声,总好比被强盗所占。《赖婚》一折,更是体现了她对封建父权制的维护。崔莺莺早年被崔相国订下了与崔母侄子郑恒的婚约。当张生献计解了危机后,老夫人又回到了父权制的圈子,做回了恪守宗法伦理的“相国夫人”,让张生和莺莺以兄妹之礼相待,从而来维护丈夫在世时为女儿定下的婚约,维护父权社会“夫为妻纲”的传统。崔、张二人的私自结合,让她的非常不满,可木已成舟,她只好先应下亲事,但又以家中不招白衣女婿为由,提出结亲条件,即让张生上朝取应,求取功名,得了官再来娶崔莺莺。试想若张生不得官,那么将莺莺嫁予郑恒就名正言顺了。所以当郑恒诽谤张生另娶他人时,崔母从未去求证,就毫不犹豫地将莺莺许给郑恒。可见,崔母的种种行为无不体现了她对父权、夫权的维护。在父权制社会中,父权思想体现在男性身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思想将女性驯化,让她们成为维护父权统治的工具。《西厢记》中最具父权思想的父亲角色虽然缺席,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权威,因为维护父权思想的崔母代替了他发号施令。崔母是父亲角色的扮演者,但是“扮演成为一个男人,对她来说会是失败之源”[7]。她不仅以父权制为女性制定的条条框框来规范自己,而且还以此来束缚她的女儿。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看来,她已经完全舍弃了作为女性的独立人格思想,她既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又是父权制的施暴者,最终使自己成为“绝对他者”。在父权文化符号系统中女性话语权有限,因此她们所受到压迫也就不被世人所重视。“在这种父系家族中,女人只能行使公婆和丈夫的权威:她自己不是权威,她自身没有权威,她从来都不是‘她自己”。[8]作为文化符号系统的操控者,他们用婚姻、家庭、伦理等概念体系铸成华丽的枷锁,直接或间接地让女性披上,禁锢其身心。父权社会文化符号体系并没有给女性独立存在留有余地,甚至用话语权将其扼杀在历史记忆盲区,将女性自主的可能彻底抹杀。
三、《西厢记》中的女性意识形成的根源
作家在创造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内心印象的影响,使笔下的人物形象既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又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愿望。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时,同样地也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元代独特的社会文化、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作家的个人境遇,使得《西厢记》表现出了具有进步性的女性觉醒意识。
(一)元代独特的社会文化
元代独特的社会文化主要表现在各民族间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与融合。蒙古族以其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气质称霸中原后,对中原汉人的农耕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给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日常行为制定了规范准则。女性要讲“三从四德”,在夫妻關系上更是规定了“夫为妻纲”“夫荣妻贵”。而北方游牧民族,生长于辽阔的草原,追求自由率性,骨子里带着粗野与悍勇,不愿拘泥于那些牵绊人性的条框,因此他们无视礼法、淡漠人伦。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稍显宽容,男女关系自由开放。在婚俗上,突厥、匈奴、蒙古等北方民族更是与中原汉族大相径庭,《史记·匈奴列传》中便有记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9]。他们民风开放,自然率性,对女子要求不似以前严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元杂剧中出现的许多如崔莺莺一样敢于违背礼教,大胆追求婚恋自由的女性形象。元代文化具有多元性,文化氛围也相对宽松。相比于明清时期常常发生的“文字狱”,元代文人因言获罪的例子很少。这种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代文化的多元化,从而也有利于元代自由思想的形成和元杂剧的发展,元杂剧作家们才敢于自由创作,敢于想象,敢于杜撰,让元杂剧中女性人物意识逐渐觉醒,形象更为丰满。
(二)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
市民阶层作为元杂剧的接受主体,其审美情趣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也随之崛起,即“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10]到了元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商业发展,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在政策的鼓励下,元代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市民阶层既没有地主的封建思想,也没有农民的愚昧无知,他们对新鲜事物敏感而好学,见识广博而深远。”[11]元代统治者轻视教化、不守礼法的行为,对那些头脑灵活、见识广博的市民阶层影响甚大,他们渐渐与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背离,在男女关系上,不再将儒家“男女之大防”的教条奉为圭臬。加之,科举在元代被停止了八十多年,下层文人失去了取士道路,为了谋生他们组织了“书会”,与“勾栏”里的歌妓合作,为她们谱曲或创作杂剧。为了盈利,元杂剧的作者往往会设法让自己的作品满足观众的心理,尤其是满足作为观众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趣爱好。因此,他们创作出了许多儿女风情戏,而且这些戏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与那些恪守礼教的深闺女子有所不同,以此来勾起观众兴趣。因此,可以说元杂剧中的女性意识的形成与作为观众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审美兴趣密不可分,《西厢记》也是如此。
(三)作家的个人境遇
作家的个人境遇对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影响。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是许多寒门弟子改变命运、为国效力的主要途径。然忽必烈即位初,朝廷对于汉族官员建议继续实行科举制总是议而不决,使得科举停滞了八十多年。儒生们失去了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怀才不遇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的主要话语。现实残酷,前路迷茫,他们需要得到世人的认可,然现实中多是对文人的歧视和排斥,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愿景倾注于文学作品,因此在元杂剧中总会出现一些不顾一切要嫁给穷书生的女性。作者将这些女性塑造成为勇敢、有远见的完美形象,并通过她们对书生的爱慕和支持来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时代昏暗,汉族文人地位低下,王实甫作为一名儒生,同样也有切身感受和痛苦经历。因此他在《西厢记》中,让相国小姐崔莺莺与白衣书生张君瑞结合,并通过“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来表达自己对仕途顺遂、爱情美满的期许。王实甫生平常流连于风月场所,对元代下层女性的生存境遇非常了解,这也使得他的《西厢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的女性意识。但是,不论是王实甫,还是其他元杂剧作家,他们都在不觉间受男权文化的影响,将女性的自我奉献和牺牲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用一个幻想悲剧去慰藉内心诉求,得到的也终是痛苦的幻想。
综上所述,元代北方游牧民族率性自然的个性与汉族市民阶层通俗文化中的个性意识不谋而合,使元代思想活跃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儒教对女性的禁锢。加之作者为满足市场的需求和表达自己内心愿景的需要,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刻画出了许多耐人寻味、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这些女性人物渴求自由婚恋的思想也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王实甫著,金圣叹批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24.
[5]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6.
[7]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4.
[8]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M].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76.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26.
[10]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2.
[11]车勇.元曲中女性意识研究[D].延边大学,2015.
作者简介:
岳宏梅,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