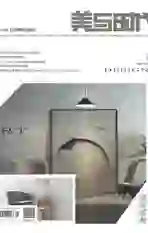当代中国城市更新中的废墟涂鸦及其问题
2023-06-06李柏乐
摘 要:近二十年来,废墟涂鸦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审美游戏,再到媒介形象的发展。现实主义废墟涂鸦作品中很明显地呈现出对城市更新中拆迁的怀疑甚至抵触。废墟空间在时空秩序中的缺席,使自身获得新的解构式的自由游戏性,城市废墟向游戏空间的意义滑动成为可能,涂鸦者们在游戏中借由涂鸦解放了自身。当下,在废墟标语图像的传播热潮中也隐含着令人忧虑的问题,如可能存在的轻浮态度、摄影式观看和超现实特征等。
关键词:城市更新;废墟涂鸦;废墟标语;摄影;媒介形象
废墟涂鸦早在21世纪初就曾因张大力的作品引起过关注,此后又沉寂多年。2020年疫情初期,一些涂鸦者们又重新被城市废墟所吸引,创作了一批与张大力的现实主义涂鸦审美旨趣完全不同的作品。本文旨在剖析现实主义废墟涂鸦与游戏性涂鸦两种不同的类型,洞察废墟与涂鸦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略谈废墟涂鸦当前的创作、媒介再现和在消费之中存在的问题。
一、废墟涂鸦与现实主义
涂鸦作为嘻哈文化四要素(MC、DJ、BREAKING、GRAFFITI)之一,在美国最初是贫民区黑人的文化反抗行为,在传入中国之时,涂鸦的具体内涵因语境的转变也发生转变。在我们早已熟悉的中心/边缘二元关系中审视涂鸦文化,似乎已无益于我们真正地直面涂鸦文化本体及其在当今的新变。剥离开人们赋予涂鸦的种种光环,涂鸦可以被定义为:在城市公共空间留下可见印记的创造性行为。涂鸦不同于墙绘,涂鸦者们选择了喷漆而非传统的画笔和颜料作为他们独特的绘画工具,其內容可以包括“数字和文字、图像符号、三维立体画或这三者的任意组合”[1]358。正如巴特对西方现代派画家雷吉肖通过创新绘画的工具和材料,突破传统绘画的编码模式,从而打破西方绘画意象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权力意识形态模式,涂鸦艺术对绘画工具和材料的丰富,也带有此类反文化的特征。
涂鸦甫一传入,其活动空间就与城市废墟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发展出了在拆迁这一现实语境下的独特的废墟涂鸦。如果我们仍简单地将涂鸦和废墟视为城市秩序的反面,则失去了一种更为开放的关系视角。伴随着城市内部的更新、拆建及城市跨越边界的蔓延,产生了如画废墟、战争废墟两种现代废墟图像模式之外的新的废墟形象——城市废墟,如拆迁地、废旧工厂、烂尾楼等。之所以将城市废墟视为不同的模式,是因为相较而言,它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它是现代资本运转中的剩余物。大卫·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认为,为摆脱资本过剩,必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断地寻找出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逻辑深深地“镶嵌”在城市化的逻辑中,这同样适用于阐释城市化所带来的废墟问题。城市废墟就是“过剩-零余”的产物,一方面,资本要不断增值,就必须不断运动,必定表现为尽可能地压缩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时间;另一方面,时间的压缩和转移范围的扩大又不得不依靠地理扩张和物流运输,因此大量资本必须转化为固定的空间性投资,以住房、工厂、基础设施等形式捆绑和固定于某地。因此城市废墟在这里应被视为更为普遍、也更具隐喻性的“剩余”。
在废墟涂鸦早期发展中,一批现实主义作品最早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最早将涂鸦引进中国内地的艺术家张大力1995年于北京创作的《对话》。人、废墟和城市的互动关系是张大力作品的主题,他以极端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城市废墟涂鸦中表达了对城市化问题的反思。巫鸿认为,张大力的涂鸦作品反映了现代城市中“毁坏”与“建设”之间的反差以及“破坏”与“保护”的双重进程[2]203。张大力通过在拆迁房屋上喷涂人头符号,向整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发问”。正在拆除中的老城与远处的大厦形成了直接的并置与对比,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这种暴力的承受者——仅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的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泯灭的主体的创伤体验。1998年,他创作了自己最为人所知的涂鸦作品——《拆:紫禁城》,从人头空洞望去,远处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角楼的屋顶。张大力在《拆:紫禁城》中发展了自己的标志性人头符号,他将喷涂在拆迁废墟上的人头凿空,更直观地展示了这种暴力与创伤。
2015年1月,上海艺术家施政和法国街头艺术家Julien Malland在上海康定路600弄共同完成了诸多废墟涂鸦作品。建筑不仅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反映,更是一种表意系统和话语方式,是一种“活着的文化形式”。康定路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承载并映射着近代上海海派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文化逻辑。艺术家团队以拆迁废墟为媒介,通过对失去了家园的孩子们的描绘,激起了与废墟两相对比之下产生的情感张力。孩童视觉形象也象征着我们对家园遥远的原初经验和共有的情感根基,体现了艺术家对城市更新中的人们被冷落和被遗忘的生活痕迹与生命体验的关切。中法艺术家协同创作的跨文化性也使作品呈现了极具特色的全球视野,表现出艺术家对全球化浪潮下的失地感以及无地方性的忧虑和无奈。正如哈维所宣告的,新的无地方性的都市环境在全球蔓延,“只要身处购物中心或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系统中,人的感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3]。这些身着世纪初中国特色服装的孩子们最终随着旧上海的“余音”——康定路600弄的铲除一并消失,而这一开始就内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中,“涂鸦,就是为了不知去向”。尽管废墟涂鸦消失了,它们仍然作为图像被保留了下来,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其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
此类客观现实联系密切,表现城市变迁中各类社会矛盾问题的现实主义废墟涂鸦作品中很明显地呈现出了对拆迁的质疑甚至抵触。已成为残骸的废墟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在城市时空秩序之外的“空壳”,既无法看见属于废墟的过去,也无法洞悉未来,主体缺位下我们不知道被伤害和破损的是什么。本雅明在他的游记《那不勒斯》中质疑了进步论,他通过对小城那不勒斯“多孔性”的阐释中集中论述了城市中新旧混杂,过去与当下、废墟与新城并置的状态。城市中正被建造的新建筑与正被拆毁的旧建筑混杂交融,在面貌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城市建设也就没有意义。他认为现代进步论建立在事物的流散和被遗忘之中,从而虚构出一条整饬的时间主流,并将自己伪装成普遍真理,让我们忽视了其虚构性的神话结构。“在本雅明眼里,那不勒斯仿佛代表了一种奇特的生产——建构的过程就是废墟的产生。在这座不断产生新生事物的迷宫中,废墟也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迷宫的各个角落,导致整座迷宫呈现出衰败的面貌。”[4]因为无论何时,城市的面貌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建构的过程也就成为了废墟产生的过程。废墟的时间是非线性的,它的重复出现呈现的不是在场而是缺席,它既是过去的重复也是未来的预演。在无尽循环的时间坐标上,新旧混杂的城市空间便无可避免地处于静止甚至退行状态。废墟对于本雅明的意义在于其再一次将历史逼迫为一个起源的时间结构,将当下爆破为废墟和碎片,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构成星丛关系的当下。本雅明在此对进步论进行了全盘的否定,使城市化变成了一个不断堆积垃圾、废墟的进程。
城市废墟是在时间中被截停的当下,它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停滞的符号,不陈述,也不发问。被压抑记忆的乌托邦潜能在时间的停顿中得以释放,从而使当下时间转变成为一个包含伦理力量的焦点时刻。在早期现实主义废墟涂鸦中,艺术家借由废墟涂鸦这一媒介完成了个体与城市的“对话”,以个体的经验和凝视将废墟这一场所带回到当下,过去与当下相互交织成为了一种“综合再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性张力。
二、作为游戏的废墟涂鸦
越来越多的涂鸦爱好者也逐渐发现了城市废墟这一重要的创作空间。废墟涂鸦创作者并不都是艺术家,一些普通的涂鸦爱好者们也乐于参与其中。涂鸦者对废墟的发现有着极为现实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当代涂鸦在中国的功能与最初在欧洲不同。当代涂鸦在中国大陆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主要由中产阶级或富裕家庭的孩子提供。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短暂的爱好;这些创造者可能会在一两年内转向其他东西。”[1]367因此,与欧美涂鸦的黑人街头文化的抵抗性起点不同,面对政府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严格管理,国内涂鸦文化的发展起初就尽量避免与主流空间之间的争夺,仅在政府为其划定的区域(如北京798园区、上海M50创意园区等)进行创作。涂鸦被降格为绘画艺术的一种类型,在语境的变迁中剥离了其应有的文化精神。
但这种丧失了秩序与破坏之间的张力的涂鸦显然损害了涂鸦的快感,另一些涂鸦者拒绝在这些特定的区域创作,轉而寻找到了一些附属于主流空间四周被人忽视的零散区域(如墙壁、屋顶、人行道等)和城市的没落空间。在这些地点中,从数量、规模及内容上看,以城市废墟空间的涂鸦为最。随着废墟涂鸦的逐渐发展,它逐渐成为了国内涂鸦的一个独特分支。在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涂鸦=反抗性亚文化”这一等式,或许将其视为宣泄人类游戏冲动的表达方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贡布里希指出了涂鸦作为权力话语实践和游戏冲动的不同:“当汪达尔人(vandal, 通常泛指文化艺术的破坏者)被一堵白墙所吸引,用原始而粗鲁的语汇在上面胡乱涂抹时,主要是为了展示他的权柄并进行某种侵犯,而涂鸦者通常愿意保有私人空间。电话旁或是会议桌上,笔记簿或文件页边的空白,都是一种诱惑。”[5]由于城市废墟与公共时空秩序的断裂,因而具有了类似于此种“私人”和“空白”的性质。城市废墟既不再隶属于某个明确的主体,也尚未被纳入到新的公共秩序中,从而成为了瓦克拉维克在《涂鸦与街头艺术》所定义的非空间,即“未经限制、不受阻碍、有待开发的区域,它们空白、孤立、被遗忘、无人经营,甚至惨淡荒凉”[6]。从时间上看,废墟既无法通向未来,又由于过去已经破碎,所以同时也不再属于过去,它承载了“悬置的时间性,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混合在一个过渡的、不稳定的时态中”[2]203。废墟空间在时空秩序中的缺位,使得自身摆脱了以稳定的时空结构为中心的被建构的不自由的状态,而获得了新的解构式的自由游戏性。
赵毅衡指出:“任何物 (或事物),都可以成为使用物—实际意义符号—艺术符号三联体,其意义在物意义—实用符号意义—艺术符号意义三者之间滑动。”[7]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指出一物的物性及其身份、时代或文化等意义已经趋近于无时,它可能被视为价值归零的垃圾,但它相应也获得了释放其艺术符号的潜能的可能性,如杜尚《泉》,西方现代艺术的垃圾美学等。城市废墟也是如此,它不再有居所或经济场所的物性,时代创伤的意义被进步的愿望不断贬抑,此消彼长之下,城市废墟向游戏空间的意义滑动成为可能。在被遗忘的真空地带——城市废墟中,涂鸦者们在游戏中借由涂鸦解放自身,获得了久违的松弛和愉悦感。
城市废墟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废墟,另一类是拆迁废墟。工业废墟由于体量等问题,一般仅被废弃而非被拆除,基本保持着封闭和完整的原始样貌,它们更多地象征着集体的历史经验。相较于拆迁废墟,它们与个体私密的情感经验与记忆更为疏离,最终形成了宏大且沉重的图景表征。两类废墟不同的空间秩序也吸引了不同的涂鸦群体。巫鸿也曾指出现代艺术家面对二者的不同态度:“面对着传统民居的消失,他们的反应往往是惆怅、内省和无助。但是当面对工业废墟时,一些艺术家则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争取把它们转变成新型的艺术空间,他们对废弃厂房的改造把自己定位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因此也使这种废墟成为前卫艺术的媒介。”[2]280如上文中提到的798艺术园区,就是经由对北京798工厂的翻新建成的中国最早由工业废墟转化而来的当代艺术空间。但这种再造是否真的让工业废墟焕发新的生命力仍然值得商榷,更多人认为此种转变是将其视为“经济链条上的可利用资源”,从而彻底抹杀了历史时间的斑斑锈迹,以现代的幻象调换了其衰败的气息中蕴含的真实经验、象征与记忆。如果重新将目光放回到废墟涂鸦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工业废墟涂鸦与拆迁废墟涂鸦的创作者之间存在的创作态度的差异。尽管在工业废墟中创作的涂鸦者们意并不在改变其原有样貌,但他们同样也不以唤醒废墟作为创作媒介的活力为目的。因此在最终的作品呈现中,涂鸦者们放弃了对废墟意义的挖掘和探索,废墟往往并不参与涂鸦主题的构成,涂鸦与废墟的互动基本限于作品及其展示场所的关系。这一点与前文所述的张大力及康定路涂鸦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
向拆迁废墟进驻的涂鸦者们则更着眼于发掘废墟空间与涂鸦的深层互动关系。拆迁废墟是由家宅空间演变而来,在巴什拉看来,“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8]5。家宅不仅是供人居住的实体空间,更关联着人的内心空间,包括记忆、人际交往、生活方式这些构成人自我认同的本质,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家宅承载并激发着记忆,同时护佑着我们在安详中做梦,反过来我们又必须通过记忆来体认家宅,在梦想中面对家宅。巴什拉认为记忆与想象二者互不分离:“双方都致力于相互深入,在价值序列上组成一个回忆与想象的共同体。”[8]4在这里,巴什拉一方面拔高了空间的意义,将其视为达到诗意的生存方式,延续了海德格尔“就人居住而言,人存在”的理路;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家宅概念的本质中根植着的内与外的辩证关系,我们借由想象家宅的庇护意义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中建构了内心空间,实现了无意识的安居和幸福。巴什拉由此论证了家宅与诗意的自然联系。拆迁废墟作为家宅破损形态的延续,同样关联着我们的内心空间,同时也开启了想象的维度。
拆迁废墟往往仍处于残存的隐蔽状态中,涂鸦者将对废墟的探索称为“城市探险”,这反映了人固有的对空间的黑暗状态和不可见性的美学迷恋。拆迁废墟与工业废墟相比,往往残存着更多的生活痕迹。在废墟中我们看颓圮的墙壁、成堆的碎石、空洞的门窗,只是对不复存在之物的凝神静观,真正激发我们想象和经验的是人类曾经在此留存的痕迹,家具、瓷砖、裸露的墙体,甚至是被丢弃在此的垃圾,只有经由这些曾在,人们才能感受到此刻的缺乏,才能想象已经成为某种遥远的过去的,共通的日常经验。总的来说,拆迁废墟对涂鸦者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踏入的不仅是单一的、具体的居所,同时也踏入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共有故乡,激发着个体生存经验的广泛共鸣。这种对拆迁废墟的内化体验,最终外化为他们在拆迁废墟涂鸦创作中呈现出的更多的感性倾向。
三、废墟标语及其媒介形象问题
涂鸦这一原本的街头互动艺术对废墟的发现和进驻,最终必然使其空间性质和意义再次发生微妙的偏移和改变,从而生产出新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后果。福柯认为,“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确保着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9],即可见性是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涂鸦对于废墟空间这一相对不可见的非空间的识别和利用,使其从非社会到社会,从黑暗性到可见性扩张,重新进入积极的生产状态和权力规训的场域。2020年初,一批以涂鸦旅行团(李翔伟、慕容亚明、盛宏达等)及其模仿者(自然男孩儿等)的作品为主的废墟涂鸦摄影在社交软件上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复制和媒介消费,并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迅速扩散和渗透。从而使废墟涂鸦进入了新的生产关系中,成为了一种精神产品和媒介形象。
与此前废墟涂鸦相比,这些废墟上的涂鸦内容变成了一些潦草的标语,如:“没有悲观的权利”“相爱吧终有一散的人们”“祝你快乐”等。其叙事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且语义更为模糊,于观者而言对所指意象的模糊体认使本就遥远的他者转化为了被陌生化的朦胧美感。我们在本文中将此类以废墟为创作空间,以标语为主要内容的涂鸦称为废墟标语。如今后现代虽然似乎已经成为了新的庸俗,但我们的美学经验仍然涌动着后现代的时代特征:小叙事的激增,对进步概念的质疑,审美的失落和空洞。一切都在坍塌,意义尚待重建。这也能概括废墟标语的审美特征。新一代废墟标语是对传统标语的形式、风格或内容的戏拟,如李翔伟的涂鸦“带走你的爱”就是对“带走你的垃圾”标语的直接改动。标语文化在中国有着强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标语往往与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流,其中红色标语在近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标语以其主题鲜明的宣传内容、简洁有力的语言风格,在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广泛的感染和号召作用,但标语所使用的煽动性和排他性的语言往往带有某些霸权和语言暴力的色彩。废墟涂鸦对标语的戏拟体现了其亚文化特征及对非官方现实的关注。尽管我们在其中能察觉到某些反讽现实的意味,实际上它并没有表现或颠覆现实世界的野心,相反它们更多地指涉自身,意在向诗性和审美的维度进发,因而成为了一种审美游戏。此外,一些废墟标语呈现出后现代式拼贴的特质。在废墟标语这一由图像和文字结合形成的新的情境化语图文本中,创作主体并不试图构建甚至在躲避严肃的终极意义,而是放任语图相互碰撞自我生成,为观者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和未定点,成为了无尽的一种能指游戏。
废墟标语被人诟病的首先是其中可能存在的轻浮态度——它似乎偏离了张大力批判现实主义的初衷,成为了可供被消费的后现代的精致的感伤,一种被浪漫化的异托邦想象。有人认为其中存在着道德伦理上的僭越和冒犯,真正的历史主体和创伤主体仍然在意义漂流中缺位和失语,我们也没有权利未经允许冒认他人的私人物体(即使是曾经属于他人的)并将其作为艺术客体。其次,废墟本身在某种程度就是一种典型的超现实体裁,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秩序之外,并获得了自主的审美价值。涂鸦者通过暗示性并置的超现实艺术方法想象并重塑了废墟的历史,使其从日常状态挣脱出来成为了偶然遭遇的奇迹。但让人怀疑的是废墟标语的超现实生产过程会不会已变成其目的本身?这种潜在的意图评判使人们怀疑废墟标语的真诚性,并指责废墟这一沉重的历史表征不应作为当下涂鸦者们个人碎片化情绪的包装。
在废墟标语中,摄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再现媒介。巫鸿在解读张大力的作品时,就曾指出废墟涂鸦经由摄影,成为独立的图像符号的隐含趋势:“一方面,它们(废墟涂鸦摄影)是艺术家从事的‘特定地点(site-specific)环境艺术计划的摄影记录;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地点计划越来越多地为拍摄照片而设计,最后以二维影像成为独立艺术作品。”[2]268除上文提到的张大力的废墟涂鸦作品、2020年初的新一代废墟涂鸦作品外,管一明主编的《非常摄影·实验报告》中冯文康的《涂鸦》系列更为鲜明地强调了废墟涂鸦的摄影作品性质。摄影既被理解为再现现实的物理刻印,也被认为是具有美学维度的艺术门类。在废墟涂鸦的摄影中,摄影作为技术手段是纪实的,但作为艺术载体,它承载着涂鸦创作者的主体观念和意识表现。就其图像叙事而言,它指涉着现实中存在的某个场景;就其审美手段而言,它是以自我指涉为基础的。在涂鸦之前,摄影的目的就早已内含于创作的过程中,这使图像从指涉事实世界的目的中解放出来,产生了以自身为目的的独立于指涉对象的新图像。
废墟标语与摄影媒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审美联系。据桑塔格所言:“摄影师最初是以捕捉城市感性的藝术家身份亮相的。”[10]57他们与城市的关系近似于本雅明的“城市漫游者”——即由收藏家、拾荒者、文人等边缘人组成的不固定的群体。游荡者不履行日常生活的基本秩序,而保持了一种自我规定的目的。摄影师与“城市漫游者”相比,他们的目光更加具有侵犯和窥探的特质,他们的兴趣“不是城市的各种官方现实,而是其污秽的黑暗角落,其受忽略的人口——一种非官方现实”[10]56。很明显,桑塔格从摄影中发现了某种超现实的特征,摄影师意在通过对现实的关注发现在日常的可见度以下隐藏的意味深长的力量。他们通过发现、聚焦和建构,将我们对日常之物的经验转移到另一个陌生化的语境中,从而使被影像截停的我们熟视如常的偶然瞬间成为一个对于接受者而言的包含惊奇和震颤的焦点时刻。
正如人们忧虑的那样,在废墟标语图像的超现实特征中,的确也存在一些尚有讨论余地的问题。对废墟标语及其图像的关注是否消耗了现实并让我们远离了现实?对于超现实主义,桑塔格和本雅明持有相反的态度,她曾强调关于摄影式观看的媒介意识——摄影的超现实特质使其与现实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半喜气洋洋,半居高临下的”[10]81态度,“世界从‘在外面被纳入照片‘里面”[10]82。布尔迪厄认为人们对摄影式观看的怀疑可能来自于摄影的行为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矛盾,摄影并不像绘画一样,需要对现实对象的长久观察和细致描绘,而是“简单地按一下按钮,便能释放出作为照相机本质特征的客观智能”[11]。也就是说,尽管摄影师身处现实,但是他们不需要介入现实就能生产影像,这种游览式描绘制造的图像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令观者进一步疏离了现实。桑塔格引用德波的景观说明摄影式观看的威胁,摄影式观看将世界视为潜在的图像,是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生产出的是以自身为目的被编码的视觉拟像。
但必须承认的是,以上提出的问题也是废墟标语摄影作为媒介形象获得广泛传播力的原因。真实的废墟场景和诗性的涂鸦文字的连缀构成了符号景观,以精致的微观叙事窥视城市的隐私,营造了浪漫感伤的对旧时的梦幻式重构,从而使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已成废墟的现实都披上了一层审美的“外衣”,隐藏了在场的编码实践。正是因为对当下兴趣的低迷,才使人们增加了对不可追回的过去的审美感觉。过去成为了难以抗拒的魅惑,怀旧成为了重塑和想象现实的方式。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被一再使用,但审美的概念始终如美学的定义一般指向不明。当我们反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究竟是在反抗审美的哪一层语义?是审美的享乐主义,超脱现实的立场,抑或对于表层现象的狂欢?我们排斥的也许正是这种人言人殊因而无法争辩的审美带来的含混,它让我们躲避了当务之急的种种问题,“在包围着我们的动荡混乱中间,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使人们“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地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12]。人们对于后现代怀旧的诘难实则凸显着对于我们失去的真实的历史感和生命体验的无能为力,我们难以面对的不只是沟壑纵横的社会历史语境,更难直面的是虚妄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含混的空洞。
回到废墟涂鸦本身,涂鸦的创作者们也意识到了自己面对的困境,李翔伟的反思切中要害:“你说你关心底层,实际上离底层很远,你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跟假想的对象博弈呢?”如果我们有能力处理他人和自身的困境,或许我们对这些问题就不会如同现在这样敏感。桑塔格在其晚年的作品《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讲道:“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不应在高人一等的超脱地位“以犬儒主义看待可能的真诚”。桑塔格动摇了她自己在《论摄影》中对景观社会的立场,她的这番自我批判或许会被视为无可奈何的妥协,但当我们以批判的立场取代对媒介奇观的消费时,也的确借由这种立场为我们并未参与到现实中去开脱。我们可能并没有比摄影师,或者本文中的涂鸦者们拥有更多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激情。桑塔格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即便它们(影像)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13]在审美过剩、视觉泛滥的时代,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旁观他人的现实和为之做出的努力,只有当我们真正地走入现实,才能找到在当下符号危机和图像时代的突围之路。
参考文献:
[1]Jeffrey Ian Ross, Routledge Handbook of Graffiti and Street Art[M].London:Routledge,2016.
[2]巫鸿.废墟的故事 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M].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包亚明.全球视野下的城市化进程[J].上海教育,2006(C2):46-47.
[4]上官燕.游荡者,城市与现代性 理解本雅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贡布里希,郑弌.涂鸦、移情与无意识[J].美术观察,2007(2):121-126.
[6]瓦克拉维克.全球视野艺术丛书:涂鸦与街头艺术[M].赵成清,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7]陆正兰,赵毅衡.艺术符号学:必要性与可能性[J].当代文坛,2021(1):49-58.
[8]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9]福柯.規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0]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1]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D].上海:复旦大学,2003.
[12]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1.
[13]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5.
作者简介:李柏乐,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图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