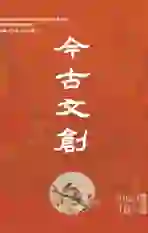《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的长江书写及其价值
2023-05-30刘九令
【摘要】 《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是竹添进一郎所著的长江书写日记,该日记以写实和文学的双重手法详细记述了长江流域的自然气候、城乡面貌、物产资源、水路交通和风景名胜,对研究中国百年前的长江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关键词】《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长江书写;竹添进一郎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6-001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04
基金项目:2021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规划项目“近代日本人对长江形象的多重建构研究”(21SKGH238)。
《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以下简称《日记》)是明治时代日本外交官、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一部日记体游记。近年来,《日记》以其优美的汉文和丰富的中国书写内容,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均没有将其作为长江书写的文本进行探究。《日记》虽然涉及了中国北方书写,但总体来说是以长江為主要路线的书写文本。竹添进一郎1876年6月22日进入长江流域的四川省,乘船沿着长江途经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最终于8月22日抵达上海。他的日记和汉诗绝大多数与长江流域相关,并且时间较早,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开创近代日本长江文学书写先河的作品。
这部《日记》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考辨扎实,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正如明治史学家重野安绎所论:“卷中记诸州,以水利为之纲,而地质、土产、漕运、纺织、阿片之患害、民物之凋敝等,触处寓慨,曲为之区画措置,一一中窾。至入陇、蜀,叙景纪胜之中,观国俗、忧民瘼之念,犹隐隐动乎楮墨间。乃经世大文章,莫作一部游记看。”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详细考察《日记》长江文学书写的内容和特色,揭示长江书写的历史价值。
一、洪炉烟雨:《日记》中的长江气候
长江位于中国中部,中游地带山水连绵,气候独特,《日记》作者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记录下了100多年前长江夏季气候特点。这一流域夏季主要特点是“雨”“热”“闷”。关于天气情况,《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记载,六月份记载最多的就是雨。如六月二十四日“阻雨”,二十五日“微雨”,二十六日“冒雨”,二十七日“微雨”,二十九日“雨”“殷雷一轰,暴雨倾注”。于是,作者在七月五、六、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皆雨。自入蜀,雨常居十之九。询之,曰:‘每岁夏天阴雨连绵。范〈记〉云‘蜀中无梅雨,未必然也。”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竹添进一郎在四川旅行过程中几乎十天中九天是雨天,于是他便开始怀疑范成大《吴船录》中“蜀中无梅雨”记载的真实性。《日记》中竹添进一郎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记录下了1876年四川省夏季气候的历史。
进入七月中旬之后,“闷热”也是长江天气的主要特征。《日记》中七月十七日写道:“宿荣昌县,夜热如蒸。”即使夜晚依旧十分湿热。七月十八日:“戴星而发,避热也。经邮亭铺,宿永川县,苦热,通夕不寐。”为了躲避炎热,他们夜晚上路,热得通宵无法入眠。七月二十八日:“绕殿多老树,阴森含风,顿忘三伏之热。徘徊移时,登舟则烈日赫赫,复在洪炉中矣。”“洪炉”即火炉,此处用“洪炉”来形容重庆夏季特点,十分恰当。由此可见,重庆“火炉”之称可以上溯到清末。八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皆阻雨。篷底闷闷,日常如年。”雨后水汽蒸发,湿气加重,又值高温,因此形成了长江夏季闷热的天气。
恶劣的天气,尤其淫雨霏霏,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体验。但是竹添进一郎却将这种天气写进了诗歌,负面的感受换变成了优美的意境。如,汉诗《成都雨夜》中写道:“帘冷香消梦后情,绵城歌管夜三更。伤心奈何天涯客,独对残灯听雨声。”“独对残灯听雨声”中的“雨声”将竹添进一郎的旅途孤寂渲染得恰如其分。《昭化阻雨》:“江城隐隐柝声沉,孤枕凄凉万里心。数尽归期闻点滴,巴山夜雨一灯深。”“数尽归期闻点滴,巴山夜雨一灯深”明显是化用李商隐的名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作者用真实的阻雨体验和中国典故相结合,其思乡之情表现得生动文雅。《天成桥上作》:“剑门疏雨散如尘,淡绿浓清点缀新。欲画不知身入画,天成桥上看山人。”“疏雨散如尘”比喻形象贴切,绝对是描写细雨的佳句。作者在该诗中将细雨中的天成桥的风景描写成了一幅清新秀丽的风景画。“栈云峡雨”中有很多和雨相关的词汇,如“微雨”“绿雨”“疏雨”“巴雨”“夜雨”“宿雨”“风雨”“雨丝”“雨声”“瘴雨”“冷雨”“潇潇雨”“骤雨”“凉雨”“听雨”等,这些词语奠定了《栈云峡雨日记》中“雨”的诗意化底蕴,同时也不经意间记录下了百年前长江流域的气候特征。
二、水村山郭:《日记》中的长江城乡
长江两岸的城市大多依山而建,或是临水而居,千百年来长江沿岸形成了独特的城乡风貌。除了我国古代的典籍,《日记》也为我们留下了清末长江流域的城市乡村的历史风景图。如,关于四川剑州的记载:“州城北负汉阳山,南面鹤鸣山。山左右合,而城适当其洼,狭而卑,其势宜攻不宜守。”作者整体勾勒出剑州城建在山涧沟壑的情景,特别从军事角度评论“宜攻不宜守”。关于重庆记述得更为详尽:“东走数十里,抵重庆府。府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蹑磴而上百八十余级,始至城门。又历九十余级,乃出街上。”竹添进一郎又依据范成大的《吴船录》记载,写下了汉诗《重庆府》:“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濛濛。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将自己亲眼见到的景象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生动表现出重庆山城的特点、所处的位置以及气候特征。诗中描述的“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濛濛”的整体形象百年未变,但是如今的重庆山风依然“带热”水却不“含毒”了,“蛮烟瘴雨”也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烟消云散。关于夔州,诗中描述道:“高城一片白云间,江汽濛濛控百蛮。腰下宝刀鸣不歇,乱山何处鬼门关。”“夔州”即奉节,白帝城所在地。“高城一片白云间”显然化用了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用诗歌刻画了夔州城高耸入云的山城形象。
关于长江两岸乡村样貌也有记录。如,《日记》七月二十三日写道:“舟入巴峡,沿岸有石山,有土山。土山率垦为田,民皆就家焉。鱼子沱北岸一小聚,人家且十余户,并在磐石上。”又:“既入两栈,山间之地,皆垦为田圃,岩缝石罅无不菽麦。”长江中上游多山,土地贫瘠,耕地稀缺,人们将土山开垦成小片农田,赖以维持生计。七月二十四日写道:“过李渡,一聚数十家,皆石上构家。石大家亦随大,不筑而基,亦一奇也。”李渡位于现在的重庆市涪陵区,据传是李白渡江之处。文中日语的“家”在汉语中是“房”的意思。涪陵地区平地少,加之贫穷,所以百姓直接将房屋建在大石头上,省去打地基的费用。在竹添进一郎看来这是十分奇特的建筑现象。七月二十九日载:“悬岩凹处或有蓄一搓土,种以谷苗,皆倒生,如头发鬖鬖下垂者。风箱峡岩上,穴居者数户,与木客相距无远矣。”并且他还将这一罕见景象纳入诗中:“上见穴居者,天半带云耕。麦禾无生意,瘦叶皆倒生。”从记述来看,当时长江居民还保存着十分原始的穴居方式,并且当地人还在悬崖上种植农作物,侧面反映了当时长江人生存环境之艰难。长江流域因其独特的地形和地质特点,形成了以山为城、凿崖为穴的独特居住样式和惜土为金的农耕习俗,这些迥然于黄河流域。《日记》中关于长江两岸独特的城乡样貌和耕作方式在其他长江游记中很少見到,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三、中国富源:《日记》中的长江物产
长江流域广阔,物产丰富,古代成都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江南亦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近代以来日本则称长江为“中国富源”。竹添进一郎对于长江流域的各种物产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关于长江上游的巴蜀物产,《日记》七月三日写道:“盖蜀地方数千里,多产金银、茶叶、煤炭、蚕丝之类,然随地气盛衰,所处亦不能无古今之异。盐源县、会理州皆属宁远,乾隆至道光出金银尤多。同治初,各坑皆废,二十年来无复兴其工者……茶树古称最多,明季荐造兵祸,斫伐无余。清兴以来,荒芜日辟,多种粳稻诸谷,获利已厚,故茶不广也……”竹添进一郎不仅写出了蜀地的物产,还介绍了物产兴衰流变,资料十分珍贵。七月十三日载:“过林江寺,宿资阳县。蜀中多产蔗。蔗有两种,紫色者少液,只供咀嚼;青者以制糖,糖价极廉。”既介绍了蜀地甘蔗的种类,又提及了价格。
蜀地产井盐古已有之,关于这一点《日记》作了大篇幅的介绍。如七月十六日写道:“路右多盐井,皆深约二三百丈,广不过尺。汲井之方,巨竹穿节,接数竿为一长筒,底施兽皮,以深插水……筒已出井,有槽乘水,以竹笕注锅中,煮之为盐,每斤七八文,至宜昌则三倍矣。”竹添进一郎详细介绍了井盐的生产流程和价格,为了解和研究当时井盐生产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关于这一点,《盐井》中也用诗化的语言进行了描述:“桶承笕送长不绝,泻入红炉鸣活活。火候渐进水气尽,无端高堆万斛雪。闻说巴东朐?井,盐水自凝形如笋。碎来万点吹不飞,咸中别带甘味永。君不见蜀江如箭石巉巉,万里不通海客帆。天心巧作生生计,海有海盐山山盐。”关于涪陵特产,汉诗《涪州》写道:“荔枝推闽中,经岁味尚美。川广虽多液,干之则瘠矣。要取其未干,健马驰千里。七日到长安,妃笑天颜喜。我来乘扁舟,溯洄涪州水。何处妃子园,日没江烟里。”据传唐代杨贵妃所吃的皇家御用荔枝来自涪州,但是到了清朝涪陵已经不再产荔枝了,《日记》中的记载也是竹添进一郎对历史的回忆。
关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物产也有介绍。如,武昌的物产:“地最肥腴,多产物,蚕丝、茶叶及棉花为之最。欧洲人买茶,多在两湖。又产煤炭,人家爨炊,其薪柴、木材取给于湖南。”长江中下游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与蜀地也有差别,尤其是棉花。更为难得的是《日记》“石首县”中还记录下了江豚的活动情况:“抵石首县……冬春水落,不至如此之迂回云。既而夕日浴波,江豚出没于紫澜漰湃之间,状酷肖花猪,但背上负一块肉如骆驼为异耳。”通过《日记》所描述江豚夕阳西下的水面上嬉戏的情景,可知在清末时江豚在长江中下游依然活跃,反映了长江生态的一个侧面。
竹添进一郎的《日记》客观介绍了当时长江流域矿产、农产品、丝织品和生活用品在内的物产,特别是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评价产业的兴衰,这对于研究长江经济发展史来说是一份可资借鉴的资料。
四、栈路峡江:《日记》中的长江交通
《栈云峡雨日记》中的“栈”指的是栈道,因此从日记的名称可以看出交通是其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广元市写道:“逾朝天岭,石磴盘空,为‘之字状。贾勇而上,前人之远者,却来在后人头上矣。盖蜀道之难在栈,而北栈凤岭为最高峻。西栈则莫过于朝天,遍山大石,皆穿百孔,自面达背,如水波冲击而成者。”正如《日记》所云,“蜀道之难在栈”,李白诗中也曾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石磴盘空,为‘之字状”可以看出石栈的高耸和形状,“遍山大石,皆穿百孔”这都是为了搭建栈道安插木桩而开凿的石孔。剑关的道路虽险但是也有修缮:“是日道路极峻险,其土赤埴而滑,坦处敷石,陂则为磴,以防颠跌。余自得剑山,步步呼奇叫快,不觉轿中倾轧之苦也。”由于道路修葺,竹添进一郎感觉不到在轿中的彼此挤压之苦。由于栈道过于危险,竹添进一郎经常下轿步行,他写道:“自入栈道,每遇高山危磴,必下轿而步,以分轿夫之劳。”并作《下轿歌》:“下山如入井,上山如升天。盘曲石为梯,岦岌马难前。轿夫跋涉云岚里,雨淋日炙无时已。昇我入井又升天,一肩积血两团紫。君不闻古圣重民力,力役三日心恻恻。又不闻良将恩如父,常与士卒同辛苦。我下轿步脚铸铁,蹈破山腹石皆裂……坦处乘轿仄处行,历尽蜀山险万变。”《下轿歌》不仅直接表现山路陡峭的状态,还通过轿夫辛劳侧面烘托道路难行。从《日记》的记载我们不仅了解当时交通的状况,也可以窥见当时轿夫这一行业辛勤劳作的场景。
除了艰险的陆路,《日记》中还记录了行走的水路情况。当时的长江水路是自然形成的,也大多十分惊险。《日记》七月二十五日写道:“将入巴阳峡,乱石堆叠,长数百丈,蜿蜒如龙,曰龙磐石。水束而逼仄,入峡益窄,若二大舟来遇,各桨相搪不可过也。”这里重点描述了巴阳峡的狭窄。而瞿塘峡的滟滪堆等江滩则更险,《日记》七月二十九日中写道:
抵瞿塘口。滟滪堆屹立于江心,嵚岈岝崿。望之如乱石层累而成者,其实一大石也,是为大滟滪。稍近北岸,双石对峙,与大滟滪遥成鼎足状者,为小滟滪。冬时水落,环堆皆石礁簇出者六七,舟曲折缝其间而行,极为危险。夏秋水涨,则并三堆皆在二丈水下矣。于水候为最好,然犹大涡汹涌,势甚急疾,舟人必随涡委曲而过……
滟滪堆、黑石滩、荒滩皆为长江上著名的险滩,不仅礁石纵横而且水流湍急、旋涡众多。作为江上的重要通道,船夫行驶到此处都心惊胆寒。位于湖北秭归的“人鲊瓮”则是另一处险滩。关于“人鲊瓮”除了用散文描述之外,还写了一首诗:
滩声怒欲卷城走,晴天雷在地中吼。
孤舟不当一叶轻,千涡万涡涌左右。
左舷桨折去无痕,右舷幸有两桨存。
迁右就左浑不定,努力撑舟抵峡亹。
宛似睢阳婴孤垒,力抗千军争生死。
又似李陵战方苦,裹创犹闻鼓声起。
忽堕涡中势不测,舟人相看惨无色。
握精投水祷江神,合掌瞑目念菩萨。
菩萨子我无宿缘,江神与人亦漠然。
竹添进一郎用诗性的语言通过人鲊瓮江流之急、行船之难、乘客之恐来表现江上行船之艰难,生动展示了当时长江的水路交通状况。新中国建立后,长江航道状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长江交通往昔风貌,我们只能借助《日记》这样的史料去想象了。
五、千里画廊:《日记》中的长江风光
长江绮丽的自然风光是竹添进一郎抒发诗情的载体。《日记》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长江两岸的美景,其文字也成为长江景观千年演变的一段重要历史记录。在一千多里的江上旅行中,多处使用“画”来形容江景之美,在他的笔下长江就是一条千里画廊。如汉诗《丰都县》中写道:“丰都一带夕阳东,树色深笼古梵宫。安得移身冥狱住,水明山绿画图中。”竹添进一郎把在夕阳下畅游丰都比喻成置身于美丽的画图中。丰都县素有“鬼城”之称,一直以阴森恐怖形象示人,而他卻将其描绘成美丽的画卷。又如汉诗《石宝寨》:“孤根拔地耸云表,天风浩浩吹不倒。绝顶现出梵王宫,十层楼阁是磴道。上方钟鼓度晨昏,画中烟水下界翻。灵境多被僧占有,乃信福地在法门。”石宝寨被誉为“世界八大奇异建筑”之一,位于重庆忠县的长江北岸,上面建有高高的楼阁,寨子上的景色倒映在水中仿佛是“画中烟水下界翻”。巫峡也有另一番画韵,汉诗《巫峡》写道:“巫峡之山高且大,峰峰直矗青天外。争奇献媚看何穷,天然一幅好画图。青则染蓝白撒盐,凿以龟坼削以铁。癯然而长毛生胫,秃然而童颔无髯。松峦相对翠屏翠,望霞还与起云媚。飞凤翩翩舞态浓,登龙跃跃鳞甲坠。”巫山十二峰高耸入云,色彩缤纷,千姿百态,是一幅独特的山景画卷。将奇峰比喻成画的还有《空舲峡》,诗中写道:“波光潋滟远涵青,无限奇峰展画屏。宛转随舟看更好,棹郎指点是空龄。”诗中将无数的奇峰比喻成展开的巨大“画屏”,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除了直接用“画”字来描述千里江景之美,竹添进一郎还用无画字之诗描绘了无数长江“画境”。如《泊施家滩》:“施家滩上泊舟时,落尽杨花听子规。山静江深天在水,一痕新月小于眉。”“杨花”即柳絮,杨花落尽时是三月份,因此诗“落尽杨花听子规”并非写实,是表达一种漂泊的羁旅之情。此种情感与“山静江深天在水,一痕新月小于眉”两句孤寂的意境巧妙结合,构成一幅独特的江上望乡图。又如《遥望洞庭湖》:“大江水与洞庭水,其间仅隔一带耳。秋江高涨一带沉,岸树点点浮如荠。湖光忽从树杪得,天邪水邪同一色。极目渺茫疑无地,龙气深蒸云梦泽。岳阳之楼在何处,欲往从之阳侯怒。君山翠黛为谁容,无人更吊湘妃墓。湖水北注江水东,江湖相会划青红。青红百里流不乱,风帆蹴破五彩虹。”这是一首写实诗,诗中描绘的是长江江水茫茫和江湖相汇的独特画面,和前诗的宁静温婉相比,该诗更加雄浑壮阔。可以说,在当时长江不同的江段呈现出处的风景和画面也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千里画廊多姿多彩的画风。
长江是一幅被描绘几千的画史,有的是用散文,有的用诗歌,有的用丹青,有的用影像。参与绘画的有中国文化人也有域外文人,而竹添进一郎就是其中之一。《日记》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用汉诗描绘了清末长江的画卷,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六、结语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日记》虽然只记录了短短两月的所见所闻,但是作者竹添进一郎以其敏锐的观察视角、深厚的文史知识、严谨的求实精神和优美的文学手法,将清末长江的历史风情片段定格在作品中,是研究中国长江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域外文献。《日记》完成后在作者的朋友圈广泛流传,特别是刊印之后,不仅对后来的长江游记创作、长江绘画创作起到了刺激作用,而且成为大正、昭和时期重要的入学考试内容,其中的汉诗还被收录到日本的汉文学史,影响广泛而深刻。特别是,作品通过长江书写在日本社会传播了长江文化,展示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独特路径。
参考文献:
[1]竹添进一郎著,周勇、黄晓东、惠科整理.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
[2]竹添进一郎著,冯岁平点校.栈云峡雨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九令,男,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