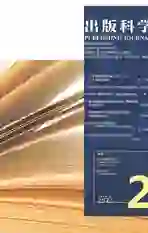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考
2023-05-30李圣杰江一帆
李圣杰 江一帆
[摘 要]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中的出版数据为研究样本,纵向梳理出版历程、横向描摹版图群像,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和活动轨迹,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关键词] 民国 日本文学 翻译出版 新文学 出版史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2-0113-08
Inspe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Books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Li Shengjie Jiang Yif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aking the publishing data in the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Translated Japanese Books and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Translated Japanese Book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study combs the publishing process vertically, depicts the group portraits of the territory horizontally, and outlines the trajectory of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offer new references on the research in publishing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民國初年,伴随着新文学运动兴起,新文学在与通俗文学的交锋中,逐步取得出版市场主流话语权,出版新文学相关出版物成为文化界与出版界的共识。为了改革旧文学、建构新文化,中国文坛开始大量译介出版域外文学著作,为新文学发展引入新的活水。这时,随着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及日本文学成功转型,西化成功的日本成为知识界的首选,作为本土文学补充的日本文学汉译出版活动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逐步从知识文化边缘运动至文化体系转型中心。一方面,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发轫者深度参与日本文学汉译出版事业,使民国时代的出版呈现浓郁的文化氛围与人文色彩;另一方面,出版界敢于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担当历史使命,展现出变革时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与爱国情怀。知识界与出版界的结盟,促使新文化催生了新出版,新出版又反哺了新文化,两者相互促进,共建了出版和文化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伴随新文学革命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思潮的深入推进,建构新式现代文学成为文学改革重中之重,域外文论、小说、戏剧等文学译作数量也随之激增。就域外文学图书国别出版量而言,《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日本文学图书种数低于俄、英、美、法4国,在这一时期域外文学图书国别数量排名中位列第5 [1]。这或许是导致日本文学译书出版研究,长期远离域外文学出版研究视野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活动是出版界和知识界对于建构中国新文学的积极尝试,它不仅对文艺思潮的引进、文学观念的转型、文体表现的新拓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作用于出版业,推动了装帧文化、品牌意识等出版文化的日益成熟。可以说,日本文学汉译图书与其他域外文学图书一起,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建,对出版文化的新旧转型与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影响甚远。
1 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活动的历史进程
本文基于香港学者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以及田雁编《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对民国时期日本文学汉译图书数量进行了统计。其中,《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是汉译日文图书统计研究的拓荒性著作,共计收录日本文学翻译图书244种;《民国时期总书目》集我国图书馆藏书目录汇编之大成,收录日本文学翻译图书344种,两版目录在学术界均具有广泛影响力;《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是出版年份最新的汉译日文图书目录著作,收录日本文学(含语言类)图书587种。上述3本目录收录的日本文学图书种数差异较大,在相互参校、剔除重复后,统计整理出日本文学译书534种。依据翻译数量可知,民国时期的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活动经历了稳步转型期(1912—1927年)、鼎盛发展期(1928—1937年)、迅速衰落期(1938—1949年)3个阶段。
1.1 稳步转型期
图书的译介出版活动服务于社会需求,如果说晚清的文学翻译以“政治改良、启发民智”为准绳,那么民国初期的文学翻译则顺应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先,出版物结构调整,选题标准发生转变。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汉译图书不仅扩充了文艺理论、戏剧、诗歌等新的文学类型,同时将既有的小说类出版物由近代通俗小说转向现代小说名家名篇。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现代剧选》《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日本的诗歌》等,都属于新文学、新思潮范畴,颇受时人瞩目。其次,出版物语言形式发生变革。不仅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且开始借鉴日本现代文文体表达,同时翻译方法也由清末的“译述”“演述”“转译”等转为提倡“宁信而不顺”的直译法。再次,日本文学汉译图书出版机构涌现。新文学、新思潮带来的出版机遇逐渐被一些善于把握时局的中小出版社发现,从1912年至1927年,先后有北平文化书社、关东出版社、启智书局、顺天时报社、中国图书公司和记、上海书店、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北新书局等20余家出版社加入日本文学图书出版事业,成为变革时代日本文学图书出版事业的排头兵。
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系统梳理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经纬,对出版界日本文学选题策划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的关系,实藤惠秀曾指出,“民国六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所提倡的新文学(一名文学革命)成功,日籍的翻译再度热烈起来,而成为这种新文学模范的确实是日本文学”[2]。显然,选题策划、出版语言及出版群体等种种变化不仅为之后的日本文学类图书兴盛奠定了根基,更是建构了日本文学类图书汉译出版事业的现代性。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未刺激中国汉译日文图书出版事业[3],但就日本文学译书而言,新文学运动显然具有界标意义。
1.2 鼎盛发展期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民国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年代。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图书出版总数达到4万种[4]。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增长,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5]。受出版业兴盛的影响,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在广度与深度上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首先,出版种数激增,结构进一步优化。鼎盛期 10年间出版的日本文学汉译图书总量为340种,年均出版量为转型期的6倍。在出版图书类型结构方面,不仅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多种新文学门类得到新增充实,而且文学理论类图书出版量大幅增长,跃居该时期日本文学译书首位。图书结构的另一个变化是出版模式由单行本向选集、丛书的发展过渡。1923年北平文化书社曾出版《芥川龙之介小说集》,1927年开明书店在此基础上增加不同体裁作品后再次出版,更名为《芥川龙之介集》,此后“选集”类型的日本文学图书不断增多,同时短篇小说集与节译的日文小说集也陆续出现。这一时期,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大江书铺《文艺理论小丛书》等均开始遴选大量日本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图书出版模式逐步多元化。为进一步挖掘图书市场购买力,出版社编译了诸如《达夫所译短篇集》《资平译品集》等以知名译者命名的翻译选集,这些销售策略为书局带来了可观的商业收益。
其次,这一时期出版物质量显著提升,出现了译本更新。据统计,鼎盛期组织更新的译本超过20余种,更新的原因在于译文过于陈旧,或因为来自第三种语言转译,或因国外出版修订本,进而产生了译本更新的市场需求。例如,1933年前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太平书店先后启动了《不如归》的重译。时人翻译家章依萍认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林雪清译本“译笔忠实而流利,实在是很完美的译本”“相比林纾的前版本高万倍”[6]。不仅如此,鼎盛期的图书装帧设计更趋美观,不仅精装本增多,译本的纸张、印刷质量均有明显改进,同时在排版上讲究图文并茂,重视封面及插图的设计,特别是《苦闷的象征》成为国内最早采用封面设计图画的文学书,推动了书籍装帧从技术手法到艺术形式的革新。鼎盛期的图书从内容到形式趋近现代出版物,推动了图书出版、发行和传播等现代出版流程的确立。
1.3 迅速衰落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全国性抗战阶段。学界普遍认为,对中国的汉译日文图书而言,战争的影响无疑是颠覆性甚至是灾难性的[7]。首先,战争对读者和译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国人在情感上对侵略战争极度憎恶痛恨,若非直接为抗战所需,是不愿热心翻译日文图书的”[8]。其次,战争导致大量老牌日文翻译图书出版社被迫搬迁或停业,日文图书出版事业几乎停摆。反映在图书数据方面,衰落期的年均译介出版图书种数为8.5种,仅为鼎盛期的四分之一,其中部分为战前版本的重印。
战时沦陷区的日本文学译书多“出自转向作家之手,为宣传日本国策或与日本国策不相抵触的东西”[9],例如林房雄宣扬“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青年》(上海太平书局、1943年)、丹羽文雄以太平洋战争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海战》(上海大陸新报社、1943年)等,这些图书公然宣扬侵略战争、鼓吹军国主义,已然沦为文化操纵的工具。战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掌控社会舆论,严禁一切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出版物出版。在艰难的战争岁月,大后方出版人始终坚持出版文化事业,先后出版了系列揭露侵略战争真相的反战文学作品,其中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最具影响力,真实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惨绝人寰的罪行。该书在大后方多次翻译出版,仅1938年一年间便先后被广州文摘社、广州南方出版社、上海杂志社3家出版社相继出版,彰显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与读者期待。
2 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活动的版图群像
2.1 出版内容
在1912—1949年间译介出版的日本文学图书中,文论以210种占据首位,其次为小说190种,两者占出版发行日本文学译书总量的3/4。
文艺理论在文学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文学启蒙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其他文学体裁,诸如小说、戏剧、诗歌等,虽可以为新文学创作提供某种借鉴,然而在文学话语范式建构、创作理论指引等方面,却远不如文艺理论直接有效,因而译介出版域外文艺理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之需。这一背景下,日本文论数量超越小说,占日本文学译书总量的40%,出版数量排名前10的作家中,有6位为文论作家,足见文论在民国时期日本文学译介出版中的强劲势头。
这一时期的文论选题全、理论性强,内容涵盖“批评与鉴赏”“文学启蒙”“文艺思潮史”“诗歌理论”“小说理论”“左翼文论”等多维论域。例如,代表性较强的“文学启蒙”著作《文学概论》,在中国学界被认为是“现代文论家和学者编写文学理论教材的范本”“带起来一股翻译外国文学理论的热潮,在20世纪上半叶好戏连台,促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型”[10]。1925—1930年6年间被3家出版社先后出版12次,影响深远。此外,其他主题同具影响力的文论,包括木村毅《小说研究十六讲》以及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等。前者是日本学界公认最早、最全面的小说理论著作,后者则是中国现代文坛了解欧洲文艺思潮的主要来源著作。这些日本文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文艺思潮与文学理论,积极推动了文学理念与创作手法的革新。
小说是民国时期日本文学汉译出版数量第二的品类,其中德富芦花的《不如归》是我国译介出版日本小说的代表性著作。作品主要讲述了日本明治时代旧式女子浪子与丈夫武男的悲情故事,其中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女性解放和自由爱情的追求崇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巨大情感冲击和思想共鸣。1908年,林纾以英译本为底本翻译了此书,进入民国后,《不如归》出现了林雪清、钱稻孙、殷雄的3种新译本。此外,小说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粤剧、新剧等,得到中国读者广泛关注与创造性接受,作为近代日本描写女性觉醒主题的文学杰作,《不如归》入选“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1]。民国时期的日本小说普遍销量较好,译书被出版社多次发行。例如菊池宽的通俗小说《第二次吻》有3个译本:国光印书局出版的葛祖兰译本、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的胡思铭译本和水沫书局出版的路鸾子译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就《第二次吻》的文学价值而论,民国文坛对其抱有怀疑,但译本的相继出版反映出商业利益与文化追求之间的平衡。
虽然戏剧、儿童文学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译介出版数量并不算多,但是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类别,这些作品依然具有影响力。1933年,中华书局曾出版发行了日本儿童文学家永桥卓介和丰岛次郎合著《世界童话丛书》;2011年,国内少儿图书发行专业机构海豚出版社重印此书,图书扉页的编者按中如此记述选编原因:“这套童话作品无论是童话的选择,还是译述的把握,都很用心,是一套耐读的优秀作品,能给每一个纯真的心灵播下善与美的种子。”[12]此外,中华书局出版的戏剧译作《日本现代剧选·菊池宽选》(田汉译、1924年)、《日本戏曲集》(章克标译、1934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鹤见佑辅散文集《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1928年)在民国也具有影响力。
2.2 作者与译者
经统计,1912—1949年间,共有151位日本作家作品译入中国出版发行,其中翻译出版图书种数两种以上的作家有85位。日本文学译书作者主要是同时期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在时间和内容上与日本学界的主流学术思潮具有同构性。
厨川白村是民国时期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苦闷的象征》《近代文学十讲》等。凭借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独特阐释,及对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渗透,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在民国时期备受好评。其中,《苦闷的象征》被中国高校用作文学理论教材,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理论的拓展以及文学学科的建设发挥了不同程度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论家很多,但研究领域各有差异,呈现百家争鸣之态势。以排名前10的文论家为例,小泉八云作为欧洲裔日本作家,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理论启蒙及比较文学研究,青木正儿则是著名的汉学家,享有“近代日本研究中国曲学的泰斗”之盛名。与此同时,宫岛新三郎以研究文艺思潮史、文学批评史见长,升曙梦则主要从事俄国左翼文学研究,其著作《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文學的曙光期》等是我国文坛了解苏俄文学的重要路径。总之,这些文论家各有特点又相互补充,翻译出版呈现繁荣有序之局面。
小说家也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出版的主要对象。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主张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其作品中的个人觉醒与个性解放意识迎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的时代主旋律。作为日本现代文坛领军人物,夏目漱石是余裕派代表作家,其作品语言风趣、笔锋犀利,内容主要关注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身份迷失与找寻,契合了“西学东渐”下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民国对他的译介出版主要集中于前期作品。谷崎润一郎文风独特,其作品意在丑与恶中捍卫美的纯粹性与独立性,在中国文坛也颇具影响力,周作人曾评价:“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13]奇特性与反叛性也是我国知识界对其译介传播的逻辑起点。可见,除与日本主流学术保持一致外,是否符合新文化、新文学时代需求也是译者的思虑重点。
上述对选题的文化取舍与译者息息相关。经统计,1912—1949年间,共计211位译者参与日本文学译书事业中,其中53位译者翻译书目达3种以上。译介出版数量排名前10的译者均为五四时期知名学者,兼具翻译家、作家、编辑出版家等多元文化身份。此外,除3位译者无相关资料外,其他译者均曾负笈东瀛。
汪馥泉是民国翻译出版日本文学图书最多的译者,其最具代表性译作便是前述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汪馥泉自1922年留学回国后,曾先后担任《现代》《学术》《文摘》等杂志主编,1928年与陈望道合作创办大江书铺,翻译出版了平林泰子《新婚》、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等一系列日本左翼作家作品,大江书铺也随之成为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出版平台之一。张资平是民国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他的新文学创作和日本文学翻译都集中在小说领域,代表性译作有《某女人的犯罪》《别宴·日本短篇小说集》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日本文学汉译出版活动的代表译者。他一生共翻译出版日本文学类图书14种,主要为文艺理论著作,翻译出版活动呈现鲜明的多元文化色彩。在翻译方面,鲁迅主张直译法,并在《苦闷的象征》《一个青年的梦》等日本文学著作汉译过程中践行了“按板规逐句、甚至于逐字译” [14]的翻译理念,引领了日本文学汉译出版物的翻译语言变革,成为众多翻译家效仿学习之模板。在选题上,鲁迅注重作品的社会功用价值,尤其喜爱那些对中国新文学建构有借鉴及补充意义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中国文学家的文化自觉。在出版发行方面,鲁迅重视图书销量与推介,展现出版人对市场的敏锐性与前瞻性。1927年《苦闷的象征》单行本发行前,鲁迅特意请来画家陶元庆为该书设计封面画,陶元庆以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的妇人人体形象为主体,采用了黑、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的线条来表现图书主题,由此开创了五四新文学图书以图案为封面的先河,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曾提到“书的销路很好,在广州连样本都卖出去了” [15]。正是源于对编辑、校对、封面装帧甚至排版技巧等流程的亲力亲为,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译者,鲁迅的翻译图书更多成为畅销书 [16]。此外,郭沫若、郁达夫、田汉、丰子恺、陈望道、任白涛、崔万秋、孙俍工、夏丏尊、谢六逸、孙百刚、钱韬孙、胡行之等也为日本文学图书翻译贡献了力量。
2.3 出版机构
在借力域外文学、建构新文学的社会思潮中,翻译文学作为文化热点,受到出版市场的关注与追捧。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思想市场是出版事业极具生产潜能的投资,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出版各种类型的翻译书籍,正如时人李泽彰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对当时译书出版热潮之描述:“自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界出书的数量大增,就中以翻译东西洋文学的书为最多,几乎出版界没有一家不出几本文学书。”[17]受此影响,日本文学类译书出版也呈现可观趋势。经统计,民国时期约有80余家出版机构参与日本文学类图书翻译出版活动。商务印书馆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周作人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等在内的78种作品。1925年创立的北新书局至1949年共出版日本文学汉译图书36种,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日本文学推介者。北新书局的“世界文学名著百种”系列,内含多部日本小说,除读者耳熟能详的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外,还翻译板垣鹰穗、丘浅次郎等稍显冷门的作家作品。开明书店由章锡琛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创立初始出版过多部理论著作,涉及日本文学共34种,以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评论》等为主要成果。现代书局自1927年创办至1935年停业,9年间出版过《拓荒丛书》《现代世界文艺丛书》,共译介出版日本文学图书27种。
除我国的出版机构外,日本出版机构对日本文学类图书的外宣和出版发挥了重要的输出作用。1938年,日本三省堂书店与华通书局经合作改组,创建三通书局。三通书局以“配合日本政府对华策略”为宗旨,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在战时,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扶植日本文学著作的汉译,妄图以此扩大在华影响力,巩固其殖民统治。
社会团体在日本文学类图书翻译出版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学术研究会和未名社。学术研究会以“研究学术、促进文化”为宗旨,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恋爱论》等知名作品均由该团体出版。未名社则是鲁迅于1925年在北京创立的文学团体,以译介域外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与出版。此外,学校、政府机构也参与了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类图书出版活动。如苏州国医学校出版林房雄小说《青年》、海军编译局出版升曙梦文论著作《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等。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部分图书是以译者个人形式出版,如葛祖兰翻译出版菊池宽《再和我接个吻》、黄宏铸翻译出版江户川乱步的《蜘蛛男》等。
3 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的特点与启示
通过对汉译日本文学图书出版历程及版图群像的考察,可发现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翻译出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阶段性发展的汉译出版历程。民国前期与后期出版的日本文学图书数量不多,大量出版集中于1928—1937年10年间。民国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日本文学汉译出版转型的契机,在经历了选题策划、出版主体及出版物语言变革转型后,日本文学迎來了鼎盛期,不仅厨川白村、本间久雄等排名靠前的作家作品得到翻译出版,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日本文学名家也有引进,即“日本近现代著名的作家、各种思潮、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大都被翻译过来了”[18]。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使得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活动全面迅速衰落。总之,民国时期的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活动在文学运动与抗日救亡的变奏中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征与复杂态势。
第二,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翻译出版主体。民国时期日本文学译者多为知名学者,身兼新文学作家、编辑出版家,如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发起人,一生创办过7个出版社、编辑9种刊物,将纯粹的文化理想投射出版行业,是文人兼任出版业的代表。有些译者为职业编辑出版工作者,如翻译《世界童话丛书》的许达年,其身份是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编辑;夏丏尊、谢六逸都是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时,完成了《芥川龙之介集》和《志贺直哉集》的翻译出版;译有《文学概论》《妇女问题十讲》的章锡琛,曾是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后来创办开明书店。有些译者的翻译活动与出版事业平分秋色,无主副业之分,如汪馥泉本人也翻译经济类书籍,不仅是文学类图书最多译者,更是翻译日文图书最多的译者[19],可以算作近代中国早期的职业翻译家。上述种种表明,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民国知识分子的谋生方式已然发生转变,在书刊商品化市场浪潮中,他们从事著译活动、投身出版事业,以知识、思想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作为职业,出版和译著成为他们谋生的归属,也是文化理想投射之所在。
第三,切合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翻译出版目的。晚清的日本文学翻译,是开发民智和政治改良的手段,而新文化运动后,民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新文学建构格外关注,使得日本文学翻译出版尤为贴合中国文学需求,即以文艺思潮的引进、文学观念的转型、文体范式的建构等为目的。因此,日本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文论,基本都围绕中国新文学建设展开,鲜有纯粹商业性消遣娱乐图书。即便是充满日本风情趣味的小说,也多强调其对文学创作观念的启发价值,比如,砚友社作家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在日本学界既是“爱而不得”的哀情小说代表之作,亦是客观描写社会“人情世态”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民国翻译引进该著作时突出强调了后者。此外,当时文论超越小说成为出版数量最多的日本文学图书类型,也反映了翻译出版者希冀为新文学话语规则建构提供有效理论指引的迫切心情。
第四,日汉直译与研究编撰同步的翻译出版方式。晚清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多以英译本为据,出版物语言使用文言文,翻译方法采用“译述”“演述”“转译”等,存在“豪杰译”“乱译”等问题。进入民国后,伴随大量留日作家学成归国,充足的翻译人才资源与日益频繁的中日交流,使得日汉对译成为日本文学汉译的主要方式。同时,在鲁迅、周作人的积极推动下,翻译方法改用“宁信而不顺”的“直译”法,强调忠实原文,且根据日语中含有大量中文词汇的特点,直接使用日语现代文词汇与文体表达,有效解决了语言转换中信息遗失问题。相较于清末,民国的译者对文本选择和语言处理显示了更多的主动性,许多译自日文的文学术语沿用至今。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译本开始附上译者或学者撰写的前言、小引、序言或后记,用以介绍作家作品,有些序言或作家评传达上万字,所言内容大多精确可靠,体现出译者对文本的深入研究。
4 结 语
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中,民国知识分子将日本文学作为向域外文学学习的主要模板之一。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日本文学著作因出版内容体裁广泛,对我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这些图书引进出版之际,日本学界的主流学术思想与文化成果得到了切实介绍,与此同时,译者们将日文中可资借鉴的词汇和文体直接译到汉语中的尝试与努力,加快了社会白话文语言变革,推动了包括出版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其次,这一时期知识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提高了出版业的社会文化口碑,推动了出版机构现代品牌意识的形成,并由此催生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此外,鲁迅、丰子恺等日本文学译者都接受过良好的美术训练,该时期风格各异的封面和插图设计丰富了图书的装帧设计语言,给出版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想。民国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与日本近代文学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在传播技术并不发达的20世纪初,实属不易。这种在时间上同时、空间上同构的特征,恰好体现民国知识分子群体极高的文化学术涵养与思想前瞻性,让日本文学图书翻译出版在民国出版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注 释
[1]《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苏俄文学译书1204种、英国文学译书794种、美国文学译书657种、法国文学606种,数量均多于本研究统计的日本文学译书534种。
[2][日]实藤惠秀著;张铭三译.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J].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10):1-28
[3]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J].近代史研究,2008(6):45-63
[4]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下册[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26
[5][14]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54,53
[6]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1
[7][19]田雁.民国时期汉译日文图书的出版:1912—1949[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2):114-129
[8][9]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84,86
[10]傅莹.外来文论的译介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译本谈起[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84-90
[11]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225
[12]许达年,康同衍.世界经典童话集[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2
[13]周作人.冬天的蝇.苦竹杂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3
[14][15]魯迅.鲁迅杂文经典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204,72
[16] 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模式:以鲁迅所译《苦闷的象征》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2017(6):85-91
[17]庄俞.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66
[18]王向远.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1):11-15
(收稿日期:202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