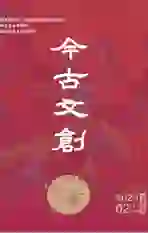浅论康德与孟子人性论之异同
2023-05-30李雪玉向永慧
李雪玉 向永慧
【摘要】 人性论作为伦理学中十分重要的理论范畴,中西方对其的研究也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而康德和孟子作为中西道德哲学不可忽视的代表,对其人性论异同的研究、对道德哲学架构的完善具有深刻意义。
【关键词】 人性论;康德;孟子;善;恶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2-005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2.018
人性论作为哲学特别是伦理学中十分重要的理论范畴,中西方对其的研究也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康德作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哲学家,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包容了善恶,认为善良意志是唯一的无条件的善;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显赫的“亚圣”孟子,集儒家之大成,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性善论”。孟子与康德分别代表中、西方道德哲学两条不同的进路,有着不同时代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思想传统、不同向度的思考方式和问题的关注点。无疑,为了更好地了解中西方伦理观念的精义、道德哲学的理论根基,现阶段对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比较研究是仍须进行的。然而,为了避免理论的理解偏颇和中西差异化语境下的误读,须先从二人各自的理论开始研究。
一、康德的人性论
受中国哲学人性论的影响,人们惯性地认为任何一种人性论都应是或善或恶,或善恶混同的,而这个理论也应是从善恶来进入的,但康德的人性论的进入是由意志自由开启的,而后才论说善恶。在康德那里,善恶判定之前需要一个逻辑前提——人具有意志,且这个意志拥有善恶的选择自由的可能。首先,人本身是具有双重性的,并且“只有一个理性存在者才能按照法则的表象,即原则来行动,或者说,才有一个意志。”[1]24就是说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之中,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受感性的物欲之恶的冲动影响,又受理性的善的感召,才拥有善恶的自由选择。其次,“善与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性的结果。因为若不然,他就不能为这二者负责,从而他在道德上就既不能是善的也不能是恶的。”[2]44既然人的意志拥有了选择善恶的权利和自由,那么人自身也须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负有责任。那么,具有双重性的人拥有意志自由,故而有了选择善恶的自由,同时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这样一条逻辑链条就完成了。然而康德的人性论究竟如何闡释人性中的善恶,从而导人向善的呢?这就需要从善与恶两个角度来看了。本质上来说,善、恶都源自有意志自由。“人自身就是其为善恶性格(性向)之原因——造成者。” [3]49就是说,意志自由使得人性善与人性恶都成为可能。
(一)以“善良意志”言善
首先,康德对人的规定性要素进行了三种划分,并称为“向善的原初禀赋”:第一种禀赋是仅有感性欲望参与的“生命性”;第二种是有理性参与但无法摆脱欲望之恶的拖累的“人性”;第三种是有理性参与同时能够负起责任的“人格性”。由于人的双重性,既可以作为感性存在追求欲望的、功利性的满足;也可以作为理性存在追求纯乎道德的善本身的实现。并且“任何人只要他在通常情况下习惯于运用理性,当我们向他举出心意正直、坚定地遵守善的原则、同情和普遍仁爱的榜样时,他都不会不期望自己也会这样思想”[4]463。就是说,这里向善的原初禀赋不仅仅是所谓的好人独有的,也不会消亡,而是恒长且普遍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之中的。这也就为偏离道德法则要求而行恶之人改恶向善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那么可以说,因人具有意志自由,且无法丧失向善的禀赋,那么人拥有善良意志就成为可能,依善良意志行善良之事也成为可能。
其次,康德认为“善良意志”必须是从“善”这一概念本身出发,就是说善良意志必然以善本身为目的,须排除一切欲望、功利的计算。并且判断一个人的具体的道德选择和行为善良与否,其标准只能是其行为的目的、动机善良与否,或者说意志是否善良。善良意志之中的“意志”既然表示一种纯然依据道德法则,即善的观念行事,而不出于任何对结果计算的人所特有的能力,那么,这里的“善良意志”的善就成为一种完全出于善良意志本身的无条件的善,道德法则就成为绝对的道德命令。综上所述,康德所说的“人性之善”是指人拥有出于善良意志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是一种无条件的善。
(二)以“根本恶”言恶
首先,同样需要以人的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作为理解“根本恶”的理论前提。“向善的原初禀赋”的论述,不仅表明了道德上行善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出了人的有限性。康德指出,“即便是最具有理性的尘世存在者,为了规定自己的任性,也可能总是需要某些自己从偏好的客体获得的动机。”[2]25就是说,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无法摆脱感性的有限性,必然无法摆脱前两种禀赋,故而自爱不可避免地越过道德法则的规制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影响。人的自由任意一旦颠倒了道德法则与自爱原则的秩序,使自爱原则凌驾于道德法则之上,恶也就产生了。
为恶的产生理清了可能性后,就需引入康德指出的人性中拥有的三种“趋恶的倾向”的表述:其一是人性的脆弱,即人在面对道德法则规制时显得软弱无力;其二是人心的不纯正,即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为一谈的倾向;其三是人心的颠倒,即接受非道德的准则的倾向。[2]28“根本恶”主要指“人心的颠倒”,即“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2]29。这种颠倒被康德称为“蓄意的罪”,是人有计划的、故意为之的自欺。明知自己在动机上是出于自私的欲念而非纯粹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却仅因侥幸在结果上未造成恶果,便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具有合法性且出于善的,自身在法则前也是清白的,并以此来掩藏自己卑劣的真实意图。这种奸诈的自欺使人不再对道德法则抱有敬重的道德情感,全然放弃了自身道德上的诉求,而仅仅将道德法则作为粉饰自身满足私欲的工具和手段。总体来看,康德更强调人的“恶”。这种“恶”是人自身有限性所致,是人性中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之间次序的颠倒。
二、孟子的性善论
对孟子而言,人的本性就是善。孟子的性善论的立足点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的例证阐明了善的行为是可以出于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意图而发生,也就证成了人之本性为善的可能性。孟子又将可以生发善行的四端具体化,认为其四端是根植于人心的,如同四肢一样是人不可分离的存在,发而外便是善行。要想深入地了解孟子的性善论的論证,就不得不从孟子与告子的四次辩论中找寻答案。同样的,对孟子如何解决恶存在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探究。
(一)以“与告子之四辩”言善
首先《告子》开篇讲杞柳杯棬之辩。告子将人之本性比作杞柳,义理比作杯盘,因柳树可以制成杯盘,便试图以类比证明可以将仁义这样的义理外在的、后天的规定于人性之中。孟子以同样类比回击:损害柳树的本性才得以制成杯盘,那岂不是要损坏人的本性才能纳入仁义。实际上,孟子是想说明仁义之义理是人性中固有的,不是外在于人的。其次是以水喻性之辩。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认为人心向善如同“水之就下”。就算有变也是外界干扰所致,并不影响向善的本性。第三是何者谓性之辩。告子言“生之谓性。”然而,天生的性质过于庞杂,会混同各种性质,从而导致非善的性质具有合法性。最后是仁义内外之辩。告子认为“食色性也”,即把人的自然之欲作为人的本性,且仁内义外;而孟子将仁义都视为人的内在根据,他提出的性善之四端,超越了自然之欲而达到了理义的高度。
(二)以“放心”言恶
首先,孟子以“放心”来讲恶的来源。所谓放心,就是迷失了仁心,恶正是根源于仁心的迷失。“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5]246因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人性天然所具备的,只要求,迷失的仁心就可以回来。
其次,孟子以“牛山濯濯”来阐释恶之根源——人为的遮蔽。因外在的砍伐放牧使得原本郁郁葱葱的牛山之木变得光秃秃的,并不能说明光秃秃是牛山的本性。同理,人性沦为兽性,也是人为的结果,而非人性本如禽兽。人心是流变的,需要人操存而长养本。
再次,是外界环境影响。“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5]244孟子认为人性之善在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也有可能被扭曲更改甚至消失殆尽。一些不利于培养“善”的客观条件,会助长欲望的增加,阻碍“善”的发展。
三、二者的比较
在理清了康德与孟子各自的人性论及关于善与恶的论述后,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就水到渠成了。总结概括了前人对其异同点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对其二人人性理论比较后的新看法。
(一)相同点
首先,康德和孟子都承认人具有双重性。康德认为人既可以是感性存在也可以是理性存在,从而既会依据理性追求道德,也会依据感性追求幸福。而孟子讲大体小体,即人性的两面,有主次、本末等价值上的区别。
其次,综合来看,二人所讲的善都是先验的、天赋的,并是内在于人的超然义理,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且判断行为是否为善的标准,就是是否出于善本身,而不是由果溯因的功利的、结果论的狡计。并将是否行善作为人禽之别的依据。康德认为人的善良意志是一种绝对的善;一行为之所以善,是因为出于善本身。而在孟子看来,人的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的发动,完全是因为心中义理的绝对命令,而并不需求之于外在的原因。四心即道德主体,先天地内在于人心之中,而四善端并非获取其他欲望结果的手段,而是绝对目的本身。
再次,二者都肯定主观因素对“善”的作用,且其所构建人性论的目的都是导人向善。康德将敬重这种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动机,由遵循道德法则的道德主体,通过自身对道德法则敬重的保持,使人行善成为可能,并通过道德法则规范行为,从而不断地导人向善。而孟子强调人作为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道德行为的主体,也应当发挥道德主体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牛山之木”之例,还是“求放心”都提倡人须自觉地寻求完成善的复归。且孟子指出“人皆可为尧舜”,认为人只要不断自觉地发展自己的良善天性和良好品德,每个人都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总的来说,其二者都认为,只要人们自觉地依义理、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仅对于个人层面道德修养的提高有所助益,而且在社会层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二者都认为克制私欲、遵循善的法则可以得到更高层次的快乐。在康德理论中,道德动机因道德法则排斥感性冲动并贬损一切爱好,故而敬重情感之于情感方面只能是否定性的,并必然导致痛苦情感的产生。但是康德指出,因为道德法则消除来自主观爱好上的自大,亦即使自己本性的感性偏好与这法则相比较而感到谦卑,所以道德法则在对主体的感性有否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唤起了主体对道德法则对意志有一种肯定性的促进作用的情感——敬重。这种敬重情感脱离了感性层面,是一种超然的、升华了的理性愉悦。而对于孟子而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296这种遵循义理而产生的道德实践所带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甚至是更高的快乐。
(二)不同点
首先,二者对于恶的规定不同:康德认为恶是先天的,是一切人先验的人性结构,都是不可改变、不可规定的;而孟子认为恶是后天的,且恶是某些人特殊性格对善之本性的偏离。康德通过“自由意志”的设定,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上的主体性,人为善为恶都将成为自己自由的选择而必然对其负有责任。而孟子的人性是直接从善开始的,以善来定义人性,恶是对善的丧失,需要求其取善复归。
其次,虽然二者的道德动机都是诉诸主体道德情感的,但对道德动机的规定不同:康德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道德动机就是“敬重”,任何感性的情感都是被排除在外的;而孟子举四端为道德情感,将情感与行为和为一体。两种道德动机比较起来,显然康德对道德情感的规定更加严格,更倾向于理性主义的要求。而康德贬抑除敬重以外的道德情感,是为了避免有条件的善(只具有合法性而不包含道德性)的行为。如对孺子将入于井而因恻隐、同情而产生的善行,虽符合帮助弱者的道德法则,却受到了同情心与见义勇为的爱好的影响,行为内含有了偶然的情感因素,即不是以单纯的帮助弱者为先在意愿与目的而实现的行为。而因敬重没有任何经验情感的目的掺杂,根本地还原了道德法则所做出的要求,那么意志也就成为“善良意志”,通过他的行为就含有了道德性。而孟子认为道德动力就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本性中,并更多注重使道德动机从政治层面、经验层面能够得以宣扬和施行便已足够。而“尽心、知性以知天”作为孟子提出的道德实践的模式,显然,对于孟子而言,天人的通路只需反求诸己而已矣,本心就已全备,只需解蔽使其朗现即可。
再次,虽然二者都强调应按照天赋的超然法则行善,但道德实现的道路不同。康德的道德哲学很难摆脱自由的悬设而自明,故而难逃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限制,对现实的、具体的人也提出了理性的前设条件,从而使得现实的实践指导意义并不显著,逐渐从人学走向了宗教学;而孟子更加肯定了社会良好规范的意义,关注点更加落到了政治的、社会的层面,诉诸礼乐来教化之,使人行善有了成圣的功利目标,较之更具有体验派的实用性。这个层面上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别,即西方哲学更加注重概念的明晰、逻辑的严谨、体系的完整;而中国哲学更加关注政治的、教化的、价值的层面。
四、结语
简言之,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和孟子虽然属于不同的文明和时代,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对人性论有不同关注重点:前者强调自由意志和道德动机,后者则提倡人性善和道德教育。然而,二者对善的不断追求应是人类精神的重要价值,且在关注人性论、弘扬人文精神等方面仍有相似之处,这一点依旧值得后人重视并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牟宗三.原善论[M].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4]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孟子著,赵清文译注.孟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李雪玉,女,新疆石河子人,宁夏大学法学院伦理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德哲学。
向永慧,女,宁夏固原人,宁夏大学法学院伦理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