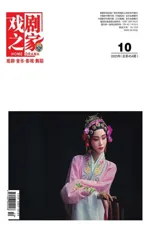推开音乐材料的门进入谭盾“风与鸟”的创作世界
2023-04-12谭婧雅
谭婧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这部作品基于传统帕萨卡利亚体裁的创作特点——固定低音与变奏的手法进行结构创作,总体上来看仍是变奏曲式,但从音乐材料的使用角度上来看,却明显体现着“呈示(5—78)——展开(79—135)——再现(136—176)”的三分性特点②,并以原型四音列为本源,展开了对国乐灵魂的追寻③。
一、原型四音列Y
此部作品在首调唱名法的前提下,以C、B、A、#F四音所构成的下行四音列作为核心进行变化创作。此四音列实则具有类似于动机的功能,也是此曲的本源所在。为方便区分变体,在此将其简称为原型Y。
作为此曲的核心,其具有极大的可变性。第一,从四音列的产生上来说,四音列对于调式调性的确立并不具有完整音阶那样的优势,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部作品中存在着多处双调性并置的地方,原因也在于此。第二,笔者认为四音列的听觉色彩更多取决于四个音之间的音程协和关系以及四音的发声顺序。在原型Y中存在的音程关系有框架音,减五度;相邻两音,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相隔一音,小三度、纯四度。以四音之间的音程协和关系来说,协和与不协和音程的比例为1:1,虽然在基于框架的不协和音程影响下,听觉色彩主色调偏冷,但考虑到实际应用于作品中的原型Y常以顺次发声形式出现,并以此为前提进行四音列和谐程度的分析,可以得到相邻两音之间每次增加一个半音且音响的听觉色彩经历了不协和至不完全协和的过程,使得四音列的听觉色彩游离于冷暖之间。因此,在原型Y的基础上进行加音变化时,听觉色彩在冷暖之间的可变性机会几乎是对等的,也带给了这个四音列在听觉色彩上更多变化的可能。
以原型Y出现的位置来看,除了在引子1—4小节出现具有呈示作用之外,在呈示部分的首5—12小节、尾75—78小节以及再现部分的首140—159小节位置均有出现。在呈示部分中,它处于首尾位置,其出现之前的音乐材料均为作曲家模仿鸟鸣的自制电子音乐,即“微信音乐”,在实际使用中带有即兴性质的音乐材料使得此处的呈示部分以首尾呼应的方式体现出了一定的再现意味。而在再现部分中,它几乎占据了再现部分一半的小节数并且只出现在前半部分,再现部分中的它并无首尾呼应。
以配器的角度来看,它通篇仅出现于两个竖琴声部,主要以竖琴Ⅰ为主奏声部,且在声部纵向的功能安排中属于色彩性伴奏。每当它出现的时候,纵向的配器安排上,声部安排较少或音色较为单一,因此能够看出作曲家企图以此种方式赋予原型Y及竖琴声部角色的含义,即本源或作曲家所构建的风与鸟的世界里自然的含义。
二、原型的变体
(一)变体A
变体A首次出现于5—12小节的长号声部。以此处为例,变体A是将原型Y全部以附点二分音符这样的长音形式保留于强拍强位,在弱拍弱位加入E、G、D三音形成了听觉色彩偏冷、带有淡淡的忧郁之感的七声利底亚调式音阶之后,通过将E换成G音的同尾换头的方式得到的8小节旋律。总体以跳进的方式进行原型Y相邻两音之间的连接,对相邻两音之间的跳进音程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同尾换头的部分,其余都是以四度向下跳进的方式进入原型Y后三音的,改变了原型Y第一次出现时小节之内均衡的时值关系,旋律线条的起伏感增强,并且以滑奏的方式减弱跳进关系带来的跃进感,使得横向的线条发展更显平滑流畅,但旋律线发展走向总体趋势向下,乐句的气息感仍旧绵长,也是听觉色彩偏冷的原因之一。
变体A在整部作品中共出现11次,其中9次为8小节,1次为9小节,1次为5小节,即在全曲179小节中共有86节都可看到变体A的“身影”。因此,它是重要的旋律材料之一,虽然其会因配器的需要,以不同乐器进行演奏而出现于不同的声部,但并不影响它处于主题层的位置。
(二)变体B
变体B首次出现于43—50小节处的定音鼓声部。以此处为例,变体B是经由在原型Y各音之前加入时值为八分的弱起音,后连接四音列中的各音进行八分同音重复并以断奏方法进行演奏而形成的。变体B为8小节,而后4小节是对前4小节的完全重复。旋律线条的总体发展趋势由总体向下转变为总体向上,并在向上之后进行直线保持,转折变化明显,转折所占时间短,凸显了分明的变化棱角。
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突出了弱起音与原型Y各音连接时的跳跃感。在音程的跳跃后连接相对静止状态的同音反复是对于变体B中跳跃感的第一个保证。而对于给弱起音加入重音符号,将原本由弱至强的力度变为由强至强,且结合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的音频中在此处同音反复部分均进行渐弱的力度处理来说,这是对于跳跃感的第二保证。变体B的跳跃距离,由减五度开始,然后逐渐缩小至小三度,紧接着直接回到减五度。首尾的跳进均是三全音的跳进,辅以断音的奏法,极大增强了听觉上的紧张感,使得变体B成为三种主要变体中紧张感最强的变体。在整部作品中,变体B处于伴奏层的位置,且作曲家将变体B进行了如51—54小节的弦乐组配器上的声部拆分变奏、如91—94小节的弦乐组同声部上加入和音的变奏等等,使得变体B拥有了自己的变体分支。变体B及其分支的出现占据了整部作品的132个小节,扮演了整部作品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伴奏层动力角色。
(三)变体C
变体C首次出现于87—90小节的长笛声部,应为8小节旋律,但变体C与变体B相同,后四小节基本完全模仿前四小节进行创作。以此处为例,变体C与原型Y在形态上已经相去甚远。但此时的原型Y各音均出现在每小节第一拍后半拍的第一个音位,因此变体C实际是以原型Y各音作为起始音进行模进写作的产物。旋律线的走向、跳进的幅度、相对固定化的节奏模型,都与变体C起始的87小节大致相同。相比较于原型Y,变体C的每一单位拍内的音符密度明显增加,速度也更快,加之断奏、跳进以及旋律高点时的重音记号,这些都使其听觉色彩更偏向暖色调。而且变体C同变体B一样拥有自己的演变分支,如107—110小节的弦乐声部即是变体C的演变分支。在整部作品的64小节中都能够看到它及其演变分支的存在,因此它及它的变体也是主要的旋律层材料之一。
三、原型及变体的关系
三个变体虽然都脱胎于原型Y,但其与原型Y之间的关系却亲疏有别,而笔者认为三个变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略,原因如下:
变体A作为第一个出现的变体,其与原型Y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入了跳进的部分,以及将四音列补充至七声音阶体现出完整的调式调性。不论是从旋律的组织形态、旋律性横向的发展走向、四音列音符所选用的时值,还是从旋律的“性格”特点等方面来看,它都是与原型Y最接近的变体,也可以说是由本源所衍生出的第一产物,并兼有本源产生的相对立个体之一的含义。
变体B因其仅由原型Y的四音构成,本应与原型Y的关系更近,但它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对于变体A中与原型Y区别最大的跳进部分进行了更好继承,并通过将变体A中的先静止后跳进的旋律写作方式改变,为了先跳进后进入同音反复的相对静止进行了更进一步发展。并且考虑到其与变体A在听觉感受上的对比关系,即与变体A的关系更近于原型Y,成为由本源所衍生又与变体A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第二产物,且与变体A形成了对比,兼有本源产生的相对立个体之一的含义。整部作品也是主要在变体A、B的不断对立中完成了呈示与展开两个部分,以及对变体C的引入铺垫。
变体C,通过采用与原型Y以四音列作为起始后接入其他音的相同方式进行写作,而保留了与原型Y的关系,但从其他如听觉感受、单位拍内的音符密度等方面,以及在旋律第4小节以原型Y#F音作为起始音进行模进时,#F音前方加入了过渡音增强了与第3小节的联系,因此而模糊了原本的模进关系来说,属于距离原型Y关系最远的变体。它与变体A也是如此,在旋律气息长短、旋律“性格”、跳进的使用频率以及速度等方面,它均与变体A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旋律气息很短,几乎每一小节都留有一个气口,旋律“性格”活泼,跳进使用频繁将变体B中的相对静止也抹去了,这些都使得它与变体B的关系更为接近。所以,笔者认为它应产生于变体A与B的对比发展过程中。
通过对比变体与原型以及变体与变体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远近,我们能够看出在速度、单位拍内的音符密度、听觉色彩、旋律“性格”等许多方面,变体的三者之间更多呈现出了常见变奏形式之间多方面的递进关系。在听觉色彩方面经历了由冷变暖的过程,在旋律线条方面经历了由斜坡向下发展逐渐转变至激烈的曲线型向下的过程等等,这些都是乐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原型Y发展至变体C实则就是在经历由简入繁的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看出变体A、B作为形成对比的两方,扮演了作品发展过程中“矛与盾”的角色,并且体现出矛盾在事物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细数其中,看似可能是单向的发展脉络,实则内里又隐藏着与本源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材料组织架构
通过对表1进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表1 ④
(一)横向的递进与纵向的并置
通过上述对于原型Y及其变体之间的演变关系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整部乐曲在材料使用上呈现出了明显的递进关系,即由原型Y逐步递进发展至变体C。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作曲家基本通过纵向的材料并置而引出新材料。并且从递进关系来看,材料的整体架构实际体现了“起承转合”的构思方式,在并置关系中至多出现三个材料的并置。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原型Y从未与变体C进行过并置。
(二)循环的“假象”
以主要作为旋律声部的变体A与变体C为参照物,对全曲的小节进行分析,我们能发现全曲中存在着一些循环的“假象”。如在43—54小节,即变体B第一次出现的位置,此处的变体A与变体B相差4小节出现,因此变体B的第一次出现不是由变体A与B进行并置而实现新材料引出,实则主要是通过“微信音乐”来实现的,过程为“微信音乐”——变体B(4小节)——变体A。回顾变体A的引出过程,即“微信音乐”——引子(4小节)——变体A。变体B作为伴奏层材料,在此处与引子相似的是都仅有一个乐器进行演奏,并且加之此处的速度进行了改变这一条件,因而容易使人进入变体B前四小节实为连接材料的听觉陷阱之中,最终被“微信音乐”——引子或变体B——变体A的循环“假象”所迷惑。
(三)再现部分的减缩
再现部分中原型Y及变体均有出现,在纵向声部关系中多为三个材料的并置,但原型Y与变体C仍然没有产生交集。除了再现部分起始原型Y滞后于变体A出现之外,可以说全曲的发展过程都被浓缩在了此部分当中,也是整部作品的“缩影”。
注释:
①在徐嘉艺《复古与趋新——谭盾〈风与鸟的密语〉帕萨卡利亚创作研究》一文中,将此归结为“四音列核心细胞”。
②源于徐嘉艺《复古与趋新——谭盾〈风与鸟的密语〉帕萨卡利亚创作研究》。
③在由首席ELITE发起,题名为《谭盾,风与鸟的永恒守望》的采访视频中,谭盾曾说:“中国国乐中有一种灵魂,就是它永远在寻求跟大自然的对话”。
④表1是以变体A为划分依据,考虑到材料的错位进行的部分较多这一因素,故笔者对小节数进行了重新划分。Y为原型Y,ABC分别对应变体ABC。B’、B”代表B的演变分支,C’为C的演变分支。在表中136—143小节处Y于140小节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