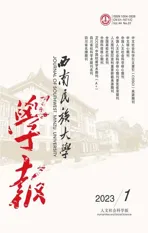“加速现代性”的解药?
——慢新闻运动的学理反思与价值重估
2023-04-07郭毅
郭 毅
[提要]在“慢新闻”(slow journalism)被正式提出至今的15年里,其不仅没有如学界预期成为趋势和主流,反而正在退潮,国内业界对“慢新闻”的热情和信心更日趋减退。“慢新闻”自西方提出,就只是搭上了21世纪反全球化和可持续运动背景下“慢文化”的便车,本质上是对文学新闻、调查性报道、沉浸式报道、新新闻主义、民族志新闻学等“传统审美品位”的怀旧与重提,理论创新相对有限。“慢新闻”是对加速的信息社会之中新闻生产的文化批判,放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看,是“西方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也恰恰因此表现出经验论、非理性、乌托邦和极端主义色彩。“慢新闻”运动从踌躇满志到逐渐衰落,提示新闻界应谨慎地以“加速的学术生产”应对加速社会。
“慢新闻”(slow journalism/news)自2007年被国外新闻界正式提出,至今已经历了整整15年。其在国外最流行的时候,不仅新闻业界以“慢新闻”的名义开展了许多实践,学术界也专门进行了研讨、提出了倡议。[1]就在几年前,“慢新闻”在国内也炙手可热。学界对“慢新闻”表达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具有叙事美学、批判美学和生活美学三重“美学指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亮点”,可以“让传统媒体柳暗花明”,甚至笃定慢新闻“将成媒体未来趋势”。①业界则纷纷以推出“慢新闻”客户端或专栏为荣。例如《重庆晚报》于2016年12月推出了国内首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慢新闻应用程序客户端,号称“新闻本质的回归”。
然而到今天,慢新闻不仅没有成为趋势和主流,反而正在退潮。特别是在国内,《金陵晚报》的“慢新闻工作室”、《重庆晚报》的“慢新闻客户端”等一度极具代表性的所谓“慢新闻”实践都不再继续。不仅如此,业界似乎也越来越不看好“慢新闻”,认为慢新闻不仅概念不清晰,而且国内新闻业界所标榜的“慢新闻”实践与西方所说的慢新闻“淄渑有别、橘枳不同”,甚至最终不了了之,“折戟沉沙”。[2]《新京报》编委涂重航甚至表示,“我们做新闻报道,就没有慢新闻这种说法,讲究的是唯快不破”。[3]
经过多年译介,关于慢新闻的定义和中外实践,国内研究已经予以充分论述,其中不乏大量的重复性学术生产,因此不再值得着墨重提。但当慢新闻从踌躇满志到深陷凄凉,不禁要问:“慢新闻”的实践为何落得如此寂寞?新闻学理论本该指导新闻实践,但为何业界对“慢新闻”这样一个学理概念越来越丧失信心?这些疑问不仅关乎“慢新闻”本身,也关系到新闻学术的理论创新。
一、“慢新闻”:文学新闻的辉煌再造
新闻学界一般认为,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格林伯格(Susan Greenberg)受到“慢食运动”的启发,最早提出“慢新闻”的概念。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格林伯格最初在《前景》(Prospect)杂志提到“慢新闻”时,其实是在向非虚构图书(non-fiction books)和纪录片致敬。她认为新闻出版行业也应该像英国的图书和纪录片行业一样,“涌现更多的投入更多时间的高水平报道、文章和非虚构写作”[4]。
对格林伯格而言,“慢新闻”并非新鲜事物,它实际上奉美国的“文学新闻”为典范。格林伯格写道,“英国在严肃的非虚构新闻(non-fiction journalism)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英国记者十分羡慕美国《滚石》杂志动辄万字的特写,《纽约客》不拘一格的‘事实报道(fact pieces)’,《大西洋月刊》全面的深度报道,以及普利策奖之类的地位崇高的非虚构新闻奖”。[4]这番论述表达了格林伯格作为英国记者兼学者对美国文学新闻的向往,也说明“慢新闻”在实质上是对美国文学新闻中某些特质的提倡。
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也叫作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它是肇始于19世纪、风靡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种“新新闻”(new journalism)样式。[5]与传统新闻报道关注战争冲突、政治丑闻、社会犯罪不同,文学新闻记者通常关注的不是那么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弱势群体,或是聚焦于对日常生活的深度透视和社会学解读。在文学新闻作品中,记者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使用文学手法(如用大量描述性的语言展现细节)进行非虚构写作,新闻报道体现出极强的故事性和表现力。不过文学新闻在20世纪的美国却始终遭到来自文学和新闻界的批评。文学批评家坚持认为文学新闻是对高雅文学的反叛,而且“总是将自身与1960年代的文化剧变以及在越南的挫败联系起来”[6](P.196)。而在新闻界,文学新闻“因为它太过广泛的概念而遭受批评”,特别是文学新闻与煽情新闻、调查报道的关系暧昧不清。[6](P.197)这对文学新闻本身的发展造成了困扰。20世纪80年代久负盛名的《纽约客》爆发“李德事件”是美国文学新闻界的巨大丑闻。它揭露了《纽约客》及其他美国媒体为了增强新闻表现力,把虚构成分混入事实陈述,使得文学新闻蒙受社会的广泛批评。当时美国的许多新闻媒体为了防止被发现编造新闻故事情节,普遍辞退了专栏作者。
“文学新闻”,这个拥有上百年历史且非议从不间断的美国新闻范式为何在21世纪初“辉煌再造”而变成格林伯格及其拥趸所说的“慢新闻”呢?格林伯格所说的“慢新闻”又是如何能够引起西方新闻学界的关注呢?这要从21世纪初人类社会和西方新闻业态所显现的“加速”特征说起。
二、“加速”的信息社会及其文化批判
在新媒体文化盛行的21世纪,西方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对“加速的社会”(speed-up society)表现出普遍关心,认为现代科技在带给人类生活便利、提高生产效率和沟通成本的同时也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压力。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的“加速的现代性”(accelerated modernity)理论极为典型,他认为“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相交织构成加速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个人来说,加速的现代性削弱了自身强烈的方向感,取而代之的是漫无目标的慌乱感。[7](P.71-80)正如日本社会学家辻信一指出,“速度病”是当下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它“毫不留情地感染着现代人,连我们的个人生活也逐渐被它吞没”[8](P.99)。
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不是21世纪才涌现的新问题,相反社会加速进程已经拥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对资本和信息高速流通的内在需求和竞争逻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加速伴随现代性而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一套人类共享的规范,型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9](P.26-28)
21世纪以来全球传媒技术的更新换代使西方理论家将对加速社会的“枪口”瞄准到加速运转的传媒系统及过剩的信息生产上。批评者认为,新媒体技术驱动下信息的高速生产造成信息过剩,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肤浅。[10](P.129)而信息生产的加速难免带来资讯的残缺甚至错误,当个体长期暴露在媒体制造的廉价的信息洪流之中时会产生“知识幻觉”(illusion of knowledge)。[11]用英国社会学家拉什(Scott Lash)的话说,当下人们所处的信息社会就是加速社会的缩影,廉价而快速的新闻供给不仅远远超出人们的正当需求,而且削弱了人们的创造性和反思能力。于是“垃圾”成为拉什对整个信息社会的绝好隐喻。信息与垃圾一样过剩,“可以丢弃,也需要被丢弃”。[12](P.150-151)
在新闻界,人们看到以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为代表的全天候信息播报模式给电视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新闻消费体验,为其求知欲和求新欲带来极大的满足。但全天候直播在带给观众情绪上的刺激感外,并不能增加观众的智识。他们断言“如果即时信息呈现比新闻调查更重要,观众则失去了收看新闻的意义”[13](P.84)。加速的信息社会最终为公众带来的是鲍勃·富兰克林(Bob Franklin)所说的“麦当劳化的新闻(McJournalism)”——媒体提供越来越多制式的、可以预测的日常新闻。这些寡然无味的、制式化、模板化的新闻最终影响到读者的新闻消费兴趣。[14](P.137-140)
在新闻生产者的角度,加速的信息社会同样令人感到担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新闻生产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记者工作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令其身心俱疲,许多职业记者颇有怨言。不仅如此,新闻生产速度加快,也对新闻质量造成消极影响。对加速社会的批判者而言,无论是信息社会还是加速的新闻生产,都亟需“解药”,使人类获得喘息。
三、“慢”:加速社会的解药?
作为与“快”相对的概念,“慢”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学者想象中的解决社会加速问题的解药。21世纪以来“慢食运动”“慢生活”“慢文化”“慢运动”等提法层出不穷。
其实,对“慢”的追求不仅仅是当下人们独创的时髦行为。18世纪的法国巴黎订书工人就为争取14小时工作日而奋斗,19世纪英国的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中的“卢德分子”(Luddites)反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没有灵魂的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极力倡导手工生产的“慢美学”。[15](P.44-45)
但社会加速问题和对“慢”的迫切追求在21世纪反全球化和可持续运动(Sustainability Movement)的语境下变得尤为惹眼。由于全球化必然讲求效率、速度和即时性,反全球化人士把社会加速归咎于全球化进程。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现象,诸如“全球经贸中的交易速度,信息的流通,消费主义盛行下延迟满足的全面退场,时尚的增强循环,缺乏环保理念的‘一次性’社会,全都指向一个逐渐加速的世界”。因此,他们努力寻求和倡导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16](P.156-171)可持续运动思潮则追溯至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从这次大会开始,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议题。21世纪的可持续运动除了呼吁保护自然环境,还格外关心社会生活中速度和时间的问题,它呼吁“为社会降速以恢复生态进程和生活的神圣节奏”。[17](P.2-8)
与工业革命初期保守的卢德分子不同,21世纪的西方社会活动家认为“快”与“慢”不仅仅是对物理速度和时间的衡量,而且是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和崇高道德。“慢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加拿大记者奥诺雷(Carl Honoré)就指出,“‘快’代表了忙碌、控制欲、攻击性、仓促、重分析、压迫感、肤浅、缺乏耐心、冲动、量比质更重要;‘慢’则代表了冷静、谨慎、乐于接纳、平静、重直觉、泰然自若、富有耐心、考虑周密、质比量更重要。”[18](P.16-17)很显然,与“快”相比,“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哲学被人为赋予了道德优势。“慢”也意味着更高的质量。正如意大利学者佩特里尼在提出“慢食运动”时所说,“回到追求质量的基本策略是恢复另一种尺度,用‘慢’作为对现行体系的外部价值补充,把它作为现行体系以外的各种价值的创造空间和交汇点。”[19](P.223)
“慢新闻”的提出,或者说格林伯格对美国文学新闻的迷恋实际上是新闻界对上述社会“加速”问题的回应。其文化本质是抵抗商品主义、标准化和肤浅的知识生产,是对快速的、一次性的消费文化的反叛,以及对某种“传统审美品位”的复兴。[20](P.9)
绝大多数当代西方新闻学者在阐述慢新闻意义或是建构慢新闻理论时,几乎都以复兴“传统审美品位”为落脚点。柏林伯格之后,澳大利亚学者马叙里耶(Megan Le Masurier)在“慢新闻”的理论建构领域里最负盛名。无论是相关文章的被引率,还是在同行学者的评价中,其影响都比柏林伯格还大,因而具有代表性。马叙里耶将“慢新闻”基本特征总结为八点:其一是深度反思的调查性报道,其二是长篇幅报道,其三是避免煽情主义,其四是事实精确且新闻消费者可以随时验证新闻,其五是关注地方性的甚至是小社群中的新闻事件,其六是不在乎是否是独家报道也不与其他媒体竞争,其七是提供协作生产的机会,其八是延缓新闻生产周期以使新闻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感到欢愉。[21]可以看到,上述特征大多不是“慢新闻”所特有的,而是20世纪新新闻主义和文学新闻的审美特征。
澳大利亚学者托马斯(Helene Thomas)在马叙里耶的基础上提出慢新闻的五个“伦理原则”:其一是互惠(reciprocity),即新闻报道能够对记者和报道中涉及的主体都有利;其二是责任感(responsibility),即报道具有集体主义的责任感;其三是尊重(respectfulness),即尊重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其四是耐心(patience),即允许采访对象用更长的时间回答问题,缓慢地展开新闻故事叙述;其五是热情(hospitality),即关心他人,与他人共情。[22]这五个“伦理原则”所涉及的是采访者(报道者)和采访对象(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处理技巧,但无论对国外记者还是中国记者而言,这些“原则”都只是常识。
丹麦学者赫尔曼(Anne Hermann)干脆直接把慢新闻等同于“民族志新闻”。她认为两个概念都是基于长时间的调查、使用较长的篇幅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也都摒弃传统新闻学所坚持的“客观”,从“本土立场”分析问题。[23]民族志新闻(ethnographic journalism)在美国和丹麦诞生,它主张将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志的方法与新闻实践相结合,把记者视作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要求记者“忽略时效性”,深入被采访者的社群生活并与之共情。记者不是通过采访手段从被采访者口中获取特定的信息,而是“理解采访对象的生活世界”。[24]沿着赫尔曼的思路走下去,提倡慢新闻的意义就变成了对“民族志新闻”(或者国内业界所说的“体验式采访报道”)的全面复兴。
上述例子表明,“慢新闻”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胶囊”,难免让人对这粒“胶囊”在解决社会加速问题方面的“疗效”和针对性产生怀疑。
四、慢新闻的价值重估
(一)假想的乌托邦及其问题
应当承认,当新闻界提出“慢新闻”时,其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慢新闻的话语建构却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秉持的“反加速社会”立场相关。
其一,“慢新闻”是对加速的信息社会之中新闻生产的文化批判,放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看,是“西方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加速社会”本身却是一个值得批判的概念。它的经验论、非理性、乌托邦和极端主义始终是其无法绕过的理论缺陷。真的存在加速社会吗?实证研究在理论推导之外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牛津大学两位社会学教授研究发现,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更新换代并没有让英国人的时间紧迫感增加。这一实证发现从根本上挑战了加速社会理论的科学性。[25]
其二,就算存在“加速社会”,把“慢”当做唯一的解药也有极端化之嫌,与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悖。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指出当代生活的加速度造成过度活跃(hyperactivity)、歇斯底里的工作和生产(hysterical work and production)。[26](P.19)但他同时认为,“交换过程既不允许太慢也不允许太快。过高的速度打散了意义;相反,过低的速度则会形成堵死任何活动的壅塞。”[27](P.52)有新闻学者指出,从受众的角度讲,新闻消费的时间性是复杂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快与慢、加速与减速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去理解”受众消费新闻过程中的时间体验。“我们应当小心评价新闻加速生产对受众产生的后果”,新闻的快速生产未必会减少读者思考新闻的时间。[28]
其实早在西方学者提出“慢新闻”之前,我国学者对新闻生产的快慢问题就提出了辩证的观点和正确的解决方案。例如刘建明指出,“新闻报道做到高时效,很难在一次报道中追求事件的完整和本质。大事件只有通过连续发展才能展示它的整体,但这并不影响报道的时效”[29](P.115)。这说明,对事件的快速报道并不一定影响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只要通过连续性的报道,就能够兼顾时效性和新闻深度。
其三,与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对加速社会的理论批判一样,慢新闻也选择对文化惯性和价值规律的潜在作用视而不见。追求快速的信息生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事情,而是人类的本能。“在罗马时代,人们就喜欢聚集在一起打听最新的八卦消息,而游吟记者希罗多德把在地中海与黑海区域的公元前5世纪见闻以最快的速度记录在案。”[30](P.17)几百年来,新闻的时效性与客观性是被所有新闻从业者共享的价值观。[31](P.163)在一个更快的、更具竞争性的新闻生产环境中,少数记者确实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但“记者对速度的需求具有深刻的文化成因——记者沉迷于呈现最新的新闻。在记者的DNA中,潜藏着强烈的竞争欲”[32](P.186)。对于整个新闻业态而言,记者间的竞争不见得是坏事,因为竞争也会促使更好的、更及时的报道。
在国内,“唯快不破”已经成为新闻界的文化惯性和牢固不破的价值取向。正如丁柏铨指出,新闻报道的快慢一直是衡量记者专业素质的尺度。[33](P.18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业界的普遍观点。例如《北京日报》社原社长满运来就指出,文章时效性不强说明新闻工作者存在“慢”“磨”“压”三个严重问题,好选题和好文章因为记者编辑的拖沓处理变成了“废品”。[34](P.72-73)安徽报业集团副总经理丁传光也指出,“快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35](P.31)。
“快”更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的集中体现。20世纪《生活》和《时代》杂志的出品人亨利·鲁斯认为慢新闻(slow news)比快新闻(fast news)更具经济效益。[36](P.62)但鲁斯的判断在当下社会是否仍然成立值得怀疑。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自不必说,速度之“快”和篇幅之“短”始终是新闻媒体的生命线。在中国,“走转改”之后,“短、实、新、深”的消息也早已受到读者市场和中国新闻奖的双重青睐。在一个抖音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碎片时间的市场环境中,鲁斯的执着真的还有“钱景”吗?
其四,“慢新闻”与西方加速主义批判理论一样,陷入了对“慢”的效果假想。法国学者内弗(Erik Neveu)指出“慢新闻”有八重意思。一是指用较长的时间收集和处理新闻素材、核查新闻。二是用较长的时间拓展信源人脉、追踪报道线索、深入采访调查。三是意味着“少”。在过剩的、重复的、无意义的信息洪流中,提取出“有意义的新闻”。四是意味着长篇的叙述。新闻报道篇幅拉长,“记者就为读者建立一个结构化的和数据丰富的文章”。五是“意味着尊重消息来源,让采访对象更加信任你”。六是新闻能够在社群内广泛传播,成为讨论和热议的焦点,进而培育公共领域。七是在受众和报道者的协作下生产新闻。八是用更多的时间“从众多的闲言碎语中找到重要的”新闻。[37](P.140-141)从这八个维度可见,“慢新闻”之“慢”,意味着高品质的采访、高品质的信源、高品质的报道、高品质的呈现、高品质的流通和消费。
但“慢”与“高品质”之间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关联。近年来国外新的实证研究对慢新闻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例如丹麦学者安德森(Kim Andersen)的最新研究表明,慢新闻所吸引的读者是那些平素较多阅听新闻且没有感到新闻疲劳(news fatigue)的人。当这些人阅读慢新闻之后,反而会对新闻产生疲劳感。因此慢新闻“最终起到了慢新闻运动所希冀的相反效果”。[38]在荷兰,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对慢新闻感兴趣,更多人喜欢的仍是免费的、形式灵活的、时效性较强的网络新闻。[39]
过分幻想“慢”的好处,就容易忽视实际操作中“慢”的困扰。在西班牙,《替代经济》(Alternativas Económicas)、《浪潮》(La Marea)、《D边境》(Frontera D)、《蒙古利亚》(Mongolia)、《笔记本》(Cuadernos)、《赤字》(Números Rojos)、《解放》(Líbero)、《白鲸》(La Ballena Blanca)、《冥想》(Fiat Lux)等所有标榜“慢新闻”的媒体都为了确保“慢质量”而选择不隶属于任何传媒集团。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它们往往采取较长的刊期。[40]然而周期越长,资金回笼越慢,资金回笼越慢,周期就越长,最终形成了“慢”的死循环。
总之,正因上述这一切,才出现了本文开篇的一幕。
(二)新闻理论创新性的缺乏及其风险
慢新闻在本质上是对“传统审美品位”的强调与复兴,其理论创新是有限的。如果非要找出它的“创新之处”,那恐怕就是它搭上了21世纪反全球化和可持续运动背景下“慢文化”的便车。用颇为时髦的话说,“慢新闻”蹭了“慢文化”的热度。
21世纪以来国内外新闻学界普遍表现出一种“用新瓶装旧酒”式的知识生产文化。近些年建设性新闻、暖新闻等“X新闻”概念层出不穷[41],虽然比不上“一天一桩谋杀案”的速度,但花哨的知识更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闻学界面对加速社会的无所适从和焦虑感。但遗憾的是人们选择用“加速”的知识生产应对加速社会,最终恰恰走向了其所反对的“加速的现代性”所表现出的肤浅。
如果新概念的提出只是用另外的名词重申某种“传统审美品位”,它必然继承了“传统审美品位”的一切缺点。例如,当把慢新闻视作民族志新闻,就完全可以预料到其巨大的生产成本,而这可能成为慢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所共享的“致命缺陷”。在与采访对象及其社群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除了需要付出时间代价之外,还要面临许多商业媒体不可承受的经济成本。勒布朗克(Adrian Nicole LeBlanc)2003年出版的《随机家庭》(Random Family)作为民族志新闻的代表作品是其11年沉浸式采访报道的产物,在此期间花销基本由其个人承担。这一缺陷对于慢新闻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重大的现实之殇。阿根廷慢新闻媒体《豪猪》(El PuercoEspín) 和秘鲁的《黑色标牌》(EtiquetaNegra) 就因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而倒闭。[42]
在慢新闻概念刚刚被引入国内时,就有学者提出“不妨也保持‘慢’的态度”以检视慢新闻是否能够有效应对新闻业的危机。[43]事到如今,慢新闻的实践困境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当一个曾经“辉煌”的新闻学概念在指导实践方面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变得无人问津,恐怕是这个概念本身出了问题。在学术界,像“慢新闻”这样的概念还不少。在经过15年的“冷静期后”对此进行学理反思不仅有助于重估“慢新闻”的价值,对我国新闻学理论的创新也应有所启示。
注释:
①参见:林玮《慢新闻:概念界定、实践模式与生活美学指向》,《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彭增军《慢新闻:回归还是反叛》,《新闻记者》2018年第11期;罗曼、张春泉《“慢新闻”:传统媒体的应对之道》,《编辑之友》2015年第1期;杜天雨《慢新闻或将成媒体未来趋势》,《中国报业》,201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