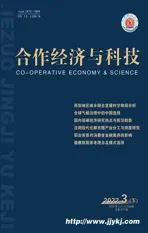论主从合同与仲裁条款效力扩张
2023-01-05□文/蒋涛
□文/蒋 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北京)
[提要]仲裁条款是独立于合同的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受合同无效的影响。仲裁条款效力的扩张面临三大理论障碍:合同相对性原理、仲裁条款独立性原理和仲裁协议书面形式要求。但是,随着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仲裁效力的扩张突破理论障碍,得到新的发展。当主从合同当事人一致时,主合同的仲裁条款效力可以正向拘束从合同;不一致时,存在当事人另有约定、从合同当事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三大例外,此时不能正向拘束。主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从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主合同当事人无效,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即从合同对主合同的逆向拘束只存在于当事人另有之约定。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与国外经贸往来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贸易纠纷,而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高效、便捷和保密等优点备受青睐,重要性也日益彰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有的仲裁制度与实践已难以满足贸易纠纷对优质高效的仲裁机制的需要。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4月16日印发了《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仲裁意见》)。《仲裁意见》中明确提及,“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发展道路”。为落实顶层设计,司法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于2021年7月30日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共计99条,比现行法增加了19条,改动幅度较大。本文就其第24条即有关主从合同方面的仲裁规则提出一些意见。
一、逻辑前提:合同与仲裁条款的关系
在探讨主从合同与仲裁条款的效力扩张之前,有必要厘清合同与仲裁条款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试想,如果连合同与仲裁条款之间的关系这一基础问题都不能厘清,又如何能够探讨主从合同与仲裁条款效力扩张这一更为深入的问题呢。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三种主要观点:主从合同关系说、民事法律行为说和附延缓条件、期限说。主从合同关系说认为,仲裁条款是依附于主合同的从合同,两者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合同。该说忽视了仲裁条款是写在合同中的一个条款的客观事实,试图人为地割裂一个完整的合同,此说不可取。附延缓条件、期限说认为,仲裁条款是附加了条件或者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观点有画蛇添足之嫌。仲裁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仲裁条款是当事人为了解决将来有可能发生的纠纷而设置的条款,但是如果合同履行顺利,并无纠纷之发生,那么依照附延缓条件、期限说,仲裁条款未生效,必然会出现合同生效但是仲裁条款还未生效的怪象,令人无法接受。仲裁制度的启动需要当事人之间达成仲裁的合意,而此合意当属民事法律行为无疑。由于仲裁的特殊性,该民事法律行为是独立于合同行为的特殊民事法律行为,仲裁的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这一点也由我国现行立法所确认。《仲裁法》第19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征求意见稿》也再一次确立了这一规则。总的来说,仲裁条款就是寄居在合同上的一只“寄居蟹”。
二、理论嬗变:仲裁条款效力扩张的理论阻碍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新型争议日益涌现,仲裁的优势日益彰显,国内外也积极立法鼓励仲裁制度的发展,仲裁条款的效力开始扩张,即仲裁条款不再只局限于拘束合同的双方,而是开始拘束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有学者形象地称其为“长臂的仲裁协议”。当然仲裁条款的效力扩张也面临着一些传统理论的阻碍,例如合同相对性原理、仲裁条款独立性原理和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
(一)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的相对性,在欧陆法中称为“债的相对性”,源起于罗马法,而在英美法中由于不存在债的概念与体系,所以称为“合同的相对性”。该原理在合同法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强调合同只能拘束合同的当事人,而不能够拘束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原因在于第三人并没有参与到合同中,并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在此情况下拘束第三人,那么就成为了意思“他治”而不再是意思自治,有违私法自治的精神。具体到仲裁条款中也存在这个问题。仲裁须有仲裁合意,而仲裁合意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并未包含第三人的意思,如果以该仲裁合意拘束第三人,确实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理论。
不过随着仲裁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实践中已经开始突破这一理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也认可这一突破。2020年的“南洋地产(南京)有限公司与南京杭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2010年5月4日,南洋公司与南京江鸿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江鸿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在合同中设置了仲裁条款,2013年4月9日两家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但是并未在补充协议中设置仲裁条款,后来江鸿公司将其债权转让给了杭成公司,南洋公司向南京中院提起诉讼意图确定仲裁不成立,南京中院的判决否定了南洋公司的请求,支持了仲裁条款的扩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仲裁条款的扩张性是有条件的承认,关于这点下文还将继续探讨。
(二)仲裁条款独立性原理。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即上文提到的仲裁条款是独立于合同的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甲和乙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中设置了仲裁条款,而后甲将债权转让给了丙,在此情形下,运用仲裁条款独立性原理得出的结论是,甲转让的只是合同上的权利与义务,而仲裁条款是单独存在的,并没有随着合同一起转让。有观点认为,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仲裁条款可以独立于合同文本,只需要看受让人是否改变或删除了仲裁条款就可以知道受让人是否有意接受仲裁条款的拘束。还有观点认为,仲裁条款独立性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它只是用来使得仲裁条款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诚如上述观点所言,仲裁条款独立是为了不受主合同无效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争议的解决,仲裁条款效力的扩张是有利于争议的解决的。如果受让人真的不愿意接受仲裁条款的拘束,那么在受让合同的权利与义务时,就应该明确地修改或者直接删除该仲裁条款,如果受让人未作修改,那么可以推定他“默示”同意了仲裁条款的拘束。既然受让人“默示”同意了,那么就表明受让人参与到了仲裁合意中并做出了相同的合意,那么仲裁条款当然可以拘束受让人,这也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
(三)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有关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对仲裁协议规定了形式要求即书面形式要求。例如,1958年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以书面协定……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在此《纽约公约》强调仲裁协议应为书面协定;而其第2条第2款又接着规定:“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这给仲裁条款的扩张带来了阻碍。不过随着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各国趋向于对“书面协定”做灵活的解释,只要有口头、书面、当事人行为或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同意了仲裁条款,就符合“书面协定”的要求。有学者认为,仲裁协议之所以需要有“书面协定”这一形式要求,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一方被非自愿地剥夺了在法庭起诉和应诉的机会,而不是仲裁协议的生效要件。既然规定仲裁协议需要“书面协定”的初衷是为了另一方采取诉讼解决争议的机会不被非自愿地剥夺,而不是故意要苛求当事人一定要采取书面的方式,那么只要仲裁合意是当事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采取书面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仲裁法》而言有了较大的进步。《征求意见稿》第21条第2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仲裁中主张有仲裁协议,其他当事人不予否认的,视为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换言之,当事人之间并不需要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只需当事人同意(包括默示同意)即可。这为仲裁条款的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正向拘束:主合同仲裁条款对从合同的拘束
仲裁条款的扩张性具有多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例如代理、合同转让、继承、母子关联公司和主从合同等。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仲裁条款扩张在主从合同中的表现形式,即主合同的仲裁条款对从合同的拘束以及从合同的仲裁条款对主合同的拘束。有关仲裁扩张在主从合同方面的相关立法付之阙如,现行的《仲裁法》并没有对此加以规定,而《征求意见稿》对此做出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纠纷涉及主从合同,主合同与从合同的仲裁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从合同当事人有效。”第24条实际上规定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主从合同都有仲裁条款,但是二者规定不一致,那么此时以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为主;第二种情况是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但是主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此时主合同的仲裁条款可以拘束从合同。诚然,该条相对于现行《仲裁法》的规定而言较为进步,但是仍然具有改进的空间。该条至少存在两个较大的问题:第一,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但是主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此时主合同的仲裁条款未必一定可以拘束从合同;第二,该条并未规定从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而主合同未约定仲裁条款时,从合同是否能够拘束主合同。在此仅就主合同仲裁条款对从合同的拘束进行分析。
(一)从合同当事人与主合同当事人一致。当主合同与从合同当事人一致时,此时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可以扩张至从合同。这是由主从合同的关系决定的。例如,《民法典》第682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从合同是附属于主合同的,是为主合同服务的,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随之无效,说明从合同处于主合同的影响之下。既然如此,主合同的仲裁条款扩张适用于从合同,自然也是属于主从合同性质的应有之义,无需赘言。“先签合同载有仲裁条款,后续合同则无此条款时,后续合同若为先签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后续合同也属于仲裁管辖的范畴。”崔建远教授如是说。
(二)从合同当事人与主合同当事人不一致。当主从合同的当事人不一致,即介入了第三人时,情况则大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当介入的第三人不知道主合同中存在仲裁条款或单独的仲裁协议时,如果主合同当事人可以主张仲裁来拘束第三人,则违反了公平自愿原则,对于介入之第三人极为不公平,不利于维护第三人的权益。还有学者认为,在介入了第三人时,将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扩张适用于从合同,会有损仲裁的保密性。上述观点均具有合理性。首先,在介入了第三人时,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仲裁条款的存在而未曾做出意思表示,或者第三人明确反对仲裁条款,仍然强行将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扩张适用于从合同,有违私法自治的精神。仲裁属于私法领域,自然要奉私法自治为圭臬,即便此时有损从合同随主合同的原则也在所不惜。其次,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原因之一就是看重仲裁具有保密性,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免于公开,如果强行将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扩张至从合同,那么就会将第三人引入同一仲裁程序,此时商业秘密将无法受到保护,有违仲裁机制的初衷。从司法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具有启发性,《仲裁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了三种例外的情况:(1)当事人另有约定;(2)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3)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这三条例外之规定可以较好地解决第三人介入引发的问题,值得《征求意见稿》借鉴。所以,第24条后半段不妨修改如下: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从合同当事人有效,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从合同当事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立法者立法时应当充分吸收成功的司法实践经验,例如在《民法典》的编纂中,立法者就将情势变更制度吸收为第533条,这样的做法也同样可以移植到将来新的《仲裁法》中。
四、逆向拘束:从合同仲裁条款对主合同的拘束
从合同附属于主合同,是为主合同服务的,那么一般来说,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可以很自然地扩张至从合同,这是正向拘束。那么如果从合同中规定了仲裁条款,但是主合同中却并未规定仲裁条款,此时从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能否扩张适用于主合同呢?关于这一点,《征求意见稿》并无规定,现行《仲裁法》与《仲裁司法解释》也付之阙如。如果此时当事人能够达成合意确定是否扩张适用,自然最好,但是如果此时当事人之间达不成协议,那么无非也就是两种情况:一是不可以扩张适用;二是可以扩张适用。
在不可以扩张适用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最后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一致仲裁,那么直接去仲裁即可,不会有不利后果,并且给当事人留下了回转的余地,比较合适。
在可以扩张适用的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例如,甲愿意仲裁,而乙不愿意仲裁,那么此时法律规定可以扩张适用,等于强行剥夺了乙在法庭起诉和应诉的权利,这对于乙来说是有失公允的。主合同到底是仲裁还是不仲裁,应当交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立法者不应当秉持“家父主义”的立场“强行出头”。如果当事人愿意主合同仲裁,那么他们达成一致自然会去仲裁,如果达不成一致,就不应该由法律规定强行使其仲裁,理由很简单,仲裁本就是需要仲裁合意的,如果两者并无合意,那么自无仲裁之余地。所以,《征求意见稿》不妨规定:“主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从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主合同当事人无效,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换言之,从合同对主合同的逆向拘束只存在于当事人另有之约定。
诚然,《征求意见稿》相对于现行《仲裁法》而言有较大进步,但是第24条未臻完善,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笔者以立法建议代替结论,具体如下:纠纷涉及主从合同,主合同与从合同的仲裁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从合同当事人有效,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从合同当事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主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从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主合同当事人无效,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