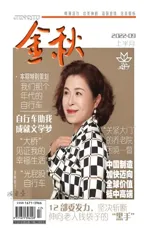伊莎白·柯鲁克的中国缘
2022-12-14潘彩霞
※文/潘彩霞

她是加拿大人,持有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却有九十多年在中国度过;抗战时期,她深入四川璧山县兴隆场,走访了千余户贫苦农家,调查笔记《兴隆场》出版后,被誉为“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齐名的中国人类学著作”。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她还是北外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拓荒者。世纪人生中,每当面临重大抉择时,她的选择无一例外,那就是:中国。
她是伊莎白·柯鲁克,2019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如今,已经107岁高龄的她说:“我很高兴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如果当年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
梦,从白鹿山开始
清朝末年,加拿大掀起了传播福音的运动,大批教育、医学传教士纷纷来华。1 9 1 2年,饶和美(HomerG.Brown)、饶珍芳(MurielHockeyBrown)相继来到当时还很闭塞的四川成都。他们一起学习汉语,一起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共同的教育理想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他们结婚了。
按照教会规定,女传教士一旦结婚,就将失去传教士身份,从而失去工作和报酬。离开华西协合大学后,饶珍芳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和成都盲聋哑学校。1915年,她又参与创办了成都弟维小学,并担任校长。也是这一年,长女伊莎白在成都出生,取中文名为:饶淑梅。
相比当地人,传教士的生活算得上优越,每到闷热难耐的暑期,他们常常携家带口到彭州白鹿山避暑。避暑房建在山顶,所有的生活用品、甚至饮用水,都需要雇当地人挑上山。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少数民族村落,小小的伊莎白总是主动和中国人打招呼、聊天。外祖母曾经资助过中国佣人,父母对衣衫褴褛、汗流浃背的苦力,也总是和颜悦色,善良和友谊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她的心里。
六岁时,伊莎白在成都上小学。正值军阀混战,停战的间隙,她常常去外边捡子弹壳玩,“就像集邮一样”。有一次,她还遇到三位军阀太太,并被邀请去家里玩。令她诧异的是,三位太太的卧室几乎一模一样,墙上挂着的,是同一位丈夫的肖像。
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们,不同民族的生活,伊莎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母亲希望伊莎白继承教育事业,尽管自己更喜欢社会人类学,但她还是听从父母建议,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课余,则辅修人类学。
1 9 3 8年,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后,伊莎白迫不及待回到中国。彼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响,硝烟四起,民不聊生,但是为了儿时的梦想,她义无反顾。
到成都后,伊莎白决定去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做人类学调研,这一想法得到开明的父母支持。在父亲的朋友帮助下,她联系到一户彝族人家,开始了第一次社会调查。然而三个月后,伊莎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多年后,她这样回忆:“我当时很傻,以为不懂游泳,被扔进海里,就会学懂;不懂当地语言,被扔进不说英语的环境里,也就会学懂用土话来沟通。”
语言成为障碍,人类学调查并不顺利,伊莎白躲在房间里哭了。母亲叹叹气,说:“我怎么觉得像母鸡生了小鸭呢,不到大海学游泳,可以先在浴缸里泡一泡呀!”
在母亲鼓励下,伊莎白再次出发,这一次,她的目的地是理县嘉绒藏羌地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沿着岷江河谷,她翻山越岭,攀了两个山头,走了五天路。期间,她住山洞,宿羊圈,荡溜索,涉溪流,一个西方传教士家庭的大小姐,为着热爱的人类学,一一克服。
一年多时间里,她与村民同吃同住,教他们跳舞,跟他们学纺线。穿梭在藏族村落,她拍照片,做笔记,走上与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
绚烂,刻在青春的里程碑上
两次独立的社会调查为伊莎白带来机会。
抗战时期,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四川发起乡村建设实践运动,转移到大后方的乡建团体纷纷响应。其中,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决定在璧山县兴隆场镇开展项目,伊莎白被邀请参加。她欣然接受,一来,这一项目极具诱惑力;二来,她想借此机会积累人类学实践经验,为将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
1940年10月,伊莎白来到兴隆场。尽管空袭警报频繁响起,旅程颇费周折,但她仍然是兴奋的。在第一封家信中,她告诉父母:“好像在探索一个迷宫。”
在工作组,一头金发的伊莎白是唯一的外国人,她的搭档,是同样有教会背景、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俞锡玑。她们的任务是对近1500户人家逐户调查,并“感知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
条件恶劣、鼠蚊横行,特有的湿热气候更使得兴隆场成为疾病频发之地,但这些都难以阻挡伊莎白的热情。换上当地人的长衫、草帽、草鞋,一中一洋两位姑娘开始工作。
然而,谈何容易。那时,老百姓被征粮、征税、拉壮丁吓破了胆,再加上匪患严重,到处弥漫着恐惧惊疑气氛。因山上人家住得分散,为防盗贼、土匪,几乎家家养狗护院。为了安全,她们出门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
阻碍调查进展的,还有村民的不信任。为了打消乡民疑虑,伊莎白操着一口四川话,利用赶场机会,请难得出门的女人在她的住所或办公室歇脚。她的真诚和友善赢得了她们的好感,当地人逐渐放下芥蒂。
逐户调查终于能顺利进行了,野狗狂吠、荒草过膝的山野里,留下了两位姑娘俏丽的身影。整整五个月,近1500户人家全部走了一遍,她们完成了长达36万字的“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从历史沿革到婚俗、宗教、种植养殖、交易等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事例鲜活,笔触细腻。她笔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民俗描绘,都成为珍贵的人类学研究资料。

除了社会调查,伊莎白和俞锡玑还肩负着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使命。她们建图书馆,推广西医,开办平民学校,一年后,乡民们的“信巫不信医”得到极大改善,教育改革也取得显著成效,女性入学率大大提高。几十年后,一位在平民学校学习、后来做了卫生员的老人,回忆起伊莎白对自己的帮助,仍然不住地流眼泪:“读了书,就写字;写了字,又读书,她教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乡下,最愉快的时光还来自于未婚夫大卫·柯鲁克的造访。
柯鲁克是英国人,比伊莎白大五岁。大学时,偶然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遂对中国革命发生兴趣,于偶然机会下来到中国。借着教师身份掩护,他一边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一边把照相机镜头对准中国底层社会。

结束上海的工作后,柯鲁克来到成都华西大学执教。有一天,在办公室里,他见到了替妹妹代课的伊莎白。对于中国劳工的同情和关注令彼此相见恨晚,共同话题不断,他们擦出了爱的火花。
1941年暑期,两人在横断山脉的皱褶间艰难行走了六个星期,只为寻找斯诺笔下的红军长征足迹。大渡河的浪花已为爱情作证,回到成都,他们订婚了。
不久,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员。而战事不断,乡建项目也陷入停顿,伊莎白不得不告别兴隆场。带着十大箱的田野笔记,去英国与柯鲁克结婚。
“遇到大卫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终于认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柯鲁克影响下,伊莎白从一个受基督教“福音”思想影响颇深的非暴力主义者,变成了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者。
人类学依旧难以割舍,一有闲暇,她就研究兴隆场的那批资料,并带着大纲去拜访著名的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教授。弗思看后大为赞赏,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指导她攻读人类学博士。弗思还为她推荐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表示同意出版,而同时列入丛书出版计划的,就有后来奠定了费孝通人类学家地位的《江村经济》。
二战结束后,伊莎白师从弗思,攻读人类学博士,柯鲁克也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办理空军退役手续时,他得知,当初从哪里回到英国,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哪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
中国,是唯一的选择
1947年底,伊莎白和柯鲁克身穿笔挺的英军军装,经香港到达天津。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穿过国民党封锁区,来到解放区,驻扎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多年后,在给朋友的赠书上,柯鲁克依然充满激动地写道:“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土改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土改运动有许多诬蔑和谣传,外界极想了解真实情况。这是兴隆场之外又一次丰富的人类学实践,伊莎白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她希望自己也能像斯诺一样,写出一部向西方介绍真实中国的作品。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山村生活条件极差,柯鲁克夫妇拒绝了特别为他们准备的白米粥、白面馒头,他们在农民家中睡土炕、吃派饭,和当地人一样,一天两顿。穿着肥大的解放军土布军装,他们学会了把手揣进袖筒,吃饭时,和农民一样,在饭场上端着大碗“一圪蹴”。
在田地间、打谷场,或是担粪路上,伊莎白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中国话和农民拉家常,和他们一起刨地。农民的个人生活,他们在抗战中的遭遇以及对土改的认识,第一手资料就这样一一获取。
在当地农民眼里,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每晚的豆油灯下,整理笔记,誊写打印,冲洗照片,装订文件。山村的夜晚已经宁静时,打字机还在啪啪作响。
在十里店的八个月,伊莎白和柯鲁克亲眼目睹了整个土改的过程。以特约记者的身份,柯鲁克把所见所闻写成稿件,源源不断地寄给英国报纸;伊莎白,则定期向弗思汇报自己的调查研究,继续学业。
土改结束后,伊莎白和柯鲁克准备返回英国,完成十里店的研究报告。恰在此时,中央外事组负责人王炳南找上门来,希望他们前往外事学校任教——新中国即将成立,培养外交干部成为当务之急。
面对邀请,他们再次选择了中国。写作计划暂停,也放弃了个人志向,伊莎白最终走上讲台,与父母殊途同归。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撰;国民党的骑兵不时来袭击,有时会在夜间转移,一走就走到天亮。艰苦环境中,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成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迁往北京,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柯鲁克任英语系副主任,伊莎白则是口语老师。身材修长的她,穿一身灰色列宁装,娴雅文静。每到星期天,她还会邀请学生来家里吃烧饼夹酱肉,尽管那时,他们的工资也是以小米来计算的。
教学的同时,夫妇俩坚持整理十里店的资料。1959年,他们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在国门封闭的年代,这本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土改运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作品驰名国际,橄榄枝随之而来,英国一所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教职工作。可那时,正值中苏交恶,“如果我们在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会良心不安的。”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留下。
不曾预料的是,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也遭遇了牢狱之灾。1967年,作为“外国特务”,柯鲁克被捕入狱。随后,伊莎白也被关了起来。吃着煮白菜,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听着鸟语蝉鸣,她“就像一只墙上的苍蝇,做着人类学观察”。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第二年,柯鲁克也回家了。带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他们又满怀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当有人问伊莎白是否对中国失望时,她的回答是:“Never.”
“有些人爱回忆的是生活中美好的事,其余的都过去了。有些人回忆的是伤心事,成了不能承受的包袱。能回忆美好事物的人,会有更多快乐、健康。我就是这样。”能够直接见证这段重要历史,作为人类学家,伊莎白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1 9 8 0年,离开教学一线后,伊莎白终于有机会继续兴隆场的研究。为了完善资料,她多次往返兴隆场,继一部三卷本人类学著作之后,《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于2013年正式出版。湮没于历史深处的芸芸众生鲜活呈现,伊莎白为中国历史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那一年,她98岁,柯鲁克已经去世13年了。

住在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北外专家楼里,翻看着柯鲁克当年拍摄的几千张照片,伊莎白的记忆一点点复活。青春、爱情、梦想,一切的一切,她都献给了热爱着的中国。
“因为我们参与了中国伟大而曲折的革命,大卫的一生和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极大地丰富了。”金发已成白发,矫健的身姿也已不再。然而,心中有爱,眼底有光,走过一百年,她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