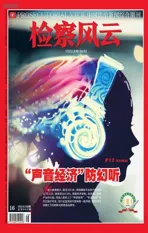鲁敏: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
2022-10-21禾刀
近年来,作家鲁敏的小说创作声誉日隆,在其既往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历史是隐约可见的线索或参照——它似乎不那么明确,却也不曾消失。作为“70后”的代表性作家,鲁敏的写作既讲究传统叙事,又蕴含思辨主题,极富试验精神与现代性。近期,鲁敏孕育20余载、书写40年改革变迁、容量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获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奖”)经译林出版社推出,引起了读者的高度关注。
苦心经营和歪打正着
您的新作《金色河流》的书名隐喻了什么?
书名我真是想了很久,这是一个有趣而痛苦的过程,估计每位作家讲到他们的长篇,可能都会有一箩筐被作废的书名。最终定下这个河流的意向,是突然而至的,但细想想也是自然而然的。大家平常都讲“逝者如斯夫”,或者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当下,河流的隐喻,都是共通的。我们的一生就像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奔流不息,或涓涓,或滔滔。我们到底将创造什么,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正如这本书我笔下的主人公穆有衡——恰恰是一个走到人生晚境的老人,由于家族儿女们有着各种复杂的状况,遂通过一纸突发奇想的遗嘱来处置他毕生的财富,阴差阳错中,就此踏入了一条他自己也从未想过的金色河流,通往了人生更加澄明的境界。
您在写作过程中精心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重大事件,这是“时代的信息”,更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路线图”。这前后您花了多长时间?
梳理信息用了3年多,但前后准备了20多年。前面若干年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因为我们似乎总有一种了解小道消息的习惯,喜欢谈论发财致富者的各种江湖恩仇与人生沉浮。从新闻剪报到席上谈资,从话本传奇到剧场表演,我们的现当代文学里,总有着“重文抑商”的顽固传统,有金钱万恶的先天性批判倾向……这些年,我的想法在发生变化,所关注的重点,不是物质与财富从哪里来,而是物质与财富要往哪里去。一旦有了这样的转变,关注和准备的素材等也就会相应地发生调整。我觉得这种想法与观念上的准备和自我发现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作品高下与难易的一个关键点。
改革开放40年的大事记我看得比较细。另外一项素材储备是收集传记,我读了好几本经商者的回忆录与口述材料,这种书通常是自费出版,写得比较“土”,但素材非常丰富,比如商人“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穿西装”等,有的连合同细节、早年的家书都有,对我而言都很有价值。
还有一个“歪打正着”的事情,在小说开写之前的一个阶段,我正好在北师大攻读学位,当时自己选择了“非虚构与虚构的不同叙事策略”作为硕士论文的开题。我就想,如何把这样的叙事策略运用到小说创作里,是不是可以给我后面的小说文本添加一个执笔者视角呢,用小说里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来解构主人公在岁月洪流中的传记式素材……这样,我的小说里就增加了一个“谢老师”的角色,写着写着,他成了陪伴主人公半辈子直至最后一程的守望者。
读者能从《金色河流》里打捞到什么
您在《金色河流》里书写有总(主人公“穆有衡”的别称)这个人物与主流改革开放人物叙事有着很大区别。事业有成的有总中风后,无论曾经多么叱咤风云、春风得意,此后便离不开别人的照料,同时也摘不掉“病人”这顶帽子。大儿子穆沧也是病人,与父亲不同,穆沧很快乐,这种快乐与金钱扯不上半毛钱关系。事实上,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与金钱保持着若隐若现的距离,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像是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履行各自的责任。改革开放,除了物质,我们还收获了什么?从有总身上,我们还有什么精神“遗产”可供打捞呢?
有总身上最宝贵的,是他对于创业、创造的激情与大胆。他是有过匮乏时代记忆的一代人,对于走出贫穷、追求富裕、创造财富有着根本的内在需求。这样一种创造是美好的,也是了不起的。我们每一个目睹、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成熟起来的人,也都随着经济进步,随着都市文明发达等感受到一日千里、结结实实的财富积累,享用着商业文明所带来的速度、效率、技术、娱乐等叫人欢喜又矛盾的“好处”。所以有总这样的创业者,留给我们的,除了日新月异的物质进步,还有这种创造和参与时代进程的激情和价值观。
“70后”作家的文学观点
看到不少关于您的报道,您的年龄频被提及,真的不在意“暴露”自己70后的年龄吗?
不介意。年纪是写作者值得珍惜和把握的财富。只有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走到一定的阶段,有的主题和命题才能成为我的书写内容。比如我早期的“东坝系列”,是来自我的乡村记忆。在南京生活多年后,我就自然而然地书写起都市灯火下的多元众生。因父亲所在国企改制,我得以观察到两代大厂人的聚散离合与努力不弃,这才有了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我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写作者很多人都是这样,徐则臣、梁鸿、阿乙、路内、张楚等都是这样,有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变迁,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京城,乃至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国际交流。这种变迁跟生理年纪成长和地理位置变迁同步相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一名读者,记忆中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这个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但是被采访时总是反复被问起。从时间上讲,在我还没有确立任何文学与写作观之前,《艺术哲学》这本著作对我的影响比较大。记得大约是1995年左右吧,我把书带到邮局(工作单位)的营业柜台去看,不免有同事问起,我总不好意思亮出封面,后来索性用报纸包起来,因为这书名在当时的氛围来说显得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其实丹纳(法国19世纪批评家)是很有体恤心的,他很平和地向读者构建他的实证主义艺术观,调子起得很低,只要稍有些文史底子并对艺术有基本常识的读者,便会一头扎进去,进入他为你架构的体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剖析各艺术门类的历史起因、风格形成、流派分别……记得我当时是做了不少笔记的,带着激动而叹 服的心情。十几年过去了,那笔记当然已遍寻不见,但那得遇良师、拨雾见光的心境一直令自己记忆犹新,我朦胧地感知道:我中意什么,我对什么敏感,我为何喜爱那些美好的东西……这跟我后来的写作,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当时起码是知道了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愿意与之发生亲密联系的,是美与艺术。其余,皆可忽略或次之。
您如何看待文艺评论?评论会左右或干涉您的创作思路吗?
评论自有它的体系与逻辑,有旁观者清的部分,写作者会觉得很有道理;但所谈论的这部作品已然完成了,而下一部未写的作品,也依然首先会服从于好奇心、灵感与热情等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我总感到,写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也许像打牌,作家看看家底子,先出一张,接着评论家也看看家底子,出一张,然后作家再出一张——但这张牌,也不大可能完全因为评论家的上一张牌,而有大的改动,因为作家手上大致就这么些牌,这些牌,跟他的知识结构、生命体验、气质趣味、写作进程、野心大小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