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着男装:唐韦浩墓《喂鸟侍女图》图像研究
2022-10-08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马金林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马金林
女着男装的侍女形象作为墓室壁画中出现较多的一种题材,出现在以唐都长安为中心的诸多墓葬规格级别较高,有明确纪年的官僚贵族的墓室中。比如,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韦浩墓等等。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韦浩墓中的《喂鸟侍女图》,行文以韦浩墓《喂鸟侍女图》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图像内容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喂鸟侍女图》中的侍女形象及其服饰类别做深入研究,指出该女子所着服饰的胡服因素,并认为该服饰风格是在汉族服饰的基础之上,吸收大量胡服因素而改良形成的。再以同一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其他墓室壁画中的女着男装的侍女壁画对比分析《喂鸟侍女图》的艺术风格,深挖画面人物形象的服饰细末。最后,结合唐代前期的社会文化与文献记载,进一步探讨女着男装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韦浩墓《喂鸟侍女图》图像研究
(一)韦浩及其墓室壁画概述
韦浩,初唐人,中宗废后韦氏胞弟,谥赠太常卿,武陵郡王,扬州大都督。韦浩其人,在正史中记载较少,多散落在其从兄弟韦温的传记当中。以《新唐书》为例:《新唐书》卷二百六,列传第一百三十—外戚中,专门为韦温列传,而韦浩则一笔带过,但我们依然能够得知,韦浩为中宗皇后韦氏同父弟,属于名门望族,外戚国戚等基本信息。原文如下:
韦温者,中宗废后庶人从父兄也,后父玄贞历普州参军事,以女为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廬陵,玄贞流死钦州,妻崔为蛮首承宁所杀,子:洵、浩、泂、泚同死。……赠洵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
关于韦浩的谱系,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六百四卷,氏族典第五十三卷中,记载的较为详细。该卷以《新唐书》为主要参照,理清了以韦后为中心的初唐韦氏一族的世系关系。该谱系行文简短,以《新唐书》为基础,加以系统梳理,不加华饰,为我们呈现了更为清晰的氏族关系。
通过文献史料记载,我们明确的得知韦浩的社会地位,由于其同胞姐妹韦氏蒙皇帝恩,余泽至身,后因“帝幽卢陵”,惨遭武则天所害,其父身亡,其也随母同死。后追封谥号,葬于长安。由于获得追封加之皇亲国戚的身份,其墓葬也必然按照贵族旧例的规格进行安葬。
韦浩墓,景龙二年(708年)入葬,位于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于1987年出土发掘。墓室内壁画众多,品类丰富。墓室由斜坡墓道、一过洞、一天井、四壁龛、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组成,全长41.5米。墓内绘有壁画,从墓道至墓室依次为青龙、白虎、狩猎出行、侍臣、房屋、天象、高士及男女侍等。本文所要研究的《喂鸟侍女图》位于墓室的后室东壁,是后室东壁的群侍中位于中间位置的两位侍女之一。
(二)《喂鸟侍女图》画面内容解读
《喂鸟仕女图》高180厘米,宽65厘米,为韦浩墓后室东壁群侍的中间两位之一,女扮男装,头戴幞头,身穿翻领长袍,下着波斯裤,足蹬软便履,袍领、袖口和前襟都绣有华丽的花边。侍女右手提一小笼、左手悠然自得的给肩上的一金丝雀喂食,颇有情趣。

图1 韦浩墓后室东壁群侍图

图2 韦浩墓后室东壁喂鸟侍女图
关于《喂鸟侍女图》画面内容的陈述,信佳敏先生提供了更加具体的阐释。为一女扮男装侍女。头戴黑色幞头,粗眉细目,身穿淡黄色翻领长袍,袍领、袖口和前襟处绣大花,花饰黄红相间,十分华丽。下身着波斯裤,足蹬软便履。右手提一笼,左手悠然自得地给肩上的金丝雀喂食。两位前辈在其著录中对《喂鸟侍女图》的画面解读较为详细,本文将对二者的解读加以整合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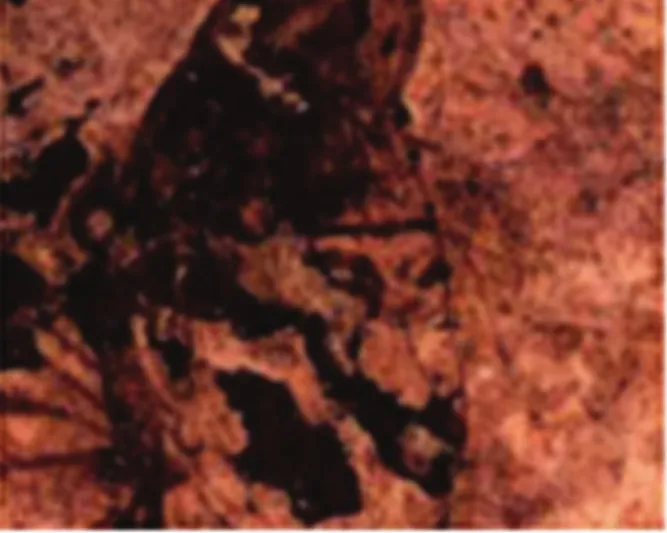
图3 《喂鸟侍女图》幞头局部
(三)女着男装的人物形象研究
《喂鸟侍女图》中,女着男装的侍女形象位于墓室后东壁的群侍中间的右侧,上文已对其着装以及动作等图像元素进行解读。那么,《喂鸟侍女图》中女着男装的侍女,其着装是从哪里来呢?此类的女着男装与同时期男装有什么异同?其与传统意义上的胡服相比较,有什么相似性与改良性?我们带着问题进行下文的研究。
我们知道,最早将胡服应用于汉代穿着的人是赵武灵王,其“胡服骑射”开胡服盛行之先河。而在隋唐,汉化后的胡服逐渐从军戎转渗到日常生活,成为男士普遍的着装。据史料记载,唐代男子的典型的日常打扮为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袍、脚蹬靴。唐代男子所穿的袍靴来源于北魏的戎装,是男子专属的服饰。
《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舆服》记载:“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乌纱冒、折上巾、六合靴,与贵臣通服……武德初,因隋旧制……(唐太宗)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同时,幞头也是男子专属的首服,应用在传统官服礼服当中。
《新唐书·卷二十五·志第十四·车服》记载:“(马周)又请:‘裹头者,左右各三襵,以象三才,重系前脚,以象二仪。’诏皆从之。”
另外,在士族女性中,女子穿着男衣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碑内外,斯一贯矣。”
《中华古今注》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在《喂鸟侍女图》中,女性着装翻领、对襟、窄袖紧身直统长袍,腰间左侧佩带红肇囊,下身穿紧身条纹裤,脚着靴或布(麻)鞋等,幞头顶凹陷,并且微微向前倾。幞头尾部似被盘起。第一,在图四中以及上述史料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男性服饰当中,幞头的佩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女性在佩戴幞头时,会根据女性特征以及审美取向而进行适当的改造。第二,《喂鸟侍女图》中,女性领口为翻领、对襟,而同期男性的服装多为圆领,翻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女性的形态美与女性特征。第三,《喂鸟仕女图》中,女性所穿长袍为紧袖直筒式,并带有多种花纹,前襟处绣有大花,颜色黄红相间。而在同期男性服装当中,多以简约样式,不资华丽。
综上,可以看到,《喂鸟侍女图》中的“女着男装”实际上就是女性穿著男性的服装,但是保留基本的女性特征。根据上文列举的史料记载,男性服装的很多元素都来源于胡服。那么,女性对男性服装的拿来,实际上也就是在对胡服拿来的基础之上而进一步结合女性的特征而折衷产出的。也就是说,女着男装是来源于胡服并结合女性身体特征而改良而来的,并不是对男装以及胡服完整意义上的拿来。那么,其相似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其改良性,也主要集中在方便性、适应性,以及以女性形体为标本的再改造。这样看来,女着男装就是在男装吸收胡服元素的基础之上,再结合女性的一些穿着习惯加以改造而成的。
(四)《喂鸟侍女图》艺术风格研究
总的来说,唐代的墓室壁画在继承、发扬了战国以来的绘画技术的同时,积极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并在民间画工的不断实践中走向了高峰。在绘制过程中大胆革新,务去陈套,不拘一格。“女着男装”的侍女形象频繁出现在以京兆地区为中心的贵族墓室壁画中。而同样是表现“女着男装”的题材,不同的墓室中在构图、设色、勾线上却各有不同。故通过对比的形式对《喂鸟仕女图》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梳理《喂鸟仕女图》的艺术风格及其价值。
在构图上,《喂鸟侍女图》夹在一幅群侍中,但是其形象特征较为显眼,处于大画面的中间靠右位置,整体上构图紧凑,画面布局合理。《喂鸟侍女图》左右空间没有采用对称的方式去留白,而是左边大,右边小,同时将画面人物面朝右进行绘制。与传统的空间描绘方式相左。
在设色上,《喂鸟侍女图》采用原色设色。通过简明遒劲的勾线和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鲜明浓艳的深刻印象。同时,《喂鸟侍女图》中也采用了晕染法,通过明暗对比,增强了人物衣着与皮肤的质感,颜面着色亦更为细腻,突出了人物形象以及服饰风格的鲜明特征。

图4 《高士图》幞头、领口局部(韦浩墓)
二、韦浩墓中女着男装题材缘起探讨
艺术最终反映的都是现实社会,某种艺术样式的出现,必然跟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密不可分。因唐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墓室壁画的绘制要一定程度的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社会以及生平喜好。故我们通过对墓室壁画中画面内容的解读,并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便可以了解到墓主人的生前状况,更为清晰地洞察当时的社会风貌,更有依据的把握女着男装的表现形式以及其盛行的原因。而女着男装作为一种艺术题材,必定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具体有三,一则为胡汉之间的民族交流与“夷夏一家”的民族政策,二则为儒学思想的淡化,三则为女着男装的自身便捷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认为,从“女权主义”觉醒的角度来研究女着男装的盛行原因,牵扯到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有些牵强附会,值得商榷,故在此不做讨论。另外,本文认为女着男装与“服妖论”并不存在明确的冲突关系,将“服妖论”的叙说与壁画中所反映的女着男装现象进行二元互证并不存在文献与图像的不相符。但有学者认为女着男装的图像资料与“服妖论”的文献记载并不相符。其实,“服妖论”最早出现于南朝宋,在《宋书·五行志》中已有记载。而“服妖论”的记述也出现在《晋书》《隋书》当中。到唐代,女着男装为“服妖论”开始被广泛接受,但在初唐民族政策“胡汉一家”的实施下并未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流。也是在统治者开明思想及“夷夏一家”的族群理念下,唐初史臣承接的女着男装为“服妖”说,才可与渐起的女着男装之风并行不悖。但随着唐朝国力的兴盛与衰弱,出现了“服妖论”与“时尚说”并存以及摒弃的几个阶段。对于此,下文将不在进行赘述,具体将从如上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胡汉之间的民族交流与“夷夏一家”的文化观念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多民族文化不断地交流碰撞。“唐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补长取短,……,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李泽厚先生在其著作当中阐明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南北融合与交流的现状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来的外来文化的盛行与传播的情况。我们知道,唐代时期,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周边的游牧民族一改汉朝时期以来的打压、歧视方式,反而推行兼收并蓄的政策,太宗时期,李世民也被周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太宗也曾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民族政策也为胡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女着男装的男装,来源于胡服,一开始只应用于战事,而后来逐渐被运用到官服上而渗透至日常生活中。也是在胡服汉化后的男装的基础上结合女性特征而改良而成的。这些胡服因素,无疑来源于唐代时期胡汉之间的民族交流。而开明的“夷夏一家”的民族政策,也让这些胡服元素被应用到唐代这一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时代。

图5 《喂鸟侍女图》领口、对襟局部
(二)儒学思想的淡化
自魏晋始,“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向愈演愈烈,三教为维护自身地位而在斗争中相互渗透,相互发展。有唐一代,开放包容的政治格局为三教提供了优良的发展环境,“尊道,礼佛,崇儒”的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应运而成。但随着佛教与统治者意识形态不断的相互建构,佛教似乎一时间成为三教之首,“众生平等”的教义冲淡了儒家“男尊女卑”的礼教观念;道教的“重母”思想以及统治者层面“李氏出自老君”言论的提出,道教也被定为“国教”;这些思想也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被广泛接受。虽然儒家礼教强调,“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但是随着礼教观念的淡化与其他二教文化的冲击,必然会导致开化风气盛行,思维大胆也促成了穿衣风格的不断改变。尽管“女着男装”被视为一种“服妖”行为,但在民族政策的引领下,冲击了儒学思想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并没有转化为当时的主要矛盾,统治阶级也并没有按照以往惯例用儒学理念禁锢人们的思想,女性也逐渐从传统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客观来讲,儒学思想的淡化与传统礼教的模糊以及道教佛教的迅速发展使得儒学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压迫,造成的儒学观念的淡化。这些因素客观上推动了女性思想的开元,也是女着男装盛行的客观因素。
(三)女着男装的自身便捷性
我们知道,自战国赵武灵王开“胡服骑射”之先河伊始,胡服便逐渐被运用到中原王朝的军事活动当中。究其原因,莫在于“胡服骑射”自身的便捷性。而隋唐以来,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将胡服运用到军事活动中,男子穿着胡服也逐渐成为一种政策指引。不可否认,从战国时期“胡服骑射”再到隋唐“便于戎事”,将胡服运用到军事层面都是及其强调其便捷性的。而女着男装的男装,大部分都来源于胡服因素,从唐代女性的出行以及参加体育活动中来看,着男装似乎比着女着更为便利。女着男装的女性形象参与体育活动及出行活动中在唐代著名仕女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也有所体现。赵彬宇指出:唐代很多女性爱好“胡服骑射”,而穿着男装或者胡服利于出行、骑马等活动,这也促使了女子着男装风尚在唐代的盛行,它的流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审美,更重要的还有在开放的唐朝,这样的服饰对于女性来说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是,我们应该对女着男装的受众群体做一个清晰的梳理,这样可以更好的把握女着男装自身便捷性是针对于哪些群体而逐渐流行开来的。根据文献记载,太平公主是第一个着男装而现于公众面前的。

图6 《高士图》长袍局部(韦浩墓)
按,《新唐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四·五行一》记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以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近服妖也”。
又,《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碑内外,斯一贯矣。”
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女着男装实际上的受众群体仅局限于贵族与士人阶级,她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唐代的所有女性,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将“女权崛起”视为女着男装的盛行原因是带有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的,也是十分值得商榷的。贵族女子着男装的心态有可能是受到所谓“女权崛起”观念的影响,但士人阶级女性着男装还是明显带有等级之分的。唐代是人物画极端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从阎立本等画家的传世作品中观察到,在唐代人物画绘制时,已经有了依据人物大小以及画面位置的排列来反映人物地位关系的意识,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女着男装的侍女题材的壁画中得知一二。所以,女着男装自身的便捷性因素才是最大程度反映各个阶级女性群体的着男装的客观因素。
三、结语
本文大致运用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壁画《喂鸟侍女图》进行图像分析,总结了《喂鸟侍女图》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对墓主人韦浩的生平及地位做了较为详细的文献考察,运用横向对比的方式对女着男装的艺术形象进行阐释,并在前人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对文献的考察与比较对“女着男装”的艺术题材的盛行补充了新的观点。但在写作研究综述查阅资料时,发现很大部分学者在图像研究的过程中忽略了对文献资料的考据,不同程度的依赖图像,对图像的分析也止步在画面内容与技法方面,对它的象征意义以及绘制原因的研究缺乏文献资料的支撑,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与猜想捏造的圈套,很难纵向而深刻的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很难得出恰当而中肯的研究结论。我们知道,女着男装的艺术形象大多都出现在皇亲贵族的墓室壁画当中,这是肯定且最为详实的图像依据。
辅之文献记载的陈述,我们可以更好地通过二元互证的方法来探析女着男装在唐初年间的盛行原因。本文在第二部分总结梳理了今人前辈学者对女着男装盛行原因的探讨,指出了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依据文献史料的记载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得出了较为客观的理论结果。认为女着男装之所以在唐初盛行是受到了上层意识形态观念的默认,胡汉的文化交流以及统治者阶级的“夷夏一家”的民族政策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女着男装自身的方便性与快捷性所决定的。
①③【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225卷 卷二百六,列传第一百三十—外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864—1865.
②⑤⑥参照:韩伟,张建林.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78.
④参照:《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640卷,氏族典第五十三卷,清雍正铜活字本.第4413—4115页.
⑦罗世平,李力.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附38.
⑧⑩【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8.
⑨【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7.
⑪【五代】马缟编撰.中华古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
⑫关于将女权觉醒视为“女着男装”盛行原因的观点,主要有:王涛.唐代妇女着男装原因探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4);孙玉荣,胡辉.唐代女性服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J].黑龙江史志,2012(9);李丽.唐代女子着装初探[J].聊城大学学报,2008(2).张江.唐代“女着男装”现象研究[J].艺术百家,2015,31(S2):120-122.等.
⑬张江.唐代“女着男装”现象研究[J].艺术百家,2015,31(S2):120-122.此文认为“女着男装”的图像资料与“服妖论“的文献记载不匹配,但不认为其相互矛盾。
⑭李志生.唐人对女着男装为“服妖”说的接受史[J].唐史论丛,2020(2):209-224.
⑮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⑯【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M].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⑰王云五编,王梦鸥注释.礼记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62页.
⑱张江.唐代“女着男装”现象研究[J].艺术百家,2015,31(S2):120-122.
⑲按,《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舆服》记载:“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乌纱冒、折上巾、六合靴,与贵臣通服……武德初,因隋旧制……(唐太宗)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
⑳赵彬宇.陕西唐墓壁画中“女侍男装”形象成因考略[D].陕西师范大学,2016.
㉑【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878.
㉒【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41.
㉓罗世平,李力.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