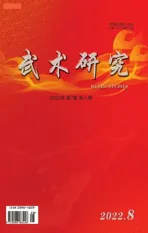中国武术之打:超越身体的技击范式
2022-09-02杨兵
杨 兵
成都文理学院体育与医护学院,四川 成都 610400
在近来的系列中国武术和现代格斗的对抗事件中,中国武术一方无一例外落败的结果对于“中国武术能不能打”的争议提供了“有力”参考。而后,学术界部分人士就中国武术的本质与功能进行理性辨析和认知引导,如“中国武术的功能不单在于打斗;中国武术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对抗规则对武术不合理”等,却难逃“避重就轻”之嫌。由此暴露出本土社会集体意识受西方文明影响导致对本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认知不足的事实,即对中国武术技击及其价值认知的片面与错误。笔者不禁反思:事件中,中国武术一方代表其个人技击水平能反映出中国武术技击的历史发展高度吗?赤手空拳地打斗是彰显中国武术技击功能或价值的有效方式吗?西方现代格斗技击功能的价值评断标准对于进行中国传统武术技击价值与内涵的判定是否合理?答案是否定的。为论证此论点,本研究以“中国武术之打”为探究对象尝试进行立体化分析,旨在呈现“中国武术之打”的特殊价值与风貌,也为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武术技击及其价值提供有益参考。
1 战争兵器与武术器械强化中国武术现实技击
武术是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武术技击亦是不断发展的。“打”是武术技击的通俗说法。武术技击也就是武术击技。传统武术击技,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由招法、打法所组成的有关技击打斗的技法系统,是一种意在制服对手的无限制的拼杀手段。人类早期对自然物质(棍棒、石器等)加以利用发展了获取与创造生存物质的技能,有效地增强了应对自然界中对自身生命安全存在威胁因素的防御能力。据此,结合“武术起源于人类和自然界不和谐因素的对抗过程”的观点,认为中国武术器械伴随中国武术的起源与发展,和“武术技击由原始的单纯搏斗动态演变至兼文化形态”是相伴相随的共生关系。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和谐因素对抗中获胜,说明了人类文明力量面对纯粹自然因素具备发展优势,也证实了人类对身体范畴之外器物的有效使用可以强化搏斗对抗能力。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武术起源于古代战争”的观点存有异议,却未闻否认中国武术和古代战争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战争更直接关于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这应该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古代战争和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技击对抗的主要区别在于战争规模更大,参与人数众多,根本目的在于致敌方于死伤而夺取胜利。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兵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及使用方法的经验理论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战争中,兵器的杀伤与制胜效率是徒手搏斗不可比拟的。兵器的发展影响着古代战争的形势与走向,战争的持续进行对兵器的更新与发展不断提出着新的要求。
在战争之外的社会领域,社会矛盾的存在使得个人和群体对自卫能力具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从而推动着民间对武术器械的创造与更新,是促进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发展的另一股主要动力。生物学领域中人的“身体”属于现实范畴的存在。身体是武术起源的基础和发展的灵魂, 因为武术的产生首先满足的是个体身体的需要。人的身体是产生武术技击功能的主体。人的生命周期终究是有限的,人体血肉之躯抵抗自然界和社会中对生命安全存在威胁因素的能力也是可穷尽的。但有幸的是,历史上的先进武术人已然深刻地认识到了人体的搏斗能力和潜力的有限性。尽管如此,手臂的打击范围有限,但是有了器械在手,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打击范围,相对于徒手来说有着巨大的优势。而如若要求更有效甚至充分发挥器械对技击功能的强化作用,便不可仅是肢体和器械的物理性地连接,还须在通晓拳理的基础上将器械再融于其中,方可达成有机统一从而达到质变的技击强化作用。如王芗斋论“拳与器械之关系”时所言“古云:‘拳成兵器就,莫专习刀枪’。若能获得拳中之真理,复对各项力之内能与节段面积之屈折,长短、斜正之虚实、三段九节之功用、路线高低之方向和接触时间之火候,果能意领神会,则无论刀枪剑棍种种兵器,稍加指点,俱无不精,即偶遇从无见闻之兵器,且执于使用该兵器专家之手,彼亦不敌,何则比如工程师比小炉匠、医博士比护士、根本无比例之可似也。”通过兵器与武术器械同身体的实践、应用、融合与再发展,中国武术技击功能的作用范围逐渐超越了现实层面的身体范畴,在时间与空间上获有显著优势。武术演练用的器械,主要由古代兵器或生产工具演化而来。古代战争对兵器发展的要求和人类在社会生存下的自卫需要是推动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战争兵器和武术器械的创造、使用与发展促使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发展突破了身体范畴技击能力的局限。
2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升华中国武术技击意识
有学者认为,中国武术在起源之初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武技为同一属性,即一种用于打斗、搏斗的身体活动能力。受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复合影响,原本同一性的搏斗技能逐渐分流演变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武技类型,如中国武术,巴西柔术,日本空手道、合气道,欧美的拳击,泰国的泰拳等。中华民族厚重的传统文化是彰显民族个性与独特魅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武技”发展为“中国武术”的重要影响因素。自卫本能的升华和攻防技术的积累是人类武技产生的根本依据,中华武术自然也是如此。但是中华武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技、道并重,内、外兼修,流派繁多,绚丽多姿,包蕴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而卓立于世界,却是由于它的技击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在古老而独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哺乳和规范之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影响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就影响着中国武术技击的发展,且是着重于对中国武术技击意识的影响。中国武术技击意识正是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得以升华,凸显精神性。
尽管学术界对于“技击是中国武术的本质”的观点存有分歧,但对于“技击是中国武术具备的重要功能”的观念立场基本统一。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武术技击的社会功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多元文化复合影响而动态地“正位”,因此,中国武术技击的社会反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尽管“技击是否是中国武术的本质”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命题,但是技击确是贯穿中国武术发展始终的核心功能。至今,中国武术已发展成为兼技击性、艺术性、教育性、体育性等多样“不打”功能于一体的功能集,其各属性均是对奠定中国武术功能基调的技击的发展体现。武术的“不打”看似背离了“打”的初衷,但从“打”到“不打”,武术始终没有离开技击的原点。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受社会上层建筑(文明、法制等)影响,中国武术的现实技击功能的发展空间逐渐被缩控,但是否因此导致了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滞缓乃至退化,研究认为,不然。“技击弱化”现象的发生,方使武术获得了巨大内容承载力,从而成就“中国武术”相异于他国武技的独特面貌,反而是给中国武术技击除“现实搏斗”之外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与空间。
2.1 兵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影响
古代兵家理论,以服务军事战争需要为己任。由《孙子兵法》得知,中国历代兵书见于著录者高达4200余种,可见理论之厚重。作为一项实用技术,中国武术技击和古代战争中的军事对抗在属性和功能上是极为相似的,兵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正是军事对抗和中国武术技击进行时共同的无规则性和“夺人而不夺于人”的“护己而损敌”的制胜需要。确切地说,武术技击,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军事战争;而军事战争,其实也就是一种集体化的武术技击。兵家理论影响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根据还在于,技击的根本原则在于单位时间内在最大限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的基础上最高效地制敌于死伤。服务于战争需要与发展的兵家理论以技击为要义,在探求技击的要求和效率上自然高于中国武术,因此,就“技击”而言,兵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影响必是盖过中国武术技击对兵家理论的反馈。如兵家之有关培养作战勇气、掌握对抗主动权、敌人而制胜等的思想方法,对于武术之技战术体系的建构,有着积极的而深刻的影响。兵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影响体现在现实层面,着重提高中国武术技击效率。
2.2 道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影响
道家理论不同于兵家理论以服务军事战争的现实需要为旨趣,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并非直接现实的影响。道家讲求无为而治,根本上悖于战争及与其紧密联系的重在实践作为的兵家理论。道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影响更多作用于意识层面。探究道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影响,需要在引用和转化道家理论以丰富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理论的背景下来进行。“道,可道,非常道”,道家理论的隐晦性恰恰为自身创造了广阈的引申与解读空间,由此具备的普适性为道家理论作为推动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理论条件提供了可能。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被看作是兵家“正出而谲用”与“示形而误敌”以及“正合而奇胜”战术理论的进一步论述,利于后者在现实层面的实践操作;又如“反动”与“弱用”为本方通过与敌方心理活动进行换位思考后在战术策略上进一步推进的经验总结,即否定之否定意识活动的具体体现;再如道家“复归于无极”的理想,又被看作是中国武术技击在“为道曰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通往超验境界的终极表达。总之,道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影响主要作为丰富技击经验的理论条件。
2.3 佛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传入中国后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家文化体系,还有特点鲜明的“拳打一条线,拳打卧牛之地”的少林武术的文化实体。技击注重胆气,胆气是影响个体技击水平发挥的重要内在因素,释此谚语如“光脚不怕穿鞋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兵家理论中,关于作战勇气,有提出“战在于治气”“斗,勇也”。在佛家文化中,强调技击对抗时的胆气,提倡“破生死关”,即是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魄。破生死关,彻底消除对死亡的畏惧,在心理上已经没有了生死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了对生命个体的任何牵挂。这对于以个体生命为最大赌注的武术技击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它已经彻底消除了生死赌博者的一切后顾之忧。破生死关,突破对死亡的畏惧,以大无畏的气势压倒对手,是武术技击实战对拳手心理素质的最高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佛家文化对于搏斗、技击提倡破生死关堪显极端,但佛家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并非崇尚争斗。不但不提倡,且是极力抵制的。少林僧侣发挥武术技击功能多为维护正义或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又或是面对险恶形势时的临危受迫之举。佛家文化的浸染为中国武术技击实践增披的是正义的外衣。此外,不得不提佛家的“禅”文化,佛家特有的“禅悟”是修行达到至高境界的意识活动,当佛教禅定被传统武术吸收利用而成为武术内功时,武术的实战技击就多了一个重要的辅助性的基础训练。受佛家文化的影响,中国武术技击不再是可供个人和群体任意拿来即用的纯粹工具,其已然成为维护正义、惩恶扬善的维护社会正义的特殊手段,更甚为修行达到意识层面至高境界的“禅悟”的重要途径,因为二者彼此以至共存与互长之态。
2.4 儒家理论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举足轻重且长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融原生文化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为一体,具有极强的价值统摄力量。这就是其对传统武术能够产生统治性影响的根本原因。纵观历史,封建统治阶级对儒学的尊崇使得儒家文化的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民众集体意识的重要部分。儒家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武术人在内的民众思想意识的同时,势必影响着中国武术和中国武术技击的发展。当中国武术技击单纯作为一项实用技术的时候,本身不具备文化内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现实搏斗对抗过程中的攻防转换与制胜。因尚不具备成为一种文化以至文明的发展条件的制约,此时中国武术技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仅是在现实层面的单向精化,所以本质上仍为一项实用技术。然而任何一个习武者,都必须生活在时代的风尘中,无法脱离现实,更不可能背弃现实,因此,习武者即实践武术技击的主体,必须把武道的最高目标从技术性的层面提升到政治与道德的高度。历史上的武术人显然是认识到了中国武术发展同国家意识相匹配的重要性,因此将儒家文化引入到中国武术发展的理念当中。其中儒家“礼”文化对中国武术技击发展的影响颇重。缓和了双方搏斗对抗过程中的残暴与血腥,使之区别于作为战争或打斗中以置对方死伤为直接目的的无限制拼杀手段;又如民间的比武切磋,受“礼”的影响,对抗目的止于比较参与者的竞技优劣,有意避免无谓的伤亡。综上认为,儒家“礼”文化助于原血腥暴力的中国武术技击在适应社会文明化发展过程中确立匹配样态,调节了中国武术技击的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兵家理论以战争谋略和技战术理论发展为旨趣,旨为在现实层面“更好地技击”提供方法支持,使技击行为在个体本能的基础上有章可循,强化了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功效,丰富了中国武术技击技法的理论体系;道家思想为中国武术技击发展提供新的思考,“为道曰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无为而治”思想为中国武术技击发展追求收发自如的超验化界提供思路引导,由此期待彻底消除中国武术技击有形、程式化的经验理路而达成“把技巧隐于无形”的理想境界;在慈悲为怀和戒杀戒斗的佛家文化影响下,中国武术技击脱离了现实搏斗工具的旧壳,蜕变为象征着新添正义色彩的惩奸除恶的手段;儒家的“礼”文化,利于中国武术技击缓和“生死之争”的血腥残暴而定位在仅需“分高下”的点到为止的较技方式,萌生出中国武术技击对抗的民族的、本土的竞技规则。中国武术技击在兵、道、佛、儒等传统文化的复合影响下升华了技击意识,使得中国武术成为重实践体验且更尚精神意识的具有显著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技发展形式。
3 中国武术之打的三个层次、两个维度和一个缺失
3.1 中国武术之打的三个层次

图 1 中国武术之打的三个层次
中国武术之打的三个层次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均有体现。中国武术技击作为服务打斗的工具,历史上现象普遍。具有典型性的“踢馆”是武林门派之间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竞争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其根本目的不外乎门派收徒、提高门派社会声望、凝聚群体势力和发扬本派拳术的社会影响等。把视角转向人类文明程度更高的现代社会,尽管昔日的武林已经逝去,但是同类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如前言中提及的社会约架现象。此类技击行为尚属中国武术之打的基础层次,由于缺乏明确合理的规则、必要的安全设施以及专业组织人员等要素,导致参与者的人身安全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此类即是一种依赖武力强制性的殴斗行为。中国武术技击作为文明社会人类中的一项身体技能,凸显了的人类文明的可取性。历史上,比武切磋采用“打擂台”的方式。打擂台属于双方在商议约定规则下所进行的较技行为,具有明显的规则色彩,反映出中国武术技击已逐渐脱胎于单纯基础性的打斗,有了现代搏击对抗的雏形。进入现代社会,受体育文化的影响,比武切磋发展为在体育竞技规则下以体育赛事的方式来进行。赛事组织包括竞赛规则、医护监督、参赛前后的身体检测等为参赛人员的生命安全提供保障措施,有效降低了竞赛周期中出现伤亡的概率。在技术层面上,作为体育竞赛的中国武术技击竞技胜负取决于规则下的技术征服,区别于缺乏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混斗。
中国武术技击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含有精神教化的作用。个人受到教化与未受教化相比,虽然还是这个个体,但却获得了深刻的精神性的转变。中国武术技击作为教育手段,通过技击技法说教的方式,经意识影响的路径以达成。在电影《一代宗师》中,当得知马三追求荣华富贵而投敌叛国,为师的宫宝森并没有对徒弟直接进行惩处,而是用了一个名为“老猿挂印(关隘不在挂印,在回头)”的武术技法暗诫他迷途知返。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武术教育的特点,即通过现实的技击技法的传授并结合说教将中国武术技击对人的影响引向超越现实的意识层面,从而达到精神教化的初衷。当中国武术技击成为一种教育手段,在摒弃了现实层面的有形的“打”而升华为无形的教化手段之后,通过意识交流与传递的途径达到教育的目的,深刻彰显了中国武术技击区别于现实对抗的“不打之打”的独特魅力。
3.2 中国武术之打的两个维度
中国武术之打以“文打”与“武打”为较技方式。
武打,是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现实直接对抗,具有显著的开放性。而直接的武力对抗,拳脚之间,你来我往,由于无法规避对双方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伤亡,导致不利于中国武术技击摆脱暴力、粗蛮的负面形象而难以强健发展。
文打,是中国武术技击特有的较技方式,呈现闭合性。双方通过与第三方标准的比较来判别二者之间的优劣,从根本上避免受直接的身体对抗所限而造成人身伤害的风险。尤其意识交流的形式更是武术造诣高超的体现。如电影《一代宗师》中,武林第一人宫宝森因年事已高,已生隐退江湖之意,在隐退仪式上,面对自己予以厚望的叶问提道“咱们今天不比武功,比想法,如何?”,随后以掰面饼的方式替代技击对抗。从其反武倾向反映出其对中国武术技击的理解已超越了有型的技能层面。最终,宫宝森:“宫某赢了一辈子,没输在武功,没曾想,输在了想法。”的言辞寓意中国武术技击发展不仅需要在现实的拳脚功夫上积极进取,更为重要的是武术人须要在意识层面具备具有可行性的发展思维。
由上认为,检验中国武术技击技能和武学造诣的,并非且不仅有直接对抗的“武打”,还有高过直接对抗而重在检验精神意识等隐性要素的中国武术技击特有的不打之打的“文打”。在中国传统武学体系中,技术层面的武术讲求“打”,那是因为技击是武术的基本特征;而精神层面的武术追求的则是“不打”,这是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和民族属性而决定的。从“打”到“不打”,体现了武术从务实到务虚、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转变。
3.3 社会对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功能需求的淡化是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发展动力缺失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曾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反之,社会一旦淡化了对某种事物的需要,则意味着该事物发展根本动力将不足。
文明与法制是维护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社会是在不断向文明化和法制化前进的,这也就注定了武术的技击表现必然逐渐异化。中国武术的现实技击具有显著的工具属性,其本身虽无正恶之别,但当社会个人或群体通过发挥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功能而达到某种目的时,无奈难以和与之共存与共生的暴力与争斗脱钩。由于暴力等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的文明与法制相抵触,因此含有暴力因素的中国武术现实技击的发展必然因此受抑。然而现代社会的文明与法制对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发展的影响从本质上是区别于封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武力发展所进行的专制性削弱和压制的。文明在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驯化和引导的正面促进作用,法制则是通过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进行管制,此正反两面的双重复合影响使得社会对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功能的需要逐渐淡化。
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在社会中的发展形势与自身被社会需要的程度紧密相关。中国武术现实技击的发展需要解决“为什么而打”的问题从而确立自身的价值定位。当作为搏斗工具被个体需要与使用时,回答了个体在主观意识当中“为什么打”的问题。而当社会文明与法制使得个体原诉诸中国武术现实技击以维护个人生命安全的需要获得替代满足,社会对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功能的需要便逐渐淡化,对中国武术现实技击的价值存在即“为什么打”的答案也逐渐模糊。中国武术现实技击“为什么而打”的答案是动态的,因此,中国武术现实技击“怎么打”必将随之而易。社会文明与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致使中国武术现实技击“为什么而打”即发展根本动力逐渐弱化,中国武术现实技击的发展空间因此缩小了,中国武术现实技击“怎么打”易于以往。
武术的嬗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需要的产物。然而,尚武意识一旦被驯服,社会就缺失了习武的社会氛围和空间。文明的一旦被树立,非文之武就必然被转化、改进和融合。
4 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技超越身体范畴方面的发展比较
初始同质的武技受不同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分流为多样化、民族化的特殊形式。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里形成了崇尚现实技击的体育格斗项目;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演变为“中国武术”这一特殊样态的民族武技。武术的概念及外延也很大,现代中国人习惯上将武术看作是体育的一部分,这种见解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不合理性。尽管武术已经发展为现代体育项目,但武术异化为体育的质变是部分质变,不是武术整体的质变,武术的本质属性仍是技击。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同样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活动,是一种身体的文化,但两者在完全不同的身体视域下源起、传承与发展,其最原真、最基础的文化形态存有巨大差异。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时代环境下,西方文明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了相当的冲击,也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土社会集体意识对于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评判,甚至不排除有意识地在西方文明视域下审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而影响着本土文化发展逐渐重视在西方文明价值评价标准中的价值实现。对武技现实技击的尊崇使得西方民族在武技发展上以集中提高实战技击功能为旨趣。受文化交叉的影响,以西方武技的价值评价标准来评断中国武术的技击价值,其实是将具备多元功能价值的中国武术技击置于“现实搏斗”的单一的功能夹层中来进行中国武术技击整体价值的探讨,而中国武术的现实技击功能恰好是在中国武术技击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的基础功能。如此而来,如何不使中国武术技击功能与价值认识的表浅与片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然是因其不同而不及。或更确切言之,正唯其过而后不及。我们不能仅仅以西方竞技文化之“打”来评判中国传统武术的是非曲直,这种截取传统武术的片段并以偏概全地深锁传统武术的整体价值功能的做法,显然是片面的、无知的、不科学的。如果片面用单一的或者静态的眼光审视武术的发展,无疑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综上认为,如若要比较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技的某些方面,为确保合理性,应将二者置于某一共同参考和标准下。研究认为,将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技置于一项技击的前置基础上,通过比较二者在以身体范畴为中介方面的发展取向及成效,得出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技之间的差异,确保了科学的合理性。
技击功能及发展是武技发展的共同追求与一般需要,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各民族武技在强化技击功能方面多有突破身体范畴的表现。如中国武术的刀、剑、盾、矛等器械,西方的击剑、菲律宾魔杖(短棍)、日本剑道等。中国武术的拳理和器械为相辅相成的互动发展关系。中国武术各拳种不光有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技术套路,还有配套式的兵器,如八卦掌取源于刀术,太极拳有太极扇、太极刀、太极剑、太极棍等。尽管其他民族武技的发展同样具有器械的创造、使用及发展,但在样式和规模及使用方法理论的厚重程度方面较之中国武术确有显著差距。中国武术器械样式庞杂,尤其,内容繁杂的暗器种类极大地丰富了武术器械体系,弥足了常规兵器的不足,大大提升了武术器械的使用空间、打击范围以及杀伤效果。就武术器械的规模和样式而言,世界上其他民族难和中国武术相比数。是否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是牵制或者助推事物发展的关键。有学者认为,中国武术的发展之路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或者追美揖欧,而是要实现对传统和西方的双重超越。本研究之所以认为中国武术技击是武技发展在超越身体范畴方面的“范式”存在,是根据中国武术技击发展实现了现实身体范畴的超越并完成了意识升华的“二重唱”。即在现实层面,战争兵器和武术器械的创造和使用强化了中国武术现实技击功能,且在器械种类与样式上较其他民族居于明显的超出;在意识层面,兵、道、佛、儒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国武术技击意识的升华特供了理论条件,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和西方的双重超越”。这是基于研究所认为的——所谓“中国武术的传统”同西方武技技击同属一物即武技现实层面的技击,所以,中国武术技击对身体范畴的二次超越即是对中国武术传统的超越,也是对西方武技的超越。中国武术竟技尽管是一项直接对抗的运动,但与西方武技所崇尚的绝对意义的力量对抗不同,武术竞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是一种谋略的对抗。即说明意识力量在中国武术竞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即王芗斋先生所说“意即力也”,没有意也就没有了力,“意为力之帅”是同理。西方搏击不是身心一体,它更强调身,忽略了心,是身心分离的。中国武术技击在意识层面的发展是始终“唯现实”技击的西方武技未曾亦无法具备的发展形式,因此,中国武术技击的发展对于世界武技的发展自有特殊意义。
5 结语
中西文化交流改变了民族本土社会意识的自然发展轨迹。但在异域文化涌入的同时,也为重新审视本土文化,找到可资比较的参照物——人们对武术之“打”的困惑因此而生。受西方体育文明的影响,本土社会意识参考西方武技的价值评判标准,聚焦武技一般的现实技击功能来审视中国武术技击的功能及价值,必然导致忽略中国武术技击发展超越现实身体范畴的特殊意义,使得中国武术技击全面的真正精神和立体化的价值功能被隔于同中国武术技击价值所不匹配的西方文化性质的“唯现实”技击的武技技击价值的一维评价标准之外,导致本土社会对中国武术技击认识的片面化。所以,当代社会武术向前推进更为需要是踏踏实实地先做好自己,若只是置身别人创设的语境,在他者思维框架下谋求自己的发展时,就只能是跟在别人身后,即便追赶上也无甚光荣;只有首先做到以“我”为主时,才能挣脱别人的束缚,跳出预设的限制,进而才可能驰骋于当世而傲视群雄。认识中国武术技击理应具备本土历史视角兼发展思维,此既是认识中国武术技击的须有素养,亦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