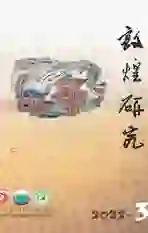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一件黑水城元代文书考
2022-07-11杜立晖
杜立晖






内容摘要: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我国黑水城文献若干件,其中有一件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取状”。由此件发现,元代在亦集乃路设有“官羊户计”,此户计并不见于其他地区。元代的取状并非登记所有取状人的户籍,除户主外,其他人员往往仅需登记其“户计”即可,取状中登记取状人的户籍应与财产的罚没相关。另外还发现,元代曾设置过塔塔元帅府,此件文书是目前所知有关该元帅府的唯一记载,塔塔元帅府可能与蒙古元帅府有关。
关键词:天理图书馆;黑水城文献;元代;取状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3-0094-10
A Study on a Yuan Dynasty Khara-Khoto Document Collected
in the Tenri Central Library in Japan
DU Lihui
(Institute of Qi-Lu Culture Studies,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There are several Dunhuang and Khara-Khoto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Tenri Central Library in Japan. One of them is a previously unpublished quzhuang document(a record of witness testimony) from the Ejina Prefec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which claims that there was an “official sheep register” in the region. No such document has ever been seen in other places, however, as quzhang generally only registered the domicile of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and the number of his family members, but not the housing information of all witnesses. It is believed that listing the domiciles of witnesses registered in quzhuang might have been related to the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In addition, the document also suggests that a“Tata Marshal House” was once set up in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as lik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onglian Command House, although this is the only historical document found to make mention of such an installation.
Keywords:Tenri Central Library; Khara-Khoto document; Yuan dynasty; quzhuang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黑水城文獻被学界誉之为我国近代以来与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档案等并称的第五大考古材料新发现[1],其对于中国古代史,尤其对于宋、西夏、金、元(包括北元)等时代历史文化研究,极具史料价值。目前,分藏于俄国、英国及我国的黑水城文献,大部分已公之于众,但仍有部分文献庋藏于异域,如日本的天理图书馆等,世人罕得一睹。对于天理图书馆所藏的黑水城文献,曾吸引了来自敦煌学界、西夏学界等多领域专家学者前去调查与研究{1},目前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其中的部分西夏文文献图版已经刊布,这批黑水城文献的神秘面纱因之也被渐次揭开。但遗憾的是,该批文献中的元代文献等,至今却鲜有提及。近期,笔者循着前人的足迹,亦到访了该馆,并对其所藏的全部敦煌、黑水城文献等进行了细致考察。为展现该批黑水城元代文献的内容与价值,今择其一对其进行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 关于文书的时代及性质判定
此件文书装裱于拟题为《宁夏省黑城发见西夏经——并元代古文书》的册子中,今将其释录如下:
(前缺)
1. □□{2} 军
2. 官羊户计,家在
3. 住坐,除高曾祖父
4. 同 在家,见存 妻 □
5. 思丁,年卅四岁;次男赛
6. 驱{3}男刚立歹,年一十一岁。孽畜:驴□
7. 见住帐房一座除外,并无隐漏不
8. 尽人口、头匹{4}、事产等物。与一干人等 每
9. 讐。取责 □□秃鲁不花与□□
10. 何倩 将职官张文秀并弟张惠安杀死,
11. 劫讫财物、段匹、抄{5}定等物。阿剌□ 请
12. 分赃。蒙塔塔{6}元帅府 罪赃
13. 官,已蒙本路取讫阿剌□
14. □ 伏 □□蒙取状□剌□
(后缺)
此件首尾均缺,上完下残,共存文字14行。此件用行草书写,部分文字笔画或过于潦草,或残损过甚,致使少量文字难以辨识,今将难以辨识的文字在录文中加框处理。装裱此件的册子《宁夏省黑城发见西夏经——并元代古文书》,其原主人为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家清野谦次,在该册子前的题记云这些文书等“是从黑城附近的流沙中发掘出来的,发掘时的状态不是很详细,黑城在宋元时代曾经是西夏的首都(清野此语有误——笔者)。因此,本卷中会出现至元年间的某个古文书,还收藏了西夏文的古书,对此不需感到奇怪。另外,总体来说,这些古文书、书籍是在昭和十二年末在北京收获的,昭和十三年初回到京都后对其进行了装裱整理。现在对此加以简单的说明。”由此可知,该册子中所装裱的文献,均来自于黑水城遗址,是昭和十二年,也即公元1937年由清野谦次在北京所获,次年被其带到了日本京都,后来入藏于天理图书馆。由清野之言可见,该册子中的所有文献均属于黑水城文献,且以西夏文献和元代古文书为主。从这一角度来讲,此件或属于西夏或属于元代文献。
再者,从文书中可识读的有关人名判断,此件所属时代当为元代。如文中有一人名曰秃鲁不花。《新元史·只儿哈郎传》曾记载,只儿哈郎之子名曰秃鲁不花,“至大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丰国公,遥授平章政事、行太府院使、西域亲军都指挥使,佩虎符。又特授左丞相、行枢密院事。至大元年,卒”。而只儿哈郎是灭里乞台氏[2],该姓氏为蒙古姓氏之一。虽然,此秃鲁不花不一定就是文书中的秃鲁不花,但由此可以推定,文中的此人应为蒙古人。另,文书中阿剌一名,在元代就更为常见,故由以上判断,此件为黑水城元代文献无疑。
就文书的内容而言,可大致划分为3部分,其中第1行至第8行的“事产等物”等,是介绍此件所涉人员的户计、住所、户籍等。可以推断,第1行或者其前所缺的内容中,应有相关人员姓名等的介绍。第8行的“与一干人等 每 ”至第12行,记载了秃鲁不花等人杀人、劫财以及阿剌请求分赃的犯罪经过、阿剌等人被捕获的过程等。第13、14行则是“本路”对阿剌“取讫”“取状”的情况。由第12行的“蒙塔塔元帅府 罪赃 ”一语推断,阿剌等人已被塔塔元帅府捕获,故第13行的“取讫”二字似有提审、调查等意。第14行的“取状”,则是元代的一种用于记录对有关人员审讯情况的文书文体。同时,由于此件系来自于黑水城遗址的元代文献,而该遗址在元代为亦集乃路总管府的所在地。故由此又可进一步推断,文中的“本路”当指亦集乃路。故此件可能是涉及对犯人阿剌等人的“取状”。因此,据以上可初步推定,此件是一件取状文书。
另,据有关学者研究,元代的取状包括“取状人的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健康状况、住址和户籍”“取状人详述事情的经过”等。虽然此件残缺,但其残文保留了相关人员的住址、户籍以及事情的经过等信息,且登载这些内容的顺序与元代的取状相似。同时,若第9行的“ 取责 ”二字识读不误,则表明此二字以下所述杀人、抢劫、分赃等的过程,是有关人员的招认、供认。而因“取责”二字恰有“招认,供认、供状”之义[3]。此即反映出,以上相关罪犯的犯罪过程并非是经由他人转述的,而是由“取状人详述”的。这也与已知元代“取状”的主体内容相似。据之更有理由相信,此件当系一件元代的取状文书。而此取状的对象,应该是文中多次出现的“阿剌”。其中第14行所载“蒙取状□剌”等字,虽然“剌”前一字残缺,但据其文意可以推断,该字应为“阿”字。此处也清楚地表明,被取状者当即“阿剌”。所以文书第一部分记载的相关内容,应是有关阿剌的户籍信息等。
综上判断,此件当是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有关阿剌的取状文书。
二 文书所见相关问题的探讨与价值分析
此件系残件,所载内容多为传世文献所不载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今就其相关问题及价值意义试做探析。
(一)关于元代的“官羊户计”
显然,第2行“官羊户计”一语旨在说明此件取状人的“户计”问题。正如黄清连先生所言:“蒙古征服王朝为了达成对中国本土内各种服务人口的实际控制,参酌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习惯,并视实际需要,而树立一种‘户计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各种民族阶级的服务人口,都被编纳到各色各样的‘户计’里。”[4]所谓各色各样的“户计”,也即元代文献中通常所說的“诸色户计”。户计制度,往往也被学界视之为户籍制度[5]。黄清连先生曾对元代的诸色户计做过统计,共发现元代至少有83种户计[4]197-215。“官羊户”不在此列。目前已知,元代在很多地方有牧放“官羊”的,如至顺二年(1331)十二月“癸丑,撒敦献斡罗思十六户,酬以银百七铤、钞五千锭。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仍以忽里所牧官羊给之”[6]。该条反映出,在至顺年间的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内牧放“官羊”,且由“忽里”来放牧。而“哈赤”似乎又与“忽里”相似,如《元史》卷100《兵志三》载:
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其印,有兵古、贬古、阔卜川、月思古、斡栾等名。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岁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驰驿阅视,较其多寡,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其总数盖不可知也。凡病死者三,则令牧人偿大牝马一,二则偿二岁马一,一则偿牝羊一,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6]2553-2554
这里牧人称曰“哈赤、哈剌赤”等。此语当与上文的“忽里”职责相当。同时,由此条可知,哈赤不仅牧马,也牧羊,且其所牧羊应为“官羊”,如文中“朝廷岁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驰驿阅视”,以及“凡病死者三”“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等。
另外,也有文献记载了哈赤牧放官羊、私用官羊等相关情形,如延祐元年(1321)中书省奏:“前哈赤节次阅讫官牝羊三十余万口,本欲孳生以备支持。因年远,哈赤等将孳生羯羊不肯尽实到官,宣徽院失于整治,致为哈赤等所私用。每岁支持羊口,皆用官钱收买。又每遇抽分时,将百姓羊指作官羊夹带映庇,不令抽分。拟依照原定则例,从实抽分。若有看循作弊,从严究治。哈赤牧放官羊,亦仰从实分拣,除牝羊并带羔羊存留孳生外,应有堪中羯羊印烙,见数拘收,如有隐匿者,从严追断施行。”[2]471由此可知,元代一些地方的官营牧场存在牧放官羊的,且往往设置“忽里”“哈赤”等职以负责对官羊的牧放。元代从至大四年(1311)十二月辛未始,置尚牧所,秩五品,掌太官羊[6]548。尚牧所隶属于宣徽院,而上文提及“宣徽院失于整治,致为哈赤等所私用”一事。由此可知,上条材料中“哈赤”所管领的牧场,应系中央直属机构宣徽院所管辖的有关牧场。前文有关“忽里”的记载所涉及的河间路,隶属中书省的腹里地区,这一地区的牧场应该也属于宣徽院所辖。故而,忽里、哈赤等职与官羊户似不能混为一谈。其中前者是负责牧放官马、官羊的职官,后者则应该是专门负责放养官羊的人户。目前传世史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元代官羊的牧放者、管理者,多为上述职官,并不见“官羊户计”。因之,仅通过传世文献无法获知该类户计的相关情况,天理图书馆所藏的此件黑水城文书,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明确记载元代存在“官羊户计”的文献,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当然,除此件外,在已经刊布的黑水城元代文献中,也有两件类似户计的文书:
其一为OR.8212/775K.K.0118(a)《元某府委官责领放官羊户麦文书》:
1. 取责领状人梁□□真{1}布 悉
2. 今当
3. 府委官,责领到马兀木{2}南子
4. 祖发鲁于放官羊户撒立蛮□
5. 麦壹 拾 麦五硕□□到{3}
6. □{4} [7]
(后缺)
此件第4行提到了“放官羊户撒立蛮□”。由此可知,“撒立蛮□”是以牧放官羊为生的户计,故其户计似乎可以视之为“官羊户计”。
其二为M1·2223[HF125正]《放官羊人户等文书》。此件由数件残片粘贴而成,其中有一件残片的最后一行载“ □□□□放官羊人户杀害是实。得此。今”[8]。显然,该行所记载的被杀害者应系一“放官羊人户”。此户的户计也似可视为“官羊户计”。
由于上述两件文书均系黑水城元代文献,故据此推断,它们应与本文所讨论的这件天理图书馆所藏黑水城文献一致,均来自于元代的亦集乃路。因此,由以上可见,元代亦集乃路存在“官羊户计”类人户是无疑的。亦集乃路官羊户计的发现,无疑是对已知元代“诸色户计”内容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应该看到,之所以在传世文献中没有官羊户计的记载,一方面反映出该类户计的人户数量有限,设置地域不广,比较的“小众”化,故很难进入传世文献;另一方面则说明,亦集乃路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此类户计的路级官府,抑或仅有该路有过此类户计的设置。
那么,亦集乃路为何要设置官羊户计呢?笔者推测,这或许与该地承担的繁重军站“祗应”,以及相关宗王、驸马、妃子等的“分例”有关。《经世大典》记载,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十一月十八日,中书省奏枢密院官铁木儿不花奏言:“去年西面川两接界地,今军当站至甚贫乏。往者军站各别乃蒙立站赤之役,已尝遣使至甘肃行省督令追复元户,有阙则佥补百姓,未见回报。今诸王宽彻暨司徒阔阔出、太傅铁哥塔失、铁木儿知院等,会议川地东西两界所置驿站,预宜斟酌给钱与马驼,仍于近境官羊内支拨供应,以济军站物力尽用之外,或遇诸王、驸马及使臣往来数多,铺马不足,则令附近军人增置。”至日具奏,上悉从之[9]。铁木儿不花指出,因西面川两接界地军站贫乏,一方面要求甘肃行省督令追复元户,签补站户;另一方面,则要求“于近境官羊内支拨供应”,“以济军站物力尽用”,也即要为军站提供相关官羊的“祗应”。
另,元代在站赤中使用的马匹,往往称为“官马”,如《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咨:近据辽东道宣慰司申准:‘宣慰使塔海奉国开,即目当职钦奉圣旨领军迤东出征,遇有军情紧急差使人员,若无站赤走递,切恐迟慢,拟于咸平府至宋瓦江斟酌安立五站,用元当站户并见在官马内,每站差拨人八名,马八匹,权且安立守等走递。更委能辨头目,专一照管。’准此。”[9]7257此件公文称军站的站马为“官马”。故从此角度而言,黑水城文书中的“官羊户”所养之“官羊”,其含义之一可能是指在“军站”中用于祗应之羊。恰恰已知亦集乃路总管府所辖的蒙古八站,都属于“专备军情急务”之需的“纳怜道”上的军站[10]。因此,亦集乃路设置“官羊人户”有可能是为军站提供“官羊”祗应服务的。
另外,亦集乃路官羊户的设置,可能还与提供宗王、驸马、妃子等的分例有关。从黑水城文献来看,亦集乃路承担着在此地的多名宗王、驸马、妃子等的分例,而分例中有一项即为“羊口”。如一件编号、拟题M1·0443[F20:W57]《诸王妃子驸马屯住分例羊口文书》的第3、4行记载:
3. 诸王、妃子、驸马屯住分例羊口,比依
4. 内府支持上、中、下等弟羊口斤重则例支付,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比例应付施行。准此。札付[8]536
此件要求亦集乃路按照内府支持羊口的标准,向屯驻于此的诸王、妃子、驸马等应付他们的“分例”。而这些作为分例的羊口,至少应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官羊户所提供的“官羊”。
因此,综上推断,亦集乃路设置的“官羊户计”,有可能是为军站提供“官羊”服务的,当然也有可能还包括为相关宗王、妃子、駙马等提供分例“羊口”的义务。由于其他地区不存在提供该类羊口的服务,故未设有此类户计。亦集乃路官羊户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元代户计制度具有“因需设户”“因地制宜”的设置原则。
(二)关于元代的“取状”
对于元代的“取状”,《吏学指南》“状词”条释曰“谓采彼情理也”[11]。由此可知,该类文书应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状词”类文书。对于该类文书,学界已有所关注,如侯爱梅在《〈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一文中,借助于黑水城文献探讨了其性质、书式、内容,认为:“接受诉状之后,官府会将原告、被告和证人等带到法庭,对其进行审问和调查取证,并详记其交代的内容,即写出取状。”取状的“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取状人的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健康状况、住址和户籍。第二,取状人详述事情的经过。第三,取状人保证性的语言,即被取问人向官府保证所说的均为事实,如有虚假,甘愿承担法律责任。例如‘所供前词是的实并无虚诳’,‘对问不实甘当诳官重罪不词’等。第四,取状的时间以及取状人的签字画押。”[12]陈瑞青先生在侯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元代取状的渊源等问题,认为取状最早出现在五代宋时[13]。另外,吴佩林先生在探讨清代的“叙供”文书时,亦提及了元代的取状,认为取状与康熙年间的“‘招状’具有相同的功能”[14]。此后,张晋藩先生则在《中国古代民事诉讼制度》一书中重新讨论了“取状”的性质,认为“在审案时,官府除寻求物证外,还需原告、被告与证人等审讯、推鞫后的供词、证词等,由办案吏员详细记录,即为取状”[15]。可以说,取状作为元代词讼领域广泛使用的文书,经学界之努力,对其性质、内容、渊源等的认识已不断走向深入。然,对于该种“状词”却仍有进一步探寻的空间,如关于取状中对取状人“户籍”信息的登载,前人即言之寥寥,仅侯爱梅之文略有所及,但其文仅指出在取状中存在登记取状人户籍的现象,至于如何登记、为何登记户籍等,侯文则未予回答。下面结合天理图书馆所藏黑水城文书等试加探析。
首先,关于取状中如何登记户籍的问题。
目前来看,取状是黑水城元代文献中所存数量较多的一类文书,学界曾做过统计,认为其数量有近30件[15]。实际上笔者统计,黑水城元代取状的数量远多于此,共约60余件。之所以存在如此数量的取状,这主要与黑水城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词讼案件有关。从中也可窥见“取状”在元代使用之普遍,对于词讼之重要。在这些取状中,确有很多文书登载了相关取状人的户籍,如编号、拟题为M1·0555[F124:W10]《拜也倫婚姻案》文书,其内容如下:
1. 取状妇人拜也伦
2. 右拜也伦年卅五岁,无疾孕,系本
3. 路在城站户张唐兀乃子失列门驱
4. 口,见在额迷渠与夫同居。除俻细
5. 词因另行别立短状,招伏,不合于至正
6. 八年正月廿二日听从夫妻朵忽
7. 说:“你向拜也伦言说我与乃立温八[8]689
(后缺)
由此件首行所载的“取状妇人拜也伦”一语可知,此件当系一件关于妇人拜也伦的取状文书。第2至4行确实登载了取状人的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健康状况、住址和户籍等,其中“系本路在城站户张唐兀乃子失列门驱口”,按取状的通行内容,当是对拜也伦户籍的登载。由此可知,拜也伦是失列门的驱口。但是,按照元代户籍制度,未经放良的驱口,是没有独立户籍的,驱口的人口信息等要登记在其户主的名下。如黑水城文献中编号、拟题为M1·0001[F125:W73]《即兀汝户籍》,第5至18行载:
5. 一户即兀□嵬汝:
6. 元佥祖爹即兀屈支立嵬
7. 人口:
8. 成丁男子:
9. 祖爹年四十三 、父速正卜年一十六、房屈真蒲年廿六、
10. 叔真玉一十三;
11. 不成丁妇女一口:祖婆略只五十五;
12. 驱口:
13. 男子: 者赤屈年四十五, 妇女:金祖廿三。
14. 事产:
15. 房五间;
16. 地土五顷四伯七十培,见种二百六十培,麦子廿二石,
17. 残破不堪廿一石子地。
18. 孽畜: 马三匹, 牛一十只, 羊七十口。[8]39
此件是“即兀□嵬汝”的户籍,而其驱口者赤屈、金祖登记在其户籍之内。同时,由“即兀□嵬汝”的户籍文书可知,在一户完整的户籍中,不仅要登记人口信息,且还要登记“事产”、“孽畜”等。另外,通过新出上海图书馆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元代湖州路户籍可知,在相关户籍中,往往先登载有关人户的“户计”,再详细登载该户的人口、事产等。如该书第1册第11叶背第1户载:
一户:王万四,元系湖州路安吉县浮玉乡六管施村人氏,亡宋时为漆匠户,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归附
计家:亲属六口
男子:叁口
成丁:貳口
(中略)
事产:
(中略)
孽畜:
(后略)[16]
故由此来看,所谓妇人拜也伦取状中对其户籍的登载,显然不是失列门一户户籍的全部信息,而仅仅是对拜也伦“户计”的登载而已。
再如,在黑水城《失林婚书案卷》中有一件闫从亮的取状,其内容如下:
1. 取状人小闫名从亮
2. 右从良,年廿四岁,无病,系
3. 巩西县所管军户,见在城
4. 家寄居,□□阿兀
5. □ [8]872
(后缺)
此件作为闫从亮的取状,基本内容也是按照取状人的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健康状况、住址和户籍等事项进行登记的。而此与上件拜也伦取状相似,对闫从亮户籍的登载,实际上也仅仅是对其“户计”的登记,并不是对一户完整户籍的登载。
取状在何种情况下才登载完整的户籍信息呢?本文所讨论的此件文书恰好可提供相关的信息。作为阿剌的取状,不仅记载了户计,而且登载了其高曾祖父、 妻 □,二男,以及驱口、孽畜等,而第7行的“帐房一座”无疑是对其“事产”的登记。因此,此件中该部分内容实则是有关阿剌的户计、人口、驱口、孽畜、事产等。显然,这些内容应该就是有关阿剌一户户籍的全部信息。之所以在阿剌的取状中登载了户籍的全部内容,而拜也伦、闫从亮取状则仅记其“户计”,个中原因,主要是阿剌为其户的户头(或称户主),而拜也伦、闫从亮等则并非户头,前者是“驱口”,后者则属于“寄居”户,他们均不具有独立的户籍,仅是其所在户籍中的附属人口。由此可知,元代取状中所谓登记取状人的“户籍”,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有取状人是户头时,才登记该户的完整户籍,而取状涉及到一户户籍中户头以外的人口时,仅需登记其户计,并不会登记该户的完整户籍信息。同时,由此也可进一步认识到,元代的户计与户籍虽然息息相关,但似又不能等而视之,户计只是户籍的一部分,户计并不能完全代替户籍。
其次,关于取状中为何要登记户籍的问题。
为何要在取状中登记户籍,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确定取状人的身份,为日后定罪、刑罚提供依据和参考。如所周知,元代属于等级制社会,在整个社会中施行四等人制,不同民族出身的人,在同类案件中所受到的惩罚是不同的。对此学界已有共识,无复赘言。而不同户计出身的人,实际上他们所受到的惩处也有差别的。对于此点,黄清连先生指出:元代的良贱之间、诸色户计之间在诉讼判决以及刑罚等多方面都有所区别。如良贱之间,诸奴婢告其主者,处死。而一般户计杀伤奴婢娼佃等贱户,其罪止杖七十七,决一百七,或赔钱了事[4]115-116。在诸色户计之间,诸如宗教户计,他们在刑罚方面如同他们在赋税等方面相似,也享受特别优待,而与一般户计相比,弓手、军户则似较受优待,等等[4]125。因之,确定取状人的身份,也即户计,是日后对其定刑、判罪的重要依据。所以,在取状中要载明相关取状人的户计。
其二,登记取状人的户籍,为日后的经济惩罚或赔偿提供依据。如前所示,在阿剌的取状中完整地登录了其户籍,其中除其家庭的人口外,还登载了相关驱口、孽畜、事产等。而这些人与物,都被视作户主的财产。元代在对涉案的有关人员进行处罚时,除刑罚之外,有时还会附带经济惩罚。如《元典章》“杀人偿命仍征烧埋银”条载:
至元二年二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凡杀人者,虽偿命讫,仍出烧埋银五十两。若经赦原罪者,倍之。”钦此。[17]
由此条可知,所犯杀人之罪的罪犯,不仅要处死,且要罚银。另外,偷盗之类的犯罪,罚没所获赃物更是在所难免,如《元典章》“拯治盗贼新例”记载,至大四年(1311)七月二十五日下达的一道圣旨云:
今后豁开车子的,初犯呵,追了陪赃,打一百七下。再犯呵,追了陪赃,打一百七,流远有。三犯呵,敲了者。又怯烈司偷盗骆驼、马匹、牛只,初犯呵,追九個倍赃,打一百七,流远者。再犯呵,敲了者。又外头偷盗骆驼、马匹、牛只的,初犯呵,追九个倍赃,打一百七者。内若有旧贼每呵,数他每先做来的次数,依已定来的例,合配役的交配役,合出军的交出军者。先不曾做贼的每,开读圣旨之后,再犯呵,追了倍赃,打一百七,流远者。三犯呵,敲了者……[17]1631-1632
此处登载了对于各类偷盗犯的倍偿规定。而阿剌的取状显示,所涉及是有关杀人、抢劫、分赃的案件。因此,对于阿剌的日后处罚,势必会涉及到经济处罚。因之,在阿剌的取状之中登记其所有的家庭财产信息,可能也是出于为日后对其进行罚没而做的准备。
(三)关于元代的塔塔元帅府
文书第12行载有“塔塔元帅府”,该机构传世文献无载,而其他黑水城文献等亦无所见,此件文书是关于该机构的唯一记载。关于此机构的相关情况,今试探如下。
元帅府是蒙元时期重要的军事机构,叶子奇曾云:“各路立万户府,各县立千户所,所以镇压各处。其所部之军每岁第迁口粮,府县关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帅总之。”[18]这里的元帅,即指元帅府的主要长官,由此可见元帅府之重要。关于“塔塔元帅府”中的“塔塔”二字之义,似可据蒙元时期元帅府的命名情况加以推断。关于元帅府的命名方式,往往冠以地名、族名、军种名、机构名、行军方向等。其中以地为名者,如东川、西川、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等;以族为名者,主要是指蒙古都元帅府、元帅府等;以军种为名者,则如蒙古军都元帅府、炮手元帅府等;以机构为名者,如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以行军方向为名者,则有征东、征西元帅府等。当然,还有一些是由地名与军种名等多名组合的元帅府,如东路蒙古军都元帅府等。元代元帅府的通行命名方式,并不包括人名,“塔塔元帅府”中的“塔塔”二字,当非人名,但也似非军种名、机构名及行军方向,故其为地名或族名的可能性较大。笔者浅见,尚未发现元代有地名为“塔塔”者,目前所知元代西北地区仅有一与之相关地名,即“塔塔里”,元廷曾在此地置屯田千户所[6]2569,但未见该地有元帅府、万户府等更高级军府的设置,也未见“塔塔里”可简称“塔塔”的记载。所以说,“塔塔元帅府”中的“塔塔”为“塔塔里”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综上推测,“塔塔”二字更有可能为族名。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塔塔”一名,应非源自于汉语,而当是来自于蒙古语。其中与“塔塔”相似的“塔塔儿”一名,又作“达达”,它们是蒙古语tatar的不同音译。“入元后,有时称大漠南北蒙古诸部或蒙古本土为达达兀鲁思。”[19]而按《至元译语》所载,“达达”即“蒙古歹”[20]。由此蠡测,“塔塔”一名或即是“蒙古”之意,而“塔塔”若作为族名,也符合元代元帅府以族名+元帅府的命名惯例。
黑水城元代文献中,恰恰有“蒙古元帅府”的相关记载。如一件编号为俄TK248的文书,第20、21行记载:“一起蒙古元帅府使臣朵卜歹等二人,前来本路,给散本管军人军粮钱勾/当。”[21]这里有“蒙古元帅府”的“使臣朵卜歹等二人,前来本路”,这里的“本路”,经诸家研究确认即为亦集乃路。而蒙古元帅府使臣来亦集乃路的目的,是为了“给散本管军人军粮钱”,即这二位使臣是来亦集乃路发放蒙古元帅府相关军人“军粮”的。这无疑反映出,蒙古元帅府在亦集乃路有轮戍的军队[22]。再如,一件英藏编号、拟题为OR.8212/754K.K.0150(b)《元至正十九年(1359)亦集乃路广积仓具申季报粮斛现在并放支军人季粮事呈文》的文书,今节录如下:
1. 呈禀□□□{1}亦集乃路广积仓照得至正十九年正月至三月终春季三个月季报现{2}粮斛已行
2. 呈了当外,据四月至六月终夏季三个月季报现{3}粮斛未曾具申
3. 实有见在粮斛取八□{4},保结开坐,合{5}行具申,伏乞
(中略)
8. 三勺 一帖寒字陆拾伍号放支朵立只罕翼{6}军人春季三个月杂色大
9. 麦柒拾石玖斗捌升陆合陆勺陆抄伍作。
10. 一帖寒字柒拾壹号放支蒙古元帅府军人春季三个月杂色大
11. 麦壹拾柒石令壹升叁合[7]226
(后缺)
这里载明,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亦集乃路所申请放支的军粮中包括蒙古元帥府的军粮。此外,还有一件编号为M1·0985[Y1:W201正]的文书残尾,也与放支蒙古元帅府军粮相关:
(前缺)
1. 蒙古元帅府春季口粮 管 军 官
(蒙古官吏名)
(签押)
2. 管军元 帅
(蒙古官吏名)
(签押)
3. 管軍元 帅
塔剌赤
4. (签押)(签押)
5. 初九日(朱印) (签押)[8]1254
由以上文书可知,蒙古元帅府在亦集乃路进行过轮戍是无疑的。因此,塔塔元帅府有可能是黑水城文书中的蒙古元帅府。另,从以上可以确定时间的相关蒙古元帅府文书来看,这些文书均属于元代后期的文书,如俄TK248文书,陈高华先生指出其应该属于元后期的文书[23],而上文所引OR.8212/754K.K.0150(b)文书的时间表明,此件亦应属于元代后期。因此,有理由相信,蒙古元帅府可能是在元后期于亦集乃路进行轮戍的。故由此进一步推测,此件天理图书馆所藏黑水城元代文书也有可能是元代后期的文献。
那么,驻扎于亦集乃路的蒙古元帅府又是来自哪里呢?据李治安先生研究,元代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其前身即蒙古都元帅府,而该府在改称蒙古军都万户府后,蒙古都元帅府与蒙古军都万户府两者依然存在“经常混同使用”的情形,该军府的管辖用兵范围包括吐蕃、甘肃。同时,李先生根据蒙元王朝“擅长搞大区制官署机构”,且“陕西行御史台掌陕、甘、川、云四省监察”的实例推断,“西部四省设一个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管辖统率,完全合乎蒙元王朝的习惯。”[24]笔者同意李先生的上述判断。又,因元代亦集乃路属于甘肃行省所辖,故进一步推断,元后期在该路轮戍的蒙古元帅府,有可能是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的派出军队,或其所辖的相关军府。
另外,前人对元代西北驻军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关系已有深刻的认识,如胡小鹏先生指出:“元朝对宗藩是削弱不削平,有意使宗王与行省并存分治,相互维持,相互监督,”[25]而“征西都元帅府”、“沙瓜州屯储总管万户府”等,又“对河西诸王起到威慑镇遏的作用”[25]213。因之推断,宗藩之外的元帅府、万户府等军事机构,除威慑镇遏宗王外,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当不外乎相互“维持”与“监督”。通过本文所讨论的文书来看,亦集乃路的军事机构与本路之间的关系还有“深度融合”的一面。如通过阿剌的取状可知,阿剌是被塔塔元帅府捕获的,而审讯工作则是由亦集乃路完成。元帅府与路总管府之间,通过协作、分工,实现了对犯人的搜捕与审讯。而此过程无疑显示出,塔塔元帅府已融入到了亦集乃路总管府的行政运作和管理之中。同时,前人还指出,元代在捕盗过程中,往往是“采取官、军、民联合捕盗的方式”[26]。但现据阿剌取状来看,对于阿剌等犯人的捕获,实无官、民的参与,而仅由军事机构塔塔元帅府完成的。这似乎又进一步反映出,元代在捕盗过程中,并非仅是多方联合捕盗的方式,亦有军事机构单独捕盗的。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蒙匿名审稿专家指正,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孙继民. 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柯劭忞. 新元史[M]. 北京:中国书店,1988:637.
[3]侯爱梅. 黑水城所出元代词讼文书中的法制术语考释与研究[J]. 西夏研究,2016(4).
[4]黄清连. 元代户计制度研究[M]. 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77:1.
[5]陈高华,等. 《元典章·户部·户计》校释[C]//暨南史学:第4辑.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154.
[6]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794.
[7]沙知,吴芳思.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第1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52.
[8]塔拉,等.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2314.
[9]永乐大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8.
[10]李逸友. 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29-30.
[11]徐元瑞,著. 杨讷,点校. 吏学指南(外三种)[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39.
[12]侯爱梅. 《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J]. 宁夏社会科学,2007(2).
[13]张重艳,杨淑红. 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整理与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297-299.
[14]吴佩林. 清代中后期州具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J]. 历史研究,2017(5).
[15]张晋藩. 中国古代民事诉讼制度[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229.
[16]王晓欣,郑旭东. 元湖州路户籍册初探——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1册纸背公文纸资料整理与研究[J]. 文史,2015(1).
[17]陈高华,等,点校. 元典章[M]. 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489.
[18]叶子奇. 草木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59:64.
[19]邱树森. 元史辞典[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828.
[20]贾敬颜,朱风. 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
[21]孙继民,等.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87.
[22]陈广恩. 黑水城文书所见元朝对西北的经营——以亦集乃路为考察中心[J]. 西夏学,2018(1).
[23]陈高华. 黑城元代站赤登记薄初探[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24]李治安. 元史暨中古史论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3,141,151.
[25]胡小鹏. 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216.
[26]韩清友. 元朝捕盗述论——从《儒吏考试程式》中的捕盜材料谈起[C]//暨南史学:第18辑.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