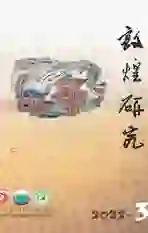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鹦鹉图像初探
2022-07-11王煜陈姝伊
王煜 陈姝伊







内容摘要: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中出现了较多的鹦鹉图像,该题材并不见于传统汉墓装饰,也未见于其他地区的同时期墓葬,而敦煌地区乃至西域正好有出产鹦鹉的记载,并深刻地影响魏晋文化,鹦鹉图像的出现应该是汉代以来传统丧葬文化与河西本地乃至西域物产、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作为神仙化了的奇禽异兽出现在照墙砖画中;另一方面固定出现在表示墓主灵座的帷帐壁画上,不仅作为一种玩好,还可能具有象征“亡人居宅”的丧葬内涵。
关键词:魏晋时期;敦煌;壁画墓;鹦鹉;丧葬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3-0031-0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arrot Images from the Wei-Jin Mural Tombs at Foyemiaowan, Dunhuang
WANG Yu CHEN Shuyi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Several images of parrot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murals in tombs from the Wei-Jin dynasty period at Foyemiaowan in Dunhuang. This motif is not seen in traditional Han dynasty tomb decorations nor in tombs of the same period in other places, though there are records that parrots were depicted in the art of Dunhu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locations that deeply influenced the culture of the period.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images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funer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s of the Hexi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parrots in the brick paintings on the screen walls erected in front of the gate to the tomb were depicted as deified birds and bea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ages painted on the curtains covering the memorial tablet for the owner of the tomb often appear in roles more akin to pets and even seem to be intended as a funerary culture symbol of the future residence for the deceased.
Keywords:Wei and Jin dynasties; Dunhuang; mural tomb; parrot; funerary culture
敦煌地區的魏晋壁画墓目前公布的主要见于佛爷庙湾墓地,规模同样庞大的祁家湾墓地中则主要是小型的土洞墓,除三块砖画墓,基本不见图像装饰[1]。而佛爷庙湾墓地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在墓室中尤其照墙上绘制了丰富的图像,反映出当时当地社会生活和思想信仰的许多方面。其中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一类关于鹦鹉的题材,而此种题材在其他地区及之前汉代墓葬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中都殊为少见,显得特别而突出。以往的报告和图录中已经辨识到此种题材,但缺乏进一步的探讨。少有的涉及到该题材的研究中,由于其主题和重点的不同,也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讨论。我们拟对该题材进行专题研究,在全面、系统梳理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图像位置、环境等因素,探讨该类图像出现的背景及在墓葬中的内涵和意义。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讨论。
一 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中的鹦鹉图像
目前所见材料中,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中的鹦鹉图像主要出现在墓葬照墙砖画和墓室中帷帐壁画的顶端{1}。
(一)照墙砖画中鹦鹉
河西地区魏晋时期壁画墓的一大特点是往往用小砖修葺照墙,刻画或绘制各种仿木建筑装饰或砖画。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最为突出:照墙往往修葺得十分高大,多以一砖一画的形式绘制大量图像,题材主要为各种神仙和瑞禽神兽,也有少量历史故事等。在众多瑞禽神兽中有鹦鹉。
M37照墙现存部分最下部为仿木斗拱和结构,仿木结构上方集中为各种瑞禽神兽,其中下数第二排两侧绘制一对相向而立的禽鸟,二者形态、色彩、特征完全一致:皆圆眼钩喙,长尾阔爪。羽毛整体涂白色,喙部涂红色,背部墨绘条状斑纹,腹部有红色斑纹(图1)。自发掘报告以来均认定为鹦鹉,不见异说,从其整体形态及钩喙、阔爪的特点和羽毛的颜色、斑纹来看,无疑是鹦鹉。
M133照墙下部仿木斗拱两侧也绘制一对相向而立的禽鸟,也是圆眼钩喙,长尾阔爪。从报告中的摹本看,似为墨绘,无涂色,背部仍有上述鹦鹉图像的条状斑纹(图2)。除无色彩外,整体形态和特点都完全一致,当然也是鹦鹉。
M118照墙下部仿木斗拱两侧同样绘制一对相向的禽鸟,以墨勾绘,更为写意,整体形态与特征与上述两对一致,钩喙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唯一不同的是,其趾爪描绘为总体向前的姿态,与上述两对前后阔爪略有不同(图3)。我们知道,鹦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前后对趾如上述两对所绘,这里的一对禽鸟似乎不符合这一特征。但是,从其整体的位置、形态和特点来看,我们认为这里要表现的题材应与上述两对一致,只是其勾画更为抽象和随意,这从其整体的风格也可以看到,因此对其的辨别应该观察其整体特征与相同位置、组合中的同类图像对照,不必完全拘泥局部细节。
此外,墓地中还出土了一些散落的壁画砖,其中也有鹦鹉题材[2],描绘或精或粗,皆是钩喙阔爪的特征,有的背部也有条状斑纹。从这些砖的形制、大小和壁画所在的砖面来看,对比上述材料,应该原来也属于照墙上的砖画。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进行调查,其中翟宗盈墓(FYM1001)是该地区最早发掘的一座画像砖墓,照墙部分画像砖现完整保存在莫高窟第143窟。堆砌于龛外南侧的照墙下部仿木斗拱两侧相对站立两只禽鸟,其弯喙,羽色青绿,长尾,圆眼,应该是鹦鹉无误{1}。
(二)墓室壁画中的鹦鹉
M1墓室后壁满绘一座帷帐,墓主夫妇对坐于帷帐之内的两个榻上,帷帐脊顶两侧绘一对禽鸟。圆眼、钩喙、长尾,头部、背部和翅膀涂绿色,背部有墨绘条状斑纹,腹部也有斑纹,爪部未表现[3]。从其整体形象和突出特征来看,毫无疑问也是鹦鹉。
M37墓室后壁也绘一座帷帐,帷帐前还设置供台,帷帐内未绘墓主人像,帷帐脊顶两侧也绘一对鹦鹉,位置、组合、形象皆与上述M1所见者相同(图6)。
与上述两座单室墓不同,M133具有前、后双室,前室北壁(墓向正西)设置壁龛。壁龛正面绘一座帷帐,前面还设置陶案等供器,帷帐内也未绘墓主人像。帐顶两端也绘一对鹦鹉,圆眼钩喙,喙部涂红色,背部和翅膀似为浅绿,背部有墨绘条状斑纹(图4、7)。
可见,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中有较多的鹦鹉图像,有的描绘较具象,甚至还敷以色彩,有的则仅用墨线勾绘,比较粗率,具体细节表现略有不同,根据总体特点、斑纹表现和出现位置予以比较,应能确定为同类。敷色者喙部基本为红色,身上羽毛有绿色和白色两种。目前所见,除一些散见的砖画外,主要出现在几座较为完整的墓葬M1、M37、M118、M133和翟宗盈墓中,实际上该墓地较为完整的壁画墓共发表5座(M37、M39、M118、M133和翟宗盈墓),其中4座有鹦鹉图像,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应该说还是比较流行的题材。
河西地区汉晋时期流行带有茔域的家族墓地,墓地中的砖室墓和壁画墓的比例都很低,根据其规格和位置,往往都是墓地中的祖墓。如M1位于家族茔域最南端,M37、M133皆位于家族茔域最北端,应该皆为祖墓。这几座墓葬的年代也属于墓地中最早的一期,报告中推断为西晋早期,并根据墓葬形制、规格和随葬品等推测为迁入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墓葬,“是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地区的改造和变异”[4]。也有學者将这几座墓的时代推定为曹魏至西晋前期,总之也属于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中最早的一期[5][6]。
然而,鹦鹉图像却不是中原传统的墓葬装饰题材。商周时期虽然曾有过一些鹦鹉形的玉饰{1},但与这里墓葬图像中的鹦鹉显然相去甚远,汉晋时期的玉饰中似乎也缺少传承。自汉代以来出现并流行的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墓葬图像中,钩喙的鸟类多是鸱鸮,并无鹦鹉。有些带有神仙色彩的鸟也被描绘为钩喙状,个别与鹦鹉的形象还颇有类似之处,如山东济宁喻屯镇出土画像石上的口吐丹丸的大鸟[7]和四川大邑董场乡出土画像砖上仓房(旁有题记“食天仓”)上的飞鸟[8],根据场景和组合它们更应该被理解为凤鸟[9],也不具有能判断为鹦鹉的较为具体的细节。应该说敦煌佛爷庙湾墓地中较为流行的鹦鹉图像是具有较为具体的时代和地域背景的。
二 鹦鹉图像出现的背景
鹦鹉原是种群众多、分布广泛的鸟类,中国境内就有分布[10]。先秦时期人们已知晓其基本特点,上述商周时期的一些鹦鹉形玉饰即为一种表现。《山海经·西山经》说:“(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2}《礼记·曲礼上》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11]《淮南子·说山训》云:“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是何则?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高诱注:“鹦鹉,鸟名,出于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缥绿,能效人言。”[12]《说文·鸟部》亦云:“鹦鹉,能言鸟也。”[13]可见,汉代人们对鹦鹉的认识已比较具体,除形态特征外,还特别注意到其学舌的特性,并以之作为譬喻,说明这一认识在人们观念中已有一定的广泛性。
除本土的鹦鹉外,汉晋时期文献中还记载徼外蛮夷和外国常向朝廷进献鹦鹉。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夏)南越献驯象、能言鸟”,颜注“即鹦鹉也,今陇西及南海并有之。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有三种,一种白,一种青,一种五色。交州以南诸国尽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盖谓此也。隋开皇十八年,林邑国献白鹦鹉,时以为异。是岁贡士咸试赋之。圣皇驭历,屡有兹献。”[14]可见,汉唐时期南海诸国一直有进献鹦鹉的传统,大概其地的鹦鹉比较卓异(如“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作为域外奇禽的代表。《初学记》引刘艾《汉帝传》云:“(献帝)兴平元年,益州蛮夷献鹦鹉三。”[15]《晋书·安帝纪》亦载:“(义熙十三年)六月癸亥,林邑献驯象、白鹦鹉。”[16]
最值得注意的是,汉魏之际兴起的咏物赋中忽然流行《鹦鹉赋》的写作,特别兴盛于魏晋,直到东晋南朝,作者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突出。其中写作最早和影响最大的首数汉末祢衡的《鹦鹉赋》[17],而其写作背景即源于西域进献的鹦鹉。据序中介绍:“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坐咸共荣观,不亦可乎?’”[18]从“有献鹦鹉者”和“此鸟自远而至”来看,显然是外方进献。祢衡的赋开篇即言“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又云“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18]611,所咏的鹦鹉来自西域。
其后,汉魏之际的曹植、陈琳、王粲、应玚、阮瑀,两晋的成公绥、张华、傅玄、傅咸、左芬、卢谌、曹毗、桓玄等人群起仿效,直到南朝的颜延之、谢庄、萧统等人还有类似作品[19],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其中,阮瑀《鹦鹉赋》云:“惟翩翩之艳鸟,诞嘉类于京都。秽夷风而弗处,慕圣惠而来徂。”[18]619也指出所咏鹦鹉来自殊方远域。傅咸《鹦鹉赋》云:“有金商之奇鸟,处陇坻之高松。谓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笼。”[19]1576提到鹦鹉来自“金商”之地,也就是西方(五行属金,五音属商)。卢谌《鹦鹉赋》云:“有遐方之奇鸟,产瓜州之旧壤。挥绿翰以运影,启丹觜以振响。”[19]1576直接将祢衡所谓的“西域”、傅咸所谓的“金商”之地比定在地接西域的瓜州。
《左传》云“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西晉杜预分别注云“瓜州,地在今敦煌”、“瓜州,今敦煌”[20]。据现代学者研究,先秦时期的瓜州可能并不在敦煌[21],汉晋时期人们确实认为其地在敦煌。除上引西晋大学者杜预的意见外,《汉书·地理志》中云“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侯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14]1614,《续汉书·郡国志》亦云“敦煌郡,武帝置……敦煌古瓜州,出美瓜”[22],皆言瓜州在敦煌。
可见,从祢衡而降的早期《鹦鹉赋》中所咏的鹦鹉极有可能就来自敦煌地区,而同一时期敦煌佛爷庙湾壁画墓中出现较多不见于之前和其他地区的鹦鹉图像,恐怕不能说全属巧合。西晋张华《禽经注》说:“鹦鹉,出陇西,能言鸟也。”[23]上引颜师古注《汉书》也说:“即鹦鹉也,今陇西及南海并有之。”看来陇西直到唐代仍然出产鹦鹉,可见上述文学作品并非臆想。不过,或许由于一方面南海所出的鹦鹉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晋室南渡之后与南海的交通更为便利,东晋以后的鹦鹉诗赋中更多属于南海诸国进献的情况。另外,敦煌地区是连接西域的关键点,从其地进献的鹦鹉是源出本地还是中转西域,由于材料无征,目前只能存疑。
三 鹦鹉图像的功能与意义
汉晋时期流行的《鹦鹉赋》主要在于借鹦鹉的特性和遭遇表达丽而被拘、慧而被笼,充当玩好而怀才不遇的情感,墓葬中的鹦鹉图像又重在表达何种意义,具有何种文化内涵呢?图像题材的功能与意义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图像场景与组合去考察。如前所述,目前所见的鹦鹉图像皆出现在照墙砖画和墓室壁画中,且二者皆具有较为稳定的图像场景和组合,这是探讨其功能和意义的关键。
我们知道,敦煌地区魏晋时期壁画墓的图像有着总体的结构:墓室内主要表现墓主的帷座和物品,以及一些生产生活题材;照墙最上部往往突出表现一扇大门,一般认为代表天门[24],最下部则为仿木斗拱,二者之间以一砖一画的形式集中排列各种神仙神兽,偶有一些历史人物。
M37、M118和M133的照墙砖画上皆有鹦鹉,总体处于各种神仙神兽的环境中,更可能是作为一种神仙化的瑞禽而描绘的。值得注意的是,在M37照墙砖画上,鹦鹉出现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鹿、象、独角兽和伯牙、子期的环境中,图像分布明显具有对称性(图5)。此外,青龙与白虎、朱雀与玄武搭配也显示出一定的设计性。鹦鹉与大象搭配。当然,这样的搭配在对称原则下可能有偶然性,目前尚属特例,难以进一步推论。然而,当时文献也确实常将鹦鹉与大象并提。如上引《汉书·武帝纪》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晋书·安帝纪》也说“林邑献驯象、白鹦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驯禽封兽之赋”注云“驯禽,鹦鹉也。封兽,象也”[25],可见,不论砖画上是否刻意将鹦鹉与大象组合在一起,在这里它们都是作为域外奇禽异兽的代表,在整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鹿、独角兽的环境中当然也是神禽瑞兽的表达。将域外的奇禽异兽进行一定程度的神仙化在汉墓图像中十分普遍,已多有讨论{1},兹不赘述。将鹦鹉神仙化大概与人们认为它智慧能言的特性有关。如上引祢衡《鹦鹉赋》即云:“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全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的志怪小说如《异苑》、《宣验记》中都有神仙化鹦鹉的故事,其核心皆与鹦鹉能言有关[19]1575。
除照墙砖画外,鹦鹉还出现于M1、M37、M133墓室壁画中,都被表现在帷帐顶部两端。M1中帷帐下绘出男、女墓主对坐像,M37和M133皆是一座空的帷帐,且在帷帐前设置有供台,其上还有陶案等供器,一般认为也是象征墓主灵魂所在并在墓中享祭(图6、7)。西晋成公绥《鹦鹉赋》云:“小鸟以其能言解意,故育以金笼,升之堂殿。”[26]壁画中成对的鹦鹉虽然没有“育以金笼”,但其栖于帷帐顶端,也可谓“升之堂殿”。东晋桓玄《鹦鹉赋》亦云:“革好音以迁善,效言语以自骋。翦羽翮以应用,充戏玩于轩屏。”[19]1577可见,魏晋时鹦鹉常作为玩好,被修剪羽翼而置于轩屏之间,与其立于帷帐之上的场景颇为一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时周宣《梦书》云:“鹦鹉为亡人居宅也。梦见鹦鹉,是亡人也,其在堂上”[26]4102,知鹦鹉在魏晋时期还被当作“亡人居宅”的象征,出现在表示墓主灵魂所在的帷帐之上的鹦鹉,是否还有强调墓主灵座的丧葬意义,由于与墓葬和帷帐壁画的环境更为贴合,目前所见的三例墓主帷帐上都出现了鹦鹉,似乎已形成一种较为具体的格套,或许具有更为特别的涵义,这种阐释方向尤其值得考虑。当然,目前材料尚有限,需要今后进一步发现和更多材料的公布来检验。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中出现了较多的鹦鹉图像,皆为钩喙、圆眼、长尾,背腹部往往有条状斑纹,其形象或具象或抽象。有的描绘出鹦鹉特有的对趾,性质十分明确;有的则为一般鸟趾,而描绘为一般鸟趾的都比较抽象、写意。从整体特征、位置和组合等因素综合来看,无疑属于同类。有的图像还敷有彩色,鸟喙皆涂红色,羽毛有绿色和白色两种,也与鹦鹉的特征相合。
该题材并不见于汉代流行的墓葬图像中,目前也未见于其他地区的魏晋墓葬。鹦鹉在中国本土即有出产,多体小而色绿,先秦至汉代人们对其已有一定认知。而殊方远域出产的鹦鹉不仅体大,且兼有绿色、白色和五彩多种,更被人们珍视,成为进献宫廷的重要珍禽,人们也更强调其来自域外,来源主要有南方和西方。恰好魏晋时期的敦煌地区据记载也出产鹦鹉,直至唐代仍颇知名。由于敦煌为汉地与西域的转接点,似乎不能排除有西域传来的可能性(祢衡《鹦鹉赋》中笼统说西域)。而从西域而来的鹦鹉更是刺激了当时《鹦鹉赋》的产生和流行,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鹦鹉题材突然流行于魏晋时期敦煌地区的墓葬壁画中,是具有中原传统墓葬文化(壁画及神禽瑞兽装饰)与敦煌本地乃至西域珍奇物产相结合的特殊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的。
鹦鹉图像比较固定地出现于照墙砖画的神禽瑞兽中,可能由于其聪慧能言,人们在丧葬文化中对其有一定的神仙化。鹦鹉与大象作为域外进献珍禽异兽的代表,常在魏晋时期的文献中组合出现,也组合出现在敦煌魏晋壁画墓照墙上的神禽瑞兽中。鹦鹉图像还固定出现于墓室壁画中表示墓主灵魂所在的帷帐顶部,或可理解为墓主居室中的玩好宠物,但其格套化明显,可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根据魏晋时期文献的记载,鹦鹉在当时人观念中可以是“亡人居宅”的象征,而出现或不出现墓主形象的帷帐正好是“亡人居宅”的表现,其前还有供祭设施和器具,鸚鹉出现于其上,可能表达了这一特殊的丧葬意义。
出现鹦鹉图像的这些墓葬往往都是家族墓地中的祖墓,是西迁河西的世家大族丧葬文化的代表,其中所反映出的结合汉代以来传统丧葬文化和河西本地乃至西域文化因素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北印度犍陀罗佛教石刻中,有一些在拱形门内雕刻菩萨像或佛传故事,而拱形门的两侧也出现对称的鹦鹉,时代在公元2—4世纪[27]。其意匠与帷帐两端对称鹦鹉有一定相似之处,由于敦煌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上述魏晋鹦鹉文化与西域的关系,我们觉得应该将这个问题附带提及,期待今后继续判别和探究。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39.
[2]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心. 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541.
[3]殷光明. 敦煌西晋墨书题记画像砖墓及相关内容考论[J]. 考古与文物,2008(2).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05.
[5]孙彦.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5.
[6 ]郭永利.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38.
[7]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 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23.
[8]大邑县文化局. 大邑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C]∥四川考古报告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393.
[9]庞政. 汉代“凤鸟献药”图像试探[C]∥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1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87-200.
[10]何业恒,文焕然,谭耀匡. 中国鹦鹉分布的变迁[J]. 兰州大学学报,1981(1).
[11]郑玄,注. 孔颖达,正义. 礼记正义[C]∥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31.
[12]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107-
1108.
[13]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6.
[14]班固,撰. 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6.
[15]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2:737.
[16]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66.
[17]金性尧. 祢衡与《鹦鹉赋》[J]. 古典文学知识,1996(5).[18]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 全汉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11.
[19]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75-1577.
[20]杜预,注. 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C]∥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55,2056.
[21]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005.
[22]司马彪,撰. 刘昭,注. 续汉书·志[C]∥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5:3521.
[23]王琦,辑注.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32.
[24]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57.
[25]范晔,撰. 李贤,注.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860-2861.
[26]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4102.
[27]湖北省博物馆. 佛像的故乡:犍陀罗佛教艺术[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