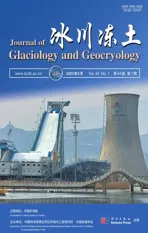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发育特征及规律
2022-06-19牛富俊林战举刘明浩尹国安高泽永
罗 京, 牛富俊, 林战举, 刘明浩, 尹国安, 高泽永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 730000)
0 引言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是世界中、低纬度地区高海拔多年冻土的代表,分布面积约1.5×106km2,占我国冻土面积的70%[1]。多年冻土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气温的微弱变化都可能导致其温度状况和稳定性发生很大的变化[2]。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环北极高纬度多年冻土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持续的退化过程[3-6],青藏高原作为全球变化的“驱动器”和“放大器”,其多年冻土的退化速率更加明显[7-9]。从20 世纪70—90 年代,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的年平均地温在非连续多年冻土区增加了0.3~0.5 ℃,在连续多年冻土区增加了0.1~0.3 ℃[7]。自1999年以来,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多年冻土活动层厚度增加了35~61 cm,年平均增加速率为4 cm[9]。此外,模拟结果表明:在年增温0.02 ℃情形下,50 年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面积比现在缩小约8.8%;若升温率为0.052 ℃·a-1,50 年 后 高 原 多 年 冻 土 将 退 化13.5%[10-11]。因此,气候变化和工程活动影响下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正处于退化过程,并且这种退化趋势将持续存在。
多年冻土退化导致的地下冰融化将诱发一系列热融现象的发育,这种热融现象在平坦区域主要表现为热融湖塘和热融沉陷,在斜坡区域主要表现为热融滑塌。热融滑塌一般指在厚层地下冰分布的斜坡区域,由人为活动或自然因素而造成地下冰暴露,在融化季节地下冰融化使其上覆的融土失去支承而在自重作用下发生塌落的现象。热融滑塌的发生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很多学者认为热融滑塌的形成不仅会导致其下部数米高含冰量冻土融化,还会导致周边数公顷范围内冻土的热状态发生改变[12-13]。同时,在热融滑塌的发生过程中会释放以前保存在冻土层中的化学溶质,使得滑坡区域土壤的离子浓度和pH 值均高于非滑坡区域[14]。因此,在热融滑塌的影响下,其临近区域内的地温状况、植被结构、生物群落以及湖泊的湖底沉积物化学性质都将发生改变[15]。更重要的是热融滑塌的发生还将导致近地表冻土层中的碳释放到大气中,进而影响区域碳循环过程及气候变化[16-18]。此外,热融滑塌的发生还可造成工程设施的直接破坏,诸如2018 年9 月发生在风火山南麓的一处热融滑塌造成铁路防洪及路基热棒设施的直接损坏;同年8月发生在国道G214温泉乡附近一处热融滑塌直接掩埋公路,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热融滑塌发生以后由于滑壁位置地下冰的暴露和融化而产生大量泥流物质沿坡面向下流动,这些泥流物质会进一步掩埋道路和堵塞桥涵,并将加速路基下部多年冻土融化以及路基软化湿陷,严重影响工程构筑物的长期稳定性。
虽然目前针对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19-21],但这些工作基本都是以单点研究为主,系统性和区域性研究工作仍然比较缺乏。青藏高原未来规划了高速公路、新的输电工程、输油管线工程甚至有可能修建铁路复线,受制于青藏工程走廊工程容量以及密集工程之间的相互热影响,新建的线性工程必将着眼向两侧的丘陵山地区域扩展。此外,随着内地资源探明储量的减小,未来各种矿产资源开采会逐渐考虑向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转移。热融滑塌的发育一方面会对这些工程设施的稳定性和安全运营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工程建设又会诱发大量热融滑塌的发生,破坏区域生态环境。因此,热融滑塌对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未来工程规划、建设及环境保护的影响将日趋突出。在未来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工程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增多以及环境保护要求提升的大背景下,准确掌握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的发育机理、特征及规律,可为区域工程规划、资源开发及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1 热融滑塌的发育机理及诱发因素
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多年冻土斜坡区域地下冰暴露和融化是热融滑塌形成的主要原因。在高纬度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一般是由河流或波浪的冲刷侵蚀[22]、湖岸的坍塌[23]、地表径流导致的冰楔融化[24]以及森林大火燃烧腐殖质层[25]等过程引起地下冰的暴露而诱发。近年来的野外调查发现,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主要由工程扰动、湖水侵蚀以及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而诱发(图1)。工程扰动型热融滑塌主要以发育在青藏公路里程K3035 路基西南侧的一处热融滑塌为主要代表,该热融滑塌是20 世纪90 年代初青藏公路二次整治过程,由于路基坡脚开挖导致地下冰的暴露而引起。该类型的热融滑塌主要发生在青藏工程走廊范围内,且目前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对工程和环境的影响较小;湖水侵蚀型热融滑塌主要发生在有厚层地下冰发育的湖岸斜坡区域,该类型的热融滑塌目前仅在可可西里地区错达日玛湖东南侧湖岸有大量分布,别的区域几乎没有发现;活动层滑脱型热融滑塌是由冻土活动层滑脱发生以后其滑壁位置地下冰的暴露和融化而形成,该类型的热融滑塌大量分布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有厚层地下冰发育的丘陵山地区域。

图1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工程扰动诱发的热融滑塌(青藏公路里程K3035)(a);湖水侵蚀诱发的热融滑塌(可可西里,错达日玛湖)(b);冻土活动层滑脱诱发的热融滑塌(红梁河附近)(c)Fig.1 The retrogressive thaw slump developed in permafrost reg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the one induced by engineering activities(K3035 of Qinghai-Tibet Highway)(a);the one induced by lakeshore erosion(Cuodarima Lake,Hoh Xil)(b);the one induced by the occurrence of active-layer detachment(near the Hongliang River)(c)
通过对目前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已调查和标记的热融滑塌(约200 多个)进行统计发现,95%以上的热融滑塌是由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而诱发。冻土活动层滑脱是指在多年冻土区地下冰发育的斜坡区域,活动层土体连同其上覆的植被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下部多年冻土发生分离并滑移的现象[26]。活动层滑脱的形成主要是因地下冰融化而形成的融水不能及时排出,最终导致活动层与冰面之间的抗剪强度减小而引起[26]。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活动层滑脱的发育与土质类型、冻土含冰量[27]以及一些特定的外部诱发因素(包括极端的夏季高温、森林大火,以及极端的降水事件)密切相关[28-29]。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罗京等人通过典型冻土活动层滑脱的现场水热监测、冰-土界面现场直剪试验以及考虑降雨和地震影响下冻土斜坡的稳定性分析,明确了极端高温和降水事件引起的厚层地下冰过度融化和冰-土界面抗剪强度减小是诱发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活动层滑脱发生的主要原因[30-31]。
2 典型热融滑塌的发育过程
本文选取发育在北麓河盆地孤山北侧的一处典型热融滑塌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其发育过程(图2)。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发现该热融滑塌发生在2015 年10 月下旬至2016 年12 月中旬之间,并且根据滑塌前缘土体被挤压形成的隆起及侧壁附近的擦痕推断该热融滑塌是由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而诱发,而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是由上限附近地下冰的融化而引发,一般发生在夏末时期活动层融化到最深的时期,由此进一步推断该热融滑塌可能发生在2016 年9 月底。在活动层滑脱发生以后,滑壁位置地下冰的暴露和融化将导致滑壁处的活动层土体变得不稳定,在张力作用下形成大量的裂缝,随着地下冰的继续消融,裂缝会继续增大并最终导致滑塌壁的坍塌和后退,滑塌的土体随着地下冰的融水形成泥流状物质沿坡面向下流动。因此,热融滑塌的发育可以简单概括为“活动层滑脱—热融滑塌—泥流”三个过程。
2018年8月现场测得该热融滑塌的最大宽度约160 m,最大长度(包括泥流)约500 m,后缘的滑壁高度6~7 m,滑壁位置暴露的厚层地下冰厚度4~5 m。根据后缘位置距滑塌壁5 m 处的钻孔勘查资料可知,滑塌后缘位置自地表而下的土层为:0.0~0.8 m,红褐色松散的细砂层夹杂碎石;0.8~2.4 m,红棕色黏土,夹杂碎石;2.4~12.8 m,厚层地下冰,含冰量60%以上;12.8~15 m,强风化泥岩。大量厚层地下冰的存在将为该热融滑塌的继续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
为进一步分析热融滑塌的发育过程,2018 年9月在该滑塌的后缘布设了8组滑塌壁后退速度人工监测点,每组监测点包括2个监测桩,每个监测桩的间距为5.0 m,每次沿着每组监测点的方位,分别测定滑塌面至各个监测点的距离。为了保证测量精度,每组监测点测量两遍,将两次测得的平均值作为计算数据。自2018年9月开始,每年的5月份和9月份对滑塌壁的后退量进行定期观测。2018年9月至2020年10月的具体测量结果如表1所示。
监测结果表明该热融滑塌从2018 年9 月至2020 年9 月滑塌壁的平均后退距离为39.2 m,其中最大后退距离为60.4 m,发生在监测断面No.4,最小后退距离为13.5 m,发生在监测断面No. 1(表1)。监测断面No.4 位于一个有间歇性流水的冲沟处,流水的热侵蚀作用加速了滑塌壁的塌落和后退。此外,从监测结果看出,2018—2019 年滑塌壁的平均后退距离21.0 m,大于2019—2020年的平均后退距离(18.2 m),这可能是由于滑塌物质覆盖了部分暴露的地下冰而导致滑塌速率减小,也可能是因2019 年和2020 年融化季节气温或降水量的差异而导致。现场考察发现目前该热融滑塌的滑塌壁高度及其下部的含冰量并未发生明显的减少,因此推断该滑塌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以10~20 m·a-1的后退速度扩张,直到滑塌壁下部厚层地下冰明显减少或者消失为止。

表1 不同时期8个监测点滑塌壁的后退距离Table 1 Head scarp retreat distances along eight transects
3 热融滑塌的分布特征及控制因素
3.1 热融滑塌的解译及形态分布特征
选取青藏高原热融滑塌发育最为密集的北麓河盆地作为研究区,基于该区域2018—2019年高分2 号遥感影像数据,通过目视解译得到区域内热融滑塌的分布情况如图2(b)所示,并于2021 年1 月对解译的热融滑塌进行现场验证,发现解译的准确率达到98%以上。本次解译得到可识别的热融滑塌573 个,平均面积2.1 公顷,其中面积小于2 公顷的热融滑塌约占64%,面积大于5 公顷的热融滑塌约占10%[图3(a)]。热融滑塌的周长在130~3 910 m之间,平均周长785 m,并且90%以上热融滑塌的周长小于2 000 m[图3(b)]。

图2 发育在北麓河盆地孤山北侧的一处热融滑塌现象及其地理位置: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及北麓河盆地的地理位置(a);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分布及孤山热融滑塌(b);孤山热融滑塌航拍照片(c);滑面的泥流(d);滑塌壁(e);前缘的隆起(f)Fig.2 A retrogressive thaw slump developed in the north slope of the Gu Hill,Beiluhe Basin:permafrost distribu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Beiluhe Basin(a);the distribution of retrogressive thaw slumps in the Beiluhe Basi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Gu Hill thaw slump(b);the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Gu Hill thaw slump(c);mud flow on sliding surface(d);the head scarp of the thaw slump(e);compression ridges developed at the toe zone of the thaw slump(f)
计算得到热融滑塌的圆度在0.07~0.64 之间,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平均圆度为0.36[图3(c)],说明该区域热融滑塌的轮廓为圆形的较少,主要以次棱角状和次圆状为主。热融滑塌长度与宽度的比值(长/宽)在0.5~6.2 之间,平均值为2.77[图3(d)],说明区域内的热融滑塌整体形态主要为长条形,而扁平状的较少。

图3 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形态统计特征:面积(a);周长(b);圆度(c);长/宽(d)Fig.3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trogressive thaw slumps in the Beiluhe Basin:histograms of area(a),perimeter(b),circularity(c),and length-to-width ratios(d)
3.2 热融滑塌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解译结果可以看出,北麓河地区的热融滑塌主要分布在盆地西侧的山地丘陵区域[图2(b)],并且在盆地的西北侧有一个热融滑塌聚集发育区(区域A),该区域分布了整个盆地80%以上的热融滑塌。为进一步分析热融滑塌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ArcGIS 软件提取了所有热融滑塌发育点的高程、地形位置指数、坡度及坡面朝向,并统计了热融滑塌在不同地形因子的分布频率,结果如图4所示。
北麓河地区90%以上的热融滑塌分布在海拔为4 650~4 850 m的范围内[图4(a)],该海拔范围正好是盆地周边高山的山麓区域及部分山地丘陵分布区,而海拔较高的山顶区域及海拔较低的盆地平坦区域基本没有热融滑塌分布。统计结果显示研究区热融滑塌的地形位置指数在-1.3~0.6 之间,约80%的热融滑塌分布在地形位置指数小于零的区域[图4(b)],说明热融滑塌更倾向于分布在洼地区域。坡度的统计结果显示热融滑塌主要分布在3°~8°的坡度范围内,且近50%的热融滑塌发育的坡度在4°~6°之间[图4(c)]。热融滑塌分布的坡向统计结果表明,北麓河地区的热融滑塌主要分布北向、西北向及东北向的阴坡区域[图4(d)],这些区域通常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较少且地表湿润、厚层地下冰较发育。

图4 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的空间分布特征:高程分布频率(a);地形位置指数分布频率(b);坡度分布频率(c);坡向分布频率(d)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trogressive thaw slumps in the Beiluhe Basin:statistic results of elevation(a),topographic position index(b),slope,and(c)slope aspect(d)
3.3 热融滑塌分布的控制因素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热融滑塌的分布与海拔高度、地形位置指数、坡度及坡向等地形因素密切相关。在整个青藏高原大尺度范围内,海拔高度决定了多年冻土的分布,进而决定了热融滑塌的空间分布范围。在北麓河小尺度范围内,海拔高度与特定的地貌单元密切相关,海拔较高的山顶区域由于风化层薄且含冰量少,而海拔较低的盆地平坦区域由于坡度过于平缓,都不适宜热融滑塌的发育,因此大量热融滑塌分布在海拔介于中间的丘陵山地区域及高山的山麓一带。
根据野外调查和统计结果,热融滑塌更倾向于分布在山前3°~8°的缓坡区域[图4(c)],因为该区域一般为地下水的汇集区且细颗粒风化层相对较厚,更有利于厚层地下冰的发育,夏季融化季节气温升高或降水增加容易诱发冻土活动层滑脱及其后缘位置热融滑塌的发生。在坡度较大的区域,虽然有较大的重力势,但通常风化层薄且含冰量小,不容易发生热融滑塌,而在坡度很小的区域,由于重力作用引起的下滑力也很小,也不足以诱发热融滑塌的发生。
在非多年冻土区,一些研究者认为坡向往往与降水量的分布以及水文地质条件有关,从而影响滑坡等斜坡失稳现象的空间分布[32-33]。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大量的野外调查和统计结果显示热融滑塌主要分布在太阳辐射较少的阴坡区域。一方面阴坡区域由于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小而导致活动层厚度普遍较浅,在夏季极端高温的影响下更容易引起活动层底部地下冰的融化及坡体失稳,另一方面阴坡区域往往积雪较厚且蒸发量相对较小,相对于阳坡区域其土壤湿度大,厚层地下冰更容易发育,因此更有利于热融滑塌的发育。
热融滑塌的空间分布除受海拔高度、坡度及坡向等因素控制以外,微地形因素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地形位置指数统计结果说明,在其他地形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热融滑塌更倾向分布在坡面较低洼的位置。首先低洼位置更有利于积雪及降水的汇集,厚层地下冰比较发育;其次在夏季融化季节,冻土层上水往往会在低洼位置发生聚集,引起孔隙水压力升高,从而诱发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
热融滑塌的分布不仅受地形条件的控制,也受冻土条件(冻土地温、含冰量、活动层厚度)及土质类型等地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冻土条件方面,热融滑塌更多分布在高温、高含冰量及活动层厚度较薄的冻土分布区;在土质类型方面,热融滑塌一般分布在黏粒含量较高且风化层较厚的斜坡地带。由于缺少冻土条件及土质类型与热融滑塌分布的具体统计关系,因此关于地质环境因素对热融滑塌分布的影响这里不做深入讨论。
4 青藏高原热融滑塌的骤变过程及诱发因素
4.1 热融滑塌的骤变过程分析
近年来的野外调查中发现,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热融滑塌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些热融滑塌诱发的时间及其变化规律,获取了北麓河地区2008—2018 年不同年份的高分辨遥感影像 数 据(包 括2008 年5—9 月 的Wordview-1 及SPOT-5 影像、2010 年3 月和10 月的Google Earth 及SPOT-5 影像、2012 年11—12 月的Google Earth 影像,以及2013 年10 月、2015 年9—10 月、2015 年8—10 月、2016 年10—12 月、2017 年8 月、2018 年10 的高分1 号及2 号影像),通过目视解译和现场验证,得到北麓河盆地不同时期热融滑塌数量和面积的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
从图5 的解译结果可以看出,北麓河盆地的热融滑塌从2008 年至2018 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总数量从124个增加到了445个,总面积从131公顷增加到了986公顷,分别增加了2.6倍和6.5倍。并且这些热融滑塌数量和面积的增加主要发生在2010 年3 至10 月之间,以及2015 年10 月至2016 年12 月之间,这两个时期热融滑塌的数量分别增加了57%和67%,由于热融滑塌一般发生在夏季活动层融化达到最深的时期,由此推断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的骤增应该发生在2010 年和2016 年的9 月份。因此,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从2008 年至2018 年的增加过程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每一年,而是集中发生在2010年和2016年这两个特定的年份。

图5 2008—2018年不同时期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数量和面积变化[修改自Luo等[34](2019)]Fig.5 The number and area of thaw slumps interpreted from satellite images from 2008 to 2018[revised from Luo et al[34](2019)]
4.2 热融滑塌骤增的诱因分析
野外调查发现,近年来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数量的剧烈增加主要是由冻土活动层滑脱发育增多而引起。作者曾基于冻土斜坡区域冰-土界面现场大型直剪试验、冻土斜坡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揭示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活动层滑脱(冻土滑坡)的可能诱发因素主要包括夏季极端高温、降雨量的增加及地震活动的影响[30]。根据国家地震台网的记录数据,北麓河地区自2008至2018年的夏季融化时期没有震级大于4级的地震发生,因此地震作用不足以诱发大规模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推断气候条件可能是导致其大规模发育的主要因素。
北麓河盆地附近五道梁国家气象站2008—2018 年不同年份融化季节(6—9 月)日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统计结果见图6。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热融滑塌剧烈增多的2010 年和2016 年,融化季节日平均气温分别为5.7 ℃和5.75 ℃,均超出多年平均值1 个标准差,而融化季节累计降水量在这两个年份并没有异常变化,均在多年平均值1 个标准差范围内。除2010 年和2016 年,另外一个融化季节气温明显偏高的年份为2013,但是该年份融化季节累计降水量为多年的最低值,仅为198 mm。从图5 的统计结果看出,2013 年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多,其原因可能与该年度降水量极端偏少有关,也可能与该年度融化季节平均气温比2010和2016 年相对偏低有关。此外,虽然2018 年是降水量极端偏多的年份,但由于该年份融化季节日平均气温在多年均值的1 个标准差范围内,单独的降水量增多并未引起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的大规模发育。此外,热融滑塌的骤增可能与极端降雨事件的发生有关,但通过对五道梁气象站2010 和2016年日降雨量数据的分析发现,这两个年份的融化季节并没有降雨强度很大的降雨事件出现,其最大日降水量均在20~30 mm 之间,并且持续的天数不超过1天,类似降雨事件在其他年份均有出现。

图6 五道梁气象站2008—2018年融化季节(6—9月)平均气温及累计降水量分布散点图:日平均气温(a);降水量(b)Fig. 6 Average daily air temperature and cumulative precipi⁃tation in thawing season from the automated weather stations in Wudaoliang Town from 2008 to 2018:average daily air temperature(a),and the cumulative precipitation(b),1 June to 30 September,2008—2018
因此,融化季节极端的高温天气应该是引起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骤增的主要诱发因素。在正常年份,夏季活动层融化的最大深度一般会到达多年冻土的顶板位置或者顶板位置以上,但在夏季气温异常偏高的年份,活动层融化的深度可能会超过多年冻土顶板而导致其下部少量地下冰发生融化。地下冰的融化一方面会导致活动层与多年冻土界面之间的抗剪强度降低,另一方面地下冰的融水还会引起界面位置孔隙水压力的升高,从而诱发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冻土活动层滑脱发生以后,由于后缘位置地下冰的暴露和融化,进而演化成热融滑塌。
降水不仅会引起坡面水位的升高,而且降雨的入渗还能促进活动层的热量向冰土界面传输,因此降水量的增多可能会促进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但从统计结果来看,降水量的变化对热融滑塌数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与北麓河地区冻土活动层的土层结构有关。在北麓河盆地及青藏高原大部分区域,冻土活动层的上部基本为渗透性极强的砂土,而下部却为渗透性极差的致密黏土,因此绝大部分降水会沿坡面或者上部的砂土层流失,很难入渗到活动层底部而引起坡体水位的升高。此外,在高纬度多年冻土区,冬季积雪厚度及春节融雪的开始时间都会对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育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在北麓河地区,冬季的降雪量一般在20 mm以下,并且持续的大风天气很难有一定厚度的积雪存在。因此,积雪也不是引起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增多的主要因素。
5 结论
本文通过野外调查、现场监测及遥感资料解译等手段揭示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融滑塌的诱发因素、发育特征、分布规律及历史演化过程,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
(1)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热融滑塌一般是由工程扰动作用、湖水侵蚀以及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而诱发,其中冻土活动层滑脱的发生是其最主要的诱发因素。
(2)基于典型热融滑塌的现场监测发现,热融滑塌的发育过程主要包括活动层滑脱的发生、后缘坍塌后退及坡面泥流的形成这三个阶段,并且在厚层地下冰未消失或明显减少的情况下,热融滑塌的溯源侵蚀过程将持续存在。
(3)热融滑塌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海拔高度、坡度、坡向以及其他微地形条件控制,其中坡度是最主要的控制因素,80%以上的热融滑塌分布在坡度为3°~8°的范围内。
(4)近年来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热融滑塌呈现出骤增的趋势,通过对北麓河盆地热融滑塌历史变化过程发现,这种骤增现象主要发生在有极端气温出现的特殊年份,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每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