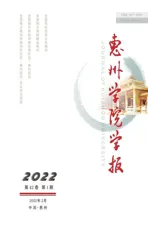王学左派对晚明艺术精神的影响论略1
2022-03-17梁愿
梁 愿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中国艺术一直重视生命精神。与传统艺术所追求的指向宇宙整体的与道合一、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不同,晚明艺术所追求的生命精神是指向独立个体的,指向当下自我的。个体生命精神是晚明艺术精神的特质所在。表现于文学领域,就是“人生而有情”的主情审美取向。晚明文论打破了传统的中和、含蓄原则,主张自由大胆、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体自我的浓烈激情,由此晚明文学塑造了一批具有独立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的人物形象;表现于书画领域,则为“老夫游戏墨淋漓”的创作追求。晚明绘画不求形似,晚明书法宁拙勿巧,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宣泄个体意绪、突显个体真性。
晚明艺术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偏离传统美学的个体生命精神,与王学左派①的濡染作用有密切关系。首先,由于王学左派的影响,晚明性灵说阐述了一种性情并育的观点,这使得晚明艺术对“情”的态度与传统美学有所不同。而且,受王学左派“不须防检”的工夫论所启发,晚明艺术置传统法度于不顾,而一味讲求以无法为法。此外,晚明艺术的通俗转向,亦与王学左派的世俗化紧密相关。
一、王学左派的性情并育观与晚明性灵说
黄卓越先生指出②,晚明存在两种性灵说,一是以虚灵为中心的去情论的性灵说,一是浑情式的性灵说。前者主要为屠隆所推崇,后者则主要为袁宏道所推崇。在黄先生的论述中,性灵被看成是与情感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因此他认为浑情式性灵说并不是晚明性灵观的主要内涵。笔者更认同韩经太先生关于“探询其自我解构之所以有自我解构之势的思理内因……有助于把握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的演变规律”[1]的观点,由此认为偏离了性灵之哲理本义的浑情式性灵说,更能体现晚明艺术精神对传统的超越之处及其特质所在。
(一)王学左派的性情并育观
对于情与性之关系的看法,是王学左派与王阳明的一个分歧所在。在王阳明看来,情是有碍回复无善无恶之心体的。而在王学左派那里,情与性在无善无恶之心体中共存共处。
王阳明把心作为本体,认为心体无善无恶、不假外求,因此他主张格心,强调顿悟。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为善去恶,并没有舍弃修行工夫。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存在矛盾的思路,是由于借鉴了转型期禅学思路的缘故。王阳明借鉴禅学思路而树立的心体,与慧能、神会所言之心体有共通之处。慧能、神会以般若空观对早期禅学的修行论进行了改造,把渐修论发展为顿悟论。但他们对般若空观的运用未能贯通修行论与佛性论,在佛性论上,慧能与神会仍未脱离早期禅学的清净本性说。清净本性说对于心体的认识是基于染净二分观之上的,七情六欲被认为是与虚明心体相对的。阳明心学对“为善去恶”的强调,正表明其对于心体的认识与清净本性说一致。阳明心学之心体虽曰无善无恶,却是偏向至善的,是与私心相对的。
王学左派也讲良知心体,然而他们对良知心体的理解与王阳明不同。在王学左派这里,良知心体被认为是现成自在的。这是随缘禅以作用为性的逻辑思路,在此逻辑思路中,良知不再是理想境界的至善性体,而是当下无善无恶之心体。对于良知心体的这样一种理解,导致了王学左派对于性与情采取一种并存并育态度。当王畿提出“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且讲求自性流行时,已经为性情并育观提供了生长土壤。王学左派认为情感欲望并非就是与性体相对立的,相反,自然之欲似乎已为性体所包涵。这在王艮处有更明晰的体现。王艮极言吾身之尊,并把身提至道的高度。可是王艮却认为,人之私丝毫不会损坏道德之性体,其明哲保身论如是道:“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2]715。人人自爱其身,以己度人,那么这种私心便是利己而不害人的。王艮以最实在的例子说明了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性情相育而不相害。结合其“身与道原是一体”的观点,又可推论出情本就与性不可分。这种情不损性的观点,得到了王学左派众多成员的认可,如罗汝芳所言:“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2]800何心隐亦云:“欲货色,欲也;欲聚和,欲也”[3]。至此,王学左派完全摆脱了传统儒学性善情恶的二分论。
王学左派对马祖一系的禅学思路多有吸收,了解马祖以下禅僧对人之私的态度,可辅助理解以上所论述的王学左派的性情并育观。印度佛学与中国早期禅学,都主张禁欲修行。当慧能提出即心即佛思想,修行工夫就从苦修苦行之渐悟一变而为一念之转之顿悟。至马祖道一,又提出非心非佛思想,对悟与未悟的一齐肯定,完全抛弃了修行工夫。于是,随缘禅兴起之后,酒肉与佛祖并存的禅宗哲学备受推崇。据载宋代一位禅学大师曾宣称,只要顿悟本心,就可以出入“四五百条花柳巷”,逛逛“二三千座管弦楼”[4]。即便没有如此极端,也一般都认同大珠慧海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5]。总之,禅宗对于情与性的看法与西方佛学大大不同了,情与性不再泾渭分明,二者可谓共生共存。王学左派在借用禅宗思想时,很明显也接纳了这一性情并育思想。
(二)浑情式性灵说对性灵思想的拓展
将晚明性灵说区分为虚灵式性灵说与浑情式性灵说,其依据的是二者对情感的不同态度。实际上,情感这一问题在晚明艺术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从晚明性灵说出现这样一个由去情到浑情的转变,尤其能看出王学左派的影响作用。
“性灵”一词并非晚明才出现。早在南朝时期,《文心雕龙·序志》已经提到了“性灵”一词。之后,钟嵘在《诗品》中赞扬阮籍诗可以陶冶性灵。北周诗人庾信同样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抒发性灵。颜之推也说:“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6]350。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但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关于性灵的主张不时会在诗论中出现。
学者们在探究性灵思想的渊源时,有将其追溯到《庄子》与陆机《文赋》的③,更多将其追溯至佛学思想④。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或可从两者的共同点看出早期性灵思想的某些特性。不管是老庄思想,还是早期佛学,其中的心性都是指向虚灵境界的。在庄子那里,心的最好状态是混沌状态,然而后世已不具备远古之世的淳朴,心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处于混沌状态,于是必须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去欲复性。庄子所要达到的至高境界,是只关涉至情至性的澄明之境。佛学亦然。对修行工夫的重视源于早期佛学对性体的认识。早期佛学基于染、净二分观来认识性体,这一性体是必须经过苦修苦行之后才能达到的清净性体。再来看陆机《文赋》。陆机“诗缘情”的思想,的确大大突破了儒家“止乎礼义”的束缚,然而这种突破不可能是彻底的。它最终把诗文的作用归结为济世明理,就决定了它无法超出儒家中和之美的范畴。可见,无论追溯至《庄子》与《文赋》,抑或追溯至佛学,都可推论出早期性灵思想是指向虚灵之美的,是超越私心的。
就指向虚灵之美这一点而言,晚明虚灵式性灵说尚未溢出早期性灵思想的义界。虚灵式性灵说同样认为须超越私心才能抒发性灵,这一点在屠隆的性灵观当中尤其明显。屠隆指出性灵对文章的重要性,之后论道:“诗道大都与禅道之言通矣。夫禅者明寂照之理……兀然枯坐,阗然冥心……余闻惟寅筑贝叶斋,日跏趺蒲团之上,而诵西方圣人书,与衲子伍,则惟寅之性灵见解如何哉!”[7]所谓“寂照”“兀然枯坐”“阗然冥心”,都是回归清净本性的拂拭工夫,可见屠隆所言之性灵是基于清净性体之上的。
公安派的性灵说与虚灵式性灵说大有不同,最为人注目的是公安派对私心私欲的张扬。首先,公安派性灵说所要抒发的并非淡泊之心,而是包含爱恨嗔痴的个体真情。在公安派这里,直抒一种带有私心、欲望的情感,并不会影响诗歌意境,相反认为此乃情至之语。其次,由肯定与虚灵相对的嚣动之情出发,公安派进一步大肆宣扬酒色财气等自然情欲。公安派性灵说对于情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仍将其划归性灵说,而不认为它是主情论,原因在于公安派性灵说的性情并育思想。虽然公安三袁时时以酒色为人生乐趣,可从未放弃读书养性。中郎之人生五乐中,便有一乐为读书著述。小修在“贮妓乐,置酒召冶游”的同时,亦不忘“右手持《净名》,左手持《庄周》”[8]。性与情于此似乎没有任何冲突,甚至到了和谐融洽的地步。袁宏道明确反对以理抑情:“今人只从理上絜去,必至内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为害也,不知理在情中而欲拂情以为理,故去治弥远”[9]1290。情不碍性,甚至性在情中,这正是蕴含于浑情式性灵说的性情并育观。
公安派性灵说的性情并育思想与王学左派的性情并育思想是一致的,分析可知前者由后者影响而来。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借鉴了李贽童心说,而李贽童心说中即有性情并育思想。李贽童心说对人之私心是肯定的,不过肯定私心只是童心说的一方面,从李贽的发愤著述言论,可了解到童心说的另一面。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提出不愤则不作。不愤则不作,也是童心说的绝假纯真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愤的内容指向什么呢?李贽在这篇点评中,对宋公明那种心在朝廷专图报国的精神大加赞赏。可见,一方面如平时所指出的李贽是肯定人之私心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于舍生取义的大公之心,同样推崇备至,这正是李贽性情并育思想的体现。事实上,童心说的性情并育思想与王学左派有着渊源关系。李贽曾与众多王门弟子有所交往,不过从其专拜王襞为师,可知更倾心泰州学派的心学思想。可以说,公安三袁对王学左派的接受,主要就是通过李贽思想来实现的。
若再联系虚灵式性灵说的思想来源,还可知,思想来源的不同决定了虚灵式性灵说与浑情式性灵说的区别。屠隆的虚灵式性灵说,其思想来源为王阳明的良知说。屠隆在《刘鲁桥先生文集序》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即人心之灵明境界,而灵明一词实属性灵之义。前已指出,屠隆的性灵说是指向清净性体的。可见,屠隆对于性灵的理解与其对良知的理解有相当关联。作为虚灵式性灵说的思想来源,阳明心学对于至善性体的坚守,决定了虚灵式性灵说所追求的是纯明之美。而浑情式性灵说对王学左派性情并育思想的吸纳,又决定了它必然溢出虚灵式性灵说的义界,转而追求感性之美。
所以,公安派虽言“性灵”,然而已大大不同于屠隆等人所言之“性灵”。浑情式性灵说所展现出来的,已不是虚灵纯明之美,而是感性真我之美。从后来清代的袁枚对于性灵的阐述来看,应该说,注重私心私欲等自然情感的自然生发,已经成为公安派之后人们对于性灵涵义的主要理解。
二、王学左派的工夫论与晚明艺术之以无法为法
晚明艺术推崇以无法为法的创作主张。以无法为法,其实是宋代活法思想的进一步延伸。相比之下,晚明艺术之以无法为法赋予创作的自由度更大了。究其因由,可发现与王学左派的工夫论不无关系。
(一)王学左派的工夫论
王学左派的工夫论与其本体论紧密相关。而王学左派对于本体的看法,由于受狂禅思路影响,从而与王阳明有差别之处。王阳明借鉴转型期的禅学思路,指出良知本自具足,不必格物,只需格心。然而,王学左派借鉴狂禅无所分别的思路,把王阳明的良知自足发挥成了良知现成。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本自具足的,但并非当下即是的,它有被遮蔽的时候,因而王阳明时刻关注如何回复良知的本然状态。与之不同,王学左派则认为良知当下即是,既然心体无善无恶,那么由它所生发的意、知、物也无善无恶,良知的本然状态即为其当下状态。因此,去蔽回复毫无必要,王学左派只追求本体的自然发用、任性流行。
王学左派对于良知之发用的偏向与突出,导致其对为善去恶之修行工夫的消解。罗念庵曾指出王畿之学“无工夫可用”“以良知致良知”[2]407。确然,王畿主张:“无工夫中真工夫”[2]249。按其观点,本体即是当下,根本无需由工夫而致。这一思想至泰州学派得以全面阐发。王艮指出本体现成:“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真不须防检。不识此理,庄敬未免着意,才着意,便是私心”[2]716。其子王襞作了进一步论述:“才提一个学字,却似便要起几层意思……”[2]721王栋也认为:“只要认识此体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2]733。罗汝芳亦论道:“工夫难到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2]766。颜钧同样指出:“性如明珠,原无尘埃,有何睹闻?著何戒惧?”[2]703焦竑亦予以响应:“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10]。以上诸说,集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工夫不仅毫无必要,还无益于悟道,这就是王学左派的工夫论。
(二)晚明艺术之以无法为法
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如何对待前人的创作经验,一直是文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一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大力主张谨守法度、渊源有自。而另外一些接受了释道思想的文人,又认为需要超越法度、自求新意。如苏东坡就提出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不过,儒家在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就算动乱年代释道的影响有所突出,儒家的主导作用也没有改变。因此,苏东坡等人对法度的打破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打破法度,另一方面又要不离法度。晚明革新派文人也倡导打破法度,以无法为法。相比之下,晚明打破法度的程度要比以往彻底得多,从此时大量出现的尤为个性张扬的艺术作品可见一二。就思想渊源而言,这与晚明理学的式微、心学的兴起,尤其是王学左派的盛行有密切关系。
晚明革新派文人之所以倡导以无法为法,与其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的理解有关。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在明代中期影响很大,他们推崇诗人情感的抒发必须合乎秦汉文与盛唐诗的格调与法度。而晚明革新派认为,复古主张是个体真情自然抒发的阻碍,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以最决绝的姿态摈弃法度,以最大热情来倡导以无法为法。
首先,李贽就直率坦言:“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11]99。李贽提出童心说,把此前为法度所有的主宰文学生成的权力,完全移交给了独立的个体之心。徐渭亦认为法度是造成情感失真从而诗不为诗的一大原因。袁宏道不止一次谈到以无法为法,他说:“仆窃谓王、李固不足法,法李唐,犹王、李也。唐人妙处,正在无法耳。如六朝、汉、魏者,唐人既以为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虽慕之,亦决不肯法”[9]753。又说:“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9]188。“决不肯法”“任性而发”,彰显了公安派文论对前人法度的决然否弃。江盈科亦积极响应其以无法为法的创作主张。此外,陆时雍也在评杜甫诗时表达了有法不如无法的思想。至此,以无法为法,在诗文领域已经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响应。
以无法为法的创作主张,在书画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傅山坚决打破古法,晚年更自称“老来狂更狂”[12]。他刻意进行字体变形,即是摒弃法度、表现个性的努力,如《赠魏一鳌行草书》,以字本身的宽松结构,以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紧凑结构,营造出全幅琳琅满目、气势逼人的效果。表面看来师古的王铎,也一直追求超越法度、彰显自我。他曾这般描述最佳的创作状态:“至临写之时,神气挥洒而出,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13]。《赠张抱一草书诗卷》《草书杜律卷》便是这种创作状态的产物。像王铎这种主张不离古人而又个性张扬的做法,可通过晚明书家对临摹的态度得到更清楚的了解。徐渭说:“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14]。临摹并时时露己笔意,这是晚明临摹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独特面貌。可见,晚明书家做到了在古人法度中自由畅游,以无法为法。
晚明艺术以无法为法的创作主张,其实是对前人活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活法思想展开于宋代矫正江西诗派的模拟僵化流弊的过程中。黄庭坚是推崇法度的,他讲过这样一段话:“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6]316。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黄庭坚所言之“无一字无来处”,即为强调渊博的学识对作诗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说明黄庭坚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同样重视转化与出新。然而,当时的一些诗人,在实际运用中常做不转化与出新,结果仅是拘守法度,一味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过于谨守法度最后导致诗坛陷入日渐僵化的困境。这时候,如何超越法度便成为文论家们所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吕本中提出“活法”的文论思想。他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6]367。吕本中以“活法”来重新突出艺术创作的自由状态。将活法思想发挥到另一高度的是严羽。严羽提出“须参活句,勿参死句”[15]来回应吕本中的活法思想。而且,在他这里,艺术创作的自由状态得到了进一步推崇,表现于以“妙悟”来取消诗法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严羽认为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兴趣”,而“兴趣”是“无迹可寻”、无法可依的,因而只能“妙悟”。严羽的妙悟思想,带有禅家直指本心的意味。可以说,妙悟赋予了艺术创作极大的自由。但是,这一自由并非完全舍弃法度的自由。后来推崇法度的李东阳与主张复古的李梦阳,都对严羽的思想有所继承,说明严羽思想中存在与法度相谐和的一面。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妙悟需习得工夫,他说:“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素而有所入也”[16]。对于“妙悟”思想当中自由与法度的微妙关系,郭绍虞先生以妙悟含有透彻之悟与第一义之悟两种意旨的观点予以解释:“我们须知沧浪之所谓悟,与其论禅一样,也应分别二义:一是所谓透彻之悟,一是所谓第一义之悟。透彻之悟,由于以禅论诗,只是指出禅道与诗道有相通之处,所以与禅无关;第一义之悟,由于以禅喻诗,乃是以学禅的方法去学诗,所以与禅有关。透彻之悟,为王渔洋所常言,而第一义之悟,则又明代前后七子所常言”[17]。可见,主张妙悟的严羽,尽管重视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却也并非绝对摒弃法度。较之前面所论述的,不难看出晚明文论在此基础上又前进了,以无法为法所赋予创作的自由显然更多了,甚至几乎到了置法度于不顾的地步。
晚明艺术这种前所未有的决意摈弃法度、一味信手信口的创作主张,无疑与王学左派那种消解工夫、率性而行的思路是十分契合的。应该说,正是王学左派的工夫论为晚明艺术之以无法为法提供了基本思路,使之得以最终超越前人的活法思想。
三、王学左派的世俗倾向与晚明艺术的通俗化
晚明艺术显露出了通俗化倾向。相对文学而言,书法、绘画的通俗化倾向略为少些,但也呈现出更融入百姓生活以及更商品化的特征。晚明艺术的通俗化倾向,从根本上来说是商品经济繁荣与市民阶层兴起的结果。若探究其思想缘由,则可发现王学左派的世俗倾向也为其提供了哲理依据。要探讨王学左派的世俗倾向之于晚明艺术通俗化的影响,首先得了解阳明心学的世俗化过程。
(一)阳明心学的世俗化
虽然在陆九渊与王阳明这里,主体性得到了更多认可,然而其所言之心体仍是普遍的道德本心。陆九渊认为理是天下之公理,心是天下之同心,王阳明则主张心体为至善心体。也就是说,陆王心学的超越性是相当明显的。不过,随着心学的进一步发展,其超越性最终被王学左派所消解。王学左派通过对良知心体的重新解读,确立了个体当下之心的本体地位。这一消解阳明心学超越性的过程,就是其世俗化的过程。
首先,王畿对阳明心学世俗化的开启作用。王畿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改造,将王阳明四句教发展为四无说,原本在王阳明四句教中与心体有所区别的意、知、物,此时已与心体浑然一体。如此一来,一方面是意、知、物获得了本体地位,另一方面又是心体被赋予了现成性。沿此思路,王畿指出良知不仅是人人所具有的,而且是人人所现有的。他说:“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损而后全”[2]255。为进一步突出良知现成,王畿还把良知本体直接安放在穿衣吃饭等日常行为当中:“著衣吃饭无非实学,一念相应,便是入圣根基”[18]330。于是,阳明心学良知本体的超越性被大大削弱了。不过王畿思想存在矛盾的一面,他既极力突出良知的现成性,主张顿悟,可又说过不能“舍工夫说本体”之类的话:“舍工夫说本体谓之虚见,虚则罔矣。外本体而论工夫,谓之二法,二则支矣”[18]212。王畿在本体论上所主张的现成说,落实到工夫论并不彻底,良知依然具有超越性。但不管如何,王畿这一没有贯通始终的现成思想为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打开了序幕。
其次,王艮对阳明心学世俗化的推进作用。王畿在其逻辑演绎中把良知本体与百姓日用联系了起来,而王艮则在其济世理想中把二者等同了起来。与王畿一样,王艮亦主张良知现成,并且将良知本体安放在日常生活中。他说:“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19]。不仅如此,出于对普通百姓的关注,王艮还努力地把圣人之道落实为日用之道。这种努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的同一性。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2]714。在这里,“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重心已经由道不离百姓日用向百姓日用就是道转移。第二,重新阐释“人欲”,肯定自然欲望。“人欲”是程朱理学所绝对排斥的。王艮的言论似乎也对之持否定态度,如“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2]715。但若细究,则可发现王艮所反对的,是着意安排的杂念,而非程朱所反对的有悖儒家伦理的自然欲望。恰恰是在对任心自然的推崇当中,自然人欲得以被肯定。第三,易简的工夫论——乐学思想。为吸引百姓,王艮指出学习圣人之道是不需要刻意下工夫的,学习的目标是指向快乐的。从以上三方面可看出,阳明心学的贵族立场已转变为平民立场,其超越性也已为现成性所取代。不过,王艮的大同社会理想决定了其对于百姓的关注是一种群体关注,而非真正的个体关注。他提出每个人都应爱惜性命,其目标是为了以此推延最后天下人人保全。的确,王艮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向前推进了,不过亦尚有可深化的空间。
最后,李贽对阳明心学世俗化的深化作用。李贽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他对王艮的思想当然是有所继承的。除了继承,李贽对王艮思想亦有发挥。王艮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然而这一肯定如上所述是在群体关怀的视域之下的。李贽则不然,他对于个体自我的关注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的群体立场,这集中体现于其为己自适思想。李贽直言:“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11]16。另又有言:“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11]70。正是由于李贽的个体立场,阳明心学由圣人之学、成圣之学彻底落实为日用之学、为己之学。
(二)王学左派的世俗倾向对晚明艺术通俗化的影响
经王畿、王艮及李贽等人的发挥,王学左派思想呈现出了注重百姓日用、肯定自然人性、崇扬个体存在等世俗倾向。这样的思想转向,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晚明艺术的通俗化提供了哲理依据。
所谓艺术通俗化,大体而言,是指艺术更通俗易懂,更符合百姓的审美趣味。早在元大德年间,由于都市文化与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民族对于戏曲、歌舞的喜好,世俗文艺已经得到了相当发展。晚明时期世俗文艺再次兴盛,小说、戏曲开始成为主流文艺。这既是基于元朝世俗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又是此一时期商业经济繁荣与审美意识转变的结果。
晚明文学以日常生活、家长里短作为重要的创作内容,与王学左派对百姓日用的推举不无关系。王学左派将其哲学视点转向百姓日用,突出百姓日用与道的同一性,将道心落实为人心,这极大地抬高了百姓日用在哲学领域的地位。受此氛围影响,晚明文人也开始投入相当热情来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晚明的世情小说中,细屑繁琐、平淡庸俗的日常生活第一次成为文人们的聚焦所在。如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就是对市井生活的生动展现,而长篇章回体小说《金瓶梅》更是晚明世俗生活的全景式画卷。除了新兴盛的小说,传统的文学体式抒情散文也开始描写日常生活。在袁宏道笔下,一些日常情景成为主题,恢宏志气与高尚道德悄然隐去,如《满井游记》。
晚明文学的通俗化,不止表现于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更重要的是对于市民阶层的价值观晚明文人是抱着认同的创作情感的。晚明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层的享乐主义日渐冲破儒家的勤俭道德观而成为一时风尚。尽管在文章开头或结尾,作者仍会说上几句劝谕的话,但他们并不真的认为逐利享乐是可羞可耻的,相反他们十分陶醉于对享乐场面的详尽而精彩的描写当中。有些时候,晚明文人对享乐主义更是毫不讳言,如袁宏道于《龚惟长先生》所描述的人生五大快乐。晚明文人的这一价值观,亦是受王学左派世俗倾向熏染的结果。王艮、李贽等人对私心私欲的肯定,为重享乐、重自适的价值观的普遍流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学左派尊重每个个体,甚至认为满街都是圣人,这一思想对晚明文学人物形象的选取与塑造皆有影响。传统文学囿于上智下愚的观念,一般认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更有表现价值。然而,晚明文学却将其笔触延伸至各色普通平凡的市井人物。于是,晚明文学中大量出现了商贾小贩、妓女媒婆、地痞无赖、尼姑和尚诸如此类的人物形象。与传统文学所更加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人物在作品里不是陪衬,而就是活动于舞台中心的主角,他们形象鲜明、富于个性。不管地位如何、有无品行,各色人物都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如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虽然是烟花身份,却是一个尽管备尝世间辛酸却仍然没有放弃对于真爱的追求与执守的女性形象。也就是说,晚明文学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再以传统道德与等级划分来作单一的脸谱化,而是将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世俗个体。这一点,当然是与王学左派对于个体价值的发掘、崇扬相契合的。
最后,从晚明艺术的娱乐精神,亦可发现王学左派世俗倾向的影响痕迹。晚明世情小说的大量出现与其普遍畅销不无关系。比如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便是由于《初刻拍案惊奇》出版后大受欢迎,在商贾力促之下继续创作出来的。在这样一种追求商业效果的氛围中,晚明艺术不得不注重娱乐性,可以说,娱乐精神已经成为晚明文人所着意追求的东西。而事实上,肯定“乐”的价值在王学左派处已有体现。王艮为吸引百姓以传播心学,提出“乐是学,学是乐”[2]718。李贽、袁宏道等人继承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李贽认为读书即追求大自在、大快活。袁宏道更是将读书之乐与酒色之乐并称为人生五大快活之一。至此,泰州学派在推进阳明心学世俗化过程中所突显出来的“乐”,已经为晚明文人们所接受。而且,在这一接受过程中,“乐”明显被赋予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即李贽所言之乐尚如泰州学派侧重悦情悦性,而公安三袁所言之乐则倾向悦耳悦目了。有此思想基础,那么晚明艺术最终在商业化大潮的推动下,走向追求以普适性、世俗性为特征的娱乐精神便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第一,王学左派借鉴随缘禅思路而形成的性情并育思想,使其摆脱了传统儒家心性学说的性善情恶论,赋予了情与性同样的合理存在地位。公安三袁通过李贽接受了这一思想,最终推出不同于虚灵式性灵说的浑情式性灵说。打破传统美学性善情恶的二分论,并且明确性情并育的合理性,这是浑情式性灵说对虚灵式性灵说的拓展之处,也是晚明主情思潮的逻辑延伸点。浑情式性灵说对于人之私情私欲所取的肯定态度,为晚明艺术的个体生命精神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第二,晚明艺术受王学左派那种消解工夫、率性而行的思路所启发,主张以无法为法。这种决意摈弃法度、一味信手信口的创作主张,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的活法思想。以无法为法,使得晚明绘画不求形似,晚明书法宁拙勿巧,最终成就了旨在宣泄个体意绪、突显个体真性的个体生命精神。最后,晚明艺术的个体生命精神又是无法脱离个体所生活之世俗当下的。晚明艺术由此出现了明显的通俗化,既开始表现世俗生活中平常、普通的生命个体,又注重追求以普适性、世俗性为特征的娱乐精神。在此过程中,王学左派那种注重百姓日用、肯定自然人性、崇扬个体存在的世俗倾向,为其提供了哲理依据。
注释:
①王学左派,指王畿与泰州学派,他们表现了一种儒禅俱显、打破传统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
②关于性灵涵义的复杂性,黄卓越先生《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之《情感与性灵:晚明文学思想进程中的一对内在矛盾》中有深入探究。本文采用其划分为虚灵式性灵说与浑情式性灵说的做法,不过在哪种更能体现晚明性灵观的内涵这一点上与之不同。
③王英志先生于其《性灵说的渊源与性灵派的背景》一文中,即持此观点。
④如蒋述卓先生、黄卓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