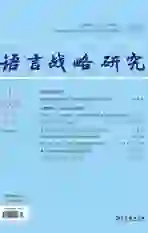普通话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022-02-22康慧琳











提 要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数据,建立序次Logit模型和KHB模型,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农民提高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是重要的中介机制,在控制住以上中介效应后,普通话的直接作用仍然显著。分地区而言,普通话能力的作用在江浙沪闽粤地区更加明显,且在这一地区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本。推广普通话,能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得农民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从而有效促进城乡融合,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 普通话;主观幸福感;中介效应;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2)01-0048-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4
The Influence of Putonghua Ability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ang Huil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in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administer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paper adopts an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a KHB model to explore how and to what extent Putonghua ability can affect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Putonghua ability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ignificant ways, whereby economic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skills are important mediating mechanisms. When the mediating effects are controlled, the impact of Putonghua remains clear and strong.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Putonghua ability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regions including Jiangsu, Zhejiang, Shanghai,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these regions,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mainly mapped as economic capital. In conclusion,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offer farmers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se potential benefits, the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can be improved, and continuous rural revitalization may be advanced.
Keywords Putonghua; subjective well-being; mediating effect;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引 言
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阶段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新的起点上如何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古以来,幸福就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最高追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需要切实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其重要路径在于破除城乡之间的隔阂、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去除农村“封闭、落后”的标签,帮助农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帮助农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对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幸福感,学界一般分为两类,即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前者侧重对当前生活的总体评价与感知;后者则着眼于未来,强调长期的自我实现与不受困的自由。我们关注的是农民当下的主观感受,故只考察其主观幸福感。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语言对于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语言既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具有工具性功能;也往往和特定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具有象征性功能。方言是我国农村的主要语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通用语言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一直将推广普通话作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农民更好地与外地居民进行沟通,获取更为丰富的信息、提高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展现现代新农民的良好精神面貌,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这些都是提高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影响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然而多数研究的讨论集中于经济层面,即掌握普通话可以帮助农民增加非农就业的机会、提高收入,甚少讨论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现有研究可以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和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影响两个方面。
(一)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
经济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许多研究表明,收入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邢占军2011;徐安琪2012)。但也有研究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不一定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也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1974:89);相对收入、收入预期、收入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更大(官皓2010;刘成奎,刘彻2018)。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贡献也得到了证实(王海英,等2021);特别是在市场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收入对农民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贺青梅,李海金2013)。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则会降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尤亮,等2019)。
在社会层面,主要影响是与社会交往相关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能够带来抵御外界压力的资源,从而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帮助个体获得安慰(House & Landis 1988;Lin et al. 1985)。人际交往质量的提高,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增加有助于增强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王海英,等2021;张彤进,万广华2020)。其中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减少经济不平等给农民带来的剥夺感,还能够调节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杨晶,等2019)。
心理层面的因素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拥有积极、乐观人格的个体具备更强的主观幸福感(Lysgaard 1955),自我控制的失败、缺乏社会认同则会降低主观幸福感(邵蕾,等2020)。有关农民的研究也发现,心理控制源(刘毅,焦江丽2013)、歧视感知会影响主观幸福感(卢海阳,张敏2020;刘杨,等2013),自尊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刘杨,等2013)。
(二)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影响
普通话能力对农民产生的影响体现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
语言经济学认为,通用语言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节约工作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效率。语言还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会直接对个体的工作获得和收入产生影响。伴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掌握普通话有助于农民扩大就业范围、更好地适应第三产业的从业需要,提高收入水平。语言学的众多研究证实了掌握普通话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王海兰2018;王春辉2018;王浩宇2019)。在此前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推广普通话也被认为有助于脱贫目标的实现,被称为“推普脱贫”或“语言扶贫”(王春辉2020)。语言扶贫能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非农生产的转移(何洋2020),会普通话使农民家庭的年收入显著增加60%以上(谢治菊,李强2020),减少了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张卫国2020)。
有关普通话能力的社会影响研究,多将移民或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而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目前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尽管研究对象不一致,但其结论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国际移民的研究证实,掌握流入地语言有利于增加移民社会资本、扩展社会网络(Bleakley & Chin 2010),进而提高其社会融入的程度(Dustmann 1994)。国内也有研究证实了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能够降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增强个体认同(褚荣伟,等2014);对于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尹悦2021)。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就普通话能力对移民或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国际研究发现语言同化有利于减少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歧视,使移民更好地适应迁入国的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满意度(Safi 2009)和主观幸福感(Angelini et al. 2015)。国内也有少量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王业斌,等2018;康慧琳2020)。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现有关于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讨论相对较少,且主要研究对象是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关于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影响研究大多集中于收入、职业地位等经济指标的讨论,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语言脱贫”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将语言的作用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到关乎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底层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对高层次要素产生更为迫切的需求。幸福感是农民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探究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具体的影响路径,有助于明确语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位置,并为国家如何更好地推广普通话提供参考。
语言的功能包括工具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工具性功能意味着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能够帮助个人获取更多的信息、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象征性功能则意味着语言具有区分内外群体的符号表征作用,特定的语言往往和身份、地位相关联。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使用“资本”的概念来概括一个人在其所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皮埃尔·布尔迪厄2015),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相比于审美趣味等文化影响,我们认为语言對农民文化层面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使得他们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技能上,因此在分析中将布尔迪厄资本理论中的“文化资本”替换为“信息技能”。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掌握手机、电脑、网络等信息工具的使用技能对于农民更好地获取信息、更新观念、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至关重要,可称之为“信息技能”。
当语言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时,它有助于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即实现经济、社交和文化层面的城乡融合。掌握普通话能够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农作物种植与交易信息,从而提高收入。掌握普通话还有助于农民更好地与村庄之外的人交流,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增加社会资本。由于互联网、大众传媒大多是以普通话的形式传播的,普通话能力的提高还有助于农民提高对手机、电脑等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普通话能力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这可以被理解为普通话能力的间接作用。由此提出假设1、2:
假设1:普通话能力能够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假设2:普通话能力能够通过增加农民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语言的象征性功能则意味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资本”,语言就像是一个人的第二张身份证,通过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就可以大致判断出他的社会地位。正如在英国伦敦腔是皇室贵族的象征一样,普通话也往往是与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居民总免不了要和本村以外的人打交道,此时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够给他人留下好印象,展现良好的精神面貌,避免因为语言不通而被打上“封闭、落后”的标签。提高普通话能力可以打破农村与城市的语言身份隔阂,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增加,这是普通话能力的直接作用。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在控制了中介效应后,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仍然有直接的提升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言使用频率、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程度等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区域,普通话能力能够对主观幸福感发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有所不同。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越大的地区,普通话的掌握难度越大,稀缺性越高,能够带来的收益越高。一些研究发现,普通话对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南方地区比在北方地区更为显著(张书赫,等2020;张卫国2020),证实了这一逻辑。而在经济较为发达、当地方言使用率高的方言强势区,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小,方言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普通话的作用,普通话的影响可能被削弱。因此,便有了第4个假设,即:
假设4: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具体影响机制存在地域差异。
综合以上研究假设,图1呈现了分析框架,实线表示普通话能力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虚线表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可能存在地区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该调查由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目的在于系统地收集中国社会有关劳动力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为政府决策与国际比较研究提供资料。《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包括个人、家庭和村居3个层面的样本信息,其中个人问卷包含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工作状况、社会参与与支持、劳动者状态、生殖生育、健康状况等模块,调查议题涉及劳动力的教育、就业、劳动权益、职业流动、职业保护与健康、职业满足感和幸福感等。我们选取其中的农村居民进行研究,共获得12 238个样本。
(二)变量
我们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个人问卷数据中提取所需的变量信息,并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生成后续建模过程中使用的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等,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劳动者状态模块调查了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赋值处理,“非常不幸福”“不太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被赋值为1~5。主要自变量是受访者的普通话能力,位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基本信息模块,我们把原始数据中的“既听不懂又不会讲”“听得懂但不会讲”“不太流利”“流利”“非常流利”分别赋值为1~5。其他中介和控制变量则来源于工作状况、社会参与与支持等模块。中介变量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经济资本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受访者的年收入对数来衡量;社会资本用餐饮网来衡量,信息技能则使用受访者的信息工具使用技能来衡量,《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还调查了用手机发短信、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和银行ATM取款的能力,我们对将这些能力的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变量。
我们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提供的省份信息,将地区分为3类,包括北方地区、江浙沪闽粤地区和南方其他地区。在使用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语言影响的地区差异时,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地区分为南方和北方(陈媛媛2016;刘国辉,张卫国2020)。我们将江浙沪闽粤地区单独作为一类是因为在这5个省份,当地方言的活跃度较高,使用范围广、使用人数多,属于方言强势区。这些省份的方言分布相对集中,江浙沪3省的主要方言是吴方言,福建省的主要方言是闽方言,广东省的主要方言是粤方言,将这5个省份单独作为一类,有助于验证在方言强势区普通话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否仍然存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普通话能力均值分别为3.756、3.309,处于中等水平。样本的平均年龄约为44岁。我们的分析对象主要为目前常住地仍在农村的农民,农村的青年流失率较高,常住农民年龄相对较大,以中年人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13年,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男女比例均衡,多数农民处于在婚状态,仅有4.54%的样本是党员。收入水平、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均值相对较低,标准差较大,可见农民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对不足,信息工具使用技能较低,且群体内部差异大。北方地区、江浙沪闽粤地区、南方其他地区的样本分别占比42.96%、27.92%和29.12%。
(三)統计模型
我们通过对主观幸福感拟合序次Logit(ordered logit)模型考察普通话能力如何影响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并进一步通过使用KHB模型对收入、社会资本、信息技能的中介效应进行分解。
1.序次Logit模型
Logit模型最早由比利时数学家维尔赫斯特(Verhulst)提出,是针对因变量为类别变量的回归模型(崔党群2005)。当因变量为定序类别变量时,适合用序次Logit模型进行解释(卡梅伦,等2008),序次Logit模型充分考虑了变量的类别次序,可以更好地估计因变量的比例发生比随自变量如何变化,也被广泛应用于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许世存2015;洪岩璧2017)。本研究的主观幸福感为取值1~5的序次变量,适合使用序次Logit模型,该模型假设有一个由J个类别组成的定序因变量Y,令:
Lj(X) = logit[Fj(X)],(j = 1,2,3…J - 1)
= log[P(Y ≤ j|X)/P(Y > j|X)]
= log{P(Y ≤ j|X)/[1 - P(Y > j|X)]}
其中Fj(X) = P(Y≤j|X)是J類别的累积概率函数。若Y会受到X的影响,则
Lj(X) = ∝j + βX
若针对有不同数值的X,即X1和X2而言,则
Lj(X1) - Lj(X2) = β(X1 - X2)
针对某个因变量类别(≤j)而言,自变量X1相对于自变量X2的发生比为X1exp[β(x1-x2)],β则为各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
2. KHB方法
克里斯蒂安·卡尔森等人开发了“混杂效应”和“标尺改变效应”(KHB)方法估量中介效应(Kohler et al. 2011),这一方法适用于序次Logit模型。假定序次Logit模型中因变量对应的连续潜变量为y*,主要的自变量是x,中介变量是Z,控制变量是C。模型(1)为对中介变量加以控制的模型,模型(2)为不控制中介变量的模型。
y* = α1 + β1x + γ1Z + δ1C + ε1 (1)
y* = α2 + β2x + δ2C + ε2 (2)
此时Z的中介效应Δβ = β2 - β1,由于y*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潜变量,在拟合序次Logit模型时,我们得到的系数是b1和b2,其中b1 = β1
σ1,b2 = β2
σ2。σ1和σ2也叫作刻度参数(scale parameter),由模型残差的标准差决定;不同模型的刻度参数不同,但都满足b1 - b2 ≅ β1 - β2。KHB方法的解决方法是,先将Z作为因变量,x作为自变量,拟合模型Z = c + dx + r,得到该模型的残差r,然后不再直接拟合模型2,而是将r代入得到模型2a:
y* = α2* + β2* x + γ2* r + δ2* C + ε2* (2a)
由于模型(2a)和模型(1)的拟合度相同,所以ε1 = ε2*,其对应的刻度参数σ1和σ2*也相同;x和r不完全相关,将模型(2a)与模型(2)对比,即得β2 = β2*。在相应的序次Logit模型中,b2* - b1 = β2*
σ2* - β1
σ1 = β2 - β1
σ1。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分解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直接作用和Z的中介作用(即间接作用大小)。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全部样本的分析
我们首先建立嵌套序次Logit模型,验证普通话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将普通话能力作为自变量,加入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收入中介变量,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餐饮网变量,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变量,模型5同时加入以上所有中介变量。
在模型1~模型5中普通话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模型1而言,普通话能力每提升一个等级,主观幸福感提升9.53%(= e0.091 - 1)。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系数显著为正,这3个变量都会显著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就模型2~模型4而言,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每提高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分别增加13.77%(= e0.129 - 1)、3.46%(= e0.034 - 1)和2.84%(= e0.028 - 1)。加入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之后,普通话能力的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3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起到中介作用。
下一步继续使用KHB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的中介效应,并计算得到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所能解释的比例。在模型1的基础上,首先分别单独加入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3个中介变量,然后同时加入所有中介变量建立全模型,表3呈现了每个中介变量可以单独解释的比例以及在全模型中解释的比例。
表3的结果显示,普通话能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单独放入每个中介变量的情况下,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分别单独解释了普通话效应的24.19%、10.87%和20.22%。放入所有中介变量时,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3个变量在全模型中总共解释了40.5%,收入在其中所能解释的比例仍然最大,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解释力相当。
(二)分地区的分析
这一部分将分地区探讨普通话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别化影响。
依据表2所示的结果,再次分地区建立嵌套序次Logit模型,考察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6、模型8、模型10是不加入中介变量的模型,模型7、模型9、模型11是加入所有中介变量的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无论对于哪个地区来说,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普通话能力的系数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比较来看,江浙沪闽粤地区的普通话系数最大,其次是南方其他地区,而北方地区的系数最小。普通话能力每提高一个等级,北方地区、江浙沪闽粤地区和南方其他地区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分别增加6.40%(= e0.062 - 1)、17.82%(= e0.164 - 1)和11.40%(= e0.108 - 1)。总体而言,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江浙沪闽粤地区、南方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收入、餐饮网对北方地区样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对江浙沪闽粤地区样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影响不显著;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对南方其他地区样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也表明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在北方地区的中介作用可能不显著,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在江浙沪闽粤地区的中介作用可能不显著。
进一步分地区建立KHB模型,分解中介变量的解释作用。表5呈現了KHB模型的分析结果,各模型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在北方地区分别解释了总效应的29.02%、19.58%和8.46%,且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间接作用不显著。在全模型中3个中介变量分别解释了24.00%、18.83%和0.53%,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江浙沪闽粤地区,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分别单独解释了总效应的20.41%、1.50%和11.87%,在全模型中分别解释了19.39%、0.80%和5.25%,且餐饮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本。在南方其他地区,收入、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分别单独解释了总效应的21.08%、11.60%和34.82%,在全模型中3个变量分别解释了17.70%、9.40%和23.16%,3个中介变量均显著,且信息技能和经济资本可以解释的比例最高。
在北方地区,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解释力很小,我们认为是因为北方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相对较小,即使农民的普通话能力不足,基本上也可以较为顺畅地听懂信息工具的提示。在江浙沪闽粤地区,餐饮网和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的解释力很小,甚至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方言在城市公共领域的使用频率较高,例如在广东,很多客服电话都使用粤方言,机场、火车站、地铁站也有粤方言广播。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对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的作用可能被地方方言替代。在江浙沪闽粤地区,收入的中介效应和普通话的直接效应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伴随着区域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加,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普通话仍然必不可少,不能被方言所替代。与此同时,普通话本身所具有的符号表征作用即使在方言强势区仍然存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具有身份地位识别的重要功能。例如,广东本地农民小艳就说曾经因为普通话讲不好而被同伴说“土”,这让她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四、结 语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序次Logit模型并使用KHB模型分解中介效应,结果发现,普通话能力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其中经济资本的解释力最强。在控制住以上中介效应后,普通话能力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即普通话作为一种象征资本能够直接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分地区来看,研究结果显示,普通话能力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江浙沪闽粤地区、南方其他地区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较大,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也较大,普通话能力的稀缺性更加突出。就中介效应而言,收入在各个地区的中介作用都很明显。信息技能在北方地区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和北方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较小有关。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在江浙沪闽粤地区的中介作用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省份,方言的使用范围比其他地区更广泛,使用方言就可以完成与城市居民交流、掌握信息工具使用技能等目的。
以上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重视语言的作用。普通话能力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助于他们提高社会交往水平、增强信息工具使用技能,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除了这些间接作用,普通话能力本身还是重要的符号资本,能够呈现农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帮助农民在正式的交流场合得到更多正面评价,提高主观幸福感。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普通话能力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在于促进以上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促使城乡居民具备共同的身份认同,使农民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生活。
这也启示相关部门,需要继续大力在农村推广普通话,有效促进城乡融合,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不断发展。相关部门在继续完成推普工作的同时,也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加强职业普通话教育,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者掌握熟练的普通话技能。同时要注重地区差异,在方言强势区尤其要重视农村地区的普通话教学,在中小学课程教育中鼓励教师使用普通话,促使村民从小建立对普通话的认同感。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尽管使用的是全国性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但在一些特殊的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农村,普通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其次,受到数据的局限,没有讨论方言对于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果农民仅仅掌握了普通话而没有掌握熟练的方言,普通话能力的作用是否仍然存在还有待讨论。希望将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研究结论进行补充。
参考文献
A.科林·卡梅伦,普拉温·K.特里维迪 2010 《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王忠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陈媛媛 2016 《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第6期。
褚荣伟,熊易寒,邹 怡 2014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社会》第4期。
崔党群 2005 《Logistic曲线方程的解析与拟合优度测验》,《数理统计与管理》第1期。
官 皓 2010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何 洋 2020 《普通话水平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2016年的实证分析》,《西安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贺青梅,李海金 2013 《社会化视角下农民的经济压力与幸福感》,《兰州学刊》第7期。
洪岩璧 2017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社会》第2期。
康慧琳 2020 《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刘成奎,刘 彻 2018 《相对收入、预期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刘国辉,张卫国 2020 《普通话能力与进城农民工心理健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刘 杨,李 泽,林丹华 2013 《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6期。
刘 毅,焦江丽 2013 《农民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研究》,《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卢海阳,张 敏 2020 《融合策略、歧视感知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福建省2393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社会发展研究》第7期。
皮埃尔·布尔迪厄 2015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邵 蕾,董 妍,冯嘉溪,等 2020 《社会排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认同和控制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期。
王春辉 2018 《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江汉学术》第5期。
王春辉 2020 《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国语言扶贫》,《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王海兰 2018 《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王海英,夏 英,孙东升,等 2021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6期。
王浩宇 2019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王业斌,韦尚玉,李晓叶,等 2018 《社会融合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第3期。
谢治菊,李 强 2020 《语言扶贫与普通话技能的减贫效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邢占军 2011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徐安琪 2012 《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许世存 2015 《城市适应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人口学刊》第4期。
杨 晶,孙 飞,申 云 2019 《收入不平等会剥夺农民幸福感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7期。
尹 悦 2021 《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尤 亮,杨金阳,霍学喜 2019 《绝对收入、收入渴望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
张书赫,王成军,沈 政 2020 《非农就业行为中普通话的提质效果及机制研究——基于CLD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第6期。
张彤进,万广华 2020 《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张卫国 2020 《普通话能力的减贫效应:基于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的经验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Angelini, V., L. Casi & L. Corazzini. 2015. Life satisfaction of immigrants: Does cultural assimilation matte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8(3), 817‒844.
Bleakley, H. & A. Chin. 2010. Age at arrival,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social assimilation among US immigra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1), 165‒192.
Dustmann, C. 1994. Speaking fluency, writing fluency and earnings of migra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7(2), 133‒156.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M. Abramovitz, et al.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ouse, J. S. & D. U. R. Landis. 1988.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suppor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1), 293?318.
Kohler, U., K. B. Karlson & A. Holm. 2011. Comparing coefficients of nested non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 Stata Journal 11(3), 420‒438.
Lin, N., M. W. Woelfel & S. C. Light. 1985.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subsequent to an important life event.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Behavior 26(3), 247‒263.
Lysgaard, S. 1955. 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79(1), 45‒51.
Safi, M. 2009. Immigrants’ life satisfaction in Europe: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2), 159‒176.
责任编辑:魏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