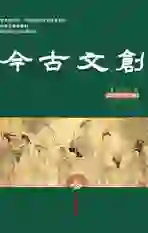《分居时期》中的伦理焦虑探究
2022-02-03黄宁
【摘要】 加拿大著名作家卡罗尔·希尔兹的长篇小说《分居时期》通过记述一对普通中产阶级夫妇因妻子工作需要,分居一年的各自生活日记,告诉读者,幸福婚姻没有捷径,唯有用心经营,全身心地投入,保持自己的忠诚和热情,才会收获稳定和甜蜜。本文以精神分析为基本理论框架,从情节、话语和心理等三个方面,透视作品所披露的20世纪后半叶北美普通民众的焦虑现象,探析希尔兹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浓重人文关怀。
【关键词】 《分居时期》;欲求焦虑;婚姻伦理
【中图分类号】I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023-03
基金项目:2019年广东高校科研平台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類项目《卡罗尔·希尔兹作品中的伦理焦虑研究》(2019WTSCX161)。
加拿大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蜚声国际文坛,是为数不多地获得国际声望的几位加拿大女作家之一。虽然希尔兹和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出生地同为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欧克帕克(Oak Park),然而两人的写作风格却大相径庭。海明威擅长塑造“硬汉”形象,希尔兹的创作题材却多聚焦于北美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虽然取材范围有一定局限,然希尔兹素以刻画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见长,同时臻于对叙事技巧和后现代主义等写作艺术的灵活运用,因此其作品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和显著的社会价值。
本文选取希尔兹的长篇小说《分居时期》(A Celibate Season)为重点分析对象,以精神分析为基本理论框架,从情节、话语和心理等多个方面,透视作品所披露的20世纪后半叶北美普通民众的焦虑现象,探析希尔兹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浓重人文关怀。
焦虑是现代西方文明显著的心理特点。“焦虑及其相关疾病是当今美国官方认定的精神疾病的最常见形式,甚至超过了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6]15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指出:“所谓焦虑,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5]8
在希尔兹的作品中,近乎“平庸”的千万平凡人物,尽管生活的家庭和工作的场所大相迥异,但他们都近乎默契地有着一致的相同点:内心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焦虑。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但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却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却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除了源于童年时代的安全感缺失,更多的是由于当前面临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因此,希尔兹笔下焦虑症患者的个人精神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乃是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焦虑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可以被视为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
一、夫妻各自的焦虑
《分居时期》出版发行于1991年,是希尔兹的第五部小说,仅比她的巅峰之作《斯通家史札记》(The Stone Diaries)的完成时间1993年早了两年。按出版时间而言,希尔兹在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技巧已经十分成熟,因此,《分居时期》也可以算作她的一个创作高峰,颇具文学价值。顾名思义,这部小说写的是夫妻长达一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作者独辟蹊径,巧妙地运用书信体裁,以一对普通的加拿大中产阶级夫妻查斯和乔克为男女主角,分别以他们各自的口吻,向配偶讲述自己以及身边朋友在不同时间里的生活轨迹。
(一)查斯的焦虑
丈夫查斯本为工程师,拥有建筑设计的一技之长,擅长画图实干和住宅设计,因为经济大环境低迷,暂时在家待业。在乔克赴渥太华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查斯承担了家中“女主人”的职责,既要操持繁重的日常家务,又要处理和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儿女们的亲子关系:担心躲在卫生间哭泣的女儿意欲自杀,幸好后来得知是因为月经初潮不懂处理;桀骜不驯的儿子因为在餐馆兼职晚晚夜归,不知情的查斯又担心他是否交友不慎或误入歧途。除此之外,查斯不但要忍受和妻子异地分居的相思之苦,还得四处奔波寻觅新工作养家糊口,差点连锅炉修理费都付不起。“已四十有七,恐怕不会觉得低三下四地求人特别容易,但似乎已学会了乞求技巧,特别是在地下室里待业九个月之后”[4]17的查斯,经常在给妻子的信中聊到自己卑躬求职的艰辛,“严酷的经济现状”迫使落落寡合的他学会了“言辞奉承”“使劲推销自己”,还得面对十七岁儿子的奚落。
心灰意冷的查斯在一次和邻居的争吵后冲出家门淋雨,“第一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细想着这荒唐的世界,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烦恼多么真实、生活多没意思、个人多么孤独,淋在雨中的失败者多么凄凉”[4]60,以至于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诗句:“每一天都是张开的大嘴,怒气冲冲地吞下时光。”
(二)乔克的焦虑
虽然希尔兹对丈夫和妻子平均渲染着墨,描写两人的篇幅旗鼓相当,但在内向清高的丈夫查斯的衬托下,妻子乔克这一文学形象明显更为立体,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乔克拥有法学文凭,事业有成,虽年逾四十仍魅力照人,是法律界小有名气的专家。但结婚多年来,乔克一直蜗居家中担任家庭主妇,日复一日从事琐碎繁杂的家务,用丈夫查斯的话来说,就是“好像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干”“围着家务活打转,一会儿去取回干洗的衣物,一会儿又去买邮票,还得不到一句感谢话”[4]135。然而,寂寂无闻的家庭生活并没有顿挫乔克强烈的好胜心,在遇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后,她便毫不犹豫撇下丈夫和儿女,独自远赴距离家乡温哥华几千里之遥的首都渥太华,加盟为妇女权益进行调研的专门委员会,以期自己的专业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施展。期间查斯出于对乔克的一片爱意,特意改造家中房屋布局,孰料在颇具女权意识的乔克眼里成了侵犯自己领地的罪恶之举,引发后者一顿雷霆之怒。接下来,乔克渴望在首都进一步拓展事业蓝图,不想回家,查斯则只求家人团聚,一如往常平静度日,两人再度话不投机,关系剑拔弩张。
在整本小说中,对乔克“焦虑”情绪的描写,几乎占据了全书内容的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风韵犹存、虽漂亮能干却充满焦虑的中年女性。
二、成因和剖析
(一)身份焦虑
“身份”(identity)一词源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 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狭义上的“身份”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广义上则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1]8
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现代社会更是把维护身份,或确切地说,维护“尊严”变成了每一个成年男性的首要任务。在主流观点中,男性人物应该是坚韧不拔、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汉形象。“职业是身份认同和代表性渠道化的一个核心因素。”[2]30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身份认同的成功男性应该是“事业家庭双丰收”的顶梁柱,能成就一番大事,创立不世之功,即便不能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能讓家人生活安稳,有所依靠。查斯非但没有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反而是赋闲在家、吃了上顿担心下顿的中年无业游民,和泼辣能干、雷厉风行的法律专家妻子刚好截然相反。善良的查斯一心支持妻子离家发展事业,主动包揽家中所有家务,岂料招致左邻右舍认为他们已经婚姻破裂的误解,面对尚不谙柴米油盐之苦的儿子的奚落,也只能故作乐观,尽力维持自己高大的父亲形象。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必然导致查斯长期无以复加的焦虑。
(二)欲求焦虑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认为,当幼儿获得语言能力时,标志着幼儿与母亲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幼儿产生巨大的缺失感,进而造成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这种欲望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不断找到替代品,比如,金钱、权力、美色等等,拉康称之为欲求。欲求永远不能被满足:它不是对于某个客体的欲求(需求),也不是对于爱的欲求,即得到另一个人对自己的承认的欲求(请求),它是成为系统中心、象征界的中心、语言自身的中心的欲。
乔克怀揣法律梦想,离开和丈夫朝夕相处二十年的家庭时,类似于获得语言能力的幼儿开始与母亲的真正分离。初到异地他乡的渥太华,乔克也避免不了常人的乡愁之苦,自感“仿佛坐在家里那只破旧的小船上绕着海峡飘荡”[4]1,向丈夫写信诉说“出门在外一个人……那滋味原来是这般空虚……初来乍到我就像个乡巴佬一样……精神不振,极度不安”[4]3。为了对抗思家的焦虑,乔克全副身心投入到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中,努力追求法律顾问事业的成功,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积极受理有关妇女的侵权投诉;飞遍各地参加听证会;为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及其他形式的救助服务等等。仅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有着事业型务实性格的乔克就开始在法律委员会大放异彩,从众多有着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中拔萃而出,成为法律界公认的专家级人物。
“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对现实恐惧的基础上,而这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她)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焦虑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她)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5]8在事业所向披靡的同时,乔克也遭遇了接踵而来的家庭危机:和丈夫因志趣不同而话不投机;对丈夫夜以继日改造的房子大发雷霆;害怕重蹈昔时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日子而焦灼不安。甚至于当丈夫提出待乔克结束目前的工作后,回家专门为他的设计师事务所“管账兼处理信函”时,她被那种“傲慢设想简直气疯了”。离职在即,乔克更是情绪阴郁,“遭受着绝望情绪的煎熬”,担心和丈夫因为分离太久而互不适应,对回家感觉怅然若失。最后,在消沉情绪的袭击下,乔克酒后失控,出轨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奥斯丁。
三、缓解和应对
(一)减少对自身的期望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这一算式清楚地表明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或者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 [1]69
四处找工作碰壁后,查斯开始降低对工作的期望值,并把精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在改建自家住房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自己改造太阳房的过人本领。本着对妻子的满满爱意,他边借书自学边动手实践,利用独一无二的构思,把自己住房的一角改建成了充满热带气息的太阳房,郁郁葱葱、漂亮得“难以置信”的太阳房在一众参观者眼中甚至成了这套房子的最大亮点。在众人的赞叹声中,查斯也收获了极大的精神满足。此外,查斯还发掘了自身的文学天赋,写起了诗歌,并屡屡见于知名报刊,受到老师和同行的一致赞赏,文学的成就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查斯对自己的信心。
(二)保持自我核心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罗洛·梅(Rollo May)认为,“在一个标准和价值观剧变的时代,一个对现在和将来所有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人们要获得长期的发展和内在的完整性,不能仅仅敢于满足外在的期望,必须重新唤醒自我。在他看来,一个人需要有自我核心和保持自我核心的勇气。他在保持自我核心的基础上参与到世界中去,直接感受他人和世界,并且有跳出来反省自己的能力”[7]40。
乔克因法律委员会的工作邂逅了同事奥斯丁,后者多才多艺,能力出众,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也是领取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的学者,同时还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朝夕共处的工作中,乔克逐渐被诗人超然物外的气质所吸引,加上因即将离职而情绪低落,在一次偶然的酒醉后,和奥斯丁发生了一夜之欢。然而,乔克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让她从小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坚信夫妻理应相互忠诚的婚姻观念。因此,虽然性格里有着浪漫的一面,但所幸乔克骨子里仍然坚守传统家庭伦理的“自我核心”,而且她尚能保持运行这一“核心”的勇气和理智。
出轨事件之后,乔克对丈夫无比愧疚,而且清醒地明白,与奥斯丁相比,自己“有另一种生活”,二十年稳定厚重的婚姻是“一段漫长的、密密匝匝结结实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有无数个独立的触角和心室,多得我永远数不清”[4]217,而对方却如闲云野鹤,来去自由无牵无挂,自己对他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
后来,在和母亲的无意聊天中,母亲的教育使乔克更深刻地认识到:忠诚是婚姻的基础,任何一份婚姻都离不开彼此的忠诚,保持忠诚是婚姻的底线,风花雪月的激情永远无法取代婚姻。婚姻是两个人身体、灵魂、梦想与需要的结合,容不得有第三个人,既然结了婚,就应该守得住婚姻的底线,不跨越雷池一步,否则前方就是万丈深渊,结局凄惨。
因此,乔克迅速调整了心态,“让家庭生活的熟悉感慢慢地渗回骨头”,并真诚地鼓励丈夫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小说的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夫妻团聚的圆满场景。
无处不在的个体焦虑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而且逐渐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实。希尔兹的作品虽然表面上聚焦于芸芸众生的平凡人生,背后透露的却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3]34,展现出对“小人物”们浓重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2]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的焦虑[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陈榕.平凡者的奇迹——简评加拿大女作家卡罗尔·希尔兹的小说创作[J].外国文学,2003,(6):34-40.
[4]卡罗尔·希尔兹.分居时期[M].逢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斯科特·施托塞尔.好的焦虑[M].林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7]徐菁菁.“不完美”焦虑:我们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吗?[J].三联生活周刊,2021,(41):34-40.
作者简介:
黄宁,女,湛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加拿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