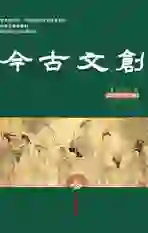体制与人性的博弈
2022-02-03申爽
【摘要】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柏拉圖提出的“乌托邦”又或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人享乐,是一个大同社会。阿道司·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似乎正是这样的一片乐土,人们没有忧愁,快乐地享受着科技所带来的一切便利。然而,在看似平静的文字中,赫胥黎将这所谓的“乌托邦”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束缚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拷问,很多学者因此将《美丽新世界》视为一部“社会文学”。可是,以《美丽新世界》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文学”却又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学。反乌托邦文学的主要人物角色是此类作品情感与意义的突破口,他们的“幸福”与“困惑”以及对于人性完整的守护使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作品中的“乌托邦”给人类价值观念带来的失衡。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也应该是一门“个人的文学”。本文借助荣格心理学理论为依托,探索《美丽新世界》中三位重要角色的人性和“美丽新世界”的体制间的摩擦对抗,并借此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赫胥黎对人类的希望:永远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信仰与对真实幸福的追求。
【关键词】 《美丽新世界》;反乌托邦;荣格;人格动力;人格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007-03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科技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荣格理论下英美反乌托邦小说的心理学视角解读”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KY-2020KYYBW-42)。
经典的伟大在于它对未来精准的预见性,赫胥黎对于未来科学技术的预言精准到可怕:《美丽新世界》构建了一个公元26世纪的“新世界”,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未来社会,科技的高度发达解决了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人们于工业化的育婴房里成批生产,在出生之前,就被预设成为贵、低、贱几种种姓。在这个世界里,克隆技术、体外受精、神经药剂学的发展等都与其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进度如出一辙。但在《美丽新世界》这部作品中,这些技术并没有如同读者想象中那样造福人类,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实现“安定、本分、稳定”的工具,这一切的制约目的皆在于使人们安然接受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即社会的控制。
在如此“幸福”的社会中,人们为何要、如何逃离他们的命运?在《美丽新世界》这部作品中,三位主要角色的精神发展以及对社会体制的抵抗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美丽新世界”中存在着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与厄普西隆几个阶级,其社会重要性依次降低。故事中,柏纳·马克斯和汉姆荷兹·华森属于社会中等级最高的阿尔法,而约翰是个来自“蛮族保留区”的“野人”。然而,不管出身如何,社会地位怎样,三位重要角色在作品中都曾表现出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的叛逆与抵抗。虽然三人最终的结局不尽相同,但是在他们与社会制度的博弈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独立自由的思想、信仰以及真实幸福的追求。而在荣格的人格理论的视角下,三位角色反抗过程中的纠结、反复、决绝似乎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讲,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很好地契合了反乌托邦文学的“个人属性”,为晦涩难懂的作品情节与行为怪诞的人物角色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支撑。
一、柏纳·马克斯:“新世界”中的摇摆者
作为“新世界”阿尔法阶层的一员,柏纳·马克斯是一个残次的且叛逆的作品。对于统治者来说,柏纳·马克斯的外形与表现都差强人意。按照道理来说,柏纳·马克斯不应该在“美丽新世界”里出现。或许因为“人造血液中有酒精”导致柏纳体格不全,筋骨弱小,这使他与他人隔绝并不断地感到孤独。他不快乐,甚至有些痛苦。这痛苦来自其他阿尔法的蔑视、捉弄,也来自当他与低阶级的人打交道时痛苦地想起自己体格上的不健全(越是低阶级的人类身高越是降低,而作为阿尔法的马克斯身高常常不比他们的高出多少)。同样地,这种不快乐也来自他内心的孤独感。他拒绝服用索麻来忘记心中的苦闷;与同为阿尔法的美女蕾宁娜在一起时,他拒绝与蕾宁娜结合,而是与她谈论“自由”。有时,他会感觉“在他真正心底深处,他的兴趣在另一些别的事情上。但那是什么?是什么呢?”
柏纳·马克斯的这个灵魂拷问贯穿了整个作品,而他的答案则是他在拜访了蛮族保留区,在经过一些曲折后才慢慢浮出了水面。当他带着蕾宁娜来到蛮族保留区,发现了孵育暨制约主任汤姆金竟然违背社会准则,与一个阿尔法女人自然生育了一个孩子。他欣喜若狂,将这个孩子——即“野人”汤姆带回了“新社会”,并以此逼走了企图将他发配至冰岛的孵育暨制约主任。那一刻,他感受到了胜利者在“新世界”中的权利与快乐。此后,他利用了“新世界”居民对约翰的好奇以及约翰对他的情谊,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新世界”的地位。然而,当“野人”不再受到他的管制,为他带来了麻烦、窘境与危险时,他又憎恨起这个“新世界”来,并最终“痛下决心”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中,柏纳·马克斯的表现不算英勇,他对于秩序、体制的质疑与抵抗来源于他的自卑,这反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浅尝辄止。在懂得了自由的珍贵后,他接受了被发配到孤岛的命运,而不是去反抗、去改革、去推翻这个世界。在很多人的眼中,柏纳·马克斯根本够不上一个“主角”的角色。然而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柏纳·马克斯却真实地展示出人的本性,即使他是一个“新世界”中在流水线上、由试管培育出的人。
荣格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个体成员的总和,并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界定为意识与无意识两个区域。其中,无意识部分又包括“个人无意识”(来自个人的生活经历,被个人所压抑、弃置或遗忘的内容)与“集体无意识”(无关种族、历史及其他差异,自人类起源依赖所积淀的典型反映方式与内容)。荣格称,只有平衡好了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个人才能健康地成长与生活。然而,无意识深藏于人的心理,其形成悄无声息,其影响又总是潜移默化。这无意识虽然躲在意识的深渊之处,但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它又常常不自觉地冲破理性的束缚,冲到意识的前面,野蛮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美丽新世界”中,统治者无视个体的需求,强行将“体制”灌输到每个个体的意识中,例如为每个个体提供睡眠教育——个体在婴儿时期即开始在睡眠中被迫聆听千百遍“新世界”的社会准则,并终身以此为人生规则。只不过,这些强迫的“体制”并不是人的内心自发的产物。当“体制”的要求与人的无意识中的内容发生冲突,势必会造成个体的痛苦与迷茫。在其幼年时,柏纳应该也曾顺从地遵循过“新社会”的准则。然而,当他成年、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后,他发出了那一句对灵魂的拷问“你难道不希望自由吗”?这其实是他内心的渴望在经历了无数个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化得出的结果,是他内在人格改变的外在展现。
在荣格看来,心理能是一个人人格所需的必要能量。就像地球上的能量是一定的一样,一个个体的心理能量也是固定不变的。心理能虽不可以像电流一样用具体的单位计算,但是它可以由无形的心理值进行衡量。在人意识与无意识中欲望转换的过程中,心理能从一个欲望流向另外一个欲望,这势必造成了个体对两种欲望的态度的改变。作为“新世界”的“残次品”,柏纳早早地在无意识中扎下了寻求自由的种子。这种对于自由的追寻来自柏纳的无意识,然而,当他揭发了孵育暨制约主任的丑事,并因与野人交好而尝到了新世界的“尊重”时,意识中对于权力的欲望压倒了他无意识中对于自由的渴望。他似乎“跟这个世界完全重归于好”,他的心里值被短暂地重新分配,然而,“他虽为成功而心满意足,却仍然拒绝放弃批评这些秩序的特权”,强大的无意识无法放过柏纳。当野人拒绝配合柏纳进行展示,他人对柏纳的质疑轻而易举地打破了这种新的心理值的分配:他又开始憎恨这个社会,他又开始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局外人。
然而,虽然马克斯产生了自我意识,但是他的自我意识主要源自其自身的缺陷和心理上的自卑,他并不理解自我意识与自由、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仅仅可以称马克斯为一个背离“新世界”价值,却并没有对“新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角色。
二、汉姆荷兹·华森:“新世界”的他者
在《美丽新世界》中,汉姆荷兹·华森是一个异端的阿尔法:即使他健壮结实,聪明能干且深受姑娘们的喜爱,但是“在他真正心底深处,他的兴趣在里一些别的事情上”。故事的开端,汉姆荷兹·华森与柏纳·马克斯交好。他喜欢和柏纳·马克斯侃侃而谈,因为他感到柏纳·马克斯能够理解自己那种不同于其他阿尔法的想法,但同时又对马克斯战战兢兢的态度表示同情与可耻。他渴望通过语言的表达获得力量,他企图通过思考去理解自己的内心。虽然在作品中,汉姆荷兹·华森并没有像柏纳·马克斯一样大篇幅出现在故事情节里,但是在几个重要情节中,作者对汉姆荷兹·华森与柏纳·马克斯只言片语的描述即可见到二者的对比:当野人约翰大叫着“你们难道不要自由、不要做人”,并把索麻一把把摔出窗户的时候,马克斯惊恐瞪大了眼睛低语道:“他们会杀了他……福特救救他!”而此刻的华森却笑着,对他来说,那是“实实在在欢悦的一笑”。
自从野人约翰出现在“新世界”,马克斯便背叛了自己与华森的友谊,而将约翰作为自己获得社会认可、消除自卑的工具。虽然马克斯不再找华森讨论自己内心的孤独与不安,华森依旧保持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当华森、马克斯和约翰因制造混乱而被引进元首的书房时,华森平静甚至开心地接受了被流放到孤岛的命运。他甚至为自己选择了具有“极糟的气候”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因为他相信“如果气候很坏,一个人就会写出比较好的东西来”。
在上述三位角色与元首对话的过程中,元首的一句话道破了汉姆荷兹·华森结局的本质:“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制约到俯首帖耳的地步,快乐就是一个比真理更残酷的主人了。”故事中,统治者为“新世界”带来了索麻与随意的性,即统治者口中所谓的“快乐”,并且要求人们臣服于这种“快乐”。而汉姆荷兹·华森无法让自己苟活在这种肉欲的快乐中,他需要的是自由、是真与美。即使在遭到昔日好友柏纳·马克斯的背叛、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华森依旧试图逃离被控制的社会命运,对既有秩序进行反抗。从荣格的人格理论来看,在华森的人格中,无意识的力量一直在推动者他对于自己内心的探索,而这无意识的力量,又不乏其“集体无意识”中本能。根据荣格的实验推断,在人类经历了千万年的历代更迭后,人类个体对某个具体的事物会做出与我们祖先相同的反应,如怕火、怕蛇,喜欢阳关与美。新世界扼杀人性,要求所有阶层内部的个体自內到外整齐划一,可是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自由、真理”是每个人类个体都会向往的意象,所有人类个体保持完全一致的生活模式与思想是不可能的。一旦一个个体的无意识强于其意识,他就会执着于对某个意像的追求并试图找到答案。
汉姆荷兹·华森对于其人格中无意识的追求与“新世界”的统治要求格格不入。就华森的社会等级来看,他是个社会精英;就其拒绝索麻与女人、坚持探索“不知道的事物”来看,他又是一个“新世界”的异类。故事的最后,他选择去孤岛上继续探索莎士比亚为他打开的另一个“新世界”。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来看,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当一个个体的无意识足够强大时,对内心的探索终将把一个个体推向一条不同于当下的道路。
三、“野人”约翰:“理想”的绝对拥护者
不同于“新世界”中的柏纳·马克斯与汉姆荷兹·华森,来自蛮族保留区的“野人”约翰一直是一个不肯向新世界屈服的个体。然而,他对“新世界”体制的抗争是从迷茫的半推半就慢慢走向了决绝。在这个过程中,约翰的人格逐渐成熟。但当他明白自己永远无法离开这个不能为他内心带来平静的世界时,他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人由实验室培育出生,人际关系早已异化人们毫不知晓过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家庭、婚姻、专一让他们感到羞耻。而“蛮族保留区”虽充斥着污物、神祇、老迈与疾病,却保留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家庭、亲情、爱情。约翰就是出生、成长于这样的一个社会。可是,蠻族保留区的居民对他孤立的态度,让他发出了“孤独,永远是孤独”的感叹。当野人约翰从蛮族保留区满怀激情地来到“新世界”时,他却意外发现在这个“新世界”中,家庭、爱情、信仰、自由不复存在。同时,他的父亲不承认与他的关系,她的母亲因纵欲于索麻而终日浑浑噩噩,他的朋友因权利和欲望将他推向新世界的“观光台”任人欣赏,这些都让约翰痛苦、无助。
最让约翰痛苦的来自他热爱的蕾宁娜。他希望能够通过蛮族保留区里的仪式求得蕾宁娜的爱情,他对蕾宁娜说,“在马培斯的人们是要结婚的”。但是他却不懂得,在“新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属于每一个人”,社会准则要求人们“应该更杂交一点”。当蕾宁娜褪去衣衫等待拥约翰入怀的时候,约翰震惊与愤怒,他咒骂并掌掴了蕾宁娜,这段情事就算完结了。约翰的内心却更加坚定地相信,新世界不是他想要的世界:“我不要舒服。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至善,我要罪愆。”
根据荣格的人格理论,个体的精神是从一种混沌的、未分化的统一状态中开始的。在此之后,像一颗种子成长成一棵大树一样,个体的精神也发展为一个充分分化的、平衡和统一的人格。在这个分化过程中,个体逐渐对现实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只有经历了个性化的个体,才能通过个性化的发展逐渐形成独立的人格。对于约翰来说,他既不属于蛮族保留区,也不属于“新世界”。她的母亲来自“新世界”,被遗留在蛮族保留区,她因为以“新世界”的规则生活而遭到了保留区内居民的抵制。因此,约翰从未真正属于过蛮族保留区,“新世界”的规则更是让他眼花缭乱。在故事中,约翰从刚开始的一知半解地引用莎士比亚作品的来表达心声,到最后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内心的痛苦。野人用死亡控诉这个灭绝人性的社会体制,证明了他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却也因此断送了自己的人格突破尘世束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荣格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目的和行动方向,而个体最终又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多数重要角色在“新世界”社会制度的束缚之下无法掌握自由意志发展的能力。在这个看似美丽却集权、麻痹、迫害人自由的世界,注定会存在体制与人性的博弈。
参考文献:
[1]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2]王奕力.《美丽新世界》反乌托邦思想述评——基于与《乌托邦》的比较研究视角[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15):28-29.
[3]约兰德·雅各比.荣格心理学[M].北京:三联书店, 2018.
[4]吴修申.《美丽新世界》:扼杀个性与个人自由的新世界[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57-60.
[5]刘柠.人性泯灭的黑暗世界——解读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异化主题[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12):99-105.
[6]李增,刘英杰.唯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双重挤压下的人性危机——论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J].外語与外语教学,2010,(05):85-88.
[7]赵怡薇.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看技术统治与极权主义[J].语文建设,2015,(02):32-33.
作者简介:
申爽,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广东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心理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