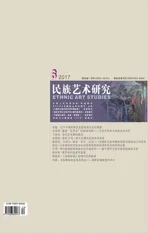跨文化接触中的转型与认同
——以南诏时期 “熔鼓铸圣” 图像和 “展衣夺土” 传说为例
2022-01-04邓启耀
邓启耀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化共存比较典型的地区之一,历史上跨文化接触的交往互动十分频繁。这种跨文化接触的交往互动,在南诏时期(相当于唐代)尤为突出。其中,南诏末年所绘《南诏中兴画传》,以长卷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当异文化进入南诏本土时,其如何通过变服从俗、考验、神通等方式,点化众生,让善者为王、愚钝者慑服的故事。《南诏中兴画传》犹如一卷图像民族志,让我们直观看到南诏时期族群、信仰、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是一件图文并重的重要历史文献,特别是图像呈现的一些细节信息,往往是一般文字类史册无法提供的。本文通过对《南诏中兴画传》中一个关键情节——熔鼓铸圣(阿嵯耶观音)以及在当地民间流传的观音传说的解析,观察南诏时期原住民及其本土文化,在和异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跨文化互动、认同并实现融合的历史场景。
一、熔鼓铸圣:信仰转型的文化象征
如果说,《南诏中兴画传》中,梵僧的几番变服,暗示着佛教密宗在异文化环境中某种程度的 “从俗” 意象的话,①详见笔者《多民族文化接触中的互动与认同——以〈南诏中兴画卷〉中人物服饰变化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梵僧施术幻化慑服众人之后,则是通过计谋,诱使他们将部落神器、祖传的铜鼓熔铸为圣像,从而产生了根本性的信仰转折。
南诏地区族群从本土民间信仰向佛教密宗的转折,以熔鼓铸圣这一文化事件为标志。《南诏中兴画传》文字卷 “第六化” 述:圣僧行化至忙道大首领李忙灵之界时,因觉此地 “人机喑昧,未识圣人。虽有宿缘,未可教化。遂即腾空乘云,化为阿嵯耶像。” 大首领惊骇,敲打铜鼓召集村人。于是,众人都目睹了圣像放大光明的神迹。
梵僧传法,无论遇到 “敬心坚固” 还是 “未可教化” 的民众,都喜施以法术,幻化身体,让大家拜服。在这一 “化” 里,他一会儿是梵僧,一会儿是真身阿嵯耶观音。当空中那个圣像令人惊骇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变成一个有铸造手艺的老人,声称自己会铸圣像,而且所铸之像,与大家所见毫厘无异,引诱大家将祖传的铜鼓 “解熔,铸作此圣容” 。大头领等听从了这个颠覆性的建议,让村人将铜鼓集中起来,交给老人铸了阿嵯耶圣像。
铜鼓是西南彝族、壮族、苗族等常用的大型打击乐器,更是民间信仰举行仪式的重要祭器。铜鼓的使用和崇拜,是古代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民族自青铜时代就延续的文化传统,至今还在一些民族中使用。但在南诏国时期,由于佛教密宗从西域传入大理地区,作为本土民间信仰的重要祭器铜鼓被熔毁,改铸为佛教密宗观音 “阿嵯耶” 像。
经过梵僧数度教化,在《南诏中兴画传》 “第七化” 里,铜鼓所化的 “阿嵯耶” 像终于肃然而立,南诏初王合掌膜拜。在 “阿嵯耶” 的莲花宝座前,是弃置以备熔铸的铜鼓。这是根本的一 “化” ——化了地方文化和本土信仰的象征物铜鼓,铸造了外来的阿嵯耶观音铜像。这位来自 “西域” 的莲花部尊的阿嵯耶观音,改变了当地民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
几十年后,这尊置于山上的阿嵯耶观音圣像,因其灵异特性,仍然令当地人十分敬畏。《南诏中兴画传》文字卷 “第七化” 述: “吾界中山上有白子影像一躯,甚有灵异。若人取次无敬仰心,到于此者速致亡。若欲除灾禳祸,乞福求农,致敬祭之,无不遂意。今于山上,人莫敢到。”①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国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147页。民间信仰中的灵异降福或作祟的观念,自然而然地化合在佛教密宗的信仰中。
皈依的代价是对原有传统的抛弃。人们熔解铜鼓,铸为圣像。到后来,佛教密宗被南诏统治者尊为国教,密宗法师阿吒力被尊为国师。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大兴,仅短短几十年,此地就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铸佛上万,遍绘梵图。

图1 《南诏中兴画传》之第七化:弃置于新铸 “阿嵯耶” 像前的铜鼓。②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国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137页。

图2 元代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高冠,上裸下裙,云南省博物馆展品,2015年(笔者摄)
这段故事,反映出当异文化或佛教传入此地时,本土文化及民间信仰与之发生冲突和碰撞,从敌视到认同并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拒不接受外来文化的部落,因难以蒙 “教化” 而被教训;而宽容开放、 “敬心坚固” 的南诏始祖则蒙圣恩,从耕夫 “化” 为诏主。这一对比的目的当然在于强调南诏王因与佛教结缘而获得的神圣地位(这在画传 “奇王祥瑞” 内容中,就已进行了充分描绘),然而,换个角度看,这不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一次重要的社会文化转型事件吗?人们把祖先传下来的铜鼓熔解,铸为具有浓重南亚、东南亚风格的 “阿嵯耶” 圣像,将铁柱崇拜或本土信仰转换为观音信仰,变部落民主制为世袭制。这不能不看作中世纪滇西族群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文化认同。而位于古道交汇点上的南诏国,以解熔青铜时代传承下来的铜鼓文化为代价,重铸了一个来自异域的新的偶像。细奴逻从此大发, “兵强国盛,辟土开疆,此亦阿嵯耶之化也” 。①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国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49页。
初王神助的传奇,在人们想把它记录在案的时候,已至尾声了。禅让的部落神话早已过时,权力争夺成为常态。铁柱和画卷,都是末代南诏王在气数将尽之时,为了强化始祖天赋神权的历史记忆而搞的形象工程。然而,铁柱铸成30年后,画卷完工3年后,南诏灭,被纪念的主体消失,只有 “形象” 留存下来。金银包装的王朝消失了,到后来连史学家也数不清那些不断复制的帝王了。《南诏中兴画传》未能描绘出希望的 “中兴” 蓝图,却留下了一件将纪实与幻化、民俗与神话融为一体的艺术作品。
二、来自异域的 “阿嵯耶” 观音如何成为 “大理福星”
经过 “熔鼓铸圣” 事件之后,观音造像,特别是 “阿嵯耶” 观音铸像,在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艺术中,十分突出。20世纪初大理地震,从千寻塔塔顶掉下一些青铜造像,这使人想起历史上那几次动辄 “造佛万尊” 的盛举。20世纪60年代维修大理千寻塔时,发现各类观音造像53尊。巍山龙于山石刻、昆明拓东经幢、大理塔藏文物和寺庙塑像、晋宁观音洞壁画、大理国张胜温梵像长卷以及各种崖壁画、书刊木刻图像、脱模泥塑等,都少不了观音造像。而且,这些观音造像,往往是位置最突出、工艺最精湛的。
在此不能不重点谈一下号称 “云南福星” 的 “阿嵯耶” 观音铸像。 “阿嵯耶” ,与密宗法师 “阿吒力” 音近。 “阿嵯耶” 型的观音铸像基本特征是头戴化佛冠,发梳高髻(或称 “菩萨蛮” 发式),上饰多股丝束,有发箍、耳饰或头套,两侧发辫对称垂落双肩。上身全裸,宽肩细腰,身体修长,男身女相;颈围联珠纹项链,项链下方有一宽扁半圆形花纹装饰带;手臂圆润,佩带三角形璎珞花纹臂钏,手结妙音天印。观音下身穿裙或东南亚称为 “笼基” “莎笼” 式薄质透体长裙,裙角微微外翘;腰饰讲究,腰带于正中打结,自然垂下,另外一条饰带则在前面半挽,掖于两侧;饰花腰箍直接套在腰肢肉体上,不具束裙作用;腰带系于裙上,末端在腹前结成一个带褶的图案,再用一个镶嵌珠宝的圆形花纹饰物固定;另有三道腰箍,半挽后细的一头掖于两侧收于身后,渐宽的半月形下垂于前,与U形的裙纹形成呼应。观音跣足,或单立,或背有镂花火焰纹背光,颇有南亚、东南亚民族的韵味。其造型和《南诏中兴画传》《张胜温画卷》上所绘 “阿嵯耶” 观音均为同一类型。铸像有金质、银质、银或铜质鎏金、青铜质等多种。最贵重者为一尊重达1130克、高26厘米的纯金观音立像,另一尊为高49.5厘米的铜质鎏金观音像,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尊 “阿嵯耶” 观音铸像。
有关 “阿嵯耶” 观音的来历,学术界说法颇多。因为它太独特了,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印度、缅甸系统或中南半岛系统;有的认为其出于南诏、大理国本土,是当地民族融合几种信仰而合成的一尊神祇。如果查史料,约绘于公元9世纪末的《南诏中兴画传》首见 “阿嵯耶” 观音之像,但画传已明明白白画的是异域梵僧来洱海地区传教,引入了铜铸的 “阿嵯耶” 观音。 “异域” 为何?《南诏中兴画传》文字卷记有一段文字: “保和二年乙巳岁(公元825年),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安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寺。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 讲完圣迹故事之后,图传文字卷还记录了南诏王舜化贞的一篇敕令,算是佛教进入洱海地区的一种权威说法: “敕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札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今世后身,除灾致福。”①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国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147—148页。
于是才有了《南诏中兴画传》。而对于 “阿嵯耶” 圣像的不断铸造,更是延续了数百年。国泰民安时铸像,发动战争时铸像,谋权篡位时也铸像。自南诏崛起初期熔鼓铸 “阿嵯耶” 圣像始,到南诏国和大理国时铸像成风:南诏王劝龙晟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送佛顶峰;丰佑时仅三塔寺即有佛一万余,还用银五千铸佛;隆舜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并改元为 “嵯耶” “大同” 等。地方头领甚至 “塑主像,立生祠以祭之曰:我百姓家宁,时世太平,不动刀兵,主之力也。” 主则忻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末代南诏王舜化贞铸崇圣寺雨铜观音。两年后,郑买嗣篡蒙国(南诏),改元安国,国号大(太)长和。七年戊辰,铸佛一万尊,为杀蒙氏八百人之赎罪。短短三十年,政权几度更迭,国号随城头大王旗飞快变幻。不久,段思平攻灭大义宁国,建大理国。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②据《白古通纪浅述》等述,转引自木芹《试论南诏王族覆灭的原因》,载杨仲录、张福三、张楠主编《南诏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70页;邱宣充:《南诏大理大事记》,载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213页。因此,在南诏大理国几百年统治期间,阿嵯耶观音仍然是王室崇敬信仰的主要神祇。此为后话。

图3 大理国(宋)时期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复制),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大理州博物馆(笔者摄)

图5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大理市博物馆(笔者摄)
画传借佛教之事,一语道出了南诏文化与几大文化交融的关系。南诏大理的众多工匠和艺术家在吸收来自各方的养分之后,都会经自己的手再创奇迹。现藏于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被称为 “云南福星” 的一尊青铜 “阿嵯耶” 观音像,就是一件出自大理工匠之手的铸像精品。有铸像裙裾背面的铭文为证: “皇帝骠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等造记愿禄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机相承万世。” 除祈福用意,明证此像为公元1147—1172年在位的大理国国王段正兴出钱为其子所铸。
据科技考古专家的技术检测,大理发现的和流散至欧美的一大批 “阿嵯耶” 观音像,都是原产于大理国时代云南的古代文物,全是真品。这些铸像严格按照统一样式制造,造像风格、手印一致,尺寸差别不大。但众多观音又不雷同,不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说明在12世纪,大理的青铜铸造水平已具规模,且人才辈出。既有不改形制的统一标准,又有不同创作者在铸造过程中的微妙变化,造型、模铸工艺和鎏金技术已是十分精湛了。①参见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图6 大理国铜杨枝观音立像,云南省博物馆(笔者摄)

图7 宋代金背光银净水观音,崇圣寺三塔出土,大理州博物馆(笔者摄)

图8 大理国铜杨枝观音立像,云南省博物馆(笔者摄)
无论怎么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是很值得研究的:它有 “阿嵯耶” 观音类型,也有藏传或汉传佛教观音类型;有男身,也有女身。笔者检索印度宗教艺术考古画册中那些作于公元7—9世纪的石雕、铜像和铸造于12世纪前后的铜像②M.Postel,A.Neven,K.Mankodi:Antiquities of Himachal,Bombay:Franco-Indian Pharmaceuticals Private Limited,1985,p38,46,47,97,98,106,108,110,122.,以及在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所见,发现这些印度教神祇的石雕和铜像,特别是保护神毗湿奴(Vishnu)的高髻(或冠)、直立的姿态、裙裾及腰带缠式、光裸的上身和项圈臂钏,乃至背后的焰纹等,与云南大理等地发现的阿嵯耶观音,在造型和神韵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这些文物是从远在印度西北部的喜马偕尔邦发现的,它们如何与东南亚和吐蕃佛教艺术产生交接,是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图9、图10、图11 毗湿奴(Vishnu)造像(9—12世纪)。采自M.Postel,A.Neven,K.Mankodi,Antiquities of Himachal,Franco-Indian Pharmaceuticals Private Limited,1985,p39,108,111.

图12 毗湿奴(Vishnu)造像(印度北部)(笔者摄)
三、展衣夺土:取代罗刹的观音

图13 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陈列品,2018年(笔者摄)
《南诏中兴画传》讲述普通农夫发迹为王的故事,在明万历《云南通志》、传元人张道宗著《记古滇说》、近年发现的传元人赵顺著抄本《僰古通记浅述》、各本《南诏野史》、清人文果《洱海丛谈》、清康熙年间喜州圣元寺僧寂裕刊刻的《白国因由》、清圆鼎《滇释记》①汪宁生:《〈南诏图传〉考释》,载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及民间传说②笔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调查采录的民间传说,指点化者为 “老君” 。中,均有记述。
无论传说还是史实,都一致确认,南诏始祖细奴逻,是被圣者点化而发迹的。这是流行的王权天授模式,古今中外,大致相似。
只有一点差异:在不同文献不同讲述者的叙述中,点化细奴逻的那个关键角色,或是来自西域由观音化身的 “梵僧” ,或是本土道教宗师 “老君” ,这要看讲述故事的人有什么信仰,取什么立场,认同什么。
作为反映主流社会信仰和官修图像文本的《南诏中兴画传》及地方史志,都说点化细奴逻的是来自西域的 “梵僧” 。南诏王城遗址出土石雕佛像、剑川石窟等,均为佐证。它们所取的是佛教的立场,这当然与南诏国君主信奉佛教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关。
作为反映民间信仰及其底层社会意识的祭祀仪式和口传文本,则说点化细奴逻的是本土道教宗师 “老君” 。这可能与土主崇拜、本主崇拜、道教和民间传说在大理地区民众中十分流行有关。直到现在,在南诏发祥地巍山,民间对道教的认同程度仍然很高。当然,后来包括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外来宗教,也是人们兼容的信仰。在大理地区,吃斋念佛和祭祀本主、演唱洞经的往往是同一批人。观音(主要是 “阿嵯耶” 型观音)、大黑天神等具有佛教密宗色彩的圣灵和太上老君、文昌武帝等道教诸神,以及遍布人间的山神水龙、野鬼邪灵,都拥有较多信众。我们只要看看民间在举行民俗法事中焚化的众神 “纸马” ,就可窥见这一地区神灵系统的浩大庞杂。
据石窟文物和古代文献考证,大约在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 “白蛮” “乌蛮” 主政的南诏大理国地区前,其地的主要意识形态还是神话、巫术和巫教等原生信仰,巫师往往凌驾或渗透在社会组织中,具有相当大的威权。当佛教密宗传入大理地区时,由于梵僧非本地籍贯,他们也曾遇到一些麻烦。除了与原有宗教权威及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外,他们在民间也遇到了一些波折,与当地土著发生矛盾,或传教无人理会。除了前举《南诏中兴画传》描述的梵僧传法遇阻事件,剑川石宝山第7号石窟还有尊观音(甘露观音)石雕引人注目。她半坦胸部,胸前有个洞,当地白族把她称为 “剖心观音” 。传说,观音初来大理传法时,信仰本土巫教的民众并不相信她。为了说服民众,示现诚意和法力,观音不得不剖开胸膛,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大家看,这才感动了人们。在大理地区,这个传说广为流传,并已经凝固在剑川石宝山石窟中那尊引人注目的剖心观音雕像上了。

图14 剑川石宝山第七号石窟的甘露观音,俗称 “剖腹观音” ,云南剑川,2015年(笔者摄)
大理民间关于观音和罗刹斗法的传说,则显示了观音的另一面,渲染了佛教密宗神变强大的法力。代表原生巫教的罗刹和代表外来佛教密宗的观音的斗法,如同佛教传入西藏时与本土宗教 “苯教” 斗法的传说类型一样,最终都是佛教占了上风。细读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隋末唐初,罗刹久据大理国,人民苦受其害。自唐贞观三年癸丑,得观音大士从西天来五台峰而下,化作一老人,至村探访罗刹及罗刹希老张敬事实。……观音大士探知张敬是阿育王之后张仁果之裔,为罗刹希老。此时罗刹为害,张敬亦无之奈何,但当日与罗刹来往者,惟张敬一人。观音遂化为一梵僧住于其家。知张敬与罗刹厚交,便于引进故也。张敬见观音温柔慈善,甚敬爱之。旬日之后,进言于罗刹曰: “我家来一梵僧,自西天来,容貌端好,语言殊妙。真为可敬。今欲他往,我再三留之。” 罗刹闻而欢悦,即令张敬引来相会。一见梵僧,心生敬爱,款待甚恭,凡出入起居,不肯相离,即以人眼、人肉为供。梵僧曰: “我受净戒,不食此物。如食之即为犯戒,他日受无量苦报。” 罗刹闻说,善念忽生,乃曰: “长者至我家,不食我饮食,我心不安。欲与我要何物,我当如命。” 僧曰: “我出家人要个甚麽!若王相爱,只乞赐安乐处地方一块,结茅居之,不识王意如何?” 罗刹曰: “如此不难,但不知要得多少来的?” 僧曰: “只要我的袈裟一铺,我的犬跳四步,就足矣。” 罗刹乃笑曰: “太少了,任意去,任意去!” 梵僧遂作礼而致谢之。
罗刹既概然以地许观音,则未识观音大神通力。越数日,乃告罗刹曰: “昨承大王悯僧远来,概然赐地,若是据占,恐招王怒,以我自思,求立一券,以为定准,方敢以袈裟铺之,白犬跳之,可求为遵守也。” 罗刹曰: “长者太过于小心矣!袈裟一铺,犬跳四步之地无多地方。我既与之矣,长者何必多疑。” ……(观音)再三求其立券而后已。……罗刹曰: “梵僧既然过虑,立券不难。” 于是观音即延罗刹父子,请主人张敬并张乐进求、无姓和尚、董、尹、赵等十七人,十二青兵同至上鸡邑村合会寺,料理石砚、石笔、石桌,至海东,将券书于石壁上,今存其迹。
观音与罗刹立券,后复回合会寺,将石砚石笔送与灵昭文帝(大理山岳之神)。今石砚、石笔在上鸡邑村西合会寺之北;石桌送在杨波远,今石桌见在杨波远村上。斯时,观音告主人张敬曰: “券虽已立,然恐罗刹之心叵测,不为万全之图不可,我愿彼父子对众立盟,才为定准。” 敬答曰: “罗刹父子心果然叵测,诚不可不令盟誓也。” 于是宛告之曰: “蒙大王赐梵僧地,此大王厚恩矣。既已立券,我知梵僧小心过疑,欲再求大王立盟,诚为远虑也。” 罗刹笑曰: “梵僧何必如此过虑。” 敬曰: “自我思之,既蒙大王赐地,又与立券已是实心,何妨再与立盟,使他无疑,足见大王爱梵僧之德意。” 罗刹信之,遂往榆城西苍山下,对众立盟曰: “天地圣贤、护法,鬼神在上,我父子对众立盟,送地与梵僧,任其袈裟一铺,白犬四跳,此外梵僧不得复求我父子,不得反悔,如有反悔,我父子堕落阴山,永不见天日,护法天神作证。” 梵僧合掌称赞。今教场西,大石版者,即罗刹盟誓处。今人于此解结焉。
罗刹随观音至海东,观山青(清)水秀,见石窟鱼窝,十分欢悦。乃凭张敬并建国皇帝大护法等,遂令灵昭文帝秉笔将券书于石壁之上。回至海西,又对众盟誓已。罗刹父子以为些小地方,不以为意,只知与梵僧亲洽相忘于尔我,又何尝计较地界之多寡与得失也,时刻聆受开示,皆忘其食人肉、剜人眼,渐生善念,若有不复为恶之状。此时,人民咸相谓曰: “美哉!罗刹父子得梵僧劝化,不复为恶矣!” 父呼其子,兄呼其弟,俱向前感谢梵僧并建国皇帝、灵昭文帝之威力,有来奉酒馔者,又有来献茶饭者。梵僧慰众曰: “好矣,尔等大王父子为善了,自从今日后,不复为恶食人肉、剜人眼了。尔等安乐之日至矣!各自向善务业,不必猜疑还如前日之为害也。” 村中人民皆唯唯作谢而去。于是观音对众将袈裟一铺,覆满苍、洱之境;白犬四跳,占尽两关之地。罗刹一见大惊,拍掌悔恨。此时有五百青兵并天龙八部在云端拥护,大作鉴证,而罗刹父子悔恨不及矣。
罗刹见梵僧将袈裟一铺,尽将大理境内遍覆;白犬跳步,自西山到东山,上关到下关。罗刹父子怆(仓)惶失色,乃曰: “了了,我国土人民悉为梵僧有矣。” 欲要反悔,则券已立,誓已盟,众人之前,自觉羞耻,乃自悔当日误听张敬之言,错与梵僧交接往来,于是父子私相语曰: “张敬受我父子深恩,反陷我国土,即那僧阳为浑厚,阴为诡诈,愚弄我父子,并吞我地界。” 虽怀忿憾,不敢反言,乃善告梵僧曰: “我国土人民尽属长者有矣。使我父子无居止之地,奈何?” 僧曰: “此亦不难也,我别有天堂胜境,请王居之。” 即以上阳溪涧内碌瓮摩出一洞,化为金楼宝殿,白玉为阶,黄金为地,化螺蛳为人眼,化水为酒,化沙为食,美味、珍馐、器具种种俱。将罗刹父子引入于内。罗刹父子见之曰: “此境界胜于旧时我国土也。” 僧曰: “此处王如不愿,仍将大王所赐我之地相还。” 罗刹曰: “此处极安乐,无不愿者,只求长者将我眷属移来,尽归于此。” 僧着护法神兵将伊家眷属尽移于内,以神通用一巨石塞其洞门,僧变作黄蜂而出。罗刹惊吐其舌。僧令铁匠李子行以铁汁浇之,又造塔镇于洞上,使伊父子永不能出此。观音神通广大,罗刹恶业当终也。①无名氏:《白国因由》,据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圣元寺住持寂裕刊本翻印。收录于[清]倪蜕纂录《滇小记》 “附录” 。载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63页。
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类型(六祖惠能也有相似的故事),其核心结构是,原住地主人或凶残或厚道,外来者取得主人信任,索求一衣所覆之地。主人答应,客人展衣,覆盖了全部疆域,反客为主。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传说,发现也是蛮纠结的。如果暂时搁置信仰正邪和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个故事倒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佛教密宗传入大理地区时的历史状态:地方巫教神主罗刹与世袭土王张敬共同管理大理,此为原始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格局。后来巫教坐大,罗刹作恶,土王无奈,教凌驾于政之上。这时外部势力介入,先来 “文” 化:观音化为传教者梵僧,在土王前表现得温柔慈善,获得信任,再通过土王接触到罗刹。罗刹初见 “容貌端好,语言殊妙” 的梵僧,心生敬爱,款待甚恭。在梵僧的规劝下,罗刹初起善念。因梵僧不吃罗刹的美食,罗刹不过意,主动提出请客人选物。梵僧趁机提出要一衣所覆一犬四跳之地,并要求罗刹立券盟誓为据,同时请来外来武装力量(天兵)作证。舆论造足,条约签订,温文尔雅的梵僧这才露出真相,一招就把罗刹的国土尽占了。罗刹这才发现梵僧使诈: “那僧阳为浑厚,阴为诡诈,愚弄我父子,并吞我地界。” 尽管悔恨,却无法毁约。这当然不仅因为 “券已立,誓已盟” ,要守信用;其实主要是上有天兵 “鉴证” ,武装威胁,下有观音在侧,软硬兼施。在强大的外部势力胁迫下,罗刹自知不敌,只能就范。认输还不行,梵僧趁势把无家可归的罗刹父子及其全部眷属,骗去山洞里封镇, “永不能出” 。
这是一个流传时间较久远,史籍和民间都有叙录的传说。②更早述及此事的,可见于[元]佚名撰:《白古通记》,载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5页;[明]谢肇淛撰:《滇略》卷十 “杂略” ,载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8—789页。另外,当代大理地区白族流传的民间口头传说中,也有类似故事类型,参见云南省民间文学办公室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293页。传说中叙述的斗法未必真有其事,但产生传说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意识形态转型,却是真实存在的。
观音信仰在佛教盛行的大理、巍山地区比较流行,而且显现不同的化身。一会儿是梵僧,一会儿是白胡子老爷爷(如大理圣元寺观音阁的 “观音波” ),一会儿是半裸的美女(男),一会儿是飘然而来的 “面目慈祥的老婆婆” ( “观音老母” ——云南人对观音的一种比较乡俗化的称呼)。
由于这种信仰,白族民间流行最广的就是观音和大黑天神的故事。密宗法师善于施展法术,表现神通,在治孽龙河妖方面十分得心应手。特别是其连天都可以遮掉的本事,让只见识过小打小闹巫教法术的当地民众为之慑服。 “观音来到大理,见苍山洱海之间的天空中一个挨一个悬满了锋利如尸的岩石。岩石的头都朝下,看着很害怕,好像就要掉下来。人们害怕,不敢看天,不敢在田里干活。观音菩萨取下头巾,把天空蒙起来,才成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天空”③杨宪典(白族)记录:《观音蒙天空》,参见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289页。。 “观音负石阻兵” 的传说,讲唐军欲犯大理,路遇观音化的老妪,背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唐将惊问老妪,你怎么可以背得动这样的巨石?老妪答,我老了,只能背那么一点点,比不得年轻人了。唐将想,老妪尚能背此巨石,年轻人不知何等本事!立刻撤兵了(又说被山洪卷走)。④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318页。这类传说是本土神话的转译,主角原型并非观音。转译内在的心理基础,是暗示观音信仰既与当地的巫术崇拜和信仰实践有着更多认知上的共同点,又在以法术显示力量上更胜一筹。所以,以观音信仰为主要旗帜的佛教密宗,很快就获得当地人认同,在南诏国立住了脚跟。
结 语
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为了让不同文化背景和族群关系中的 “众生” 接受,需要跨越文化和族群的界限。信仰佛教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傣族、白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及东南亚的掸族、缅族、高棉族,东亚的朝鲜族、大和民族等,以及曾经信仰过佛教的突厥、回鹘等古代民族,他们的种族和文化差异都很大,具有明确的族群边界。但佛教都能够予与包容,并且,为了 “顺蕃俗” ,不断变服从俗,与当地原生文化进行有效互动,融入其中,获得认同。在佛教造像中产生的各种 “民族风” 元素,呈现了其在不同传播地民族化、在地化的情形。
《南诏中兴画传》形象化地叙述了外来文化(佛教密宗)于中世纪传入云南大理地区的传说。这些传说以及根据传说 “书写” 的画传,因是为权力所役使,所以照例充满了 “君权神授” 的想象和幻化的东西。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得以窥见地方社会在异文化冲击下,对抗、融合和互动的历史细节。从变服从俗的在地化适应,到熔鼓铸圣的文化突变与展衣夺土的社会转型,《南诏中兴画传》及相关传说,折光地反映了一个时代意识形态与文化精神的微妙变化。通过铜鼓、圣像及民间传说这类艺术象征物和口传文化,传递出多民族地区在与异文化发生接触的过程中,如何自我调适,进行文化认同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