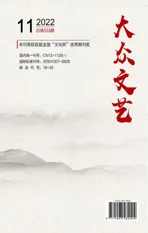论阳明学中的浙学精神
2021-06-25倪福东
倪福东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关于“浙学精神”,朱晓鹏认为,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来自草根的平民哲学,求真务实、讲求功利,实践理性追求,独立自主精神,包容开放精神。本文从阳明学中的“亲民”“心即理”“知行合一”思想为主线,分析这些思想中所蕴含的浙学精神。
一、来自草根的平民哲学
历史的看,阳明学是一种平民哲学。朱晓鹏认为:“在浙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立足于朴实温厚的平民精神,自觉吸收底层的社会实践与平民思想,形成了平民哲学的基本特色。”从阳明学内部看,阳明学在如何“学为圣人”这一问题中,提出“圣凡一体”的主张,即凡人可通过“返俗入圣”的路径成圣。这意味着,阳明学是一个希望平民以成为“圣贤”为目标的学说,就这教化意图来看,体现了其学的平民精神。从阳明学所处时代的外部环境看,阳明学的提出,亦是对官方正统朱子学的挑战。葛兆光认为,在阳明所处时代的士人,对“四书五经”的学习多出于入仕、考试的考虑,而在士人内心中,已将其视为是对自身思想的钳制,对此不再认同,并有了更多的思想取向。可见,阳明学的兴起,不仅是由于其思想有很大的吸引力,更是因为时人对压迫的、禁锢学术思想自由的官学的不满。
那么,阳明学中有哪些思想蕴含了“平民化”的特质呢?王阳明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思想的:“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这是阳明子在《答顾东桥书》中对顾东桥的回应。顾认为,阳明学由于“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导致其学坠于禅学的“心性”“机锋”之中,致使后学在“师传”的过程中,往往执于一端,流于片面,传出“谬误”。这是理学学者对于心学学者的一贯判断。由于阳明主张“心即理”,使顾东桥误以为以心“度”理是一种纯主观判断,其实本非如此。因为,阳明的“本心”是受到限制的:“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阳明认为,心是人心,更是道心。心是人与道能沟通、融合的媒介,而当人心上升为道心时,心所作的判断,是符合道的,即客观的。不仅如此,心还是实践的。对于心性的锤炼,阳明倡导“事上磨练”“省察克治”,即在挫折、困难的现实中,求得“道心”。换言之,即对意志的锤炼。阳明认为,其所属时代由于受正统理学的影响,时人不再注重笃行,一味向外追求虚无的“本体”,学风由“经世致用”转向“虚无空谈”,重“经”(义理)而不重“史”。如顾东桥,他虽认同在“尊德性、道问学”问题上应该“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但在“工夫”中仍应分个先后之差,这是当时朱子学人所共识的。这就导致,朱子学人对现实的忽视。相反的是,阳明学人,以“心”为主旨,以“实事实功”为目的。不仅如此,阳明学还以当时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并反思学理中的伦理道德价值,就此而言,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进一步言之,阳明学思想的平民性就在于,其学从本心出发,不再复杂深奥,能使学识浅薄但心向圣学之人能容易进入。而且,在事上磨练的“践履”能使无法“不事劳动、养尊处优”的平民百姓也能结合自身情况,在“事”中磨练、学习。这种践履之学的“教化”作用,对平民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就阳明学而言,与顾所认为的“立说太高”恰恰相反,阳明学确实“立说不高”,并正是由于此才彰显了平民性。
阳明学的平民性,还体现在其“教化”意图上。关于阳明学的兴盛,根据吕妙芬分析,其时间节点在“主政江西时期,尤其在平定江西、湖广、广东诸寇(1517-1518)以及平定宸濠叛乱(1519)之后”,阳明立“社学”的时间也与此相接近。可见,阳明学以“教化”为旨归的办学促进了阳明学的繁荣。阳明立社学的目的很明显,即教化民众,涵养民风。通过对在盗贼众多的地区加强教化,“怀柔”地改变地方风气。换言之,即以“开导训诲”的方式来代替“严刑峻法”。这正是阳明在正德十三年正月时,寄书杨仕德“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提出的,“破心中贼”最彻底的办法。同时,这也体现了阳明学的亲民思想。阳明坚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圣的要义在于心是否纯乎天理,在各色各样的人中,人与人之间的天资、悟性或有不同,有高下之分,但无本质区别。
阳明认为,以成圣为目的的圣学,是不在乎修习对象起点的高低,换言之,圣学是开放的、不设门槛的,只要有这追求的人,都能参与其中,而且,成圣的决定因素,不在于个人的天资等先天条件,而在于是否有坚定成圣的决心,使自己的心渐渐与天理相近,直至相同。阳明认为,成圣是“为己之学”,要改进和磨炼的对象也是自己。
阳明认为,人应于现实中磨炼成圣,而不是空有一个“圣人”的概念不诉诸行动。在阳明所处的时代,时人对于成圣,往往是描绘的越来越细致,提出成圣所需的越来越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圣人只是人们心中一个完美全能的“超凡成圣”的概念或想象中的图景,而绝不可能是现实之中“由凡入圣”的真实案例。阳明认为,圣人不仅是知识上的“学者”,更是行动上的“道德楷模”。简言之,当所学的知识、所得的见闻,有损于自身道德时,以致夹杂了人的欲念,损害了天理,那么还不如不学。阳明将圣人的条件限定在道德领域内,也是和当时社会的道德日下,以及儒者重视才学后,忽视自身道德修养,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息息相关的。就阳明提出“圣凡一体观”的进步意义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对自朱熹之后影响的官方正统儒学予以了一定的挑战。对当时的入仕者予以一定思想上的冲击。吕妙芬认为,程朱学被奉为科举教材之后,考试、入仕的功利性目的渐渐“剥落”了程朱的“学圣精神”以及对义理的钻研。这对于当时的人们,多少有切身之感,这也是阳明学兴起的原因之一。第二,重道德教化,使阳明将士、农、工、商等都纳入关怀视域之中。阳明将圣学理解为道德伦理学之后,把道德实践等作为主要内容,所学的知识也以道德知识为主。所以阳明的宣讲多以讲学、讲会为主,区别于文人结社谈论的辞章之学,阳明学的讲学讲会内容分为两个维度:庶民式(平民)讲学、讲会,多以乡约、教化为主;学院式讲学、讲会,多以朋友间切磋论道视“以友辅仁”为旨归。第三,阳明反对朱子在《大学》中将“在亲民”理解为“作新民”,而应回归到古本的“亲民”之中,这也是其亲民思想的体现。在阳明对徐爱关于“亲新之辩”中,所呈现的尤为突出。阳明和朱子的“亲新之辩”来自对经典《大学》的不同阐释。首先,“亲”字在古代是通假字,所以‘亲’和‘新’在古代是通用的。朱子认为“在亲民”应理解为“在新民”可以与《大学》后文相呼应——“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在《大学》开篇理解“大学之道”时,就会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理解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进程,即限于“内圣”一域。阳明认为,这种过于注重“独善其身”式的道德修养,而没有参与到现实社会环境之中,对于社会而言,是没有积极价值的,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造成的社会冷漠现象,是违背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观念的。阳明曾言:“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这也是阳明出入佛老之后,回归儒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从文本上看,阳明推敲《大学》全文,发现内容与“亲”字关联处甚多,其表达的内涵也多是类同孟子的“亲亲仁民”之意。所以,“亲民”是体现儒家“仁”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将《大学》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理解为道德的“内圣、外王、内圣外王合一”的过程,才是更加完整的。正如阳明所说,“明明德”是“修己”,“亲民”是“安百姓”,“仁”的精神是要有不断外扩的过程,就像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来描绘在“仁”的运动轨迹下,所产生的“群己关系”。而阳明将“亲民”等同于“安百姓”之后,在实施具体办法上,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民之父母”为角色基调,教民养民是具体的政治举措。所以,阳明在任,多重民生教化,家庭伦理。以“齐家”的观念,在治下“治民”。不可否认,在当下我们来回看阳明的这些言语,溢出不少“慈父哲学”的味道,但是阳明将“民众”纳入自己政治实践的主要对象,并多以教化代替刑罚,这在当时的境况下,多出了一丝人文关怀。
二、求真务实、实践理性追求
阳明学的兴盛,不仅是因为其思想充满了平民性,更是因为其思想倡导经世致用,不再将知与行分为两件事,而是知行合一,以求能“学以致用”。阳明学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能体现其求真务实、有着实践理性追求的特点。
什么是“心即理”?阳明认为,心是主宰人的身体、躯壳的主观意识,是有知觉的,而且人的心又多秉受天的意志,有着客观、公正的特点,所以合于天理。阳明更进一步,推为“心即理”。接下来,笔者将具体论述“心——理”的推进过程。
关于“心”,阳明曾言:“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这里体现了心的感知功能,同时,阳明想表达的这种知觉,亦是自然的、真实的。他将五官的感官功能类比于心,认为心也被赋有这种功能。阳明认为“心”是人身体知觉的反应,而这种反应,通常是具有普遍性的,如耳朵的听觉、眼睛的视觉等,这都是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如阳明在提出“凡知觉处便是心”之后,进一步讨论了“心为身之主宰”。可见,阳明描述了心的两个阶段,即感知、克制(主宰)阶段。这两个阶段,也恰好贯穿了知与行的整个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阳明的知与行是在道德领域之中的,或者说是对儒学中“仁”的知与行。阳明先提出“心者身之主宰”的观点,将身体所感知到的“视、听、言、动”(“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描摹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发即身体所有的自然反应和感知;而自觉即对身体的感官、人欲都有一定的抉择,而抉择的尺度就在于其“心”正与不正。前半段描绘了心在正时,“视听言动”都能有一个正面的反馈,即在“视听言动”上都是符合礼的。而后半段,则是在处于非礼的情况下,采取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行为。而这么一个完整的在“礼”“非礼”的行为,阳明称之为“正心”,亦称之为“修身”。还应补充说明的是,关于“非礼”的“勿视听言动”正是孔子所认为的“克己复礼为仁”,即是一个“行仁”的过程。在符合“礼”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所以,心之正处,即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廓然大公,亦是天理流行之状。
在把握“心”与“理”的关系之前,阳明先提出了“什么是心之本体”这一问题。关于对“心之本体”的探究,阳明阐释有以下几点:
至善是心之本体。
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知性。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阳明把心之本体称为性、至善、良知、天理。我们可以看到,在阳明追寻对心的本体化的过程中时,他是希望将心形上化,将其从个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人类所普遍共有的品质。而且,这共有的品质也逐渐从人类的美好道德价值过渡到天理上,即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上升到宇宙世界真理之中。基于这个逻辑推演,“心即理”所要真实表述的,其实是“心之本体即理”,即“性、至善、良知、天理即理”。而且,因为“心”先验式地赋有天理的特质,所以对天理的追求进路也是从心中求,而不是在“心外求”。所以,阳明认为,“格物”不再是追求天理,而“诚意”“致其良知”才是求得天理的最正确的办法。不仅如此,阳明认为,“心即理”并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逻辑推演上的概念性的命题,更是一个与现实联系,以实践、践履的方式来努力追求的一个超凡入圣的境界。
在阳明论证了心与心之本体之后,便很自然地将心与理联系起来了,一是心有根植于天理的,具有天赋性的心之本体以承载;二是,从心的动态运动中,即在现实社会中的活动中,有从“私心”向“公心”转向的路径,即“人欲”与“天理”之间,在现实运动中,有了调和的可能:或是抑制了过分的“人欲”,或是更多彰显“心性”中合乎“天理”的部分。至于“心外无理”“心意之物”的逻辑展开都是以此为起点的,在此不再赘言。“心即理”思想,体现了阳明认为人有把握真理的可能,这也是人认识真理的前提,而且“心即理”也是重视过程的,有一个实践的阶段,综合来看,“心即理”体现了阳明兼顾了圣学与现实之间差异,讲求“求真务实”地为学。
阳明提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命题,就是“知行合一”。关于“知行”问题,阳明从知行的关系、知行本体、知行功夫乃至知行合一进行了层层递进式地探讨。先说说“知行本体”。首先,阳明关于知与行,就其语境来看,是侧重在道德伦理领域之内的。其中选择了孝悌、对好恶的评判皆是将知与行引入了有着价值标准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理解的现实世界还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道德领域下,阳明是更重视“行”的,“知”也是为“行”所服务的,只有达到了“行”这个过程,之前的“知”才能称之为“真知”;相应的,只有“行”符合“知”的规定、标准,才能称之为“真行”。所以,其中的“知”,与现实世界的“知”不同,不是要用认知的方式来探索与确认,而是通过以得到“行”的反馈的方式,以及在能更好地改造和完善“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也是阳明所说的“知行本体”。吴震认为:“阳明所说的‘知行之本体’,指的是知和行的本来关系或本来意义。”“从本然意义上说,‘未有知而不行者’,有之必有行;如果‘知而不行’,那么还不能说已经‘知’了,只能说还是‘未知’。”“阳明想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具有本然意义,是人们无法违背的实践原理。”因此,阳明在“知行”问题上已经定下了基调——“知行合一”即“知行之本体”。首先,“知行合一”之后,说明人的“知”就是“真知”了,是有能驱动“行”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概念,却不能化为行动。而正是如此,方能说明,知与行是一体的了,原本被“私欲隔断”的问题也被解决了。其次,“知行合一”之后,两者之间的联系会愈发密切。正如阳明所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之后,才能使人们更好地坚持道德实践,提高道德素养,并获得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知行合一”之后,也是实践与理性之间的结合,正是这种对实践理性的追求,可以使人深知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使人通过实践的方式,逐步地向上超越。圣学是超越现实的,需要通过不断地道德实践来接近。正如陆澄问阳明“上达工夫”,阳明认为“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所以,阳明深知前人对“知行”问题没有全面的认识,没有融合入日常生活中,虽然现实中有些人“冥行妄作”“揣摸影响”,却没有好的“良药”来“对症下药”。阳明就只能在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之后,更进一步,捅破了“知行”之间的窗户纸,不让“私欲”成为流弊继续阻隔“知行合一”。
顾东桥对于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提出过质疑,“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阳明就此认为知行体用一源,不可分离,即知行在本体上应“知行合一”,在实践中(用),同样要“知行合一”。阳明更加紧密联系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关系。我们可知,阳明认为,古人乃至与其同时代的人由于视“心理”为二,以至把“知行”也当作两件事。“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就是很鲜明的例证,以往的学者都认为外于心的“物理”是不能在心中求的,但其实阳明以为,他的知行合一,恰恰是能将所谓的“物理”从心上求得,而且以躬行的方式求理,比学者的“格物穷理”更真实。当然,在笔者看来,阳明还是将问题所转换了,他的论域还是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在道德领域下,确实是动机比概念(认知)更重要,即心之理重于告子“义外”之说。在知与行的体用关系上,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可见,阳明对“真知”的定义还要求“真切笃实”,而这只有通过“行”才能实现;同理,“真行”要求的“明觉精察”,需要知的“思惟省察”才能不断完善。这么一个完整的求知躬行的过程,就是阳明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是”的完整逻辑。所以,阳明认为“心与理一”到“知行合一”是“体”与“用”之间的一贯相承。而再将此二者“合一”,就是阳明之后提出的“致良知”,“良知”就是“心之本体”,也与“理”同;而“致”,就是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使良知充盈的道德实践。
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可以理解“心即理”为本体,“知行合一”是工夫,而“致良知”就是本体与工夫合一的动态状态,人们需要在“心即理”的主导下,不断地“知行合一”,最终能“致良知”。而“致良知”是一个在生命中永不停止的过程。在阳明的这个活的思想中,很明显地体现了其求真务实、追求实践理性的精神,当然他是侧重在“道德伦理”的范畴下,或者说,整个实践的过程,就是以“主体道德”超越“客观现实”为目的,希冀能在困厄、艰苦的现实环境下,还能保持高尚。
三、独立自主、包容开放
纵观阳明毕生,他在思想上经历过“五溺三变”,沿着“辞章之习”“宋儒格物之学”“出入佛老”“归本儒学”“龙场悟道”这一大致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可见,阳明心学建构之前,其学涉猎甚广,以先“博”后“约”的方式,最终形成思想,其中对各家学说的吸收毋庸置疑,同时也有对各家学说的批判,大体上是以一种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的方式融扩进自家学说,以此可以看出他与各家学说的关系是又包容开放,有独立自主的。以下将先从其与各家的交流上予以例证。
阳明认为,儒学和佛道之间,佛道有很多值得肯定和吸收的部分,应当为“吾之用”。关于阳明以在“儒学正统”立场,对佛道两家的价值贬低,暂且不谈。从文中透露的事实来看,可以得到以下三点:1.佛道在某些领域内,是值得儒家吸收和学习的,正是由于其“用”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阳明若想复兴儒学,须吸收之后,为我所用。2.阳明“三间共一厅”的类比,间接说明了儒学如果不吸收佛老的精华之处,就不能见“圣学之全”,导致“举一而废百”。3.阳明将圣学比为大道,而成为大道的先决条件是要吸收各家精华之处,并以“天地民物同体”,方能成为大道。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阳明没有向后儒一样秉持“门户之见”,推崇吸收各家的精华之处为“吾之用”,这很能体现他的胸怀,也体现其学的包容开放。试想,如果儒家秉持“门户之见”,或许也是“自私其利”,那和儒者对佛道所认为的“自私其身”也没有太大分别,都是“小道”罢了。正是阳明这个“大道”的视野,给了其学“包容开放”的气质。然而,阳明肯定了佛道在“用”的一面,对其“自私其身”的出发点予以否定,认为圣学应该与“天地民物同体”,即与“万物一体”,这又是反映了其“包容开放”的超越性,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还需补充的是,阳明在之后用道家道教的术语、思想方法、工夫修养等来构建其心学体系,也正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真正的吸收融扩、为我所用,其学的包容开放也在此。对于此,学者朱晓鹏有系统性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在《明儒学案》中有阳明关于三教问题的论述,他觉得圣学之全,在于“精一”,即本体上的同一与器用上的统一。这跟之前的“三间共一厅”又递进了一层。基于此,章学诚认为,后世文化的衰退就是有意将“三教统一”演变为“三教对立”,而对立的原因不是因为对“道”有更细微的体认,而是为了“争文”“争名”“争心”所作的“欺世”之举罢了。
阳明所处的时代,就有这种风气,学派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而认同却越来越少,原因就在“争”,为“私利”而争,为“道统”而争,而往往争其名后却不充其实,导致出现名不副实的怪象。所以,阳明推崇“去其藩篱”,也是有去除现实上“私利”“私见”的涵义在的。这也是因为阳明为学求真,求公,而后使其更重视“大道”之同,而不为“小道”之异所偏。正是阳明这种“以道观之”的胸怀,使其能以包容开放心态学习各家学说。
再说阳明学的独立自主精神,还是以其重视主体意识、为学“为己”、重在“自得”得以体现。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就《大学》古本和朱子注本的争论中,阳明就提出为学贵在“自有所得”。所以,在阳明看来,为学要自得,更要自主,所学的知识,对其正确与否因是由自己的良知来评判,而不应受外界的干扰,就算跟权威、正统之说背道而驰,也要坚守自身良知,这正是彰显了其学独立自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