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隐
2021-05-18苏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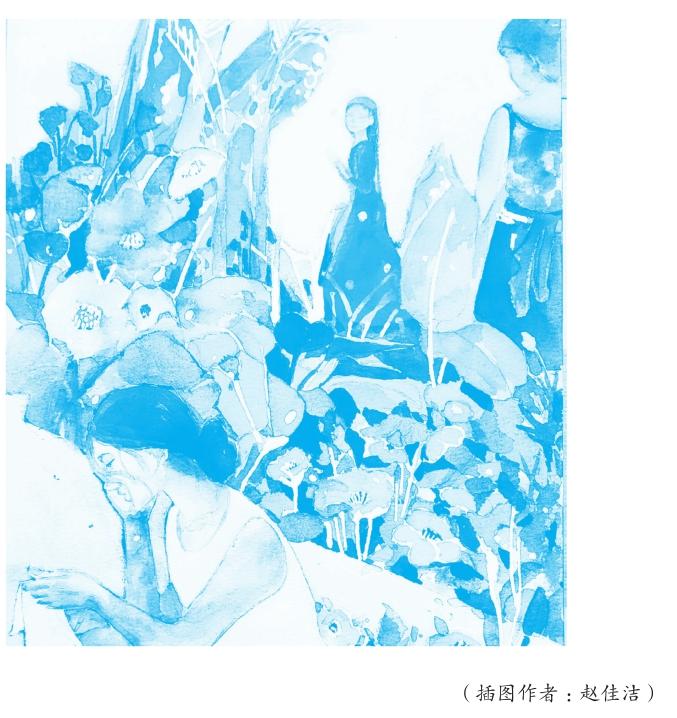
苏蔓坐在巷子口,穿着一件红色衣服,夕阳穿过远处的古宁寺塔,被柔和的塔尖划过一道暗伤,流水一样落在她散开的头发上。她在补一双鞋。她坐在修鞋匠旁边的小凳子上,神情专注,她没有看到我。我站在她身后不远处,背靠着墙壁,尽量把自己藏起来,紧张而欣喜地看着她。那年我七岁。墙壁很冷,秋风刮着我和落叶,一样地毫不留情。
那时的苏蔓,大概有十四五岁,她身材高挑,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夏天是一条长长的暗红色裙子,秋天是一件红色说不清面料的短风衣,头发也长长的,一弯腰就垂下来,让她看起来像个大姑娘了。她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画夹,从小巷子里穿过。墨绿的画夹在她的背上,长长的头发随风摆动,让她看起来也像一幅画。
那条巷子大概不到两米宽,青石板路,她走过的声音像远去的快板,咔咔咔,咔咔咔,欢快而生动。我跟在她身后,穿着软底布鞋,声音轻得自己都听不到。每次,我都跟她到巷子口,然后,假装系鞋带,把头深深地低下去。苏蔓习惯在巷子口拐弯的时候,回头看一眼。我跟了她那么多次,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我。她回头的样子很好看,长长的头发被风吹起,在半空中散开,飘到脸上,挡住她的眼睛,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穿过长发,绵绵地落在我的脸上。我不敢抬头,心里第一次因为小小的身不由己而落满悲伤。我不知道她要去哪里,听说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一心一意地学画画。说实话,我当时是很羡慕她的。每次她转弯后,我就跑回家,脱掉软底布鞋,换上破了洞的白球鞋,把布鞋藏在床底下。有好几次,我做好这些的时候,猛一抬头,发现母亲正隔着窗棂在看我,她目光很轻,很淡,无影无形。我就羞愧地低下头,等着她问我点什么,可是,她没有,一次都没有。这时,我就会觉得很对不起她。
苏蔓总是在黄昏的时候出去画画,我就在学校里先把作业写完,再读一会儿书,估计差不多了,就跑步绕路到小巷子里,坐在一块大青石上,看着夕阳从古宁寺塔的塔尖,一点点地坠落,半推半就地,含义深刻地坠落。每当咔咔咔的脚步声响起,我就弹跳起来,像个小矮人一样跟在苏蔓的身后,看她换的新鞋子,看她各种红色的衣服,还有那个永远不变的墨绿色画夹。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久,大概有一两年吧,直到有一天,我没有在小巷子里等到苏蔓,黄昏将小巷子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土黄色,古宁寺塔完全看不见了,我才心情低落地回到家。看见苏蔓居然坐在我的家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想到的,包括我的爸爸。
我家当时在村子最东头,院落还算整齐,屋子却只是盖好的空架子,连墙都还是黑乎乎的水泥。黯淡的灯光下,苏蔓坐在我爸爸面前,姿势有些僵硬,似乎坐了好久了。她看见我进来,转过头,笑了笑。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的笑让我很紧张,我快步走进里屋。母亲躺在床上,病了一样灰黄着脸。我说妈。她没动,也没有看我。我就在母亲身边坐下来,隔着墙壁,听苏蔓和父亲含糊的低语。他们似乎在商量着重要的事情,说一阵停一阵,说的时间短,停的时间长。过了好久,母亲明知故问地问我,你回来了?声音绵长而无助,仿佛我们跟全世界都断了联系,我们变得孤苦伶仃了。我点头,看着她,心突然变得沉重起来。屋子里没有开灯,有种心事重重的暗,窗外的风,抓到什么是什么似的猛烈地吹着,母亲又问,你吃饭了吗?我摇了摇头。她忘了她还没有做晚饭。
过了会儿,苏蔓走了,父亲走进来,叹息着说,她要去外面学画画,得很多钱……有钱你就给呗。母亲少有地顶了他一句,翻了下身,对着墙壁。我哪里有钱。父亲叹息着站了会儿,又出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把外祖母给她的玉手镯给了苏蔓。外祖母祖上是玉石世家,后来败落了,那只玉手镯是外祖母唯一的遗物。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苏蔓,那条小巷子也一别经年,等我再去的时候,已经是八年后了。
八年后,我上初三了,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每次走到村子口,还会听见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她们说,像,真像,越长越像。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刚从东北搬到古城的时候,村子里年长的妇人湊在一起说话,看到我,就会说,看,她俩长得多像,那眼睛,都那么大。那身条,都细细地。像她爸。我开始不知道她们在说谁,直到有一天,心直口快的桂花婶,指着我的鼻尖说,你呀,还有个姐姐,就住在巷子里。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我当时又惊讶又兴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眨着眼睛躲着桂花婶指点着我的手指,看见天空落下一朵无色的花。从那时起,我就每天去小巷子里看苏蔓。
我再去小巷子是因为苏蔓出嫁。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无论女儿走多远,身在何处,出嫁那天都要从娘家出门,这样一生都会平平安安,喜乐无边。按说,我家就是苏蔓的娘家,父亲也是这个意思,可是苏蔓坚决不同意。她说,她从小跟外婆生活,虽然外婆不在了,可老房子还在,她就从小巷子里出嫁。她没有邀请我们全家,包括父亲。但是父亲还是去了,他很尴尬,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么多年,他们之间早已生疏了。关于苏蔓,父亲知道的也寥寥,他们仅有的几次见面,苏蔓一次比一次冷淡,父亲给她钱她也不要,她也没去找她母亲。那她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我常常想。
我站在苏蔓外婆家大门口,向里面张望。屋子里亮着灯,没有声音,一片陈旧的寂静。还有两三天呢,到时候就热闹了。我想。心里突然一阵孤绝的怅然,我抬起头,又看到了古宁寺塔,黄昏中,灰灰的塔尖有种古兵器般的沉重和凝滞。
你进来吧。一个女孩子站在屋门口叫我。她不是苏蔓。
我进了院子,站在一棵葡萄树下,看着她。
给你的。女孩子转身从屋里拿出一样东西,苏蔓给你绣的。
你认识我?我惊讶地看着她。
认识苏蔓的人,都认识你。女孩子很大方,我是苏蔓的好朋友,她出去买东西了,你进来坐吧。
我没有进去坐,我站在那棵葡萄树下,打开一个塑料包装袋。
是一幅手工刺绣,绣的是我的样子。十五岁的我站在巷子里,背后是高高的塔尖,夕阳落在上面,像要永生一样明亮。
我的泪突然涌了出来。我低下头,将刺绣仔细地叠了起来,塞到包装袋里。
听说你也喜欢画画?女孩子问。
我的确是喜欢画画,我还获过市里的奖呢,可她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无法回答她,心里像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回一样地难过。我点了点头,抱着包装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没有去参加苏蔓的婚礼。
苏蔓嫁了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做生意的,到处乱跑,死了老婆有个儿子。这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怨恨,又不知道该怨谁,脾气一下子变得好大,老师和父母都归结为青春期。我想,那个背着画夹,翩翩走过小巷子,让黄昏瞬间深情起来的苏蔓,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没有问父亲,苏蔓到底嫁到了哪里,只知道是在本省的一个城市,不远也不近。上高中后,我似乎不再关心苏蔓,那些温暖如歌的儿时记忆,终究不会长久。我渐渐地忘了她。
我第一次真正面对苏蔓,是在她结婚多年后的一个夏天。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那天刮着大风,大得像整个世界都握在它的手里。苏蔓请我们全家在古城最好的饭店吃饭。这个消息是父亲告诉我的,我告诉母亲的。母亲犹豫了好久,她还是去了。她化了妆,穿上久远的连衣裙。我印象中她从来没有穿过裙子,这让她看起来别扭又陌生,像个高仿品。
苏蔓婚后就彻底离开了古城,她外祖母家的老房子也卖掉了。父亲对他这个女儿,好像也淡忘了。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朝小巷子里走去。母亲是从来不提的。有次他们吵架,母亲又控制不住地诉起前尘往事,说到气愤处,她说了句,那孩子从此跟我没半点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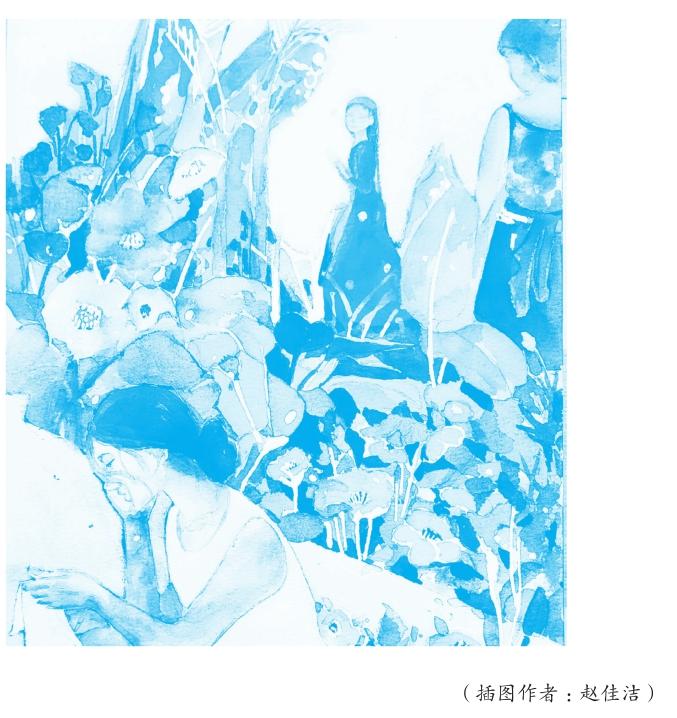
整个晚餐,似乎只有苏蔓一个人在张罗,她很用心地做着每一件事,而我們,就像一群木偶,连捧场都不会。盘子挪来挪去,她让我们吃这个,吃那个。又给每个人倒酒,说,都喝点,来,都喝一杯。
你妈妈当年就喜欢喝酒。你也一样。母亲沉沉地说。
苏蔓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她瘦弱的手腕白得涣散,我真担心酒瓶子会突然脱手,掉下来砸烂桌子。
酒倒好了,我们都没有动,酒杯透明得像没它事儿似的。杯子里的酒在灯光下,一圈圈摇晃,像布下的一个个迷局,没有人敢去碰。
苏蔓的身材真好,那么像一个人。我担心地看向母亲。她果然愠怒了,面色冰冷,眼皮下垂,往日的温柔再也不见了,整个人冷气森森。
我小声叫了声,妈!
你闭嘴!母亲毫不留情。母亲的心情我是懂的。因为苏蔓母亲的原因,她似乎不能看见苏蔓,一看见苏蔓,她就想起往事,锤炼着她的神经。我不敢再说话。
我看向苏蔓,她艰难地笑着,慢慢地坐下来,手里的酒瓶重得似乎拿不住。她把它放到一边,看着母亲。窗外狂风呼啸,每一次都像运了好久的气一样,使劲地拍打着玻璃窗。苏蔓的声音也昏黄暗淡,像断成一小截一小截。她说,阿姨,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您不要再生气了……
这是苏蔓跟母亲说的最长的一句话。母亲本不是狠心肠的人,听了后,自己先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她哭得很伤心,倾着身体,这让她看起来更加地无助。饭店的服务员以为出了什么事,跑步进来,看了看,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那顿饭,我们谁都没怎么吃。出来的时候,像踏进了荒漠,路两旁的树木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整个世界变成了简单的黑白两色。
苏蔓吃完饭就走了。她走后我才知道,她的家就在我工作的城市,一个东边,一个西边,我们隔着整个城市,万家灯火。
虽然是同一个城市,可我却从没想过要去找她,我甚至拒绝了父亲硬要塞给我的她的地址。
我毕业后一个人在临城工作,酸甜苦辣不足为外人道。特别是男友的突然离世,让我陷入滔滔的绝望和痛苦之中,眼前常常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就在我们全家和苏蔓吃过那顿饭后不久,我的男友,就因意外事故离开了我。无数的夜晚和黎明,当风吹过古老的枯水河,听着河水柔情略带苦涩的声音,我的泪就无法抑制地流下来。在寂静的夜里,我像背对着一个朝令夕改的梦,无法复原又无法自拔。这一刻,我就想到了苏蔓,觉得只有苏蔓才能救我,我就特别特别地想念她。
有时清晨醒来,睁开眼睛,想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我长得那么相像的人,我的心就会突然地踏实下来。我就坐起来,披一件衣服,找出苏蔓为我绣的画像。窗外慢慢透过一丝亮色,我渐渐感受到了苏蔓的温度,就像我身上的这件墨色风衣,有种萧萧的暖。
那段日子,我总是一个人在枯水河岸独坐,河岸有好多条长椅,散布各处,高高低低,我有时能坐一整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枯水河的水长长久久地流着,永恒极了。
那天黄昏,落日的余晖层层降落,没有尽头。我坐累了,想换个地方继续坐。深秋的风比祖父还苍老,吹得我的脸木木的,我整个人也跟着木木的。就在我站起身时,我看见了苏蔓。
苏蔓坐在离我十几米远的长椅上,在看一本书。她的侧影消瘦极了,比我上次见她的时候还瘦。头发很短,像刚刚才长出来。她真的不像苏蔓,可她确确实实是苏蔓。苏蔓看着我,起身向我走过来,我一点也没有吃惊,我听见自己的心在焦灼地呼喊,是她,是她……
苏蔓在我身边坐下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厚厚的。
你下班了?她淡淡地说。此刻,最后一缕霞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脸愈发白得寂寞。
下班了。我说。其实那天我根本没有上班。我连续上班一天一夜,然后休班一天。我把自己投入到巨大的忙碌里,然后又把自己抛在巨大的空虚里。
你也在这个城市?我说。
她很为难地笑了,是啊,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可我无法说出口。我说,你怎么也在这儿?这么远……
她冷笑一声,远吗?想去一个地方,在哪里都不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了会儿远处,又问她,你住哪儿?
医院。她淡淡地说。
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合上书,用手摸索着书粗糙的封面。
我看着她短短的头发,想起多年前小巷子里的苏蔓,心里一阵疼痛。
明天就出院了,小毛病。她平静地说。
深秋的风,吹得身后的白杨树叶子纷纷而落。
苏蔓没有穿红色的衣服,她穿了件深蓝色风衣,眉眼依然好看,只是你知我知一样遥远了很多。
我慢慢坐下来,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就要脱手而出一样地空。黄昏的风深情极了,我看见眼前开满了冥花,一点点地放大,布满了天空和大地,闪烁着一串串让人止步的冷光。突然,我看见了男友的眼睛,正满含忧伤地看着我。他不说话。我的泪汹涌而落,无声无息。
苏蔓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她把书放到一边,手托下巴,幽幽地看着河水。河水依然奔腾不息,晨昏定省,像藏着无数整装待发的生命。
你要坚强一点,别一天到晚坐在这儿,也不要再哭了,哭有什么用?她有些鄙夷地说。
我呆住了,黄昏中,她的脸苍凉得立体,下巴尖尖,像被雕琢过。
我一阵委屈,苏蔓站起身,准备走的样子。别哭了!她说。我抬头,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脸。她三十五岁了,比我大了八岁。除了瘦,她还是很年轻。她几乎是我们苏家女儿中最漂亮的。她表情平淡,看着远处,盛大而深情地长长叹息一声。
我说,你要走了?
她点头,看向河面。
团团雾气从水面飘过来,像移动的黑色花海。
我说,那你走吧。
她突然露出一丝惊喜,就像一切都还来得及的那种惊喜,她说,你看你哭得都有白头发了,她居高临下地指着我的头,还哭!
我怀疑又有些怨恨地看着她。
苏蔓又坐了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給!
我一看是个地址,显然是写过好久了,皱巴巴的。我呆呆地看着那几个字。一阵风过,我的手指一松,那张纸像被另一只手给抽了去,飞到了半空中。它飞快地旋转着,起落着,向远处飘去。
啊?她急促地叫了一声,表情惊愕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她,我出神地看着那张纸片,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感到苏蔓的整个身体都在慢慢地变冷,我看了她一眼,她不知道,那个地址我已经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我们谁都不说话了。听着枯叶在脚下翻转,看着河面上飞过的大鸟,叫不出名字,也看不太清楚,只看见空中不时划过一道道弧线,冷清清落在此岸或彼岸。
暮色苍茫的时候,苏蔓走了,她走的时候我正在低头看手机,等我抬头时,她已经走到那堆鹅卵石旁边了,那堆小石头是小孩子们自发收集起来的,洁净得仿佛被上帝洗过。苏蔓在鹅卵石前停了停,又慢慢地走了。
接下来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
可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就是那么地巧合。
第二天下班,我没有去枯水河岸独坐。朋友打电话说,她做了好吃的,让我去她家坐坐。她家在东边,尽管很远,我还是坐上公交车去了。
公交路过一居民小区时,我看见小区门口围着好些人,我以为出事了,再一看又不像,像是有人在吵架。恰好公交到了站牌,我一抬头,看见小区的名字,心猛地收缩了下,站起身,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
我在人群背后,一眼就看见了苏蔓。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苏蔓。只是此刻,阳光还很耀眼,苏蔓的脸白得让人心生凉意。她拉着个拉杆箱,手里提着个大大的塑料袋,有个男青年站在她面前,表情冷漠,眼睛歪着,像是刚刚被人打了。旁边有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场面乱糟糟的。
男青年说,要不是你,我爸也不会死得那么早。说完,四下里看,像在寻找证人。没人理睬他,他又转向苏蔓,他活着的时候,给了你多少钱?这套房子怎么说也不能再给你了,它是我的,你无权居住。他说得理直气壮,低头看着苏蔓。他长得很高,比苏蔓还高出半个头。
我大吃一惊,原来苏蔓嫁的男人已经死了。那个男人我只见过一次,现在早就忘了长什么样儿了。我心里突然抑制不住地难过,天高地广、水深火热地难过。不是因为那个男人,而是苏蔓。苏蔓木木地站着,也不争辩,她的嘴唇干裂,眼神涩涩,肯定是连家门都没有进去。
这时,一位老太太走上前,拉住苏蔓的手,走,进去。有说理的地方。又指着男青年骂道,你有没有良心,你爸病了那么多年,是谁一天天伺候他?你跑哪去了,啊?你个龟孙!
男青年看了她一眼,没理睬,继续用眼神驱赶着苏蔓。
苏蔓一脸平静,站在那里,像在等待一个人,或等待一段年华。风吹起她的风衣,让人想起遥远的从前。我又想起那个背着画夹,一头长发,穿巷而过的苏蔓。我拨开人群,正要冲过去,好好教训下这个混蛋。突然,我看到了苏蔓的眼神,冰冷,倔强,孤傲,还——脆弱。我停了下来,手脚冰冷,有种后怕的恐惧。苏蔓又站了会儿,转身,拎着她所有的家当走了。
别走啊!有个女人在后面叫她。她很着急,还跺了下脚。
苏蔓回头,眼神很轻,像是在安慰她。
一阵大风呼啸而过。
这里的秋天就是这样,风大得能把人刮倒。我把外套卷起来挡着头部,听见那个鬼影子一样的男青年说,我不怕,总会有人帮我的。
帮你?你以为老天爷是你朋友啊?你个龟孙……又有人骂道。
我没有去找朋友,我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家。我给苏蔓发微信,我说,你出院了吗?来我这里住几天吧。我将卧室整理好,把几天没洗的衣服都找出来,放入洗衣机。把床单被罩枕头套统统换成新的。我一腔悲愤地做着这一切。这个租来的小屋,里外两间,外面还有一个小床,我也铺上了新床单。我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最后,把苏蔓给我绣的画像找了出来,平铺在书桌上,心突然变得无比伤感。多少的日子都过去了,记忆还是那样的血肉丰满,我也老了,如今都有了白头发。我不敢再看下去,又将画像收了起来。天完全黑了,满屋子都是拥挤的黑暗,苏蔓还是没有回复我。我给她打电话,电话响了会儿,就挂了。又打,还是挂了。我怀疑苏蔓是不是看到了我,她不肯见我。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好久都没有做过梦了。
梦里,我站到了悬崖边上,壁立千仞,我无路可走。
梦里,苏蔓依然明媚,像一朵不老的花。她在跟我道别,很郑重地,带着微笑,我走了。我说,你去哪里呢?她抬头看了看天空,说,去个好地方。我说,跟我回家吧。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反正说完了我才感觉到,这是我们家从来都不敢提及的话题。我母亲整个一生都在为另一个女人纠结,她无法改变又无法释怀。
苏蔓摇头,很郑重很朴实地说,谢谢你!我说,你不要难过。苏蔓又摇头,不难过。又说,你要好好的,不要再哭了。
梦里,我和苏蔓说了好多的话。
梦的最后,夕阳如火,有种残酷的热烈。苏蔓走了,我又回到了枯水河边。无数的落叶簇拥在河面上,互相取暖的样子。
我很难过,这样美好的感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梦里?
此后,我又好多年没有见过苏蔓。这好多年,我换了工作、住处,却依然喜欢在枯水河岸独坐。我告别了那些与机器相伴,恐怖又寒冷的女工生活,通过考试,进了一家事业单位。我离开了工厂,并不是因为厌倦了那里的生活,而是因为一件事。
那天我值夜班,厂里丢了几个重要备件,我成了怀疑对象,因为我调整机器,也到备件库里找过东西。备件库就在我们的休息室,平时我们都是可以去的。领导不相信我,几次找我谈话,明说暗指,我说我要那有什么用,还不如拿块擦机布,回家当抹布用。领导嘿嘿一笑,你没用,不一定别人就没用。他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我没再说什么,收拾收拾东西,写了个辞职报告,斩钉截铁地离开了。多年后,每在枯水河岸独坐,我都会想起,感觉是那样地遥远。无数的阴冷黄昏,我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听河水春去秋来地流着,就像听着自己的生命在缓缓地流淌。
我的生命里,也曾有过重要的人,我的一个同事,和我是同一个部门的,我们谈了两年,后来,他通过考试被遴选走了。他很高大,有种残冬一样忧郁又清冷的气质,很吸引人。他走的那天,还告诉我,会很快和我结婚,可是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我。他喜欢上了别人。我常常想,在他决定离开我的那一刻,是否会想起,是我替他照顾住院的母亲,他才有时间安心备考的。我同样没说什么。
这好多年,我用了各种方式,都没能联系上苏蔓。父亲也一样,他一直在打听这个女儿的消息。他苍老得很快。直到今年五月,我去都灵山旅游,才再一次见到苏蔓。
都灵山在临城西北,是个很偏远的小景区,从去年才开始收门票,原来也有人来,不是游人,都是些上香的老人。山上庙宇很多,可供求的菩萨也很多。
和每个景区一样,山下都免不了有卖山货的。这里的山货主要是山核桃,很小,但皮薄,用手一捏就碎,很多游人买一包走着当零食吃。在这些众多卖山货的女人中,我突然听到了苏蔓的声音。她的声音和别人的声音不同,像被岁月漂洗过,有种浓郁的苍凉。
我站住了,慢慢地回头,我怕我回头快了,这个声音就会消失不见。
真的是苏蔓。可她太不像苏蔓了。
她皮肤粗糙,白发累累,特别是她的眼神,苍老而空无一物,有种让人走神的寂寞,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往。她穿着简单的衣服,亚麻色,在一群女人中依然与众不同,是的,苏蔓从不潦草。黄昏来了,游客们陆续下山,苏蔓忙了起来。她平静淡然地忙着,时间在她的手里缓缓地慢了下来。我走到她身边,蹲下身,苏蔓看到了我,停了下来,像一脚踏空一样颤栗了一下。你来了?她说。声音淡淡,好像我们经常见面一样。我只觉得喉咙紧痛,说不出话来,我点了下头,拿起个山核桃,用手一捏,剥开吃了。
好吃吗?她问我。
好吃。我干涩地说。
苏蔓很高兴,拿了个塑料袋开始给我装山核桃,边装边说,这个好吃,适合你,你太瘦了……
我低头,很冷淡地说,你一直在这里吗?这么多年……
苏蔓的手停了下来,她顿了顿,说,这儿挺好的。
我扭过头去,看着暮色下沉如暗语的大山,心如荒冢。
你还好吧?苏蔓给我装好核桃,塞到我的双肩包里。
我点点头,告诉她,今晚,我就住在山下的农家院里,就是那个唯一的红房子那家。说完,我就站起身走了。我转上小路,确信她看不到我了,我站定,回头,没有顾客了,苏蔓坐了下来,两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那么孤独那么安静地坐着。
我看不见她的白发了。
四周突然万事皆空般地静。
我抬起头,望着天空,天地缄默,青山渐隐,我想,这天地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唯有希望——
【作者簡介】苏薇,河南安阳人。作品散见于《清明》 《特区文学》 《湖南文学》 《短篇小说》《草原》 《都市》 《雪莲》 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