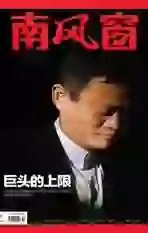反垄断法新规释放信号
2020-12-14何治民
何治民

今年双十一交易额再创新高,但依旧没能阻挡互联网巨头企业股价下跌。当天,美团、阿里、京东均跌超9%,腾讯跌超7%。
在此之前,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反垄断指南”)。
作为《反垄断法》的补充,这份指南参照《反垄断法》中判定垄断行为的基本框架,将更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专属商业行为和指标纳入,实操性强,堪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量身定做”。
这份指南在平台经济双十一狂欢前夕发布,显然不是偶然,用意明显,也宣告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包容审慎”式的宽松监管一去不复返。
谁将以身试法?
互联网平台企业,如阿里、腾讯、美团等等,平台化的运营方式,天然具有规模效应,往往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中国10强电商》榜单显示,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三家企业合计占中国线上零售额的90%,占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2%。
《反垄断法》2008年就有了,但快12年过去了,互联网行业依旧没有一起反垄断案例,这背后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以往反垄断职能分散在商务部、发改委、工商局三个部门的分割,也有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包容审慎”监管的惯性,但症结在于,《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认定,无法适应平台经济领域的商业模式,执法机构很难以此发起它们的反垄断调查。
如今,风向变了。
今年1月,《反垄断法》迎来第一次修订,明确将互联网经营者纳入监管范围。此次反垄断指南,更是开门见山地明确了平台就是指“互联网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指南并没有限定是指电商平台,意味着BATJ、TMD等各类购物、出行、社交、游戏领域的互联网巨头,都可能适用。
据《反垄断法》,垄断行为有四种,签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很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
市场热议的“二选一”作为被明确认定为“限定交易”,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
现实中,互联网巨头惯用的“二选一”等平台规则、“大数据杀熟”的營销、通过控制稀缺的数据资源实现的限制竞争、用协议控制(VIE)在国内的开展的并购等等,这些做法或造成消费者福利受损,或挤压了中小创新企业的成长空间,且都已为平台获得垄断收益,实际上已达到垄断效果。但根据既有的法律,反垄断机构的执法往往无充足的依据。
如今,反垄断指南根据平台经济的特点,对上述前三种垄断行为,细化了适合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的认定条件,将上述已实际产生垄断行为的方式纳入其中,换句话说,互联网巨头们触发反垄断审查的阈值降低。
先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般而言,要认定某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一步需认定它服务的相关市场,这一直是各国在反垄断调查时遇到的首要难题,当对象是跨产品跨市场的互联网平台而言,对相关市场的认定也更艰难。
此份指南明确提出,平台经济的相关市场界定,可以不仅仅局限平台服务的相关商品市场,应考虑它们的网络效应,并“对平台功能、商业模式、用户群体、多边市场、线下交易等因素进行需求替代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指南甚至对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特定个案开“小灶”,“可以不界定相关市场,直接认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这样对相关市场的界定就容易一些了。
相关市场界定后,界定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是,认定企业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
一般而言,市场份额是基本的参照。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指南,在考察平台的市场份额时,将平台的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用户数、点击量、使用时长等指标也都纳入,丰富了考察维度,让执法依据更具体,操作性提高。
确定平台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后,如何裁定平台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
市场热议的“二选一”作为被明确认定为“限定交易”,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同时,互联巨头惯用的“大数据杀熟”“不公平价格行为”“低于成本销售”等行为也有相应的细则来裁定,均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可能触发反垄断调查。
这些都是互联网巨头惯用的平台运营手段,杀伤力不小,或将带来互联网巨头运营方式变革。
数据和算法纳入垄断认定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垄断和创新有着天然的联系,垄断是激励创新的动力,如果没有垄断利润,就没有企业家愿意创新,这意味着,对于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垄断行为,反垄断应该谨慎。
这也是政府对包容审慎监管的初心。反垄断法起草者之一、反垄断专家王晓晔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审慎包容也是对的,但不代表“不作为”和“放任”,对于一个新东西,还没看懂就去执法,对经济发展不利。然而,近几年互联网发展,行业内限制竞争的问题越发明显,但仍未见到有关部门认真调查。
从社会发展或大众的角度,是否反垄断有更通俗的标准,即企业的商业行为是否导致消费者福利受损、是否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传统经济模式,判断影响消费者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价格。而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下,这个指标似乎不太起作用。
平台经济模式往往是流量思维模式,最终将流量变现,在这个过程,用烧钱补贴大战来获得流量往往造成消费者获得较低的价格。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此时消费者受损的福利不再是显性的价格,而是被遏制的多元选择权,如今,消费者线上生活的入口,几乎都会互联网巨头们把持。
流量思维背后的核心是数据以及对数据的运用。在这些互联网平台上,消费者享受较低的价格,却让渡了自身的身份信息、交易、出行等各类数据。
如果说互联网巨头的发家,是抓住了中国人口红利和技术变革的机遇,那么,通过将平台化运营获得的庞大私有数据变现,才造就了它们如今在市场上的垄断格局。而平台获得的各类数据,并在生态内实现数据共享才是它們构建垄断商业生态的逻辑,也是专属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新特征。
重点来了,反垄断指南在考察上述两种垄断行为时,把互联网企业平台对数据的使用和控制都考虑在内。
具体来说,平台具备对关键性、稀缺性资源拥有独占权利以及该独占权利持续时间,平台掌握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对数据接口的控制能力将会被认为是互联网平台对市场的控制力,这就是平台经营者集中的一种表现,可能触发反垄断审查。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组后,原本分散在商务部、发改委以及工商局多部门的反垄断职责被统一归口到新设立的市场监管总局下的反垄断局,反垄断执法更集中、高效。
同时,对垄断协议的考察也不仅局限在书面的协议,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数据和算法等实际达成的垄断协议也算。
进入互联网下半场,并购是互联网平台企业获得垄断地位的方式,在201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领域曾掀起一场并购大潮,也催生出美团、滴滴、携程、58同城等一批新兴的互联网巨头。
但这类并购并没有触发反垄断审查,原因之一便是这些互联网巨头普遍采用协议控制(VIE)架构,钻了《反垄断法》对境外企业并购模糊表达的漏洞。商务部对涉及VIE 架构在国内开展的合并,也都是包容审慎态度。
如今,反垄断指南明确,协议控制(VIE)公司境内并购也属于反垄断审查的范围,未来,发起并购前,互联网巨头要事先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这会让它们在并购时有更多监管风险权衡,靠并购来增强垄断势力将不再是捷径。
不难看出,针对前三类垄断行为,指南针对互联网巨头都有较细化的执法条件,也堵住了过往因模糊表达而造成的监管漏洞,为未来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方向。
监管正起变化
疫情之下,以互联网平台驱动的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此时出台这个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指南,又有何深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反垄断指南并非心血来潮。近年来,反垄断被反复提及,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也开始成为新趋势。
这一趋势有两大政策背景。
其一,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组后,原本分散在商务部、发改委以及工商局多部门的反垄断职责被统一归口到新设立的市场监管总局下的反垄断局,反垄断执法更集中、高效。
近段时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除了发布反垄断指南外,还发布《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监管互联网平台交易的文件。
其二,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的修订、《电子商务法》的出台,逐步完善了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依据。例如,今年1月《反垄断法》修订,就将互联网领域纳入反垄断范畴。
此外,互联网领域“强者恒强”局面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开始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10月31日,金融委曾发声,“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过去两个月,原财政部长楼继伟、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各地公众场合发言称,不约而同表达了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的担忧。
如周小川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式上直言,“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控大量数据和市场份额,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
的确,如今互联网巨头,凭借技术、数据和资本优势,逐渐投行化,构建起各自的垄断王国,极大压缩了其他创新或创业公司的成长空间。
反垄断指南的发布,在释放监管态度的同时,必将敦促互联网巨头主动合规,并倒逼它们在存量竞争时代,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改进、服务提升和模式创新,而不是通过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来谋取利润。
如周小川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式上直言,“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控大量数据和市场份额,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
同时,通过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也能降低创业竞争的成本和门槛,为初创企业提供发展空间,从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动力和活力。
此外,如今全球都在加大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审查,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四大科技巨头深陷其中,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统计,谷歌面临27起、亚马逊和苹果面临22起、Facebook面临13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指南的发布,也将为这些互联网巨头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提前做好必要的合规准备。
可以想象,未来互联网巨头,将面临来自金融监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多方监管压力,既然监管无处不在,那么主动拥抱合规,将反垄断规则培训融入平台的日常运营、加强数据使用安全,或许更能抢占新一轮发展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