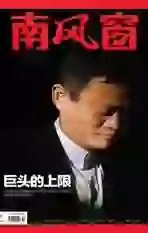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融合深化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2020-12-14
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融合深化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郭凯明、黄静萍
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20年第11期
一方面,中国正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一过程需要不断提高产业附加值比重。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融合深化,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水平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正不断提高,许多领域供不应求、依赖进口现象正得到扭转,这一过程需要不断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融合深化,也有助于提高服务业水平和生产率。

本文通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动因,为中国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具体的,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多部门嵌套的产业结构转型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提出,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价格效应会产生使货物和服务生产部门投入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所占比重变化的集约边际影响,以及使货物和服务生产部门产出比重变化的广延边际影响。收入效应只会产生使货物和服务生产部门产出比重变化的广延边际影响。集约边际影响方向取决于货物和服务生产部门内部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广延边际影响方向取决于货物和服务生产部门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的差别、货物和服务的替代弹性以及货物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本文详细展示了这些经济机制和前提条件。
之后本文将理论模型应用于评估中国、日本和韩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中国和韩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但提高了日本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日本和韩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但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其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日本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但提高了中国和韩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但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提高货物生产部门产业融合程度,而且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产出增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会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但是会提高服务生产部门产业融合程度,并显著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产出增长。
本文发展了结构转型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领域的定量研究,也为中国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两点政策启示。首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部结构升级,而且还应以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重点,从产业相融相长的宏观全局视角统筹产业转型升级。由于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货物生产过程中呈现出高度的互补性,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能够在提高产出和福利水平的同时,有效拉动貨物生产过程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促进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建议政府立足于生产技术的这一现实特征,加大对制造业投资和研发的支持力度,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升级和传统制造业转型,以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重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其次,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还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提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这是因为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不但从产业来源构成上高度依赖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信息技术、金融和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投入,鲜明地体现出产业深度融合特征;而且能够直接推动新一代通用技术发展,增强先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动能,从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因此,建议政府在中长期规划中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发展目标和落实措施,把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向新型基础设施适度倾斜,促进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的统筹与融合。
中国私营企业主多代流动的分源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 吕鹏,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范晓光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毋庸置疑,多代流动效应可能因为社会群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可能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譬如,财富的多代传承可能比职业要更为持久。本文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主这个精英群体而言,超越两代的地位传承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我们提供了有关此问题的一个基础证据。本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确实部分地存在第一代对第三代的直接效应,尤其在第一代为体制外精英的家庭中更强。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分源模式”,表示这种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依据第一代的体制和职业位置(源)的差别而有所分化。多代流动并非不是马尔科夫效应就是非马尔科夫效应的绝对现象。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我们曾经在一篇有关代际流动的论文中论述过精英代际流动的部门分割现象。这项研究表明,这种部门分割在三代流动中也依然存在。精英继承的路径分割表明,市场经营者的第三代的再生产具有明显的马尔科夫效应。相应的“,草根逆袭”也存在体制分割:体制内普通劳动者的子代和孙代在成为党政干部上没有劣势,但在成为市场管理者时存在明显劣势;体制外草根的子代和孙代在成为党政干部上具有明显劣势,但在成为市场管理者上没有明显劣势。

本研究支持了多代职业地位的相关性,但没有最终回答“如何相关”这样的问题。第一代对第三代的影响,是不是要通过第二代的“调节”才能发挥影响?这既是一个方法上的挑战,同时可能更是一个情境性的经验问题。尽管如此,基于既有文献,我们仍然试图对多代流动效应的机制提出几点理论解释。
首先,最直白的机制就是直接的传承,比如大规模财产的传承或投资。不过对于当下的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说,这可能更多的是发生在“父—子”两代之间的故事。在微观层面,除一部分关注诸如家庭结构、性别、权力和人力资本这样的机制,多数研究所讨论的机制都涉及文化,只不过概念化和测量方式有所不同。事实上,即便对于精英地位来说,代际优势的传递也不是“乍一看就可以保证的”,教育依然是维系代际优势的重要中介机制。
同时,我们也并不认为体制位置和职业地位之间的多代相关就必定意味着一种结构决定论。事实上,第三代在职业选择上更大的自由度为解释“第一代—第三代”的相关性增加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子辈并不是木偶人,并不一定遵循着“子承父业”的“绝对继承模式”,即使最后接班,也有可能是一种自我的文化生产的结果而不一定就来自长辈的压力或影响。尤其是社会选择自由度的增加和父辈威权文化的降低,为职业代际相关性的解读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当然,时期效应也很重要。索罗金早在上世纪前期就曾敏锐地指出,优势地位在多代间传承的程度可能没有变化,但这种传承发生的机制却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第一代企业家与其父辈之间的代际流动大多发生在改革开放早期的“第二次大转型”时期;第一代企业家与第二代企业家之间的代际流动则要平缓得多。
从收入、体制位置或分层框架中计算而来的流动率对人们有很直观的吸引力,但如果脱离了对个体复杂的生活背景的思考,未能充分估计环境制约个体成就的程度,就会产生某种误导。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影响并不像估算出来的净效应那么简单直接。多代流动研究的实质是要我们将对社会流动的考察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元素上,从核心家庭到扩展家庭,到家族、宗族乃至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职业地位分布的结构性转变,最终关乎的是社会闭合的程度以及阶级边界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