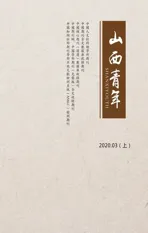文化的批评与重建:重读《四世同堂》
2020-12-08付丽洁
付丽洁
聊城大学季羡林学院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近几年的研究学者更喜欢称老舍是一位“文化型作家”[1]这在《四世同堂》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正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去构建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每一类人物都是一个文化符号的代表,他们共同建构了老舍的文化观。
一、文化审视——东西文化观
审视《四世同堂》实际上是对老舍笔下的东西方文化观念的探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不仅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还刻画了不少外国人,其中最为鲜活的就是英国人——福善先生,它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是一个“中国化了的英国人”[2]。既然是“中国化了的英国人”,在他身上必然保留了某些英国人的本质特征又沾染了些中国人的习气。他仰慕中国文化,痛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但他不曾有一刻忘记他代表的是英国人的立场。“他为中国人着急,也为英国人着急,但是,他又以为英国到底是英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肯承认中国与英国一同立在危险地位”[3]。这其中包含着富善先生作为一个英国人满满的西方民族主义和侵略扩张的思想,可见富善先生骨子里的英国人的文化内涵不曾改变。老舍在富善先生身上所倾注的情感恰恰体现在这里,他是本着一种东西方文化开放的姿态去展现东西方的文化观念的。老舍对于外来的文化观念绝非全盘接受,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观念有一种天然的自信。与此同时他通过富善先生来衬托中国人文化中的懦弱与卑微,以及一切在老舍看来应该摒弃的文化糟粕,但是老舍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点是坚持本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他力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能处在同一地位,平等交流。即“老舍创作所建构起的中华民族主体性实质上具备了与其他民族主体间共在的和谐共存,平等对话的意识”[4]。这是老舍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一个显著地特点,在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文化批判——新、老市民形象的解读
在《四世同堂》中有两类鲜活的人物形象,一类是以祁老太爷和祁瑞宣为代表的老派市民,另一类则是以祁瑞丰为代表的新派市民。老派市民是老舍笔下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他们是在民族矛盾日益突出、中华儿女受苦受难的背景下存在于人群中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代表。祁老太爷是“四世同堂”的第一代,他竭尽全力维系着“四世同堂”的光辉景象,所以当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时,他依旧认为只要备下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可以渡过难关,这是一种固执封闭的落后思想,也是植根于中国人思想深处的文化糟粕。而作为“四世同堂”第三代的长房长孙祁瑞宣继承了爷爷老一辈的思想,但不同之处在于他身上流着新时代的新鲜血液,他认识到了时代的变革,他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但却被所谓的“四世同堂”牵制住了脚步,沦落成与爷爷一样的人。但是他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与复杂性,这也说明了虽然同为老派市民但是不可否认老派市民也是在不断进步的,由此可见老舍对社会与文化寄予了深切的期盼。
有人称老舍是一位“文化型作家”,究其缘由主要是在老舍的作品中蕴含着老舍独特的文化观。虽然同为老派市民,但是从祁老太爷到祁瑞宣中间有一个明显的过渡,这说明老舍在本质上是认同传统文化的,虽然对于固有的文化糟粕嗤之以鼻,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信心。
从对老派市民的解读中,老舍流露出了对于消极的传统文化与思想的批判,但相较于对新派市民的刻画这种情感是较为缓和的。老舍对于像祁瑞丰这样的“新派”人物是毫不留情的,他们是在中国文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次品”,他们穷形尽相想要趁着国家大乱,争做时代的“弄潮儿”,将崇洋媚外的姿态展现到了极致,在对新派市民刻画中包含着老舍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老舍看来西方文化也并非无坚不摧的,他也有着内在的缺陷,特定的文化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土壤的,移植到一片新的土地上必然会“水土不服”,除此之外文化是成体系的,仅仅学习外来文化的表象必然不会成功,所以祁瑞丰的下场是悲惨的。从这里也能看出老舍对于外来文化绝非奉为圭臬,相较于对于固守传统文化的老派市民的批判,对于盲目学习西方文化的新派市民的嘲讽显得毫不逊色,这与老舍身份的多重性以及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是分不开的。
三、文化重建——对理想市民的憧憬
老舍是一位有始有终的作家,他不曾辜负其“文化型作家”的身份,在对原有的文化进行了批判之后,仍不忘对文化建构提出新的设想。《四世同堂》中的理想市民形象就包含着老舍对于文化重建的设想。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了像钱默吟、瑞全等一批理想市民,钱默吟本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诗人,但是他在遭遇并且目睹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凌之后,他比小胡同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觉醒的早,他不动声色将诗人的身份化作战士的伪装,投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中,还有一个人老舍着墨不多,但他在老舍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容小觑,老舍并没有对他进行过多的限制,实际上是为了让他在新的社会中自由的探索,对于他的发展老舍像读者一样的期待,这个人就是瑞全,他是唯一一个冲出“四世同堂”的天地,投身革命的新时代青年,在他身上老舍寄予了无限的可能。可见老舍对于理想市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文化重建的过程更是需要不断探索的,所以老舍在此处实际上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在《四世同堂》中,不仅有像钱默吟、瑞全一样高大的男性形象,还有不少是“柔弱”的女性形象,像韵梅、高第等等,他们不比男性逊色丝毫。韵梅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孝敬老人,照顾孩子,勤俭持家,对于“知识分子”式的丈夫,她选择支持与相信。当家庭陷于危难之际,她也会挺身而出,去“挤粮食”,即使她的内心是无比恐惧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女性并没有为国家做什么突出的贡献,但是在老舍看来这样贤惠的中国传统妇女也是值得歌颂的。当然这与老舍自身的文化观念是密不可分的,老舍对于理想女性的解读是传统的。不难看出,相较于对男性形象大胆的独到见解,对于女性的刻画,老舍就显得“蹑手蹑脚”,仿佛与女性刻意保持一段距离,虽然老舍生活在新文化下的中国社会,但他笔下的许多女性形象却缺乏气息。现实生活中的老舍亦是如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老舍将传统的女性作为理想的市民形象,而没有去塑造新的新时代女性,这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
不论是对于小说地域的横向分析还是对于小说内部人物的纵向解读,老舍对于文化的审视、批评与重建都贯穿于小说《四世同堂》的始终,小说人物的文化符号表征性与老舍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从文化的角度重读《四世同堂》不失为一种解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