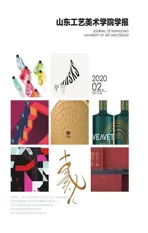浅论文学图像论视域下中国画诗性精神的建构
2020-12-06
从图像的角度看,中国画依靠意境的同构使图像突破了媒介的限制达到了与诗歌同一,获得和诗歌一样表达主体情感与心中之“意”的功能。从诗歌的角度看,中国画还以书法为纽带和桥梁直接把题画诗置入画面,从内在的意境到外在的形式都和绘画图像互相交融补充,成为画面的重要图符和画面意境的锚定者。而且题画诗甚至是高于绘画图像的,因为当图像与诗歌不能相互印证或者对图像的想象、期待有很大不确定性时,往往会按照题画诗重新赋予图像以新的意义。中国画在语言符号对图像符号的长期渗透、笼罩并左右中形成的这种诗性精神是中国画的灵魂。它既表现为水墨语言的诗意性表达,更表现为精神层面艺术家胸中块垒、主观感情、胸怀气度、品格理想等的抒发和表达。在当下被机械图像包围的视觉中心主义时代,重新反思和回归经典艺术最耐人寻味和最富文化内涵的部分,对于回答好中国画的民族化与全球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等时代问题,对于提高艺术学界之专业素养,甚至提升整个社会的视觉教养,皆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画;诗性精神;图像;诗歌
当下这个图像时代或者说视觉时代、读图时代,所谓图像其实更多是指视像、影像等利用光电技术或数字处理技术等科技手段制作出来的机械图像或者说数字图像。绘画虽然也属古老图像之一种,但在图像时代却受到了机械图像、数字图像的巨大的冲击与挤压,或者趋于机械图像,与影像、视像等复制性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混淆。或者为了背离机械图像而标新立异越来越不像绘画。中国画曾经拥有的诗性精神不再,而机械复制艺术却越来越有诗情画意般的美感,成为新的艺术门类。绘画在图像时代到底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不被淹没或取代?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拨开机械图像的重重笼罩,找到绘画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回答好中国画的民族化与全球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等时代问题的基础。从理论上看更是建构文学图像论的必要一环,从现实意义上对于提高艺术学界之专业素养,甚至提升整个社会的视觉教养,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文学与图像作为承载人类文明的两大载体,一直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正如米歇尔所说:“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1]所以讲绘画不可避免地要讲文学对图像的影响,讲文学和图像的关系,即诗画关系。再加上中国画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孕育起来的,可是西方绘画与图像时代的双重合围,使很多人忘记了中国画应该具有的传统文化底蕴,忘记了所谓的现代性应该是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风貌。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有必要追本溯源,重新回到中国画依托的传统文化中去了解中国画曾经的诗画互文的历史,体悟中国画曾经拥有的诗意情怀和诗性精神,以期在图像爆炸的时代帮助建构中国画的价值理想和精神高度。
1.意境:绘画图像获得诗性精神的内在路径
不同于西方的诗画异质论,在中国更强调诗画同源、诗画一律,更强调文学与图像的共通性和共生性。宋代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次韵吴传正枯木歌》)元代杨维桢说:“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故其道无二致也。” (《东维子集》卷十一《无声诗意序》)意即苏轼在欣赏王维等人的诗画时注重的不是诗、画两种艺术类型的异质,而是意识到诗画都是文人士大夫精神追求、心灵栖居的载体,二者均贯注着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精神,在“与道为一”即“外在自然宇宙生命与人的内在精神生命融为一体”[2]的境界中融合相通。也就是说主体的情感和生命精神作为艺术的本体打通了各类艺术的局限,诗画两种不同的艺术最终在“与道为一”的高度上达到了艺术构思、审美追求与创作方法等的“一律”即共性。这是绘画走向诗歌获得诗性精神的重要理论依据。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本来是并列的,无高下之分。但因为中国古代诗歌居于正统地位,又发展繁荣,所以很多其他的艺术样式都会不自觉地向诗歌靠拢,借助诗歌的成就、地位以及话语权来丰富、发展和提高自己,甚至获得社会认同。具体到诗画关系上,既然诗画是一律的,所以绘画慢慢地也被纳入了诗歌的评判体系,成了“诗之余”。所谓“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在文学的改造下图像脱胎换骨,开始突破媒介的差异有了语言的功能和属性,不再拘泥于造型的写实、外在的形似,而是开始追求以形写神,更强调像诗歌一样表达主体的情感和精神追求。李公麟说“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宣和画谱》)。绘画如同写诗,目的都是“吟咏性情”。这显然超越了一般画工执着于“技”与“象”的层面,而是以“意”入画,所谓“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苏轼《书朱象先画后》),最终绘画从写实被提高到了写意的层面。当然这个“意”指的是文人士大夫的襟怀抱负、高雅情怀和审美趣味等,如苏轼评价燕肃的山水画“浑然天成,烂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跋蒲传正燕公山水》),肯定其绘画摆脱了画工的法度,获得了诗人的清丽。也就是说绘画不能停留在画工仅仅追求“象”的层面,而是要有文人的“意”,要在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精神情感等的基础上和诗歌一样传达诗意的生存情怀,引发欣赏者对宇宙生命本体的感悟。而由外在的画工技法到内在的文人情怀的表达,由客观的物象、人体的描绘到主观心灵意趣的传达,正是绘画对于自身作为造型艺术的超越,也是运用语言文字符号的文学对运用图像符号的绘画的改造和提升。从此对客观物象、人体等的描摹只是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浅层追求,由“象”引申进入的“意”的层面才是其终极审美追求。
比如宋徽宗画院考试时“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邓椿《画继》卷一)宋徽宗录取的第一名,其画境不在表现“野水”“孤舟”“乱山”“古寺”等外在物象,而是意在突出“尽日”“无人”的悠闲以及“藏”带给人的韵味和回想。这显然不仅仅是考画家的造型能力,更是看他们是否具备通过外在物象的描摹创造诗境的能力。还有米芾在解读苏轼的绘画时也不仅仅停留在外在物象上,他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画史》) 这也是由“象”的层面进入“意”的层面,意识到虬曲怪奇的枯木是苏轼自身颠沛流离、盘旋郁结的象征。当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融入了文人的精神意趣与审美理想,成了文人抱负、遭遇等人生经历的写照,成了文人胸襟、修养、格调等理想人格的象征,此时绘画已经突破了自身的媒介限制,实现了与诗歌的交融相通,变成了和诗歌一样的抒情艺术。所以黄庭坚以“无声诗”称呼李公麟的画,他说:“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钱鍪也称画为无声诗:“终朝诵公有声画,却来看此无声诗。”(《次袁尚书巫山十二峰二十五韵》)石涛也说:“予拈诗意以为画意……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以此哦之,可知画即诗中意。” (《画语录》)都是把绘画看成诗歌。
可绘画与诗歌毕竟是不同的艺术门类。诗歌是语言艺术,以文字符号传情达意,而绘画是视觉艺术,靠笔墨、线条、色彩等图像符号描绘客观物象、人体,那绘画是如何超越媒介的限制从而像诗歌一样抒情写意呢?这就得讲到诗画艺术共同追求的也是二者致力于达到的最高境界——意境。正是在意境同构的层面绘画克服了媒介的局限实现了对诗歌的模仿。
意境起初是诗论的重要范畴,如王昌龄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其中物境侧重于描绘客观景物,情境、意境侧重于饱满、强烈的主体情感的宣泄。后来司空图提出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二十四诗品》)。意境越来越强调虚化客观景物和情感描写等,越来越强调通过描绘外在“物”“象”“景”等引导诱发出一个审美的想象空间。所谓“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也是强调意境不可言说、语言难以到达,但又必须在语言的基础上借助想象、知觉来达成。因此,意境的重要特征是具有由有限到无限、由实到虚的超越性、无限延伸性和空间转换之美。它能引导人超越外在语象、物象等表象,进入一种包含无穷韵味、能引发人生感、历史感等哲理感悟的审美想象空间,亦即由“象”进入“意”。
到了宋代随着诗画一律的提出,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也开始追求意境,追求由“象”向“意”的演变发展。这不仅是诗歌对绘画的强势笼罩,也是绘画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成。比如早在南北朝时期谢赫就在《古画品录》中言:“若拘以形体,则未见精辟;若取之象外,则方见高腴,可谓微妙也。”虽然没有用到意境这个范畴,但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绘画不能只描绘具体的物象或人体,而是要通过外在物象、人体等的描绘,引导观者走向饱含着丰富言外之意的无限审美想象空间,让人感觉韵味无穷,这已经是意境论的萌芽了。苏珊·朗格认为绘画是虚幻空间的创造。她说:“虚幻空间是各种造型艺术的基本幻象。构图的各种因素、色彩和形状的每一种运用,都用来创造、支配和发展这种单独为视觉存在的图画空间。”[3]苏珊·朗格所谓的虚幻空间,其实就是在画布上涂抹出来的“图画空间”。但对于东方艺术来讲虚幻空间、图画空间并不是艺术的终点,由虚幻空间、图画空间引申而进入的饱含着情感色彩和生命律动、充满了象征意味的无形又广阔深邃的情感空间和想象空间才是艺术的终极追求。所以尽管绘画与诗歌媒介不同,但是不同的媒介最终的指向是相同的,二者建构的是共同的意境。在意境的同构的层面,绘画突破了媒介的限制最终实现了生命境界与艺术境界的融合,达到了与诗歌同一,从而获得了独特的诗性精神和诗意美感。
当然,也有人用比意境更小一级的语象联通文学与图像,认为“所谓文学图像化,比如诗意画、小说插图、连环画等,都是语象的外化和延宕;而文学对图像的模仿,例如题画诗……,则是语象对图像的造型描述。”[4]“文学语象是文学图像的生成之源,而‘文学的图像化’说到底是语象的图像化。”[5]也就是说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学的图像化是语象的图像化,是语象、图像的转化形成了文学与图像的转化。那勾连文学与图像的到底是语象、图像的相互转化还是意境的同构呢?其实语象、图像是外显的,而意境是深隐的;语象、图像描绘出来的画面只是文学、图像最浅层的意蕴,还停留在写实的层面;语象、图像描绘出来的画面触发了读者或者观者的艺术的想象和联想,从而在读者或者观者头脑中形成的主观的审美想象的空间,这才是文学、图像的深层意蕴。如宋徽宗画院考试众多考生都做到了将“野水”“孤舟”“古寺”等语象转化为了图像,但仅仅做到这一点对于任何艺术来讲都是不够的,因为包括诗意图在内的任何艺术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写实、造型等浅层的表达,而在于能创造“象外之象”,能“意在笔墨之外”。所以语象、图像只是引子,作为“象外之象”的意境才是文学、图像之作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也就是说诗画的融合相通不仅仅是语象、物象等的外在转化,关键在于精神、心灵、生命感觉的融合相通,在“与道为一”的心灵高度使人物我两忘,内心一片澄澈,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而从外在的视觉再进入内在的心灵,这显然也符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语,见《历代名画记》卷一〇)的绘画创作理论。宗白华先生说:“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最深心灵究竟是什么?答曰: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一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烦恼苦闷,彷徨不安,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6]也是强调艺术是心灵与自然宇宙的体合为一。由此可见,仅仅以语象、图像的转换来解读图像向文学的靠拢显然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图像应该是在建构共同审美想象空间即意境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诗歌的攀附,达到了内在的语图融合,以此实现了表意与抒情的最大化。但图像毕竟是一种虚指性符号,而文字是一种实指性符号,所以图像在表意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最终使其必然要借助诗歌一起共同完成诗意的表达。再加上绘画与诗歌一律,这也为诗歌直接融入绘画提供了基础。所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绘画在画面中对文字的排斥,中国画是把题画诗直接置于画面,从而由内至外达到了双重的语图融合。
2.题画诗:画面获得诗性精神的直接来源
在“诗画一律”的启发下衍生出了“书画同源”的理论。“书画同源”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张彦远。他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异名而同体”“工画者多善书”,强调书法所写的汉字因为象形所以与绘画相通。后来元代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题)》中进一步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以书法之飞白画石、籀文画树、永字八法画竹,更强调书画二者在笔法线条上的相通。从文化同源到法理相通,至此“书画同源”理论初步定型,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画的创作。
虽然对于“书画同源”的内涵理解不一,甚至还有人持反对的意见,但不能否认书法、绘画作为相近的姊妹艺术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彼此会交融相通,互相影响。比如郑板桥正是在书画的彼此借鉴中进行书画创作,他说:“文与可、吴仲圭善画竹,吾未尝取为竹谱也;东坡、鲁直作书非作竹也,而吾之画竹往往学之。黄书飘洒而瘦,吾竹中瘦叶学之;东坡书短悍而肥,吾竹中肥叶学之。此吾画之取法于书也。至吾作书又往往取沈石田、徐文长、高其佩之画,以为笔法。”(《题〈墨竹图〉》)还有徐渭的写意画纵横驰骋,大刀阔斧,又饱含激情,明显有狂草的风范。书画的界限与壁垒被打通,也表现在外在形式上书法就被援引入画,成为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与“诗画一律”携手,促成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最终书法成了诗歌和绘画能并列于同一文本的载体和桥梁。
书法是在对汉字形体的书写中,利用多元化的视觉因素寄托情感、传达审美的笔墨艺术。其本身包含双重功能——文字符号的表意功能和线条符号的审美功能。文字符号组成的题画诗能传达字义信息,与绘画图像形成文本互文,在意境的层面获得勾连,共同完成形象文本。因为“所有图像都是多义的。在图像的能指后面,隐含着一条所指‘浮动链’。”[7]也就是说图像符号“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固定的,具有诸多可能性,所以题画诗并置于画面,和图像一起互相指涉,能将所指浮动链加以固定,起到深化画境、固定画境的作用。比如唐寅的《桐阴清梦图》,从画面上看是一株梧桐树下一位士人仰坐于交椅之上,闭目养神。这是罗兰·巴特所谓的外延图像,包含着无限可能的意义,但又不能确指。此时左上角的题画诗“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试醉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起到的就是锚定功能,将图像的阐释导向了主体的心灵空间——科举舞弊案之后惨遭“断仕”的抑郁和凄凉。题画诗的文字信息既阻止了“所指”被扩散到其他领域,又使图像超越了画面形而下的物理空间的局限,上升到内涵的层面。再比如同样是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外延图像上看大同小异,都是几丛翠竹疏朗挺拔、笔力劲瘦,但图像“所指”的多重性、自由性与不确定性,就使其题竹诗千差万别: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清风江上作鱼竿。(《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题画竹》)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新竹》)
兼济天下的品格,独善其身的节操,绘画理论的总结,乃至以老竹根上生出新竹贺人生子等,所寄寓的意境与主体情感都截然不同。所以题画诗会引导观者超越外延图像,深入领悟画外之意,等于是把中国画充溢的文人意味升华并予以锚定,堪称中国画的点睛之笔。当然,因为形象文本中语言和图像的关系是相互补充、互为表里的,所以题画诗的意义其实也是在图像的描绘中被呈现出来。图像是诗歌表情达意的起点,同时也使诗歌的情感抒发直观可感。所谓“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吴龙翰《野趣有声画序》),在文字与图像的交流对话、映发补充中,绘画从内在的精神意境乃至外在的形式上都与诗歌相通相融,从而达到了由内至外双重的语图融合。
除了表意功能之外,题画诗以书法的形式被写入画面,还会变成具有审美功能的线条符号,“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8],而绘画也正是借助笔墨线条完成造型、表达情感。所以题画诗在形式上看乃是与图像同质、同源,在形象文本中二者最终由异质媒介变成了同体互动,具有彼此亲和、呼应的关系。比如徐渭的《榴实图》,画面右上方是一首题画诗:“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整首诗以连绵飞动的狂草写成,宛若牵丝连线,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甚至行与行之间都有气韵通连,一气呵成,笔势连贯。题画诗下方的绘画图像无论是榴实、折枝还是叶子,用笔、点画都如草书挥洒,与题画诗相呼应。其枝干由粗变细,自右上延伸至左下。正锋用笔,苍劲有力,又出以破笔、断笔,给人笔断意连、富有节奏的美感。画面中心的破壳石榴,开口向上,石榴籽随意点染,用笔草草,不求形似,正是“向天开口笑”的诗意。而石榴的叶子点画纷披,也似书法随意的撇、竖、捺,正和书法线条相呼应。还有他的《墨葡萄图》,题画诗的书法与绘画图像的线条也是彼此相通,共同完成主体情感的抒发。所以形象文本中字与画是互通互补,彼此协调呼应的。正如潘天寿所言:“画上所画的意趣,系清疏秀丽者,题款的书法,亦须清疏秀丽;画上所画的意趣,系大气磅礴者,题款的书法,亦须大气磅礴;画上所画的意趣,系质朴古拙者,题款的书法,亦须质朴古拙;方能互相调和配合。”[9]强调的都是形象文本中字与画的审美联觉效应。所以题画诗兼具语言与图像的双重特征,在共享文本的话语空间中推动了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互动,增强了绘画的诗性美感。
而从画面构图来看,题画诗也与图像巧妙相连,其在画面中的空间形态既可以弥补画面空白,增强画面的饱满度,又可以平衡画面,使画面达到空间均衡。“如左有高山右边宜虚,款诗即在右。右边亦然,不可侵画位。”(孔衍拭《石村画诀》)而无论题画诗的空间形式如何演变,其对图像形式上的和谐调配作用始终是不改变的,“或长行直下,使画面增长气机;或拦住画幅的边缘,使布局紧凑;或补充空虚,使画面平衡;或弥补散漫,增加交叉疏密的变化,等等”[10]。所以题画诗的空间介入在画面布局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和图像的空间形式一起,从形式结构层维系着视觉结构的均衡、稳定,增强了文本空间的表现力,又从意义层强化了图像的意境。徐复观说:“用与诗相通的心灵、意境,乃至用作诗的技巧,画出了一张画,更用一首诗将此心灵、意境咏叹了出来,再加上与绘画相通的书法,把它写在画面空白的地方,使三者互相映发。”[11]以书法为纽带和桥梁,诗歌直接置于画面,从内在的意境到外在的形式都和绘画图像互相交融补充,成为画面的重要图符和画面意境的锚定者。所以题画诗绝不仅仅是“画媵”(《四库全书总目·竹嬾画媵》)——绘画图像的陪衬,而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高于绘画图像的。因为诗与画“这种融合、这种并置其实是等级制的、字本位的;‘题’即书写的文字进入图画的肌体中支配了画面,左右了对图画理解的方向。”[12]比如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从画面上看就是一位仕女手持团扇侧立在斜坡上,周围有一丛修竹、两块山石,从图像中可以感受到荒寒之气与寂寥之情,也可以感受到团扇似乎隐隐指向了失宠之悲,但一切都是模糊的、无法确指的。可一旦联系画面左上角的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一切都豁然开朗。“秋来纨扇”明显是化用了班婕妤的《怨歌行》,借秋扇见捐抒发被遗弃的伤感,而世态炎凉的一番感慨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寅科举上的遭谗被摈。晚明项元汴收藏此画时曾作跋曰:“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此图此诗,盖自伤兼自解也。”从这幅画中读到了唐寅抑郁不得志的伤感,题画诗可谓功不可没。所以鉴于图像与文字指涉属性的差异,当图像与诗歌不能相互印证或者对图像的想象和期待有很大不确定性时,人们往往会按照诗歌重新赋予图像以新的意义。所以“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没有纯粹的图像,没有独立于整个‘文’的传统的图像传统,没有独立的图像意志,图像已是‘文’的一部分。”[13]这也正是米歇尔所说的“如果这里在词语与形象之间有一场争斗,显然话语将有决定权。”[14]
二
“诗性”或“诗性智慧”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指的是原始人凭“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5]来创造的原始思维方式。其特点是用直觉、想象等方式来理解世界,其来源乃是因为心灵的蒙昧无知以及好奇。后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诗性色彩。虽然维柯说诗性具有人类的共通性,也是一切文化与艺术之源,但西方终究是理性与科学占上风。正如勃纳德·贝伦森所说:“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16]“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因而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17]相反在中国文化中诗性精神却是绝对的主宰,“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18]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19]而中国诗性文化的土壤上孕育的中国画,在语言符号对图像符号的长期渗透、笼罩并左右中,通过意境同构以及题画诗直接置于画面,也形成了浓厚的诗性精神。具体来讲,这种诗性精神既表现为水墨语言层面的诗意性表达,更表现为精神层面艺术家胸中块垒、主观感情、胸怀气度、品格理想等的抒发和表达。
第一,水墨语言层面的诗意性表达。
中国画的诗性精神寓于笔墨语言之中,正如《宣和画谱》所谓:“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强调正是水墨语言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即在不依靠文字符号的情况下,完全通过水墨语言塑造的视觉世界表现诗意,但其实从深层看水墨语言的隐喻性,仍然是要借助诗歌比兴象征的方式处理视觉意象的结构。比如梅兰竹菊等象征君子的高尚品格,山水往往是隐逸人格的表达,还有唐寅《秋风纨扇图》中的“团扇”在诗歌中多喻失宠之悲。这些诗歌常用意象的寓意往往内化于绘画,成了绘画的诗意。除了水墨语言的比兴意味之外,丰子恺先生在分析中国画的诗趣时曾特别强调“诗与画的内面的结合,即画的设想、构图、形状、色彩的诗化”[20]。也就是说水墨语言的形式也要能给人带来诗意的美感。比如马远、夏圭删繁就简,一改全景式的山水为“马一角”“夏半边”的构图,给画面大量留白,以表现天地氤氲、青山绵邈、江河静远、烟波幽眇。“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华琳《南宗抉秘》)也就是说这种画面中的空白渲染并不显得空,反而给人空灵淡远、意境幽深之感,就像诗歌给人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一样,反而能给人带来诗意性想象。再比如从色彩上看,中国画并不崇尚绚丽的色彩,而是主张以墨代色,以淡为宗。这也和诗歌语言推崇的清淡质朴、清新自然如出一辙,同样会形成画面诗意朦胧的美感。
第二,精神层面诗歌的情感表达。
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从唐宋以来图文关系获得重构,中国画不再是“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教化之具,也不再致力于探索图像与可视世界的客观关系,而是与诗歌合流,致力于创造与诗歌相类的意境。甚至直接将题画诗纳入画面,最终在语图由内至外双重融合中将绘画导向空灵的精神层面,使其成为艺术家抒发胸中块垒,表达主观感情、胸怀气度、品格理想的载体,成为具有抒情言志功能的类诗文本。无论是董其昌说的“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容台集》),还是倪瓒说的“逸笔草草”(《答张藻仲书》),“聊以写胸中逸气”(《题自画墨竹》),抑或是莫是龙说的“写胸中丘壑”(《画说》),都是强调绘画虽然运用笔墨技巧,但又绝不局限于笔墨本身,而是将笔墨技艺作为通向精神升华、心灵感悟的途径,最终在吟咏情怀的过程中达到物我合一、与道合一,在与天地宇宙的融合贯通中获得生命的解放、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逍遥游。所以中国画的诗性精神从深层来讲指的是绘画以造型艺术的笔墨线条为基础,通过模仿诗歌而形成的文学化、诗化倾向,更注重“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也”(《苦瓜和尚画语录》)。更注重创作主体抒情言志等类诗化的主观感情表达与诗歌的审美体验。比如徐渭、唐寅、郑板桥等人都有浓郁的诗人气质,他们的画都从内心的焦虑与困惑出发,在传达艺术家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探寻与思考。既有一种大展宏图的渴望和济世安民的入世情怀,也有一种摆脱世俗藩篱之羁绊与束缚的超脱,这使他们的画不仅是视觉之物象、人体的描摹,更是上升到生命之思,是对生命的关注、感怀与表达。还有很多文人画则是省略了生命蝉蜕与升华的过程,直接表现创作主体在与自然山水、天地宇宙的贯通中获得的精神的逍遥与灵魂的高蹈,从而使画作哲思与诗情并存,充满了深沉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这种以“意”为先,以吟咏情性的诗性言说方式使“象”得以呈现与升华,获得浓郁的抒情意味,使得中国画在内在的精神上当之无愧呈现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当然这是作为语言符号的题画诗和作为图像符号的绘画合体表意共同形成的诗意。
总之,中国画的命脉当之无愧属于图像。光有追求神似、表达思想的诗性精神而缺乏具有造型功能的图像则画不成画,因为“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邹一桂《小山画谱》)。但光有图像而缺乏诗性精神的话,也算不得气韵生动的佳作。所以诗性精神算得上是中国画的灵魂,其从审美、语言、形式、内容等方方面面都对图像予以界定和笼罩。也就是说虽然语图异质,但是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语言一直渗透于图像之中,并且凌驾于图像之上。但这并不是说语图互渗是图像单方面向语言靠拢,进入图像的语言符号也不可避免地要符合图像的规则。比如题画诗是以书法即图像符号的形式进入绘画,而且要在形象、审美等各方面和图像保持一致;还有中国画的诗性精神也不是赤裸裸艺术观念的呈现,而是要投射于图像,借助图像的造型功能完成,所以有着异于语言表达的朦胧性、不确定性和暧昧性,需要观者根据一定的知识水平、文学修养、文化习俗等做出解读。由此形成的这种体验性、多义性与用话语直接分析明显是不同的。语言在渗透进图像使图像获得诗性精神的过程中从实指转向虚指,而图像的直观呈现性又有趋于浅薄化的倾向,这也导致进入图像法则的语言很难深刻。所以钱钟书说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是画中高品或正宗,但是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却绝不是诗中高品,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的诗歌。[21]
三
通过对中国画绘画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画特别强调绘画与文学的关联,尤其是与诗的渊源。但随着时代的巨变和东西方思想的碰撞,随着古典向现代的转变,随着语言中心向图像中心的转向,中国画越来越溢出诗歌的笼罩和规范,绘画本体越来越受到重视,仅仅是笔墨就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可是当语言符号被驱逐和摒弃,语图之间不再是相互生发相互阐发的对话共生关系,绘画图像很容易变得单薄、浅薄,变成西方表现主义的模仿,或数字图像的嫁接,从而使中国画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民族质感。对于中国画来讲,当然不能一味停留在守势,仅仅满足于传统或前人审美图式的复制。在当下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与绘画错综多变的格局中做多种探索与开拓是应有之义。但是只有以诗性传统为引导,在文脉传承的新视野下进行新的绘画语言探索,从而将传统艺术观念与当下结合,生发笔墨的新表现性,才能传承中国画的文化基因。正如范曾先生所言:“中国画是哲学的,是诗性的,是书法的。如果这些方面修养不够,显然你会离中国画距离很远,也许你能画出一张好的画。好的画不等于好的中国画。”[22]诗性精神是中国画的精神中心和技术要领,也应该是新时代艺术家自在艺术精神与艺术活动的根基。“变易人间阅桑海,不变民族性特殊”(黄宾虹《画学篇》),只有以诗性精神为发端,才能扎根传统探索出具有深度文化气质的绘画语言,从而形成新语境下气韵生动又贴近时代的造型艺术。而只有保证“变”中的“不变”,才能保住中国画的血脉和基因。
注释:
[1]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2]杨吉华:《道、艺、志的互动:苏轼诗画论中的“文人”探绎》,《思想与文化》2007年第2期,第459页。
[3]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6页。
[4]赵敬鹏:《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学术论坛》2016年第4期,第 107页。
[5]赵宪章:《“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25页。
[6]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7]罗兰·巴特:《图像修辞学》,参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编:《语言学研究》(第6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8]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9]潘天寿:《潘天寿美术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
[10]潘天寿:《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特点》,《美术》1978年第6期,第36页。
[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4页。
[12]孟华:《文字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13]刘泰然:《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第147页。
[14]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55页。
[15]维柯:《新科学》(全二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88页。
[16]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17]陈炎:《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理论学刊》2000年第6期,第118页。
[18]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2月。
[19]同 [18]。
[20]丰子恺:《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21]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22]《范曾谈中国画创作的三个基因:哲学、诗性、书法》,http://www.yczihua.com/article-9230.html,2014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