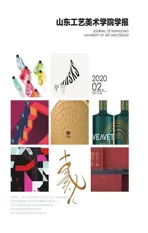安东尼·布朗绘本中的视觉符号暗示
2020-12-06
本文以绘本的图文关系为立足点,探讨安东尼·布朗绘本如何运用色彩、图形、空间布局作为载体呈现暗示功能,并分析出暗示的目的是推动情节发展、强化文本、增强绘本的趣味性表达。通过视觉符号的暗示使得图像的意义更为深刻,耐人寻味,与读者之间建立沟通对话的桥梁。
安东尼·布朗;绘本;视觉符号;暗示
1.视觉符号及暗示的界定
暗示指在无对抗的条件下,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对受暗示者进行诱导,并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一种作用。这种影响作用,常常会使人无意识地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或者无抵抗、不批判地接受某些意见,最终使其思想、行为达到暗示者期望的结果。[1]通过暗示人们将已知事物与未知事物建立相似性联系,从而提炼出作品传达的意义。根据瑞典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由物质、行为或表象载体所充当的对符号意义的指称或指向。它是较确定的,又称之为“明示”。“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它是不那么确定的,联想性的、富于感情色彩的,又称之为“暗含”。
因此,绘本作为暗示的载体,从符号学的两个角度实现了个体与外界,主观与客观的联结。其一,包括形状、色彩、肌理,乃至布局、空间、方向等可被直接感知的“能指”部分;其二,则是主观心理层面上结合读者的知识经验、联想等产生的对符号形态的理解,即“所指”。暗示便是通过“能指”来实现“所指”。
就绘本的叙事结构来说,通常分为图像叙事为主,文字补充性呈现图像未能传达的寓意,以及文字承担主要叙事责任,图像展现文字没有阐述的部分这两种共融型叙事。这两种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暗示的体现。[2]
2.暗示的载体
本文论及的暗示是不见诸文字、不使用语言的非言辞方式,以双方或多方表情达意、传播信息为目的的叙事手段。
2.1 图形符号的暗示
图形是绘本中最感性直观的信息载体,汇集一切视觉符号的容器,并且在解读过程中较少出现国界及语言上的障碍。画面中运用具象或抽象的图形符号,引起视觉的聚焦,对读者产生暗示。
环衬,一般来说,是绘本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部分。然而实际上,绘本的环衬不但与正文的故事情节息息相关,有时还会通过暗示的运用,达到提升主题的效果。[3]例如绘本《隧道》,前后环衬的画面背景均是左边为花卉图案的墙纸,右边为红色的墙砖,分别用以代表男孩和女孩。然而作者独辟蹊径的设计体现在,前环衬花卉图案下还有一本书,后环衬这本书出现在红墙砖一侧,与一个足球靠在一起,暗示着故事发展的结局是兄妹间的“和解”。而这一暗示的意义正与绘本通篇阐释的兄妹间不可抗衡的情谊的主题不谋而合。
绘本中还有一处图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这就是从扉页开始出现的图画,它常常被作为故事的引子,设置悬念。例如,在绘本《我妈妈》的扉页上出现的爱心图形,便给读者心中埋下暗示的种子,到进入正文部分,文字仍未提及,但爱心图形却几乎贯穿了图像部分的每一页,出现在主人公妈妈身上的各处。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随着情节的发展最终向读者印证了爱心图形就是通篇表现的妈妈无微不至的“爱”,引申出主题,深化了妈妈的形象。当读者恍然发现这一巧妙的暗示时,便会与作者诙谐奇妙的思维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感。
职业培训。2010年,华南公司和全国10多家三级甲等医院合作成立了扬州华南职业培训学校,设校本部和省内外10个教学点,开办养老护理、病患陪护、育婴(含月嫂)、家政服务等6个专业的初、中、高级培训项目。目前,学校已成为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扬州华南培训中心,国家民政部4A级社会组织,江苏省家庭服务职业培训示范基地,扬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核准的职业技能定点培训基地。
绘本正文部分出现的图形有时看似无厘头,然而结合故事情节便能挖掘出隐晦其中的暗示意义。在绘本《胆小鬼威利》中,威利家墙面上意外出现的水仙花图形,虽然没有文字的描述及图像的铺垫,但水仙花生机勃勃的形态暗示了威利照镜子时,对通过锻炼塑造成的当下健美体魄的自信。作者以水仙花这一物象的表达,形象地反映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类似这样的细节图形暗示的案例还有《动物园》。画面中排队购票的人脚下却长出鳄鱼的爪,头上的牛角、鸟嘴以及模仿着动物吼叫的画面中,本应处于读者与他们之间的笼栏被作者巧妙地移到了他们的身后,暗示着被囚禁者角色的反转,直戳人类与动物互换处境这一敏感话题,抗议批评人类不智和残忍,发人深省。
2.2 色彩符号的暗示
“色彩之于形象有如伴奏之于歌词;不但如此,有时色彩竟是歌词而形象只是伴奏;色彩从附属品一变而为主体”。[4]因此,色彩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使其无论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沟通语言,心理层面的情感传递抑或是其引发的语义联想,都能起到良好的暗示效果,用于表现愉快、愤怒、忧郁的情绪以及兴奋、痛苦等难以用语言形象表述的心理状态,增强读者内心的情感体验。绘本《捉小熊》每页都安置了至少一块以上的红色,形态各异。包括小熊的红色领结、在猎人驾驶的绿皮车上的红色大圆点等的互补色对比,增强了画面的活跃度。但偏暗调的红色在活跃度上相比于纯度较高的红色是有所控制的,暗示了小熊深处危机四伏的森林中的紧迫感,又与小熊机智化险的情节设置相得益彰。
绘本中色彩的明度、纯度,既能帮助我们分辨图像中不同物件的质地、触感等,还能表现故事中没有描述的叙事环境,暗示人物关系。例如绘本《大猩猩》中,安娜和爸爸面对面坐在餐桌上的那一页,爸爸身后的厨房以及脚下的地砖都呈现出僵硬、呆板的几何形冷色调,暗示爸爸和安娜两人关系紧张、冷漠。而到了故事的结尾部分,简陋、毫无生气的背景已经被暖色调的花墙所替代,暗示父女关系缓和,充满温情。同样以环境的色调暗示人物关系还有《公园里的声音》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在一片冷绿色调的森林里,两只狗互相追逐玩耍,一道奇异的光束穿过森林蜿蜒而过。这束光的出现暗示了两只狗追逐奔跑的速度之快,反映出它们的愉悦与活力的心理状态,彼此是亲密无间的伙伴。而两只狗的深厚情谊,实则暗示了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虽然内心渴望成为一起玩耍的伙伴,却囿于两家之间的贫富差异以及阶级隔阂让两个孩子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故事以荒诞的手法刻画环境要素,从侧面暗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分化现象。再如绘本《谁来我家》以一个女孩的视角展开。凯蒂和父亲的二人世界自由温馨,作者使用较为明快的色调,而在他们的生活被父亲的女友及儿子的到来打乱的画面中,则选用了较深的色调烘托家里的紧张氛围,暗示凯蒂内心的压抑和失落。而后再度出现明亮的色块时已是故事尾声,凯蒂内心的结打开了,慢慢接受了家里的新成员。作者对于色彩关系的把握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前后照应地呈现了叙事的完整性。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则通过色彩的纯度变化表现出的光影,将男孩的心理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小凯一个人坐在沙发时,周围的一切便开始发生了变化,沙发逐渐变成一只猩猩,旁边还匍匐着一只鳄鱼,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小凯的腿上,影子投射在沙发和地面上,如同一组栅栏困住小凯,暗示了他内心的恐惧与迷茫,推动了后续情节的发展。色彩对人物内心的暗示在故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2.3 空间布局的暗示
绘本中除了形状、色彩等视觉符号有直观的暗示作用,多数出色的绘本亦将暗示渗透于绘本画面的空间布局之中,观照人物的内心感受。在《朱家故事》的前半部分,朱太太以一个衣装朴素暗淡、忙于家务的卑微女性形象出现,她的轮廓被限制在四幅排列紧凑的暗黄色调的方格中。这些视觉元素对于形象的阻隔,暗示了她内心的压抑以及在家中完全失去自我的地位。此时的她与高大活力、面带微笑的丈夫形成较强的反差。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朱太太回来拯救几近失控的家,推开门的那一刻,门框后投来的亮光暗示了朱太太救世主一般的光辉形象。而朱先生和儿子发生改变之后,朱太太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微笑的脸庞、鲜艳的衣着,以及没有边框限制的构图,无疑成为最具表现力的视觉语言,暗示了她内心的愉悦与自由的活力。朱太太首次以正面且高大的形象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同时暗示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已从原先的边缘走向家庭的核心,从被家人忽视走向被家人尊重与需要。
此外,空间布局的暗示也呈现出许多文字并未表达的细节,调动读者最细微的感官与认知。不同的空间布局亦能映射出不同的叙事风格,营造不同的阅读体验,是绘本暗示中艺术性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得体的运用有助于深化绘本的叙事性,避免枯燥单一。如绘本《大猩猩》的文字不算少,但只说父亲如何忙碌,从来没有时间陪伴安娜,甚至连一个类似“孤单”这样的字眼都未曾出现。但正文部分一开始就用早餐时安娜与面无表情的爸爸之间的餐桌占领了画面的视觉中心,这样的布局暗示了父女间疏远的关系。而后的画面中安娜站在父亲背后欲言又止地望着他,地上是安娜长长的影子,以及漆黑的房间里,安娜一个人缩在墙角看电视。作者有意将安娜画得很小,房间则画得很大很空,强烈的空间对比暗示将安娜的孤独渲染得淋漓尽致,形成强烈的戏剧性冲突,激起读者共鸣。再如《走进森林》的画面中,作者将男孩置于画面左下角的框线部分,男孩的一只脚已经跨出框线之外。这是作者在故事的结尾向读者暗示男孩不再胆怯,敢于突破内心的恐惧,下决心要走出这片森林了。而紧随其后的一页就印证了读者的猜测,他逃到了奶奶的小屋跟前,为读者营造了阅读的愉悦感。
归根结底,在绘本中的暗示,有别于日常生活中我们赋予物象的特定含义(如:笼子——禁锢;蜘蛛网——纠葛),更多时候,物象本身并无明确的指代性,恰恰是图形、色彩、布局之间的关联架构,巧妙组合叠加为绘本开拓了一个更为微观细致的意义世界。
3.暗示的目的
绘本图像中视觉符号的暗示,利用类比联想,抑或是构建相似性,使似互不相关的视觉元素或事物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将现实世界中难以用文字描述、画面难以绘制或如按常规描述很容易落入俗套的抽象经验和思想化为可能。暗示则更像是一种范畴的错置,是一种比较型的修辞。人们将某一领域得来的经验来说明另一个领域的经验,通过感知的相似感互相阐释。[5]故视觉符号的暗示功能在绘本中具体能够达到以下目的:
1.推动情节发展。绘本中,常常隐藏着许多作者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埋下的细节暗示。它们有的只是增添趣味,与主题无关,有的则是故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但烘托故事的氛围,暗示故事的走向,还赋予了故事一种荒诞的意味,从而达到批判现实的作用。在绘本《朱家故事》中,妈妈离开后,作者运用越来越多的动物元素。两个孩子进门时,墙上的电源插座和门把手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当朱先生推门而入的时候,插座和把手都变成了一张动物的脸,暗示了父亲与儿子两人濒临崩溃的生活,逐渐将故事情节推向矛盾爆发点。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暗示使读者比故事中的人物先一步察觉到家里的变化,领会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符号线索。
2.强化文本。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文字读物可以唤醒读者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图像的深刻内涵和思想深度方面,有着特殊的表意功能。印刷物的图像化也就是将文字的深义具体化和直观化,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视觉快感,抽象文字的深义表述和直观形象的图片互为阐发。[6]而这种互为阐发的叙事方式就是利用暗示,强化读者对文本所传递的观念、思想等的认同感。例如作品《我爸爸》中,通过孩子夸张的幻想,塑造了一个滑稽幽默却又高大可爱的爸爸形象。其中爸爸穿的那件睡衣的棕色格子图案,先是出现在环衬及扉页上,而正文部分便成了面包片的纹理,鱼身上的鱼鳞等。这些虽然充满超现实主义的荒诞,但它的不断重复出现,潜移默化地让读者体会到暗示这一表现技巧的独到之处,并加深了对于父亲这一形象的感知。而另一种确认文本则是通过“反语”的方式实现的,即文字与图像的表述不再呈现互文性,二者完全在阐释截然不同事物。例如在绘本《动物园》中,左页文字部分描述了一家人满怀期待地来到动物园,孩子们又累又饿漫不经心地观赏,右页图像则是背对观众的长颈鹿、被牢笼所困的老虎等。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表述,但我们能深切读出这些动物的体态特征所传达出的忧伤。作者对动物们的身体与它们所处的环境的刻画也别具匠心。他让老虎的头尾刚好卡在画框边缘,使其王者风范随即消失;犀牛在坚硬的墙壁和巨大的岩石衬托之下,也呈现出不合常理的温文尔雅;最后特写聚焦的大猩猩眼睛凝望着远方的眼神以及下垂的眼角,流露出它难以启齿的哀伤。这样的反语表现增强了文本的叙事表意力度,暗示了结局动物与人互换角色,引发读者的思考。
3.强趣味性表达。安东尼·布朗绘本的每一页场景都是靠细节暗示穿插连接变成有趣的情节,但是整个故事内容却像是安静耐心地为读者讲述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将读者设定为“探寻者”的角色,挖掘其中的深意。比如在《隧道》的第二个画面里,房顶的烟囱上放着一顶女巫的黑色高帽以及窗户上一只黑猫的剪影。第四个画面中,大衣橱边挂着的红色外套。这些元素不仅为了丰富画面,而且也体现故事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当读者读到绘本的最后便发现这些元素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女巫的黑色高帽、黑猫,暗示了即将到来的凶险,而红色的外套则是后来妹妹勇敢走出森林时穿的。发现这些趣味性视觉元素的过程本身也给读者带来了良好的阅读满足感。再如作者新作《威利的故事》中,正文部分的一跨页中威利化身为童话中的主角,但作者并不点明人物的背景及名字,文字部分全部在左页排版,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故事的动态过程,而位于右页图像部分则只选取了故事中最关键的时刻来表现。作者甚至在一旁提示问道:“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这些鲜明的视觉符号一方面向读者暗示了作者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增添了绘本的互动性、趣味性,充分调动了读者追根溯源的阅读兴趣。
4.结语
“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当代文化逐渐从语言主因型向图像主因型过度,对主体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更愿意图像类读物认知事物,因为这类读物对眼球更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安东尼·布朗抓住了这一人性特点,在绘本中巧妙地将棘手枯燥的家庭、亲情等问题,通过视觉符号的暗示转变成有趣的故事情节,同时削弱了文字在故事中的统摄力量,让读图亦可带来“美”的视觉感受。
看安东尼·布朗的作品最大的乐趣,是找出隐藏在绘本里的小细节。“在好的图画书里,有着各种各样隐藏的信号。读出它、发现它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在这一瞬间,就好像作者的眼神相遇后相对一笑的感觉。”[7]暗示就是让图像发出信号,激发一整套洞察力及思考,使图像成为多层暗示语系的视觉符号。图形、色彩、空间布局等暗示技巧的运用,一方面使得读者即使不看文字也能较清晰地理解其中情节,激发读者感官经验及心理更深层面的共鸣;另一方面也变相向读者吐露作者自身的存在及创作初衷。
注释:
[1]杨清:《简明心理学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3]彭懿:《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北京:接力出版社,2011年。
[4]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5]汪雨璐:《图文关系“陌生化”在绘本创作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16年。
[6]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7]松居直:《我的图画书论》,徐小洁、郭雯霞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