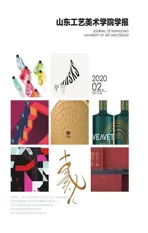健康传播视野中的“抗疫”主题设计
2020-12-06
笔者现年72岁的母亲是一位医务工作者,由于医院的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在笔者的记忆中,自己童年的80年代初期几乎是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母亲工作的医院里长大的。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家医院的模样:一上楼梯,就是可能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医院都能看到大幅语录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虽然那个时候不能确知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含义,但对那红底黄字的毛体书法至今记忆犹新,以至于当时每次走过那个大楼梯,都让人对医务工作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就是一种针对健康和医疗的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设计界一般采用台湾译名“视觉传达”)。对于设计界来说,视觉传播作为平面设计的代名词,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不再陌生的一个专业,但针对健康和医疗的视觉传播,却还没有引起艺术和设计界足够的重视。
2017年,在北京大学原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的倡议下,北大医学部与笔者所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始联合招收“健康传播”方向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MJC)。由于也兼任这个新设立的专硕专业的导师,笔者也常常在想自己的专业背景可以怎样为这个专业贡献些独特的价值。在检索、翻阅了不少国内外前些年出版的“Health Communication”的教材和文献之后,笔者惊讶地发现,这个专业领域内的大量文献都集中在医患沟通、健康公共教育、药品广告监管或是医疗健康类媒体发展等方面,对于健康传播中重要的一环——即关于健康的视觉传播,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也几乎没有得到医学和传播学界的充分关注。
有感于此,2018年,笔者曾在参加有医学、传播学两种学术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的“医疗、人本与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的多元进路”学术论坛时放胆提出,希望今后的健康传播研究和教学能够多多关注视觉的议题。笔者当时举例说,自己在国外旅游或考察的时候,经常愿意到当地的医院或医学类博物馆去转转,其目的不是关注医学的发展,而是留心世界各地医院内部的视觉导视系统、标准字体和色彩的应用、医院空间中的公益广告设计,乃至病历、医疗卡片的设计等。按说,这些都是一个平面设计的研究者的专业工作习惯使然,没想到会后竟有多位医学院教授和临床医生主动找到笔者,纷纷表示类似的研究在医学领域中还没有开展,听起来新鲜而有价值。其中,本校公共卫生学院孙昕霙教授还因此邀请笔者为其正在编写的《健康传播学》教材撰写“视觉健康传播”一章,系统综述视觉健康传播研究所涵盖的诸领域。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笔者那次会议上的呼吁,竟然意外地由于COVID-19的疫情,这么快就在现实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进而引发了笔者对于此次疫情中视觉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的进一步的思考。
对于抗疫设计,其实设计界已经不再陌生。2003年的“非典”疫情肆虐期间,正值笔者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研究生入学的那一年,在笔者的印象中,当时的视觉传播设计师就曾经一度大显身手。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何洁主创的抗击非典疫情的标志设计——NO SARS,当时就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和各种媒体,甚至还登上了国家正式发行的邮票,一时间洛阳纸贵。无独有偶,当时刚刚合并到清华大学不久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还主办了一次“爱心、信心、决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抗‘非典’文化衫设计”活动,可谓今天诸多抗击COVID-19疫情主题设计的先驱。只不过与2003年的“非典”艺术设计活动相比,此次我们多了更多新媒体传播的途径,以至于在疫情过后,很可能这些抗疫主题的艺术创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中对于“视觉”这种传播手段的关注。
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包括书法、美术、摄影、设计等领域的艺术工作者,与医务工作者一道,共同联手为抗击疫情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一些重要的艺术创作、教育、研究机构和行业组织,纷纷组织和动员所属艺术家为抗击疫情创作作品,或为医护人员造像,或记录下生死瞬间,或宣传防疫知识,或号召齐心协力……不一而足。综合此次艺术和设计界“抗疫”的主题创作的公众反响和社会效益而言,总体来看,通过设计手段的创作传播效果普遍要优于中国画、书法等纯艺术手段的创作。究其原因,恐怕正是体现出设计艺术不同于纯艺术的一些特点,才使得它可以在这次抗击疫情主题创作中大显身手。
在诸多通过艺术设计手段创作的抗疫主题作品征集与展示活动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传播的“防疫创作”系列,以其持续性的投入与作品数量尤其引人注目,必将在今后撰写的中国当代设计史乃至公共卫生史上留下痕迹。截至笔者撰稿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已创作各类“抗疫”主题创作的作品上万件,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近百期,为人民网、中国政协等媒体采访或报道,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等专家纷纷撰写评论文章,应该说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
第一,海报、宣传画、标志设计等平面设计形式,可以有效地利用各种视觉修辞的手段参与宣传,达到让抗疫理念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疫情中有很多的纯艺术创作,例如为钟南山院士画像,虽然初衷很好,即通过艺术创作给我们的防疫工作带来一些正能量。但是社会效果并不太好,甚至引来一些微信公众号和热心网友对所绘形象的质疑。毕竟,绘画、雕塑等纯艺术形式在今天更多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创作,艺术家的个性表达不太容易跟这种实效性的主题宣传结合在一起,对这些限定的内容进行艺术表达与发挥。也有一些书法家表示,为了让大众看得懂,书写一些抗疫口号需要使用自己平日在创作中并不熟悉的楷书字体,在诸多限制性因素的作用下,创作起来总感觉没有进行草书创作那样自然。也正因此,关于美术、书法等纯艺术是否适合进行“主题性创作”,其实近七十年来在艺术界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议和不同的声音。但设计艺术就不一样了。从一开始起,设计艺术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尤其是平面设计,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助力于各种信息的传达。正如潘鲁生所说:“特殊时期,宣传画要做到信息准确、用设计语言打动人,才能更好地起到战‘疫’宣传的作用。”因此,与纯艺术相比,设计艺术在进行各种宣传的时候就更加得心应手,因而更有用武之地。
第二,比起传统的绘画,设计的形式更容易拓展到手机H5、互联网、影视等多种终端,实现综合的传播。比较此次疫情中的艺术设计活动与2003年的区别,显然就体现在通过互联网或手机的微博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传播方面,给这些作品提供了更多接近公众的渠道。毕竟疫情期间无法在美术馆中举办实体的画展,而且即便是疫情解除后,想把一般的社会公众请进美术馆来也并非一件易事。因此,在新媒体传播条件下,这次的抗疫主题创作要比2003年的非典数量更多、传播范围更广,因此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更大。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根据新媒体传播的特点进行艺术创作。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接受口味也不断抬升,传统的纯静态作品已很难适应受众的需要。相比较纯艺术创作,设计类作品的尺幅、字体等,天然地容易和iPad、手机等屏幕相契合,达到更理想的新媒体传播的效果;此外,配合动画、H5等形式,设计作品也更容易在手机上实现交互传播。笔者注意到,此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所创作的抗疫主题作品中,除了传统的平面设计、漫画、摄影等门类,还包括大量视频、H5、微信小程序、互联网表情包等动态乃至互动作品。此类动态、交互作品在2003年“非典”期间还是比较少见到的,能够更有效地传播时代精神,因而也更利于表现抗疫作品的时代性。
第三,此次疫情中的设计类主题创作,可以通过多种设计的形式给后世留下关于历史的视觉综合纪录。就视觉传播而言,各种视觉传播的手段本身就是记录历史的鲜活的手段。比如,今天说到中世纪的黑死病,就马上会联想到当时穿着鸟式防护服的医生的形象;说起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就会联想起那个时代的宣传画,等等。诚然,与绘画、摄影、视频等作品相比,艺术设计作品在客观呈现和记录真实方面并不是人们的首选,但是,艺术设计作品却可以弥补绘画、摄影作品在诸如记录情绪、观点等方面的不足。抽象的图形、寓意和文案等的相互配合,让后人不仅能够了解这个特殊的时代影像的一些侧面,还能够以视觉的形式记录下当时社会的整体心态,从而为后来的“心态史”研究也存留宝贵的资料。在这方面,笔者注意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主题创作中,既有对“武汉解封”、网络授课等时代议题的视觉记录,更承载了这些重要事件背后的心情,是对于这个特殊时期全方位的历史记录,也体现了艺术设计类作品在相关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应该说视觉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碰撞,不仅为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有待展开的全新领域,也为视觉艺术和设计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笔者看来,目前的健康传播研究,虽然研究的重心和热点已经逐渐从传统的医患沟通转移到了各种医疗、健康信息在新媒体上的传播,但是关于艺术设计的新媒体健康传播,却仍然是健康传播和艺术设计两个领域中共同的空白。健康传播并不等同于医患关系、卫生新闻、健康教育等,视觉的健康传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无论在医学还是视觉文化领域中,在今天都变得非常需要。学者埃尔金斯在《图像的领域》这本书里就提到,“医学影像学”也应该是当代视觉文化、图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今天,学者们已经不是仅仅从临床应用的角度去看X光、心电图、CT片、B超单等各种检测报告上所携带的医疗信息,更应该把它们当成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毕竟今天临床中越来越依靠的这种医学影像的“视觉叙事”,在检查手段方面几乎已经完全取代了以往的“望闻问切”,成为当代医学乃至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除了传统上通过视觉手段呈现的健康教育、医疗公益广告等内容,其实还有很多现代设计可以介入的健康传播领域,往大里说,医院建筑、救护车、防护服的设计等,往小里说,包括医院内部的识别字体、导视系统、信息设计,甚至一个病历设计等,都是视觉文化的重要内容,对此还应该发挥此次系列抗疫创作的后续效应和持续的影响力。对此,工业设计实践领域已经开始展开探索,一些国内的医疗器械公司也已经开始了与专业工业设计机构的合作,从功能、外观等几方面提供改良和创新设计的可能性。然而,此次疫情期间关于雷神山、火神山和方舱医院的建设方面,除了建设效率,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艺术设计的介入,这足以说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对艺术设计的认识还停留在“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附属地位。甚至相比较工业设计领域这些年来的一些进展,笔者也注意到此次疫情期间,我们在一些诸如确诊人数统计图表的信息设计等方面,相比较2013年却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如何综合利用新媒体环境中视觉、图形的传播手段让信息更有效地得到传达,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总的来看,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防疫创作”系列艺术设计创作为代表的此次抗击疫情的艺术设计活动,不仅为时代进行了记录和公益传播,显示出艺术和设计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也为视觉艺术乃至健康传播学科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反思,也提出许多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值得深入面对和思考的新情况、新问题。相信此次疫情过后,无论是视觉文化研究还是健康传播研究都会因为此次的防疫创作得到了推进,让学科间的对话成为必要和可能,进而在极大程度上丰富未来艺术学、传播学乃至医学交叉互动的学科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