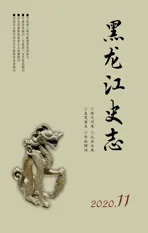新旧之间
——民国修志思想的转移
2020-11-17申津宁
申津宁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方志或称地方志,为中国文化之特有。因其包含了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及艺术等等,陈正祥认为:“方志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但也非完全相同。[1]”由此可以看出方志的记录内容极为丰富,且极具研究价值。方志之名公认起源于《周官》,而《周官》一书,系成于战国时代,由此可知方志历史之悠久。唐以前方志,大多不复存在。宋代是方志发展的兴盛期,方志的修纂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清代为中国方志的全盛时期。到了清季民初,时事动荡,新旧思想交替,各种思潮涌动,当时士人中出现了一个重大分歧,即如何对待我们的文明,是走温故知新、古学复兴之路,还是面向未来、推陈出新,再造一个新的中华文明?二者道路不同却指向同一个问题。世变愈急愈大,则史学变得愈快愈新。史学如此,方志亦如此。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方志修纂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之当时士人趋新并去旧之倾向,对于方志何去何从,曾引发过一场争论,即“方志废止案”,守旧者有之,改良者有之,替代者亦有之。在争论的浪潮过后,方志最终保留了下来,但是对传统方志进行改革成为了这一时期方志编纂思想的主流,绝大多数民国方志学家都对方志进行了改造,构建了新的方志理论,如傅振伦、黎锦熙等人,为方志近代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方志于近代的转变体现时移世变,而其背后的思想转移则值得重视。
一、由政统之科学——走进方志的赛先生
提及方志,清朝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为中国方志之鼎盛时期,尤其是章学诚将方志推向巅峰。梁启超评:“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2]”章学诚编纂的现存唯一完好的志书为《乾隆永清县志》,现抄《永清志》目录如下:
纪二:皇言、恩泽
表三:职官、选举、士族
图三:舆地、建置、水道
书六:吏、户、礼、兵、刑、工
政略一
列传十
另附有文征五: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
此志体现了章学诚“方志分立三书”的编纂思想,但是皇言、恩泽、职官、选举、士族等仍然体现了方志中的忠君思想与价值体系。
有清一代,另一部较为著名的志书为谢氏《广西通志》,抄其目录如下:
训典
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
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政经、前事、艺文、金石、胜迹
二录:宦迹、谪宦
六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诸蛮
戴震所编《汾州府志》里还有星野、山川等篇目。从上述志书可以看出传统方志的内在渊源根底在儒家的世界观与伦理道德,星野对应天、舆地山川等对应地、列传等对应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与敬天法祖不谋而合;抑或呼应了君、地、臣、民的三纲五常体系。从修志者身份来看,修志者本身就是儒家群体,所以所修之志书学术之根底亦为儒家之思想,这深深体现了儒之道统。而修志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在儒家体系之下进行,为证明政统之正统性。皇朝的政统则体现在政治的中央集权,全国性交通网的建设与方志图经的编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交通网的建设又加强着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强盛的王朝为了加强对本土及番邦的控制,必须建设交通网,包括漕运、海运和驿站。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各种地理知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地理资料。故就皇朝而言,编纂方志与加强统治是相辅相成的。方志中的人文价值导向其实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一致。清朝方志重人文,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不外官吏政绩、士绅行为、寡妇贞操以及地方学者之著述或吟咏。[3]”上述皆体现了深刻的皇权特色,如皇言、恩泽等,还有一些如星野、祥异等虚无缥缈之说,传统的方志还有代圣人立言,替君主歌功颂德的特点。宦迹、人物、烈女则为官员、士绅、民众提供行为典范,从而起到教化作用,文征艺文之流亦多议论,上述诸类皆有着价值观的导向。而加上方志本身具有的官修性,教化性与官修性相结合,从而达到弘道之效果。凡此种种,皆阐明了修志这一行为本身的政统性。
晚清之时,国家危势呈时不我待之势,而为强中国,讲求西学已经成为新教育的主流,而提倡中体西用者重点在西用。清末民初,外有列强窥伺,内有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思想亦为动荡,如何改造中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断。到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趋新趋势依然明了,陈独秀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文学。[4]”由此可以看出时人趋新并去旧之倾向,所以“方志废止案”应运而生,方志却依旧得以留存。但是“方志废止案”之后的方志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志。
从上文可知传统方志体现了政统性,而民国的方志则体现了科学性。朱维铮先生将中国古代关于“学”与“术”概念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这种“术”,科学在学科中应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明确指出,中学以致用为要,由此可知,当时之中心在于西学为用。其后五四运动,“赛先生”——科学一经传入便引起巨大反响,此点于方志中有深刻体现,学科的分类打破了原有方志的编纂方式与篇目形态。民国以前的方志编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统,而民国方志编纂的目的则是为了“资政”,一改前朝方志的重人文轻经济的倾向,民国方志的中心逐渐往工业、经济转移,这就要求方志吸收现代科学知识。民国的志书十分注意运用和吸收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测绘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的积极成果,从此点看民国时期的方志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性与科学性。
而民国方志中比较有代表性为黎锦熙所编《同官县志》。《同官县志》依照《方志今议》之拟目,全书共三十篇,每篇为一卷。冠以序、目、凡例为卷首;跋为卷末。目录如下:卷一为疆域总图;卷二为建置沿革志;卷三为大事年表;卷四为地质志;卷五为气候志;卷六为地形志;卷七为水文志;卷八为人口志;卷九为生物志;卷十为农业志;卷十一为矿业志;卷十二为工商志;卷十三为交通志;卷十四合作救济志;卷十五为吏治志;卷十六为财政志;卷十七为军警志;卷十八为自治保甲志;卷十九为党团社会志;卷二十为卫生志;卷二十一为司法志;卷二十二为教育志;卷二十三为宗教祠祀志;卷二十四为古迹古物志;卷二十五为氏族表;卷二十六为风俗志;卷二十七为方言谣谚志;卷二十八为人物志;卷二十九为艺文志;卷三十为业录。
从篇目上看,如志书中出现的《工商志》《地质志》《自治保甲志》《军警志》《司法志》《党团社会志》《卫生志》《教育志》皆为当时新传入事物在志书中的反映。而《地质志》的内容皆经过科学测绘,地图、等高线、地层名称都按照国际通用名称,部分名词辅以英文加以解释。植物也是一样,传统方志按照习惯名称,不加分类,而《同官县志》中按照属、目、科加以分类,并对其性状详细描述。而《矿业志》下属之目主要记述了煤、瓷及水泥的产量,开采方法,运销及价格。而篇目内容最多者当属卷二十七《方言谣谚志》(计二十二页),此篇页数冠绝诸篇,详细记述了当地的方音(声母、韵母),方言词汇分类、俗修类征,通俗文艺。同时编纂方志亦运用了社会学调查方法,编纂方志之前,编纂者拟定《陕西省第三区各县续修方志工作准则》及《陕西省第三区各县续修方志预拟篇目及采访须知》,并参照城固县志委员会所印之调查表式,共制定挨户调查表式三十种,挨保调查表式十一种。乡镇调查表式二十二种,其他调查表式五十种,印发各县,以资参照,这样的调查方法深受社会学的影响,参与《洛川县志》编纂的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科长史宗沂于《洛川县志》序中形容道:“分门别类,悉据科学。”这种全面采用现代科学、社会学的方法深受西方科学的影响,使得方志不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呈现出了多学科交叉的新形态。黎锦熙更是明确提出方志“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而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劭力子亦在《黄陵县志》序中写道:“今日编纂志书时,应利用天文台气象报告,方能配合时代。志书必须随时修订,早为识者所公认,而今日修订志书,必须为科学工作,则更为明显。……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这是更值得赞美的。[5]”由此可见在民国后期,志书的科学化已为各界有识者所公认。
传统方志到民国方志的转变,深受“世变”之影响,修志者群体由原来的官员和儒家读书人转变为接受科学民主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所以方志的篇目设置和内容都呈现出了新的形态。其实质是编纂的话语权由儒家体系转向近代西方科学体系,此点与当时的社会意识与思潮保持一致。
二、由官本至民本——方志内容的书写的改变
受世变之影响,与赛先生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德先生。“君史”与“民史”之争为20 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热议的话题。“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君史之敝,极于今日。[6]”由此可见境外思想对中国史学之浸染,受此思潮的影响,批判君史,倡导民史为清末民初学者之诉求。至于五四运动,德赛二先生一起走入中国,民主之风愈盛。方志学与史学关系紧密,亦受民主之风气的影响。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方志中出现的新篇目,这些篇目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出现的新生事物,其中如黎锦熙所纂的《同官县志》中的自治保甲志与司法志;黄炎培所纂的《川沙县志》中的议会志和司法志;余绍宋主持修纂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中的议会、行政、司法;陈训正修纂的《民国鄞县通志》中的议会、司法、自治。从上述志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民国的五权分立,五权则是考试权、监察权加上西方的三权,三权分立是共和政体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孙中山对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改造,而五权分立的基础为民权,而这种政治体制正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的政体形式,而五权分立则体现了西方文明与中华传统的结合,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五权分立皆建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此点在民国方志中得到了体现。
而自治一词更具民主之风,孙中山强调建设地方自治是训政时期的基本任务,国民党建国大纲程序中,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大时期。而训政时期以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以完成县自治为主要工作。县为训政实施单位,亦为地方自治之单位,而地方自治要者有六,清户口、立机关、订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7]”孙中山主张训政时期,以县为基本单位,在地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建设,移官治于民治,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为进入民主宪政打下基础。而此点在志书中得到了体现,志书受到自治之政策的影响,而志书中的资料又为自治提供资料借鉴。此外,工商志、农业志、矿业志等的设立,记载了大量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内容,如工商业活动,交通信息,农产矿产种类、产量、销售等。
民国方志学家在篇目中删去了体现皇朝特色的“训典”“皇言”“恩泽”等篇目以及玄而又玄的“星野”“祥异”等,如《洛川县志》因其前志“星野”旧说几近玄虚,而当时已经泾渭分明,所以删除,仅存旧志“井鬼分野,入尾十度”一语,以存掌故。而在民国志书中人物及艺文的地位及占比降低了。传统方志重人文且重古而轻今,而民国方志学家则重现在而轻过去,重演变而轻不变,重群众而轻个人,在《民国鄞县通志》中人物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而只作为文献志下属一部分,不设人物传记,而《洛川县志》二十余卷,人物仅余一卷且还为承袭前志,仅寥寥数页。这与旧志极重人物的做法大相径庭。
而方志对于城市的书写亦发生了变化,一座城市的建筑其实是一个地方的纪念碑,而方志记录的建筑往往具有社会与政治的双重属性,而方志书写中对空间的叙述与当时之政治、思想、文化密不可分。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几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公署廨舍、坛庙、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这是我们认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8]。《汾州府志》中有关城市的篇目依次为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坛壝、关隘、营汛、驿铺。而《光绪顺天府志》中京师志包括城池、宫禁、苑囿、坛庙、祠祀、衙署、兵制、官学、仓库、关榷、厂局、坊巷,水道、寺观。地理志则包含城池、治所、祠祀、寺观、村镇、边关。从旧志的城市书写中可以知道,在古代,城的功能为防御,所以城墙为城最重要之标志,城的存在也给了居民与驻军安全感,中国城的发展受政治影响最大;军事防御次之;商业和交通等的需要,都只是陪衬。一个地方被选为行政中心,就可以筑城……中国目前至少约有2500 座城,其中绝大多数是各级行政区划的治所[9]。所以古代志书通常将城池放在第一位,城池为城墙与护城河,是古代城的基本特征,也是城之所以称为城的基本要素,而其次则为宫城和官署一类,在京师则为宫城,在地方则为官署。对于大多数发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盛官”——诸色公署公廨、营房及官员、士绅(官员候选人)、衙吏住宅与苑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最重要的位置,并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10]。无论是宫城还是衙署其政治寓意是不言而喻的,建造宫城与衙署象征着对于城的掌控,象征着皇权(官方权力)对于城市空间的大一统政治控制,而祠祀、寺观等则扮演了公共角色,维持了统治的权威及构建大众社区两方面。最后才是坊巷、村镇一类。由此可知在传统方志关于城的描写中政治为第一位,其次为军事,最后为商业交通及生活。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对于城的叙述方式几近消散,如《同官县志》疆域现势包括位置及面积、行政区划、各乡沿革及所属保村谱,城池及衙署等仅以图附之。方志中这种对于城的叙述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影响的削弱以及方志的关注方向的下沉,由“官”转向“民”。
究其根本,民国方志学家的做法与当时的社会及思潮紧密相关,“民史”作为一种史学思潮也是戊戌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与戊戌维新运动同步产生的。戊戌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保种、保国、保教’,其具体实现步骤非常明确:“在政治上,开制度局,设议会,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现政法体制的转型;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创造发明;在社会教化上,从德、智、体等方面塑造‘新民’[11]”,民史的提出在本质上是适应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回应民主思潮与社会改造的对传统史学的革新,通过革新,让国民史观成为与国民国家相适应之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2]。而方志也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到了民国后期,方志从关注极少数的个人到关注普罗大众,从而实现由“君志”或者说“精英志”到“民志”的改变。
三、民国方志学家知识结构的改变
其实无论是西学东渐之风,抑或是世变之急,确实对方志影响很大,但是最直接影响方志编纂的永远是方志学家。方志的变化的实质是修志思想的变化,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都与民国方志学家的知识结构密不可分。而探究民国方志名家如李泰棻、傅振伦、黎锦熙、甘鹏云、寿鹏飞等的知识结构有助于阐释近代民国方志的转变。
上述五位民国方志学家年纪最大的是甘鹏云出生于1862 年,其次为寿鹏飞1873 年,最小的是傅振伦出生于1906 年,五位方志学家皆出生于清末,前有东学西渐之风,后又时值中国历史之未有大变局,从魏源到郑观应再到孙中山,师夷以制夷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士人从西学,孙中山亦以学西方而超西方。中国晚清的士人正由重经学经典转向积极入世,救亡图存,此时西方思想也逐渐传入。在此潮流之下,中国的士人呈现出了一种趋新的趋向,西学日尊,形成了一种“新的崇拜”。其中尤其是甘鹏云、寿鹏飞,甘鹏云提出重今事民事,寿鹏飞亦提出了志义民本。此二人接受教育于新旧之间,甘鹏云先后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传经书院,后进入武昌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曾取得进士授工部主事衔,入进士馆学政治法律三年,1906 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入度支部。民国成立后,历任杀虎关税务官监督、吉林国税厅厅长、财政部佥事、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而寿鹏飞出生于绍兴书香世家,父亲为塾师,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优贡,次年优贡会考获一等第一名,调为东三省屯垦局科长,兼屯垦养成所所长、东三省盐运司科长,曾被派去日本北海道考察,回国后撰《调查日本北海道拓殖报告书》。二人皆接受过旧式教育,后在政府中任职,甘鹏云主攻财政领域,寿鹏飞主攻农业,二人皆从旧教育中走出,在接受新教育后完成向专业性官员的转移。而黎锦熙、李泰棻、傅振伦出生年代较之甘、寿二人较晚,他们都接受了新式教育。黎锦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1914 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教员。后担任西北联大国文系教授。李泰棻18 岁考入北京大学专攻史地,但因学杂费高昂,遂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22 岁时,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傅振伦192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执教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并在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处任职。黎、李、傅三人皆接受过新式的分科教育,也都曾留校执教,三人的知识结构更偏向西方的分科教育体系。黎锦熙提出方志四用“科学资料”“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李泰棻主张方志性质属史,内容应“三增”,体例当反映时代性和科学性。傅振伦提出详今略古,广增门类,注重科学方法。三人的修志主张皆有明显西方分科体系的影响,修志思想趋近科学。
晚清科举制的变革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如新式学堂的建立、课程设置与学科分类的转变、教科书内容的变化,加之社会各种思潮迭起,传统读书人思想的变化使晚清民国方志思想总体处于新旧杂陈、逐渐趋新的状态,五人的修志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加之自身的独特教育经历,其知识结构发生了改变,反映在方志中就是修志思想的改变。
四、结语
民国时期是思想激荡的时期,同时也是方志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方志学家对明清的方志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了较多新的观点。受世风之影响,民国方志最大的特点即为科学性与民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意识与学术思潮密不可分,方志的转型实际是方志学家修志思想的改变,而方志学家修志思想的改变体现了民国方志学家知识结构的改变。而这种知识结构的改变受到世风之影响,其实质是修志思想从儒家体系转向近代西方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