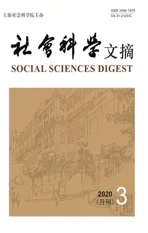魔幻现实主义与幻觉现实主义文学生产肌理的比较
2020-11-17
两种美学内涵的历史嬗变
幻觉现实主义生成的元语境是德国19世纪著名女诗人安内特·冯·德罗斯特-徽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的诗歌。经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克莱门斯·黑泽尔豪斯(Clemens Heselhaus)在其专著《安内特·冯·德罗斯特-徽尔斯霍夫的作品与生平》(1971)提出,幻觉与现实两词的矛盾组合被视为矛盾修饰法。他指出她的诗歌多涉及一种濒临死亡的或宗教的幻觉和梦境主题,“将细节的观察、现实的刻画与丰富的想象力相结合,处于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但又不属于二者中的任何一种”,由此称为幻觉现实主义。1981年《牛津20世纪艺术词汇大全》将其作为一种超现实主义风格收录,定义为“精细正确的细节描绘,但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描述外部现实,而是用现实手法描述梦境和幻想”。30年后,诺奖征用这个术语为莫言的创作风格命名,在时间和空间语境上存在了双重跨越,在译介转换中经历了延宕误读,因此值得析出它与莫言创作的汇合点,进而定位莫言带给它的新坐标。它在瑞典语版本中为“幻觉般的敏锐”(hallucinatorisk skärpa),在英、法、德、西班牙文报道中以“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这一概念形式出现。我们承认以概念形式为莫言文学定性比描述性的语言更为直接决断,更有助于与魔幻现实主义形成泾渭分明的格局,尽管这个概念本身与莫言的创作存在差异。所以中国学界在接受这个名称之余,需着手以莫言的艺术风格去丰富和发展甚至重塑这个概念的内涵。以此为目标,本文以莫言与马尔克斯的创作为例,比较分析以莫言为标识的幻觉现实主义与以马尔克斯为标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生产肌理。
1983年德国学者林德勒(Burkhardt Lindner)教授在《新批评》刊物上发表的《幻觉现实主义:彼得·魏斯的作品〈抵抗美学〉,注释和艺术的死亡区》一文。他认为彼得·魏斯发表《抵抗美学》的同时附上的作家与众多政治流亡幸存者的访谈对话以及作品创作过程的细节记录,与作品文本构成互文,让读者发掘到一种不同于历史书写的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如作家所言:“已经分辨不清哪些是真实的(authentic),哪些是创造的(invented),它们都是一种真实”。这样的“真实”用彼得·魏斯为其剧作《托洛斯基》的评论来解读:“(该剧)有些方面的纪实,更适合采用一种幻象的,近乎幻觉的形式。”这种创作方法让林德勒认为“幻象(vision)、幻觉(Hallucination)和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具有将令人怀疑的判断复制成真实的生活感受”的效果,属于幻觉现实主义。“就是试图将众多人物特点融入进一个富有广度的、开放的、神秘联系的、同步发生的记忆网络中的‘我们’”。最终“追求到的是一种类似梦境的真实”审美旨归。这段表述具象地解析了幻觉现实主义的建构肌理,即凸显其个体的、主观的现实特性,兼顾了心理衍生的诸如梦境这类艺术形式的运用。2001年,美国伊丽莎白·克瑞莫(Elisabeth Krimmer)教授研究安内特·冯·德罗斯特-威尔斯霍夫诗歌中的死亡意象及其女性作者身份的特点时,认为“向梦幻世界的过渡因为有对自然环境的详尽描述作为铺垫而更加引人入胜”,肯定这个矛盾修饰法的美学价值。此外,较之文学批评,这个术语更多出现在影视评论,强调以梦幻式的蒙太奇影视记录现实的方法让观众对真实现实产生新鲜的体验而受到推崇。
相比幻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名称出现之初有同样的“矛盾情结”(ambivalence),其肇始于绘画而声名远播于文学,同样历经40余年。1925年德国画家弗朗兹·罗(Franz Roh)首次使用它,旨在倡导表现主义渐行渐远的抽象态势向现实主义的回归(这个回归成为后表现主义),即对“奇幻的、异域的、遥远的对象”的青睐,这奠定了魔幻现实主义审美内涵的基本框架。选用magic而不是mystic,是因为罗要明确笼罩被表征的世界的不是神秘,而是“隐藏在这个世界背后的悸动”,且以此区别于超现实主义。1927年这篇文章被译介到西班牙语世界时,“魔幻现实主义”被置于后表现主义的前面而得到凸显,引发拉美文学界的关注。1948年委内瑞拉作家阿多诺·乌斯拉·皮耶特里(Arturo Uslar-Pietri)将这一表述应用于拉美文学,定义为“现实世界的第三维度,是人原初心智中真实和幻觉、现实和超自然的融合”。但1943年底亲身旅行拉美的侨居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拉美作家家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提出“美洲的神奇现实”一说,指出“神奇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和人为的综合想象颠覆或超越现实发现的,而是根植于自然与人的时间和空间现实之中。在这里无需昭告,拉美多变的历史、地理、人种和政治让不可能的并置和神奇的混合发生”。虽然择词不同,但他更好解读出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美学的核心内涵。1955年,美国魔幻现实主义研究学者安吉尔·弗罗(Angel Flores)提出魔幻现实主义的起点为1935年,以博尔赫斯发表的文集《耻辱通史》为标志。因为博尔赫斯受卡夫卡的影响,尤其对“现实与奇幻融合”的叙事手法的借鉴,以及对《变形记》的西班牙语译介,都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体,包括对马尔克斯产生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促成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今天来看这种影响和后来马尔克斯对中国当代作家包括莫言的影响模式非常相似。1967年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及批评家路易斯·累尔(Luis Leal)以“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的句式,清晰阐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性。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没有像超现实主义那样应用梦幻母题;也不像奇幻或科幻文学那样扭曲现实或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也不像心理文学那样强调人物的精神分析,他们从不去发现行为背后的理性或没有能力去表现他们自己。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像现代主义那样是一场由创造精美形式为旨趣,也不以创造复杂结构为旨趣来主宰的美学运动。[……]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魔幻文学。它的目的是表现情感,而不是唤起情感”。而关于魔幻现实主义是什么,他说:“魔幻现实主义尤其是通过通俗的或优雅的形式,以精致的或淳朴的风格,以封闭的或开放的结构表达出对现实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现实并努力去整理现实,去发现事物、生活和人类行为中的神秘。”这个阐发与罗存在本质上的共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魔幻现实主义与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本质上的差异。此后在魔幻现实主义风行的半个世纪里,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从没达成一致过而持续被阐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德巴·加伦特(Jeanne Delbaere·Garant)对英语语境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类型的三类划分:通灵现实主义、神话现实主义、志怪现实主义。从这里不仅可以窥见魔幻现实主义的多样性趋势,还会发现其难以界定的缘由恰恰是,这种超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民族美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大大激发出了新的文学生产力,强劲地驱动了文学的不断创新发展。
由此可见,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从魔幻现实主义到幻觉现实主义,再一次验证了文学形式陌生化进程的轨迹。超现实主义实现了对呈现现实的艺术路径和技术的理论建构,其背景是心理科学,其创意之奇属于发明;魔幻现实主义追随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指导,但其背景是人类学,其创意之奇属于发现,再现了原始思维之妙。所以欧洲超现实主义在创作个体的追求新奇发明中走向小众,而魔幻现实主义则专注拉美民族的独特心理,凭借人类原始思维审美下的集体无意识,获得世界读者的认同和赞赏。这一与民族美学结合的方法论,取得了毫无争议的成功,并启发各民族美学的喷发,包括唤醒中国作家对本土现实和艺术宝藏的开掘,促成了幻觉现实主义的生成。面对幻觉现实主义的降临,国人没有准备,瑞典学院院士、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教授解释说:“我们采用hallucinatory realism(HR)一词,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MR),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这里谈到的“过时”,意在标识HR与MR的不同;“影响”则肯定了幻觉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如诺贝尔奖官网发布的莫言简介中所明确提及的“他叙事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印记”,但真正使其担起不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则是其凸显的本土化因素。当时不懂外语的莫言在媒体最初误译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语境下曾毫不犹豫地表达这个HR应是“与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这样“中国的魔幻”(相对于拉美魔幻而言)注定要让原西方语境下的基于精神分析的幻觉现实主义概念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仅以现实描绘梦境的艺术手法发展成为一种融入了“中国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社会”所建构出的凸显中国民族美学要素的幻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魔幻现实主义和幻觉现实主义美学需依托公认代表其美学的作家马尔克斯和莫言的作品来具象呈现其生产肌理,所以依据文学创作原理从“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因素所营造出的“独特的腔调”,比较作家文学生产的价值观、文学生产的美学路径、文学生产的本土化策略。本文基于这三个维度论述经典魔幻现实主义和幻觉现实主义文学生产肌理的不同美学旨归。
文学生产的价值观:“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文学生产的价值观决定了作家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它在马尔克斯和莫言对文学生产资料上所选择和处理的叙事立场中反映出来。他们分别截取了社会现实的两端,莫言选择发生在社会底端民间的故事,而马尔克斯选择社会顶端的权力阶层。在叙事立场上,莫言运用普世情感支撑起自己的民间叙事立场,盯着正史所轻视的人写,写他们的现实处境,写他们人性中的崇高、伟大,把他们被压抑、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声音从传统高雅文化的层层遮蔽下透射出来,这种举轻若重的责任感成为莫言作品的现实力量之源。而马尔克斯则以剖析拉美民族政治独裁统治的精英立场,锚定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穿越权力的重重迷雾,揭示出这些人的残暴虚伪、孤独胆怯、荒诞猥琐,对拥有至高独裁权力带给民族深重灾难的他们进行戏谑与嘲讽,在沉痛的历史现实深处传递给读者举重若轻的气度。
文学生产的美学路径:自出机杼与破茧化蝶
马尔克斯和莫言通过创作个性实现各自美学的经典化,这两种美学特色主要由作家的本土文化背景及其自身文学素养两大因素的化学反应来成就的,而这两大元素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混杂”和“系统”。如果说系统和混杂的本土文化生态塑造了莫言和马尔克斯的文学生产审美意识,那么混杂的和系统的文学修养则催化了莫言和马尔克斯的个性审美路径的走向。马尔克斯的本土文化背景是混杂多元的,文学修养则是系统的。多元文化赋予他感性的自由,系统修养赋予他严谨的欧洲式理性。他以西方美学价值观与方法论理性审视这个土著文化、欧洲文化、非洲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交融混杂中的美学样态,找到以魔幻统筹审美、催化艺术、诗化现实的力量,从而自出机杼,析出代表拉美文学巅峰的魔幻现实主义经典美学。而莫言的本土文化背景是系统的,文学修养是混杂零散的。系统的中国悠久文化不知不觉中润染了莫言的美学底色。混杂的文学素养留给他不畏经典束缚的自由天性,让他后来没有受到本土文学经典系统性的限制与禁锢,也没有在西方文学强大的影响下失去自我。所以面对厚重的传统,莫言既顺应也破坏,既解构也重构,但从未动摇其传统儒释道美学思想的基础;面对蜂拥而入的西方文艺思想,他先拿来,再改造,再制造。这种对传统的和外来的大胆借鉴、大胆实践、大胆表达的气度,决定了他在破中探索出拥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莫氏美学路径,通过破茧化蝶蜕变出当今世界文坛代表中国美学意蕴的幻觉现实主义。
文学生产的本土化策略:“移植”与“嫁接”
在世界文学共和国中,魔幻现实主义和幻觉现实主义美学都以民族特色见长,其生产策略都明显呈现对外来文学的本土化趋势。横向地看,这种趋势的背后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所推动的跨文化交流版图延伸密切相关。纵向地追溯,马尔克斯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质料主要来自欧洲文学,尤以超现实影响显著;而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本土化的质料则来源更广,可以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整个西方文学,不过以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最受关注。外来元素的汲取既有利于促进本土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本土文学的世界接受,马尔克斯和莫言的成功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此。比较它们的本土化策略,我们采用“移植”与“嫁接”这对植物学上的概念来描述。移植指将植物移动到其他地点种植;嫁接是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马尔克斯笔下的隐喻、创作手法无不可以找到欧洲的根脉。他正是将这些欧洲理性移植到拉美的感性文化与美学土壤中,培育出魔幻现实主义美学之花。莫言的美学则一直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即使接受的外来影响都是翻译的,而翻译后的西方文学在莫言看来已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这注定了他在本土文学审美的枝干上嫁接外来美学的枝芽,催生出今天幻觉现实主义的硕果。可见莫言文学生产肌理构成以本土为主,外来为辅,马尔克斯则恰恰相反。这样本土和外来两方面因素的融合模式决定了他们文学生产美学的不同样貌。
这两种策略直接影响了他们作品的世界接受。莫言多依托本土历史事件,以此开掘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引发共鸣,但基于历史的建构往往提高了跨文化理解的难度,让作品的传播遭遇困境,这也是其译者葛浩文的感受。而马尔克斯则跳出历史,在建构微观生活时空里投射拉美历史,将读者的期待视野建立在行动的演绎中,这极大减少了阅读背景知识的阻碍,便利了其作品的世界性传播。
综上所述,从魔幻现实主义与幻觉现实主义概念沿革,可见出这组概念自产生到进入文学生产的曲折历程,发现历史和时代因素已无法界定其统一的内涵,但民族性成为他们的归属港湾。马尔克斯和莫言的文学生产实践推进了魔幻现实主义与幻觉现实主义的经典化,让两种现实主义文学生产及其肌理的分析与比较有了代表性的文本支撑。从中可见,这两种美学都扎根于民族本土心理现实传统,马尔克斯给混杂与狂欢的拉美文化以理性,重在拉美美学体系的建构;莫言对固若金汤的传统价值体系以挑战与突破,重在张扬其个性的美学重构,在这里它们“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文学生产价值观、自出机杼与破茧化蝶的文学生产美学路径、移植与嫁接的文学生产本土化策略得以辨识和归纳,进而使读者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文学生产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