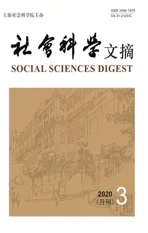“权力政治论”还是“共生机遇论”?
——与金应忠教授关于战略逻辑的对话
2020-11-17
2019年12月3日,笔者收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耆宿金应忠先生的新作《为什么要倡导共生机遇论?》(以下简称金文)一文,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金文紧紧围绕国际战略判断的学理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在批判了建立在“实力-权力论”基础上的“力量对比论”的基础上,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鞭挞了时下国际学界盛行的“权力转移说”,深刻反思了西方战略思想中的内在困境,指出了“共生机遇论”的逻辑机理以及保卫和平发展机遇期的鲜明主张。金应忠先生对国际战略判断的思考是文化自信的产物,其中展现出了深厚国学功底和哲学功力,这对新时代的中国走出西方战略思想的窠臼,开创新的战略思想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迪意义。
国际战略判断的核心问题之我见
把握国际形势,做出明确判断,是国际战略判断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常做常新的问题。战略的核心就在如何通过“庙算”和“运筹”力求做到“舍鱼而取熊掌”、两利相权取其重或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战略判断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致人,还是如何不致于人,两者为战略之道的一体两面。
战略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古今中外皆有无数英雄豪杰对战略有着不凡造诣。若从哲学基础来看,西方的战略智慧倾向于将战略放在战争目的之下,以战争统摄多样的战略手段,着眼于战,服从于战,是一种以准备战争、谋划战争、打赢战争为中轴的冲突主义战略观。近代以来,从殖民扩张到世界大战,从冷战到霸权,贯穿西方战略思想史的主线无非就是将战略理解为战争之道。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与西方人的战略智慧相比,中国人的战略智慧的确有非同一般之处,它不以战争为目的,而以非战为目的。中国的战略智慧追求非战,是一种以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追求长治久安为中轴的和合战略观。贯穿中国战略思想史的主线始终是将战略理解为和平之道、大同之道,这和西方的战略之道大异其趣。
事实上,金文所界定之战略与西方之战略在内涵存在些许差异,西方之战略在认识论上已经呈现“主客体二分”之格局,其所虑之重全在于如何摆脱敌我之困境,故有权力政治之学和权力转移之论,说到底是在心底深处的“找敌人”。而金文之战略在认识论上实在是源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民胞物与”“和合共生”之道,其所念兹在兹皆为如何探索如何实现玉宇澄清、天下大同之境界,故有和合共生之学和“共生机遇”之论,说到底是心底深处的“找朋友”。“找敌人”与“找朋友”,一念之间,战略之内涵迥异,如此而已。
战略之道与时代之问
事实上,战略之道,奇正之间,找敌人和找朋友是战略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战略之道的精髓是变化之道,战略之道的最本质特征是法无定法,通权达变,只有不断积极回应各种内外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才能真正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玄妙境界。战略虽源于军事,但不局限于军事,商业、政治、社会各界皆有其战略之道。然而,在不同领域,内外条件变了,战略之道就必须相应变化。在军事领域,战略之道确乎全系于胜利之道。相比军事战略之道的集中,商业战略之道的细分,政治战略之道的精髓在于持中守正,确立起为各方接受的正当性基础,社会文化战略之道的精髓在于和谐共生,努力实现相互呼应、彼此包容的文化繁荣局面。因此,在进行国际战略判断时,必须既要把握全局的主要矛盾,又要充分照顾不同领域的特殊矛盾,统筹协调,合理谋划,方可找到积极稳妥的战略路线图。
战略之道非独因地而变,更在于因时制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表现形态也是根本不同的。战略最初表现为军事战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军事与其他领域是分开的,一切都取决于战场。战略特指军事战略,战略和政略是分开的。近代以来,拿破仑战争推动战略实现创新,尤其是普遍征兵制、军事技术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打破了军事战略主导的局面,政略与战略相互耦合,军国大计与民生安危彼此共生,逐渐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国家方略。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了,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逐渐统合,国家战略形态又发展成为大战略,亦称“高级战略”,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领域挺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让大战略思维遇到了新的困惑。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赢得了伊拉克战争,却输掉了伊拉克的和平,打出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当今国际战略的态势越来越呈现为“非对称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战略格局下,传统上那种依靠统筹国民资源打总体战的大战略思维已经不足以对付非对称的威胁,全球化时代的战略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战略已经不能仅靠大战略了,而是依靠新的战略形态。此种新的战略形态是什么,还在探索之中。
当今世界处于转型过渡期,各种因素叠加震荡,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机会同在,如何辩证分析转型过渡期特点,统筹兼顾机会与挑战,成为一个国家战略判断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习近平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提出的“时代之问”,面对这一时代之问,中国在战略上应当做出何种抉择,是争霸、决斗、还是卫和、合作,的确是一个事关中国民族复兴大局,同时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课题。
“权力论”与“机遇论”之间的新战略学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之问”,的确需要重新审视当今世界与当今中国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从战略之道的高度做出明确的判断和慎重的选择。究竟是沿着西方战略界流行的“权力论”逻辑,一步步步入所谓的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另辟蹊径,追寻中华文明古老战略智慧的“共生论”逻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战略之路,这就是金文贯穿始终的主线,也是其智慧闪光的所在。金文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批判,而是阐发其“共生机遇论”的鲜明主张,他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机遇论的学理基础,从人类社会的共生性和群体性、对当今世界多元多样与和合共生的认识来解释“共生机遇论”的逻辑,尤其是从共生性需要的角度,分析了机遇何来以及如何抓住机遇的问题,许多地方不乏智慧见解,令人拍案叫绝。
在金文看来,“共生机遇论”的逻辑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共生性、群体性,认为万物互联之中有万物“共生性需要”,相互具有吸引力而非“权力论”看重的排斥力,社会行为体之间可以通过社会交往获得共生性机遇,因而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而排斥或拒绝交往、交流至少意味着拒绝发现共生性机遇的可能。显然,这是一种关于世界可能性的哲学智慧,并非是世界必然性的理论逻辑。相比“权力论”的必然性科学逻辑,“共生机遇论”强调的是一种可能性哲学逻辑,至于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机遇,金文看上去还没有令人信服的严格理论解释。同时,“共生机遇论”还忽略了风险和成本的问题,万物互联能够创造机遇,但也会积累风险,当下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逆全球化思潮从根本上都是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太大和成本过高的一种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存在着非理性的情绪,但的确揭示了全球化带来的高风险和不平等等问题,这一点也是“共生机遇论”必须要重视的。事实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世界绝非方外之人,皆为棋中之子。无论如何批判“权力论”之荒谬,均无法说服西方大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权力论”与强权政治在方今之世亦难免大有拥趸,面对“时代之问”,“权力论”仍然可能是为数不少的国家所持有的战略之道。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中国选择“权力论”,还是选择“机遇论”,在其战略实践中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很可能是两手并用,奇正相合,是一个战术问题。“权力论”和“机遇论”的关系也许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比的关系,这是本文与金文见解的不同之处。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的战略判断也需要基于力量对比论,提高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本领,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合作。但是,在另外的条件下,中国的战略判断就需要基于共生机遇论,从共同利益出发,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换言之,“权力论”有解释权力角逐的优点,“机遇论”有拓展合作的优势,在战略判断中应权衡再三,不可偏废。只有两个方面都搞好,在战略上方能更加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传统的战略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和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国家利益复杂化了,国家的身份和认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家之间争夺权力和斗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战略问题已经不再是国家之间争夺资源的权力斗争,而是国家之间争夺网络合法性及其影响力的斗争,全球化时代的战略问题就是网络间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etworks)。国家之间的斗争很多时候不过是网络斗争的表现形式,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就是如此。如何才能把复杂的网络整合为一个新的政体(new polity),是新战略学的新问题。如何将领导者个人、团体、组织与官僚、国家特性、国际体系、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整合到一个框架内,是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战略学构建中的“文艺复兴”阶段
在新战略学构建过程中,非西方文明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金文则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国学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指出了一个构建新战略学的出路,那就是挖掘非西方文明所蕴藏的战略智慧,实现战略文化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事实上,与以地中海文明为根基的西方文明一样,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为主要代表的非西方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了丰富的战略智慧。近代以来,因西方文明独领风骚,势头强劲,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非西方文明战略智慧的释放。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针对中世纪秩序的危机,用复兴希腊精神(理性精神)和罗马美德(爱共和国)的所谓“文艺复兴”实现了战略智慧的创造性再生,进而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秩序和在主权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数百年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矛盾,西方现有的战略智慧已经越来越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因此,近年来在国际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核心在于针对困扰主权国家秩序的恐怖主义、金融危机、非西方群体性崛起等挑战,需要进行战略文化的创新和世界哲学的更新。不过,在西方思想界看来,“第二次文艺复兴”更多强调对西方地中海文明古老智慧的挖掘、整理和提升,而金文则强调跳出地中海文明的框架,倡导挖掘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众多非西方文明的战略智慧,从古老的中华文明智慧(崇德、尚义、重礼)、古代印度文明的智慧(顺世、包容、多样)和古代伊斯兰文明智慧(和平、顺服)中来寻找解决当下世界问题的药方。从历史上来看,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延续了上千年,在化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方面蕴藏着大量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当下世界面临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以中华文明为例,五千年的文明积淀蕴含了宝贵的战略智慧,完全可以成为21世纪新战略学构建的基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一家的世界,认为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强调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德行和民心是战略智慧的核心,中国人的战略思想不完全是战略智慧,而是更复杂的政略智慧。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让精神和敬德保民的政略思想受到严峻挑战,但始终没有动摇其根本。在春秋时期,敬天保民的思想设定了“天下无外”的轨道,凡接受周礼教化,均可得到支持。在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各家均强调以民为贵,重视民对国的基础意义,这一框架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自秦汉以后,礼定天下、以德服人的战略与政略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渐成正统,尤其是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后,历经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最终儒释道三教合一,百川入海,确定了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战略思想。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家与国同构,民和邦共生,导致中国人处理各种纷争的战略智慧在于强调天下一家,化方外冲突化为方内伦理,一切政治关系均被赋予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以伦理之玉帛,化天下之干戈,以修身之自省,止四起之刀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是一种有容乃大的战略理想,对内追求克己,对外追求和谐。协和万邦的核心精神是“和”,非在战,而“和”之根本在于“中庸”,讲究持中贵和。在中国文化看来,中庸之道强调中正平和,不偏不倚,认为过犹不及,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即便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文化强势打击下,中国士大夫也固守“中体西用”的主张,不愿意放弃中华文明的正统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追求和平共处,梦想“环球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贯穿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方面面,凝练成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和合天下的战略之道。因此,中华文化中的“协和万邦”与“和合”思想是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母体,也是指引中国战略思想的精神支柱。“和合”精神强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圆融,不以任何一方为重,其所追求的境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共生机遇论”之学理不足
“共生机遇论”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上海“共生理论”的新发展,对于“中国学派”建设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就学理而言,仍有一些有待阐发与完善之处。一是它过于偏重哲学的可能性逻辑,从而忽略了哲学的现实性逻辑,也忽略了科学的必然性逻辑。哲学思考是我们研究现实问题最深厚的认知基础,哲学的可能性是我们创新理论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金文在提倡“共生机遇论”时,完全让该理论置于一个哲学可能性的环境之中,明显缺乏哲学的现实性和科学的必然性。二是它过于偏重共生机遇与合作,从而忽略了其所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问题。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共生机遇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