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生态批评:佛教唯识学与生态批评跨学科探索①
2020-09-10张嘉如
[美]张嘉如
(纽约市立大学 布鲁克林学院,美国 纽约 11210-2850)
一、前言
“唯识学”源出原始佛教里面的十二因缘法,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佛门各宗的必修功课。唯识学又称为有宗或法相宗,由唐代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基大师(632—682)创立,对华严宗、天台宗与禅宗皆有深刻的影响。唯识学具有完整的体系和精密的理论,可与西方哲学分庭抗礼,因而成为近现代中国佛学的显学。民国思想家如熊十力、梁漱溟、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无不研究唯识学。关怀生命最终极问题(如众生因果相续、生死流转)的唯识学,在世俗的层面上,呈现出心理学、认识论与现象学等面向。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兴起,台湾和香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佛教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唯识学跨学科的世俗应用。(1)佛教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的成绩斐然,在此略举一二:林国良:《荣格心理学与佛教唯识学思想之异同》,《上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蔡伯朗:《佛教心心所与现代心理学》,《中华佛学学报》2006年第19 期;陈兵:《佛教心理学》,台北佛光出版社2007年版;吴汝钧:《唯识学与精神分析:以阿赖耶识与潜意识为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7年版。
本文尝试探究唯识学与生态批评之间的关联,寻求跨学科对话的可能。唯识“内观式”的意识审视,可以反思“外观式”的西方生态环境论述,提供一个对其追本溯源的诊断。在尝试建立“唯识生态批评”跨学科论述之际,首先要澄清的是,作为一个佛教派别,唯识学的宗旨有着宗教和本体形而上学特性。唯识学所阐述的 “万法唯识” 的缘起观,旨在“破除众生对世界实体见的执着,深入明白依他起的道理”,从而获得解脱的智能。(2)陈玉玺:《建构佛教心理学的新典范——唯识学八识学说的现代省思》,《新世纪宗教研究》2006年12月第5卷第2期。又,印顺导师提到唯识可以分成知识论唯识和本体论唯识两种,认为佛教的唯识是先出于知识论,又达到本体论的。参见印顺法师:《唯识学探源》,台湾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然而,本文不将唯识派视为宗教学,而是关注唯识学观点的世俗应用。作为一门精密的意识分析学,唯识学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了解意识(识)、感官仪器(根)与环境(尘)的关系,以及意识改变外在环境的能动力。
由于西方环境人文论述与佛教研究重视伦理与实践面向,而非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做“戏论”的探讨,因此“唯识生态批评”可在当今物质主义转向的生态批评论述之外,提出一种新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唯识生态批评可与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量子物理学里面物质“内部之间纠缠互动”(3)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gag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07.的概念比拟,解构我—它对立的思考模式。唯识生态批评强调意识与外境流转互摄,突出“观察仪器”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构成佛教生态哲学的本体认识论基础。与此同时,唯识生态批评也可以指导生态实践。作为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其终极层面上除了关注存有意义(即如何解脱烦恼),又带有入世关怀,呼唤世间有情的行动意识(如菩萨道里的六度万行实践)。唯识生态批评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扩展了人文领域里的生态思想和批评视野,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建设。(4)如蔡伯朗在对唯识学进行的伦理学、心理学层面的分析中指出,与其将“唯识无境”理论当成哲学上存有论或认识论的分析,还不如把它当作一个佛教里联系之实践基础,扩展他所称之为 “唯识故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的觉知境地,以达 “彻底去除在佛教伦理学上的恶”,也就是 “错误认知以及会导致痛苦的负面心理与情绪”,进而获得佛教伦理学目的上的善,也就是解脱和智能。参见蔡伯朗:《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2017年第82期。
生态论述的唯识转向的贡献有三:第一,建立非二元(或“不二”)唯识观与本体认识论。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唯识学可以解构主客体二分思维对“环境污染”的错误认知,解决二元思维下产生的主体与环境客体的对立思考模式,提出心物不二的本体论,即一切现象(不管是物质的或是心理层面的)皆源自第八阿赖耶识。第二,解构个人或自我中心主义。“唯识无我”一说解构以物质色身和个体为单位的 “自我” 观,强调从意识出发的、辗转相依的“无我唯识”整体论思想。第三,建立“唯识生态批评”。唯识学对意识系统的构建,以及对意识、感官器官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互依缘起)的精密分析,亦可提供一个探讨从意识出发的生态道德与美学论述的平台。本文无意以唯识学专家自居,去爬梳唯识学复杂的历史脉络。(5)参见欧崇敬: 《唯识宗的“解构与超解构型态存有学”与创造转化的重塑叙述》, 《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2年12月第2期。在跨学科的语境下,尤其是环境人文的框架里,我感兴趣的是俗谛层面上的唯识学可以为当今生态批评论述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此阶段性研究仅为抛砖引玉,唯识瑜伽行派博大精深,难窥究竟。盼更多学者入列,为建构东方环境人文论述尽一番心力。
二、“环境污染”与“碳足迹”的错误认知:心意识转向的必要性
环境危机、全球暖化等议题早已成为日常语汇。然而,无论是媒体、政治家或普通群众,在论述环境议题之际,往往将环境问题视为一个外化的客体,号召人们去制伏、控制或对抗,“向污染宣战”等口号不胜枚举。这些口号背后潜在的多半是一种二元式的想象思维:人类与大自然恒处于敌对状态;人类必须不断与自然抗争,使之完全屈服于人类科技文明。在探讨环境危机的根源问题上,环境哲学家戴维·马考利 (David Macauley)认为,环境危机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是一个 “将元素与环境驯化”,“改造并社会化驯服非人类的东西、动物与地方”所产生的危机。(6)参见David Macauley, Elemental, Philosophy: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as Environmental Ideas.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9, p.1.这种驯服关系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是人类中心主义呈现出的对他者的征服想象和欲望。瓦尔·普姆伍德(Val Plumwood)认为,此二元性阶级思维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带来的心物二元意识形态的危机,同时也是文明的危机。(7)参见Amitav Ghosh, 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在想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上,除了隐藏着“人类—非人类”的二分法,在面对无法驯服的自然时,更呈现出罪归自然的现象:不是将极端气候想象成会威胁报复的对象(如 “大地反扑”),就是将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归结于无辜的物质,如二氧化碳等气体化合物。这里隐含一种 “想象力危机”。想象力危机并非只是想象力的缺乏,而是在科技现代性话语下,将一个复杂共生的生态体系想象成一个完全为人类服务的花园,二元地划分为对人类有害跟无害的物质。那些不利于人造花园建设的是有害物质,被贴上卷标毒物、超级物体、慢暴力的标签。虽然此标签可以在策略上提高公共健康、环境正义等意识,故而有其合法性;但是从深层非人类视角观之,此举将自然物质污名化,掩盖了“人类世”危机背后的主谋。例如,我们通常将燃烧石油、煤炭产生的有害气体称为 “空气污染”,却转移了真正的污染源——制造空气污染等的人类本身(当然这里所指的“人类”主要是指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制造、生产与消费体系下的个体)。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归结于环境本身,就是在政治上推责给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将环境污染归罪于一个集体主义机器(如国家或资本主义),我们便继续重复着无需改变的生活,仿佛环境问题只源自立法不周与执法不力。主流社会的消费中产阶级则置身事外,扮演无辜的受害者。而资本家没有消费者督促,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劳工和地球进行剥削。这种由推卸责任而衍生的恶性循环(国家、消费者与企业间互相推责)所造成的 “环境危机” 远比没有想象力来得更可怕,因为它揭示的是人类本身缺乏内观审思的能力。这就是“环境危机为人类文明危机”一说之故。不难发现,“环境危机”下的卸责式话语,隐藏了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那就是,全球暖化、物种灭绝等“环境问题”不仅是环境管理的失职。从根源上看,这些都是主客体二元思维下产生的排他 “自我” 意识(包括自我观、个人主义、家族主义、部落主义、国族主义等身份认同意识)过度扩张的后果。因此,当前的 “环境污染” 论述掩盖着一个更深层的人文危机,此危机包括认知、思考与想象各种层面。同时,环境问题也指向“问题意识”的危机,即固守二元思维,错误地将环境污染归于外界因素。因而,在探讨环境议题之余,我们不仅要从环境科学入手,关注人类制造的碳(环境)足迹,更要审视我们在地球上烙印下来的、那些看不见的足迹,尤其是法国作家兼佛教僧侣马蒂厄·里卡德(Matthieu Ricard)提出的 “意识足迹”(8)Ecology, Ethics and Interdependence: The Dalai Lama in Conversation with Leading Thinkers on Climate Change, So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18, p.101.。
“物质导向” 的生态批评多半围绕在“碳足迹”和减碳等相关议题上。(9)对物质生态批评理论有兴趣者,请参考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Theorizing Material Ecocriticism: A Diptych”,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Vol. 19, No. 3 (Summer 2012), pp.448-475.此本无可厚非,但是对“碳足迹”的追寻却忽略了其根源问题,即我们的意识或心识。环保不仅是政策法规或科学技术的问题,它更与个人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历史轨道、艺术文学,乃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世间万物的生成(包括环境污染),无不与意识相关。因此,“意识足迹” 除了影响“手足迹”(经由人为产生活动而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地球产生影响足迹。所以生态建设的进行必须将意识纳入考量。“意识足迹”反映出我们对环境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多半由一个无所不在的 “我”的意识所主导。一个以非生态为导向的“意识足迹”衍生出去的 “碳足迹” ,实为导致生态危机背后更可怕的隐形慢暴力。因而,内观式的唯识生态批评,可以让我们理解到意识在环境危机里所扮演的角色。
最早系统地将“心识”纳入生态论述探讨的为格雷戈里·贝森 (Gregory Bateson)。他在1972年的《心识生态》一书里提出“心识决定论”。贝森认为,“心不只具有人的属性,也包含宇宙的属性”;在解构心物二元时,他写道,“我们通常认为外部的‘物理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与内部的‘心理世界’是分开的”,然而“心识世界——处理讯息的世界——不受限于皮肤之内”。(10)Gregory Bateson, Steps toward Ecology of the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461.贝森将“我”视为宇宙意识的一部分,并不是那么特别,因为它属于一个更大的心识的一部分。(11)参见Gregory Bateson, Steps toward Ecology of the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471.因此,心识是问题症结,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定位我们的心识。在唯识学探讨上,我以“意识”一词取代“心识”,(12)我以“意识”取代“心识”的原因是“意识”指涉的层面是认识论,可以避免落入唯心论的巢窠。再者,这里的“意识”指的特别是唯识学里面的“八识”。强调错误认知对于环境的危害,也就是: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类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万物主宰,认可适者生存说(而非复杂性与共生说)。在贝森看来,人类要存活下去,唯有重新定义“生态”与“存活”:将生态视为“想法之网” ,进而以 “想法系统生存”取代 “适者生存”。(13)参见Gregory Bateson, Steps toward Ecology of the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467.要解决环境危机,应该将我们的心识扩大,并对现实世界的实相做出正确的理解。只有转变人类狭隘、扭曲的意识(转识成智),才有办法扭转当前的环境危机。(14)唯识学里面“万法唯识”一说并不是对外在环境的否认,详见蔡伯朗:《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2017年第82期。
三、论心谈识,莫过“唯识”:唯识学略介与生态批评应用
解决污染问题,首先要破除此二元主客体认识论的迷思。唯识学的“万法唯识”和基本佛教里面的“依他起”(六根、六尘与六识之间的互为缘性)的思想,可以扮演介入者 (interventionist) 角色,反思当下物质取向的生态批判论述。接下来,我简述唯识学基本概念——意识、根、境、污染、万法唯识、转识成智,然后阐述这些概念如何构成唯识生态文学批评论述的观念基础。
(一)前五识:纯粹感官经验
大乘佛教里的唯识学派将意识分为八识,由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识),加上第六识(又叫作意识)、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五识借由五根(眼、耳、鼻、舌、身根)缘于五境(色、声、香、味、触,也就是外在的物质环境)。此五识在未进入第六、七识之际,为纯粹的感官体验,不具认识作用。以眼识来说,眼的意识得以产生必须先有眼根(眼睛的器官、神经等),借由眼睛如录像机般全然地摄入外境、产生影像,进而生成对形色世界的认知。然而,此时的“录像机影像”尚未进入第六识,因而不具认识、思考与分别作用,单纯呈现为感觉印象。第六识将前五识所摄入的影像进行认识、分别与思考,进而产生主客体的价值判断(如善恶、喜好或美丑)。前五识与第六识合称“六识”。
由于前五识与第六识几乎同时作用,一般人无法进入第六识前的纯粹感官经验。(15)缘于外境的六识即称为“五俱意识”,即意识与前五识俱时同起作用的意识,帮助前五种意识产生种种区别。正如作家吴明益所言,区分第四识(舌识)与第六识极其困难,因为“味觉的感受恐怕跟念头一样快,我们常在吃美味食物时瞬间感到‘原来如此’的释然,我怀疑修行者能完全将它去除”(16)吴明益:《蝶道》,台北二鱼文化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106页。。从胜义谛(意指胜于世间世俗义的存有实相道理)的层面上看,这句话里面的“瞬间感到‘原来如此’的释然”,指的是顿入无分别心介入的“不二”体性(即主、客体合一,或根、境、识三者合一的感受)的顿悟的境界。禅宗所谓的“言前道德”由此展开。俗谛上来说,“味觉的感受恐怕跟念头一样快”说明前五识与第六识近乎同时作用,很难将它们区分。也正是因为获取“言前”纯粹经验十分困难,因而,我认为有必要发展出“言后”(或第六识)道德论述。
(二)第六识:思考与再现的功能
第六识的思虑与再现功能在文学艺术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六识不仅可以缘外境(如吃到食物,并品尝出其美味),也可以不依靠外在环境因素,不与前五识俱起,只缘内境而单独活动。此缘内单独活动的意识分为四种,即独散意识、定中独行意识、梦中独行意识、狂乱独行意识。其中定中独行意识需要极高的定力,全神贯注地集中思考一件事情,或观察意识的流转与变现。不仅是禅修者,哲学艺术家都能进入此定境。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会饮篇》中描述的连站一天一夜全神思考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很好的哲人 “思定” 的例子。由此可见,第六识为开展人文活动的意识场域。再者,第六识的再现功能也凸显其中介的角色,可以进行过滤和翻译。譬如说,物境要进入语言,甚至是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系统,必须通过第六识(也就是进入识别、思辨、审美判断等活动范畴)得以进行。由此可见,第六识既是文艺哲活动的意识载体,也是开展生态批评的绝佳场域。
(三)第七识:烦恼与我执的生态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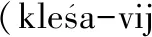
佛教将烦恼与污染并置,虽然讲的是烦恼作为轮回的起因(因我执而产生烦恼与相继的轮回),却也暗含着一丝生态环境论述的意味。然而,在做此跨学科转化之际,或者说,在世俗谛与胜义谛之间术语互用时,我们有必要先厘清其定义。以 “烦恼”一词来说,烦恼在佛教的实存层面上的意义为:因错误理解真实世界而陷身的苦痛。如果说烦恼是一种对真实的错误认知,那么,此番定义的生态伦理层面的意义是什么?它又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当下对环境污染的认知呢?
(四)第八识:唯识本体与转识成智
唯识学里面最重要的意识为第八识,又称为阿赖耶识、“如来藏”或“种子识”,意为“含藏”。它具有收藏包含前七识所造作出来的善恶诸业种子的功能。也就是说,第八识能够将前七识运作衍生出来的思想和行为,重新熏回到第八识,成为未来的种子(因),因而形成一个因果回路。此“种子说”原本是用来解释因果轮回的,这里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俗谛的诠释与应用。从唯识缘起本体论的观点来看,第八识的功能,可分为相分与见分两个部分:向外变现六根(感官器官)和六尘(外在环境),此为第八识的相分;向内变现前七识,则是第八识的见分。可以说,整个物质界和意识均为阿赖耶识(宇宙意识)的虚幻意识“变现”,或者用生态批评的术语来说,我们的世界是通过“物质化”或“现象化”而生成的。
在阐述阿赖耶识作为形构世界的主体与其伦理意义时,佛教学者蔡伯朗指出,有情生命之间,以及有情生命与器世间(物质环境),有着依存互融又不断变动的关系。首先,他指出第八识的主体地位以及万物共构生成与依存的关系,“阿赖耶识除了作为能作(亦即能认知)的主体之外,同时也是形构世界的主体…… 在此除了彼此涉入彼此之外,彼此之间尚有休戚与共的依存关系,人不是孤立的 ,世界也不是与个人无关的,但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人(众生)与人(众生)之间是彼此交融,互相影响、互相涉入的。”(21)蔡伯朗:《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2017年第82期。由于万物共同形构成此世界,因而,要如何转化、净化自我心识的认知,实现与他者的互动,才是瑜伽行唯识派的终极关怀和伦理诉求。这里以第八识作为本体认识论出发的 “关系说”(即众生与众生之间的“彼此交融,互相影响、互相涉入”),可以作为唯识生态伦理学的前提。因此,“识的转变”(即转识成智)凸显出意识具有能动性,可以将染污的第七意识转变为接纳平等的生态意识,从而为建构 “生态我” 提供论述与行动基础。
(五)“八识转四智”:生态批评应用
由宗教出发的唯识学不但自身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而且提供了实践的蓝图。因此,在探讨唯识生态批评论述的实际意义上,我们必须进入唯识学探讨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转识成智的学程。唯识学提出“八识转四智”之说,将八识所转的智能分成四种: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和大圆镜智。在转智的实际操作上,六祖惠能法师曾提出的 “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圆”的次第说法,强调要转变我们的污染意识,必须先从转化第六、七识开始,只要转化了第六、七识(在因地中将此两识转成妙观察智和平等性智),前五识和第八识就随之转化了(即“果上圆”,在果上得到成所作智和大圆镜智的智能)。要注意的是,这里我将转识成智做一个世俗或入世的诠释与应用。这里意识的转变,如妙观察智,不是在修行证道的层面上来谈。在世俗层面上,妙观察智所产生的智慧意指对内外境的一个非二元的直观。
由上可以看出,转识成智也是一个去除自我污染意识、训练正确判断力的过程。就第七识的转智来说,虽然被称为污染意识(也就是第六识依着它而起污染),但第七识也有其正面积极性(也就是第六识依着它而清净)。当第七识的“我执”减弱时,在进行自然书写之际,会倾向选取一个比较“无我”(非人类中心)的态度来书写此书写者以外的事物。同时,对前五识进行了识别的第六识,在转识成智过程中,也倾向于一个 “妙观察智”的意识转换描述,在对自然的观察中获取博物志式的认知,而不再以生态殖民者的姿态对自然进行剥削,或以资本家的视角对自然进行工具性的消费和利用。唯识生态论述旨在建立一个相依共存的平等共同体,纠正人类特例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颠覆将人类放置在生态体系顶层的阶级式结构。
就发展唯识生态批评论述而言,平等性智有助于呈现自然书写里的生命价值与生态道德论述。去除个人或人类中心主义意识(也就是将第七识的我执意识转化成众生平等的智能)也可以帮助作家观察大自然,以及在记录、写作过程中,敏感地注意并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他者”或生态系统的投射。同时,众生平等的智能可以让作家和读者接受不同物种的独特生物性,以及不同感官器官和意识所衍生出来的不同的世界观与感官经验,进而发展出一个多物种美学和伦理学。
四、言前、言后的道德与美学说
唯识再现说与生态论述里对再现与真实的探讨,以及言说主体和道德动能,有许多可以对话的地方。在阐述佛教的缘起法相,即自然现象的道理时,学者鲁·乔纳森(Rune E. A. Johansson)认为,早期佛教并没有想象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世界处于动态生成的过程(dynamic process)之中, 不断生成,同时由我们的感官意识、思想欲望等所建构。(22)参见Rune E. A. Johansson, The dynamic psychology of early Buddhism, London: Curzon Press, 1979.这并不是说我们和世界不是真实的。物体真实地存在,但我们对物体的感知,为物体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客观和主观的分裂从未发生,意象形成的主观过程实为物体存在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佛教的唯识观不同于西方的唯心论,因为“一般的唯心论,只涉及唯识哲学的第六意识,而佛教所说的识,不但包括第六识,还有第七识、第八识等非常微细的心识活动”(23)星云法师:《星云大师文集》(佛教丛书,宗派6)。网址:http://www.3fo.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49&item=63&bookid=2c907d4945ac514c0145c0bf2cc60099&ch=8&se=4&f=1。检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威廉·沃东(William S. Waldron)指出,唯识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同在于,唯识里面“这个了别认知的意识的现起过程,受限于感官器官与感官物体”;此类说法也得到科学家的认同,智利生物学家汉伯托·瓦雷拉(Humberto Varela)和弗朗西斯科·马图拉纳(Francisco Maturana)认为,“没有任何东西独立于认知的过程。也就是说,没有东西客观地存在于结构;没有一个在地图制作之前的一个预先给予的领域:地图制作本身产生出领域的特征——”(24)Capra qtd. in William S. Waldron, “Buddhist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Thinking about ‘Thoughts without a Thinker’”, in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Vol. 34, No. 1 (2002):1-52, 31f, p.271.。此类观点更是呼应了最近生态批评论述里的“解构转向” (deconstructive turn),尤其是凯瑞·沃尔夫 (Cary Wolfe)提出的“文本化的自然” (textualized nature)。生态批评学者提姆西·克拉克 (Timothy Clark)认为,此说法为针对文本性和互文性相关联的存在模式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论点:与文本性和互文性相关联的存在模式更普遍地表征现实。(25)参见Timothy Clark, “Deconstructive Turn in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in Symploke,January 2013,21(1):11-26.
需要注意的是,唯识生态批评与强调主体性、身份认同政治取向的生态批评无相妨碍。以这个因缘和合而成的“我”(文化身份认同的我,如性别、阶级、种族、物种,等等)来言说阶级或身份差异所带来的诸多环境正义问题有其急迫的正当性,因为阶级剥削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这个“我”的存在是一个假象、无定性的,于因缘相互生成过程里凸起,如海洋里的小水滴。由于世间种种的差异性衍生出来诸多问题,一个具有价值判断、辨别是非的主体便有其必要性。故而,唯识生态批评可以权宜地承认主体的方便存在。
(一)禅宗与生态批评:言前道德和美学
言说主体性和再现与真实的探讨,为当今的种族生态批评 (ethnic ecocriticism)的核心问题。克里斯汀·施密特-基尔布(Christian Schmitt-Kilb)在探讨生态批评里的主体性、再现与真实问题时,指出生态批评由于内部分化(开展出性别、种族的种种政治认同的批评),尚未回答生态批评如何面对再现真实这样的问题。他列举了一些不同派别的学者对真实的看法,如深层生态学者阿伦·奈斯(Arne Naess)、布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凯瑞·沃尔夫(Cary Wolfe)等人的观点。随后他指出,这些学派之间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拒绝将语言(或逻各斯)视为自然的他者,反对将语言对自然的统御合理化。他们也拒绝人类运用工具性语言控制进入语言系统的东西。(26)参见Christian Schmitt-Kilb, “Untranslated landscape: Recent Poetic Prose of Kathleen Jamie and Paul Farley/Michael Symmons Roberts”, in English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6, p.27.这里,唯识学比较接近沃尔夫的解构学说(也就是我们所认知的自然为一个再现的自然,因为它必须进入人类意识认知系统)。在进一步阐述此再现与道德的关系前,我先稍微触及语言前际的道德和美学论述。
生态批评与唯识学所指涉的真实的异同性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生态批评下的真实指的是一个尚未进入语言再现的自然(或非人类物种)世界,而唯识里的真实为清净无染污的真如佛性或真心,在禅宗意义上指向大自然,如赵州禅师(778—897)的前庭柏树子。正因为这样的相似性,唯识学与生态批评道德论述存在着对话的可能。罗伯特·马泽克(Robert Marzec)指出,生态批评的道德和美学论述着重的是语言前际的真实,进而开展出一个“言前” (speaking before)的道德和美学言说。如迪拉德(Anne Dillard)笔下所经验到的化身为雪松的光,让她激动地“站在全是火的草地上”,理解到生命原为此刻而活。(27)参见吴明益:《蝶道》,台北二鱼文化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49页。此时主客体合而为一的“言前经验”,是宗教经验上的,多半以美学的话语表述出来。继之而来的,就是道德人生的开始。这里的道德就是“言前道德”。中国百年来的禅宗在表述“言前美学”和“言前道德”之上,已臻至成熟。禅宗在引导学人切入当下“不二”的真实经验时,除了留下无数公案教案和具有艺术价值的禅偈,十牛图里面所勾勒出求道的十个阶段里面的最后两个阶段,更是点出“语言前际的真实”与道德的关系。第九图“返本还原”,可以将之归类到美学的范畴,与最后一幅“入尘垂手”里所描述的精神境界(即自性所映照出的法相),以及后续返入社会的六度波罗蜜菩萨行,可以将之视为一种“言前道德”的实践。
(二)唯识学与生态批评:言后道德和美学
继马泽克的“言前”的道德论述之后,施密特-基尔布发展出另一个“言后”(也就是进入语言再现之后)的道德论述,即“言后道德”,指自然书写中呈现的意义和其相应的价值取向。回到自然(或生命)书写文类来说,他认为,将一个尚未被“翻译”(即尚未进入语言符号系统之前,也就是前五识所缘的五境)的风景转化成自然书写,是一种“言后”实践。此实践有两层意义。首先,就生命书写的意义来说,作者借由写作来深入了解自己以及环境对他们的意义。在此层面上,作者将他们成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尚未进入语言系统的non-place)赋予一个声音与表达方式。第二,就生态批评的意义来说,借由观察这些曾经一度被过度管理的地方“解放”出来,用传记的形式重新展现野性,作者帮助将自己生长的地方“复原”。施密特-基尔布写道:“未驯化的自然的重获野性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我们人类霸权的能动性是否出现在文化风景的建立上,这个‘被缩减、消极的物质界终将重新获得其自身本拥有的动能’。”(28)Christian Schmitt-Kilb, “Untranslated landscape: Recent Poetic Prose of Kathleen Jamie and Paul Farley/Michael Symmons Roberts”, in English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6, p.38.因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个形成人与非人关系、具有创造性的生态系统,认识到“相依互性的风景”。
由此可见,“言后”发声回答了思考自然书写(或生命书写)背后与真实链接的动机。这里施密特-基尔布提出了一个用书写“解放自然”的策略,尤其通过非虚构(non-fiction)文类。这里唯识学可以介入对话的是,虽然唯识不同于物质取向,特别强调物质活力的生态批评(毕竟从唯识的观点来看,器世间或物种世界也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并不是外在的他者),但是唯识对意识的检视与转化的能动力量,能够帮助理解意识在自然书写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迪拉德在观察自然时,不仅“有意识地检视概念本身以及意识的分类,并将之视为审视的主要对象”, 她把所注意到的不同意识称为 “意识的垂直移动”,写道,“内心活动是不断在一个垂直移动上,意识每个小时像长号喇叭一样上下移动。它(意识)梦见意识底层的东西,注意到上层的内容,它也注意到自己本身,并且意识到自身的警觉”。(29)Ann Dillard, “To Fashion a Text”, in Inventing the Truth: The Art and Craft of Memoir, ed. William Zinsser, Boston: 1998,p.144.
迪拉德的表述是西方心理分析学式的,侧重于梦境和潜意识(可算是第六识的梦中独头意识),而唯识学可以与之对话的地方,除了在作家第六识上的探讨之外,更在于作家的后设意识,也就是,作家对自身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的审视与觉知,以及意识与外境的互动。此后设意识正是一位关注意识如何觉知外在世界的自然作家所必须具备的。从唯识视角来看,在后设意识的警觉下,作家能够避免第六、七意识里面“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认知,在行文中流露出一个内观审思的“转识成智”的过程。
五、结语
在面临“环境危机”之际,我们必须要超越局限于“环保式”的意识形态。如加拿大女性主义哲学家洛琳· 科德 (Lorraine Code)所言, 尽管“生态”已经成为热门词语,但人们往往将之和环境或自然混用,而忽略了生态思考更深层的意义,亦即关于“理想的共同栖居” 如何得以实现。(21)Lorraine Code, EcologicalThinking: ThePoliticsofEpistemicLoca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4. 唯识学的本体认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唯识学是如何看待物质环境、寻求建立唯识生态批评的可能性的。此唯识转向论述目的在于,彻底解构心和物的绝对二分,但又不流于唯心论的巢窠。唯识生态道德的意旨为:我们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世界,就必须从改变我们的意识开始。在思考 “唯识生态”时,我们也必然重新扩大了生态的定义。唯识学树立“万法唯心造”的世界观,强调第七意识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所以,清净国土必先清净污染的第七意识,而不是仅仅从法律、行政措施、科技层面上来处理环境问题。我们若有正确的意识,那么我们感官所接触到的,以及第八识所变现的就自然也跟着清净,这就是楞严经里的“心净则国土净”。
唯识学与当前主流的物质主义取向的生态批评看似两个极端立场,但它们之间却有许多相互补缺之处。唯识出发的生态批评贡献在于它将生态批评做一个“意识的回归”。唯识生态批评论述里开发出来的平等方案是以第六、七识转化后的智慧和行动为基础的。存在现象、环境的一切借由再现或翻译得以进入心识和语言系统而被感知(进而加以保护或破坏)。唯识生态批评的任务就是去关注人文工作者如何将文艺哲当作一个帮助读者转识成智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