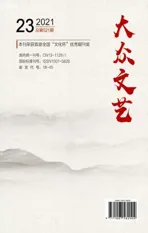回归与超越:正始、竹林玄学中的文人音乐美学
2020-07-12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500)
一、玄学中文人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
魏晋时期哲学的代表形态即为玄学。玄学思想来源于《老》《庄》与《周易》,玄学的探索凝聚深邃的智慧,它将一种“自然无为绝对化、抽象化。以道家思想为主,调和儒道思想。从形式上讲,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而玄学则表现为思辨性的理论。”①玄学本身带有的理性思辨性和理论性的彻底性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玄学的创作思维规律更令此时的音乐美学独具一格。
由于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导致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在音乐美学创作中,文人对“有无”“自然”等范畴的辨析,使音乐的本质、审美、效用、形式特征和价值方面的问题得以被直接探讨。音乐作为文人“推类辨物”之处,超越了功利色彩。魏晋人以艺术和审美作为个体精神的解放与救赎,玄学被融入人的生命,有了精神与实践的属性。音乐本身作为一种人心人情交流的特殊方式,魏晋文人在音乐中安顿心灵,为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物累。新的自然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出现,引发人的审美取向从社会回归到自身,有了超越物质性感知的审美意识出现,使人不再依附汉代经学教条的伦理体系,更注重个体精神的体验、满足与价值。“称情”和“率性”不仅成为魏晋名士的人格标识和理想,也是魏晋玄学论证的核心命题②。此时人的主观玄思达到高度敏锐,使音乐能够从“知政以审音”走向“声无哀乐”,形成道德到才性再到神韵的审美转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超漠鸿而远迹,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嵇康《答难养生论》中“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音声之“美”从无限、自然和人格自由中来,个体有限而生命精神无限的境界通过与“自然”合一来达成。价值观念与生命意识的更新与出现二者互为因果。
在魏晋以前《礼记·乐记》、荀况《乐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都不同程度谈道关于音乐起源及与政风教化的关系问题,较少谈及音乐本身。音乐对人心与人情的交流与感动深深地被道德伦理牵引、压制。“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③太平之世,音乐充满和美与安乐,乱世之时,音乐充满哀伤与悲凉。“乐”不但无法纯粹通过音乐的“声”表达内心的“情”,还要遵守“仁”的道德规范。雅乐要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只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八音克谐”(《尙书·舜典》)的雅乐才被儒家乐论所推崇。“乐”与“礼”并用为治国的方略,行“乐”时情感要和合社会人生各处,作“乐”时又要基于伦理道德与人情民风来建构,这与注重内心体验,投入个人情感而行或作“乐”的意义完全相悖,音乐本身较少有自由独立发展的可能。
魏晋文人将玄学自然观中自然、无为、自在的本质贯彻进音乐美学思想中,对于问题的探讨不仅限于音乐本身,还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以自然观和情理的角度来审视魏晋时人精神深处的变化,可对音乐美学的理解有一种超越历史内在表象的把握。
二、音乐中“自然”的回归
1.王弼音乐美学中的“自然”
音乐作为典型的审美意象而非形象。正始玄学以王弼为代表,他将玄学自然观中自然、无为的本质贯彻进音乐美学思想中,从“无”与“有”之辨,再到“自然”之境界。他以“大音”为本,“五音”为末,以举本统末理念,调和二者。“举本统末”的理念一直贯穿在他的音乐美学思想中。
在老子“大音希声”思想中,“大音”即是无声,它属于感觉范围但又超越感觉的存在。王弼从老子中凝练出“无”作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形而上的本体范畴,认为“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不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④这里“分”指局部,“众”指整体,有声只包含局部,无声则包含“音”的整体。人为的音声,只能表现部分美,而失去整体的自然美,但他并未同老子一样否定掉具体音声的存在。音乐离不开音声,但音声只是作为将我们引领向音乐所表现的一种意境的媒介,单靠人耳无法听见这种意境,要借助人的思维、联想、情感等因素,借助内心的领悟与体知,这显然已超出了对音声单纯的感知。一般人对于音乐的鉴赏,都要经由“有”到“无”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由于王弼“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⑤的理念,他的万物逻辑原点即为“无”,万物“本无”且生成万物,然又回归于“本无”,“本无”可看作无数美的东西之所以为美的逻辑根因与规律。“本无”要超脱音声这种具体事物,给“无”根本性地位,好把握无限抽象的本体。所以“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⑥他并未否定音声的存在,而是将“无”看作具有统摄万物的作用。“大音”必须要存在于具体的大音中,所以王弼“无”的本体论思想中又包含着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万物回归自身、自我实现,都有赖于“无”,“无”是使音声成为可能的最终保证,作为一种实然概念。
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言”的目的是“得意”,前者作为工具,后者作为目的,人不能拘泥于工具,而忽视目的。王弼在此又引入“象”之意,认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得意在忘象”。“象”既包括主体知觉中的表象,又包括记忆中的表象。“意”是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投射流变的产物,是意识境界的心灵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内容。不执着于言辞,而应宣心写妙、言短意长或意余言外,若执着言、象,则无法领悟言外、象外之意,音乐也是如此。王弼对“无声”之美的解释,就是以无声之处求音,呈现“扶弦节于稀,畅微言于象外”的意境。黑格尔认为音声“是在艺术中最不便于造成空间印象的,在感性存在中随生随灭,所以音乐凭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发源地。”⑦,一种无声之外的音声美。音乐的美既有声又无声,当人沉浸在音乐的美的意境中,就会出现一种无法言表的联想和感受。
王弼对老子“五音令人耳聋”的解释是“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⑧。因为老子认为心会因耳听到五音而聋掉真心,“五音”刺激,令人耳聋,这不符合自然生命之道,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五音只能提供人感官享受,无法达于“道”至善至美的音乐境界,应被彻底否定。而王弼的“为腹”即往内,就是人不该因外物所累,被困于“以物役己”中,同时他又并不否定“外物”的存在。由于老子“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反对一切与客观自然万物相对的伦理秩序,否定人情感的自然。但王弼并没有这样,他的自然观使他认为人类社会需要合理、规范的等级制度,需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所谓“大成之乐,五声不分”,“大成之乐”为“无”,雅颂之乐为“有”,“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不同于老子神秘、直观、朴素的自然观,而是将其建立在纯粹的哲学本体论上。他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强调,给人以对自然情感存在的合理的认识,认为“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⑨即为合理的体现。“万物以自然为性”,自然之性即作为一切活动的前提,包括情感在内。他的玄学理论深刻影响了后来阮籍、嵇康的音乐美学。
2.阮籍、嵇康音乐美学中的“自然”
到竹林时期,阮籍、嵇康的乐论在玄学理论中进行思辨、解答,与儒家音乐美学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以一种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来诠释音乐。首先阮籍到后期思想转至道家“自然无欲”,“和”而“无欲”以玄学之道体来隐喻音乐美学,将音乐本体化,主张音乐的本身也是来自自然本源,并非人为产生,而是“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以“开群万物之情气”。并借音乐以感化人心,追求心性本真之自然。他对于乐声善恶的评判都要与音乐自身相契合,认为“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只有“雅乐”或“至乐(大乐)”才能达到“无哀”的要求。这种“至乐”是“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平和自若”的,能让人无欲,心气和定。
阮籍、嵇康思想汇通儒道而形成元气论,自然是充满“气”的无边宇宙,衍生万物,使万物一体,“自然一体,万物经其常”。(《通易论》)视“自然为元气,自然为混沌(玄冥)、为法则(秩序)、为和谐(天和)”。⑩自然为统一和谐的整体,和谐的宇宙自然对人类社会有引导作用,音乐的自然目的就是“顺天地之体,成体万物之性也。”(《乐论》)、“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声无哀乐论》)、“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声无哀乐论》)。这样的音乐美学思想超越了以往群体伦理导向,可以让主体直接对音声美进行感受。
阮籍把本体视作“自然”,实则也是自己的人生行为审美准则。他尚“自然”,认为“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循自然住天地者,寥廓指谈也。”“道者,法自然而为化。”。顺应本心即是阮籍“放逸”“放诞”或“逸荡”人格美的体现。他音乐美学思想里,美和合于“至道之极”,“美”必定是自由、自然,能以平淡无味的方式感染、启迪人心。而且“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乱;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有常处,故其器贵重;有常数,故其制不妄。”这里“八音”“五声”合乎自然本体,“常处”“常数”乃自然之乐前提。他从音乐本体、自性出发,把音乐制作过程中“常处”“常数”内在化,这明显带有一种音声自身具有的形式美的规律意识。同时他强调要在不违逆名教的条件下寻求心灵的自由,如“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调和“有无”,达到音乐的“稀声”之美,通过“和”而“无欲”。(11)但嵇康则亦然,既崇尚“志无所尚,心无所欲”,又承认情感作为人的天性,与王弼有相承之处,认为和乐能给人带来情感快适。嵇康将音声与人情分离开后,强调音乐感人的力量应该回归到音乐内在的自然律度之美上,在《声无哀乐论》中认为“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他在一种纯粹形式意义上来强调音乐内在的和谐、自然的状态。音声之美在于形式、律度的和谐,这即是音乐美学走向自觉的重要表征。
论乐之“体”“性”,即美为自然的观点。阮籍《乐论》中言:“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他主张顺乎自然之性,并将人伦次序与自然之性沟通,如“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殊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平”。“和”被视作音乐美的本质,在追求次序和谐,音乐齐一化的同时,还要顺乎天地万物自然之性。
《乐记·乐本》中载“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认为“大乐”可体现天地万物内在和谐,而能化生万物。但阮籍在玄学儒道融合的思维方式下,对音乐理解产生形而上的一面。在音乐本体与功用层面上,突出“本真”与“自然”。认为“大乐”是“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乐论》),“大乐”则是天地万物的内在自性。他并未完全否定儒家音乐的伦理教化功用,还注重从音乐中求得大道,体悟大道,不能仅沉迷于曼妙的乐声变化重。若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而不能达音乐的本体,那也就不能达于大道。他认为“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乐论》),这是玄学观念在美学中的体现,如上面提到的言、象作为达于言外、象表之意的媒介,若执着于此,就无法达于言外、象外之意,不要执着于言辞,而应宣心写妙、言短意长、意余言外。同样,再美妙的音声,仅是作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的媒介,只有超然于音声之外,打破表象,才能体悟音声之外的自然之道。
三、音乐中“情理”的回归
1.阮籍、嵇康乐论中的“情理”表现
“情理”作为艺术形象的重要内容,是艺术创作过程中主体情感与思想的体现,它同“性情”“情志”“心声”等概念交错或相通。到阮籍、嵇康,玄学则出现了自我深化的一面。
《乐记·乐本》中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则是通过主客体融合,突出音乐“抒情”的本质特点,但此时之“情”还并未达到人的“个性”的情感表达。相较阮籍《乐论》中“因情生诗,因诗有歌,因歌有音,音而为乐;律吕和声,情为声母,天地之性,人之性情”中的“情”是强调顺其自然,由心而生,由人内在的“情”而自发产生出乐。《乐本》中“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表情说,则主张以德抑情、以度限声,为“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的需要,通过情来表现道德性。同样在《乐象》篇、《乐化》篇等,有关音乐的教化与功利性从未消失。所以《乐记》中“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的愉悦之情,则是带有理性约束的情,是一种束缚了人之本性、个性的情感。
汤用彤先生认为嵇康“首则由名理进而论音声,再则由音声之新解而推宇宙之特性”,这与他“和声无象”,“不以哀乐异其度,犹之乎得意当无言,不因方言而异其所指也。”(《声无哀乐论》)的理论相关联。嵇康论乐重纯美,借玄学“得意”之意,认为心不系言,言不能证心,无定旨,同样声只是带有和音,而哀乐则无关和音,主要在于人心中情感的不同。嵇康认为和声“无象,哀心有主”“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度虽众,亦大同于和”。(《声无哀乐论》)
从“得意忘言”的玄学思维下转化至音乐领域的“形神之辨”,有一种追言此意彼得玄学的效果。“重神轻形”在阮籍美学中体现音乐要顺乎人心、万物之自然本性,将音乐本体化,借音乐以感化人心之力量,追求万物宁静与心性本然的境界。阮籍乐论重元气,以清虚、恬淡、“泰志适情”的玄学之道为其美学核心。认为“乾坤简易,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乐论》)他沿着这种理念将“乐”带回到本体位置,平淡简易的音乐才是符合乾坤、天地的大德,顺应阴阳、万物的本性,是一切符合复杂音声组合变化的起源。由于阮籍思想里的传统儒家音乐观念未完全摒弃,令夏侯玄对此进行了批判,为了始音乐的和谐不要与自然界阴阳等之间有任何牵绊、关联,认为“阮生云‘吕律协,则阴阳和;音声适。则万物类’;‘天下无乐,而欲阴阳和调,灾害不生,亦以难矣。’此言律吕音声,非徒化治人物,乃可以调和阴阳,荡除灾害也。……岂吕律不和,音声不通哉?”(12)他的观点与嵇康一致,音乐本身自然情理的特性,即为“和”。由于雅乐在当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远,所以夏侯玄同嵇康一致都是从新的视角来审视音乐。
虽然阮籍音乐美学思想一直被很多学者看作是“矛盾”的结合,但从他所处的不得志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美学思想也较为合理。他对音乐本质的问题,立足玄学又继承、区别于儒家,肯定音乐对于人心的化定作用,美学理念涵盖儒家君臣伦理,讲究次序和谐、合理,认可“礼废则乐无所立”“乐失其序则亲疏乱”“乐平其心”“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又以玄学自然无为、顺应本性、清谈平和等为基础,这样儒道共融的美学思想,使音乐回归于自身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音乐美学观。虽属形而上,但希慕原始之和谐,如“去风俗之偏习,归圣王之大化”,“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乐论》)注重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之美。嵇康也同样关注音乐本身的主客体之纯美,如“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声无哀乐论》)虽论证出“声无哀乐”,但他的理论思辨则系于王弼“得意忘言”之上,对此汤用彤先生的解释是“声无哀乐(无名),故由之欢戚自见,亦犹之乎道体超象(无名),而万象由之并存。八音无情出于吕律之节奏,而自然运行,亦如音乐之和谐。”(13)所以嵇康对于“和声”的自性、本体,则是在音声与人情之间的顺利结合中表现出来的,可二者内在的关系已被分离。
2.“情”与“乐”的分离
对于嵇康“声无哀乐”中情感与音乐的分离问题,我们也可这样来理解,就音乐自身而论,它作用的极限就是让人达到“和域”,这其中是没有哀乐感情的成分存在的。但人听到音乐感动,就会不知不觉将音乐与自身的情感相连。其实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分析,作品在表现某种情感时,就会给欣赏者呈现出某种情感的典型特征。科林伍德说:“某人要表现情感时,……他意识到有某种情感,但却没意识到这种情感时什么,他所意识到的一切是一种烦躁不安或兴奋激动,他感到它在内心进行着,但是对于它的性质一无 所知”(14)。他以直觉—表现论认为当艺术家在表现之前并不知道要表现的确切内容,只有通过成功的表现才知道或直觉到自己的表现内容。如演员表演哀伤或喜悦的人物时,是否此时真的具有哀伤或欢喜之感对于表演艺术而言并不是首要的,也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观众首先是从表演者对于哀伤或喜悦的特征中去判断人物的处境,而后自己内心的各种情感被引申了出来。在中国戏曲表演中,演员在完成喜怒哀乐惧的情感时,是有一套程式化的表演方式的,即使作为演员,也不一定就会采用这套方式来表达出内心真正的情感。同样在语言艺术中,具有丰富情感表达的诗歌并不能证明诗人写作时就同时具有激动、兴奋等情感出现。艺术表现实则与人的内在真实情感有很大距离。艺术并非仅仅通过传达、再现、模仿人的情感特征而实现其目的,它还通过表现情感产生的情境来唤起人的内在情感。科林伍德说:“一个唤起情感的人,在着手感动观众的方式中,他本人并不必然被感动;他和观众对该行动处于截然不同的关系中,非常像医生和病人对药物处于截然不同的关系一样。”(15)由于音乐与其他艺术之间的特殊性,不是一种语义明确或像图像那样具有实物存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明确性,乐音的运动只能证明它作为能指的自身,所以“音乐的本身就是对象,它本身就是目的。”(16)所以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音乐不具有表现情感本身的特征,但却具有表现音乐情感的形式。以此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来由及推理证明完全成立,使音乐中的“情”和“理”都能够回归到人的自身中来。
四、音乐本体的超越:音乐中“和”与“哀乐”
通过玄学“无”与“有”在音乐中的运用,可以深入理解嵇康“和”与“哀乐”的关系。嵇康音乐美学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礼乐对音乐自身的束缚。他运用玄学“推类辨物”的论证方法,以触类旁通的方式,形成对音乐之理的认识,以解决音声与“哀乐”的矛盾问题。“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声无哀乐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音乐本身无“哀乐”之情的论证来达到音乐“和”的境界。因为嵇康心中音乐的本体即为“和”,它超越哀乐,但又能表现具体的哀乐,最终导向自由人格的境界。可见玄学对“有”“无”关系在乐论中的表现,也是一种自由、超越的人格本体追求的表现。
嵇康认为“声比成音”,而音在于“自然之和”。他把这个“和”抽离了出来,“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将人的主观好恶情感从聆听乐音中分离,那音乐是如何实现自身的?嵇康认为从“和”,即至和中实现。他竭力从音乐本体中去除不属于音乐的东西,证明音乐自身所具有的和谐特性“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特别是情感“哀乐者,情之主也”,即心中本有哀乐之情,因感和声而发耳,因感和声之特殊色泽而引起人心的哀乐之情,所以声音只能引发躁静,不能引发哀乐,即“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声无哀乐论》中秦客在第三次反驳嵇康中假设了一个平和之人,在没有任何情感在心中时,让他听各种不同的音乐,则“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即形体躁动,志气激昂,“闻琴瑟之音,就体静而心闲”,就是不同器乐所奏的音乐,会给人内心带来相应变化,有躁动,有安详。如果嵇康承认这个观点,就证明了音乐对人内心的情感还是有细微的影响的。可嵇康反驳认为,由于筝笛琵琶乐器的特点“间促而音高,变众而节数”,而琴瑟音乐的特点“间辽而音悲,变希而声清”,音乐形制的不同,才会使人心中有情绪的变化。筝笛琵琶在古代作为俗乐,而琴瑟则是雅乐,君子之乐,“非君子不能弹也”。所以并未改变音乐“和声”的本质,“和声”是一种通性,“孟静之音,各有一和”,只因音乐的速律变化,但本质仍然是和声,“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所以能引发人产生激越躁动或平稳的心态,但并不能让人产生哀乐之情。和声本无喜惧哀乐之情,但可有特殊之音色,无欢戚之相,但是可有色泽之相,色泽之相即可引发不同的反映。
对于儒家音乐美学中音乐与情感密不可分的看法,嵇康认为“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嵇康将音声与臭味视为同物,为了证明这种物的存在是个体的、独立的、不具依附性的。他把音声与气味看成天地间的自然存在物,这体现出他的哲学宇宙论观。甘苦是物自身所有的,喜怒是人对他们的感受,主客之分清晰而独立。如西方自律论美学观认为“主体(即个人)的自我意识成为哲学认识的核心乃至唯一对象”,相应的美学之思被内化入人的感觉和情感之中。这种自律论审美经验,强调一种“非功利”的主观愉悦性,这种愉悦是同实践的、伦理的、财富的、政治的实用相互隔绝的独立价值(17)。因此可见嵇康对儒家音乐思想予以绝对反驳,而将音声内在的律度之美,视为是自性的、本体的。他提出“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声无哀乐论》),在变化万殊的音声中发现无象无变、恒常如一的“和声”,提出了“和声无象”的乐象观,认为“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而后“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所以“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声无哀乐论》),就是哀乐是先于人心之前的,借“和声”之式被自然带了出来,因而得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而无关哀乐。内心以哀乐情感为“主”,所谓“有主于内”,借音乐而“发其所怀”则为“用”,“主”与“用”被嵇康分得的很清楚。他又以酒来比喻“和声之感心,亦犹醞酒之法人性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声无哀乐论》)音乐仅是声音,仅是和美的音乐,人听到音乐而情绪产生波动,内心欢戚借此触动而宣泄情绪,这是人心主动发出的情感,无关乎音乐给予人情感。所以“以心为主”,实质上还是说的以“和”为主。因为乐的目的是使人心达于“和”,只要人心得“和”那么即使没有音乐,人民也能安乐的生活。(18)
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音乐作品中一整套有组织的声音系统,仅仅是一种声音的表达,而不具有现实存在的情感主体。所以对于“哀乐自以情感,而无关于声”的结论。声音同气味、颜色一样乃是“自然之物”,声音之和美,取决于乐音形式的配合,同时还需借助乐器的辅助表现,由此可见音乐“个性”的独立。对于音乐的内容形式而言,音乐教育家雷默认为,音乐中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有意味的超越性情感,音乐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的所指内容,而是揭示本体深层的情感和深刻思想,希望将创作者与演奏者相结合这样能出现一种共同体验,因而才能把某种真正的情感内容融于音乐之中,给人带来感受—思想的混合物(19)。“感受—思想的混合物”即指音乐的声音形式。嵇康继承王弼“以为为本”玄学思想,提出“和声无象”,认为“音声无常”,将人本身具有的内在情感视为附于音乐之上的各种变象,强调审美因在“心”与“声”的相应中完成,这样的审美体验,简单来说就是“在对音乐的回应中被深深地触动”(20),这种审美体验特征具有多层含义,其中内在性特征,即体验的价值,就是来自自身的、自在的,摆脱实用的、功利的,如“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种受外物刺激的引导,而自然产生不同的情感反映。
嵇康以玄学“推类辨物”的论证方法,使“和”超越音声本体,“哀乐”回归人心,给“声无哀乐”做了严谨而逻辑的证明,让音声与人情分离,这完全超越了传统音乐美学对音乐的束缚,给了审美主体和艺术思想认识一个深刻合理的解释。
五、结语
在每个时代的社会中,总有些人对事物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对宇宙本体论和社会的运行之道有着非比寻常的思考。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文人以“心”作为主体对音乐审美的回归与超越,以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音乐本身的理念出发来探讨音乐。这不能忽视玄学影响下玄远、淡泊、自然和愤世的人格“自觉”的品性的形成。传统音乐美学那种定向对音乐理解的方式当然是无法满足魏晋文人自由精神的需求。知识分子的活动是其禀性的表达,是可供人欣赏的象征符号,是所属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王弼对音乐“和”的解释“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大成之乐,五声不分”认为音声要相互协调应前后相伴,只有回归于自然的状态,音与声之间才会相和,会通合一则和矣。同时以回归本无,回归自然的状态,而达到人内在的平和。到阮籍“主乐宣平和而讥世人‘以哀为乐’”,似嵇“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一样,他们都有对音乐“中和”性质的强调。王弼的玄学理论性更加纯粹,玄学思维处于较为平稳、“宁静”的层面,当过渡到阮籍、嵇康时,他们则在万物浑沦的一体中阐述其音乐美学的理想境界,更加注重音乐的形式美,都视音乐平和淡泊为至美。音乐的功用就在于化定人心、纯化人情,使人和万物能依照各自的本性呈现出来。
以上可见,魏晋玄学被文人用以独特的方式,站在独立思考的超然立场,形成以个体为主的审美标准,透过理性的思辨,令感性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回答了音乐本身自由、独立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
注释:
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中华书局出版社,第3页.
②章启群.《论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古典形态的情感哲学——从历史与逻辑两个角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③(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策林》第六十四目“复乐古器古曲”,据《四部丛刊》本。
④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⑤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⑥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页.
⑦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第1981年版,第349页.
⑧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⑨王弼《论语释义》.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第625页.
⑩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11)叶朗,朱良志.《中国美学通史3·魏晋南北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12)《太平御览》卷十六引,《四部丛刊》本。夏侯玄《辩乐论》已佚,仅存残篇。令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二一.
(1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14)(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The Principles of Art).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15)(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The Principles of Art).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16)(奥)爱德华·汉斯力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17)聂郑斌,王柯平等(著)《艺术哲学与艺术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1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19)Bennett Reimer,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Advancing the Vision,3rd ed.,N.J:Prentice Hall,2003,p.57.
(20)David J.Elliott(eds),Paraxial Music Education: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