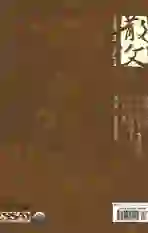里斯本;佩索阿的碎片
2020-06-03蒋曼
蒋曼
观看,以隐身的形式
1912年,佩索阿在文学刊物《鹰》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评论《从社会学角度看葡萄牙新诗》。后来,他和友人创办了《流放》《葡萄牙未来主义》《俄耳甫斯》等文学刊物,宣传现代主义。虽然这些主张也遭受到保守派的非难和讥笑,但佩索阿仍是葡萄牙现代主义的活跃领袖,有自己的追随者。
他的密友安东尼奥·费罗在萨拉查政府主管宣传。在朋友的鼓励下,佩索阿参加了全国宣传委员会组织的诗歌比赛,《音讯》因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获得了二等奖,因此得已出版,这是他唯一的正式出版诗集。据说之所以获得二等奖,是因为他的书在长度上没有达到一百页。
彼时,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沉睡在他的木箱里。他习惯随手写下脑中一闪而过的文句,他的遗稿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翻译作品,甚至占星术。它们散布在笔记本上,活页上,信封、信笺、广告传单和一切能写字的纸屑上。
“我从来不求被他人理解。被理解类似于自我卖淫。我宁可被人们严重地误解成非我的面目,宁可作为一个人被其他人正派而自然地漠视。”
“即使你不能把生活塑成你希望的那样,至少也要竭尽所能。不跟世界接触太多,不要参与太多的活动和谈话,以免降低了生活。”
他严肃地提醒自己远离尘世,也不渴求被人理解或者发现。即使一生都在虚无与迷惑中探索追寻,但他对自己的才华与智慧一直深信不疑。他对同时代成名诗人的批评尖刻直接。他还写了好几首流行风格的诗,只不过是为了说明: “你们看,我也是能写这种诗的,而且写得比你们好,我之所以不写,就是因为我不写。”
“我渴望默默无闻,因默默无闻而享有宁静,因宁静而成为我自己。”
他承认自己和他人的雷同,然而,“在这个雷同的后面,我偷偷地把星星散布于自己个人的天空,在那里创造我的无限”。
不同于狄金森在马萨诸塞的小镇阿默斯特把自己隐居成一个影子的传说,佩索阿的隐身衣恰是城市的平凡与普通。他并不像其他潦倒的诗人,满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愤怒。他的息交绝游是主动的疏离,这恰是他的迷人之处。
世俗名利常常被隐世者鄙弃,而名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人生中比较醒目的定位坐标。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点来确认价值感和成就感,以填满人生的虚无。只不过这些纵横的经纬有时也是蛛网,把人粘附其上,使其失去了开拓游走的可能。但我们总得交换点什么吧。佩索阿拒绝交换宁静与自由,他刻意用平庸单调的外衣来掩盖迥异的天赋和才华。
他对自己死后的成名早有预感。在1914年6月给母亲的信里,他说:“我的朋友们说我会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即便他们所言不假,我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荣誉近于死亡和徒劳,胜利则与腐朽相似。”他的虚无连名声与荣誉也不能填满,注定他只能在现实与虚构的夹缝中寻找某些新的意义。
1935年,感覺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写下决绝此生的告别:“我犹如一个渡者,为了向此岸作别而将桥焚断。我已准备妥当让自己解脱。我要了断自己,可我至少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一部知性的回忆录,尽可能用文字准确地展现出我的内心世界。
这将是我唯一的手稿。我把它留下来,不是像培根那样为了得到后世仁慈的念想。我无意模仿谁,我考虑的只是未来的同道。”
他将和追随者在未来相逢,他度过的每日成为未来人类的心灵坐标,他的日出与日落比贝伦塔更动人心魄。他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不知道明天将带来什么。”
他不仅预知死亡,也预知重生。他制造一个巨大的谜团,如同里斯本那些错综的街巷。两万七千页的遗稿,他在一切可以写字的纸上随意地记录自己。他无意中以这种碎片化的方式写作,却刚好切合了几十年后信息时代的传播。
今天,这些只言片语是最好的向导,它让我们撇开蓝天、明亮的阳光、香甜的葡式蛋挞、鲜艳而古老的建筑,离开观光客的视角,走向里斯本的深处。这个在里斯本驻足三十年的诗人总是以“局外人”的目光来巡视日常。他的疏离确是我们共鸣的捷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诗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段落。他比时代先行了一步。他的文字是写给未来的预言。他的拥戴者潮水般的应和与敬意,他听不见。出生与死亡的两端都是黑暗。而追随者在他的光亮中赶路。
关于异名,一个人的交响曲
里斯本加雷特大街上有佩索阿生前最爱的咖啡馆——巴西人咖啡馆。现在,他的铜质雕像坐在咖啡馆的外面,他不再真实地穿梭在人群中。但是,他还在观看,戴着他的黑色毡帽和圆框眼镜,忧郁而漠然地看着人来人往。他的模样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三十来岁,清瘦,个头相当高,穿着上稍有一些不经意的马虎,坐着的时候腰弯得很厉害。他苍白而平常无奇的相貌上,既没有明显的磨难感平添惊人之处,甚至连一线磨难的痕迹也极难找到。但这张脸上可以说具有一切:艰难、悲痛,或者完全是曾经沧海之后的一种淡然处世。”他跷着腿,沉静地正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如他生前渴望的那样——他总想观看,好像除了眼睛一无所有。他在观看,观看自己,也观察世界的喧嚣。他像一个真正的孩童,在街角的台阶上,饶有兴趣地释放好奇。
推开巴西人咖啡店的深绿色木门,天花板垂下古旧的吊灯和风扇。客人们靠着镜子排排坐,深红色的墙壁上,挂着南方风格的画作,在咖啡机吱嘎的响声中,热闹和嘈杂一如百年前。虽然话题已经从过去的东印度、美洲新大陆变成了欧盟和摇滚马拉松,然而在黑咖啡的浓香中,你看得见佩索阿所能看到的一切。
佩索阿热爱这条大街,除了巴西人咖啡馆,他还为异名者索阿雷斯虚拟了一个会计的职业,他上班的公司连同公寓都在这条大街上。
佩索阿最让人着迷的是他的异名写作,和大家所理解的笔名不同。佩索阿所虚构的不仅是名字,他还帮他们虚构了完整的人生,有相貌,有职业,有生平的故事,有社会关系,还有完全不同的个性,各自的文学主张,甚至安排了他们的出生和死亡。他们的性格和经历有的与佩索阿迥异,有些又有着他本人的影子。
据研究者统计,佩索阿一生共创造了七十二个不同的异名,宛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佩索阿”在葡语中有“个人”“面具”多重含义,无数的面具恰是一个人无数的可能性。在这些分裂与重组中,佩索阿把一辈子过成了三生三世。
佩索阿的第一个异名帕斯骑士出现于他六岁时,即其弟弟夭折那一年,这位骑士用法语给他写信,安慰这个接连失去至亲、陷入孤独不安的孩子。这也许可以让人们略微理解异名者对于佩索阿的一部分意义。
他这样解释道:“从幼儿时代起,我就总喜欢幻想在我的周围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幻想出一些从来不曾有过的朋友、人物。自从我意识到我之为我的时候起,我就从精神上需要一些非现实的,有形象,有个性,有行为,有身世的人物。对我来说他们是那样的真实,就如在面前。”“我为他们编造出姓名、身世,想象出他们的样子——脸孔、身材、衣着、风度——我会立即看到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就这样,我结识了几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朋友。”
最有名的异名者是阿尔贝托·卡埃罗。1914年,3月18日这一天,他用阿尔贝托·卡埃罗这个笔名,在数小时之内,一气呵成写出了组诗《牧人》四十九首中的大部分诗句。阿尔贝托·卡埃罗,佩索阿为他编造的身份是生于里斯本,却长期居住在乡间的自然主义者,没有职业,没受过教育,幼年失去父母,靠微薄的租金生活。他生于1889年,死于1915年。这个田园隐士,和佩索阿一样的天才,敏感孤独。
另一个异名者是里卡尔多·雷斯。佩索阿称此人1887年生于波尔图,毕业于一所耶穌会教会学校,是一位医生,从1919年到现在一直居住在巴西。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拉丁语语言学家和自学的半个古希腊语语言学家。里卡尔多·雷斯追求闲适的田园之乐,把中庸和无为视为人生最高美德,极力摆脱世俗的烦扰,平静地看着生命之河缓缓流淌。这颇有中国老庄的无为之趣。
最顽皮的异名者是阿尔瓦罗·德·坎波斯。这位出生于苏格兰海港城市塔威拉的造船工程师早年游历世界,后来定居在里斯本,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早年写过激昂的颂诗,后来却成了悲观主义者。1929年,偶尔代替佩索阿约会的坎波斯自作主张,写信给佩索阿的恋人奥菲利亚,劝她把对爱人的思恋扔进马桶里。
异名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还有频繁的互动。这些诗人构成了佩索阿诗歌的小宇宙。在这个小宇宙中,田园诗人卡埃罗是其中最重要的核心。他就像太阳一样,而其他诗人,都在行星的轨道上围绕他旋转。他们之间互相评论,多有纸上的交情。
鉴于他祖母疯癫的事实,这种来自于家族的精神分裂基因风险猜测并不算是空穴来风。但和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不同,精神分裂导致的幻觉及想象中的人物给纳什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佩索阿的幸运在于他的主人格能够相当熟练地安放这七十二个异名者。他们友好相处,颇有情谊,即使也有一些促狭与不同的见解,也能彼此宽容接纳。
1928年,佩索阿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啊,政权更迭期间的空白》,并创造了他最后一个异名者:特夫男爵,禁欲主义者,追求完美,由于不能完成作品他决定自杀。此后,他回归到真正的空无之中,一个人守护一个世界。
佩索阿在作品中多次谈到自己的分裂,谈到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是一个群体的组合,自己是自己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异者,“我的内心是一支隐形的交响乐队……我听到的是一片声音的交响”。
众多的异名者见证着佩索阿的矛盾和对立,在想象的世界里,他纵容着自己的无限可能,任由自我分裂和繁殖,他把人性中的矛盾和纠葛发挥到极致。在他创造出的第八大陆里居住着他分离出来的七十二个异名者,他们共同组成的世界比现实更加丰富、有趣。而他早已习惯躲藏在异名者的背后,用虚构来串联真实。千变万化中恰是自我的随心所欲。
“于我而言,我想象出来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对于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我的热爱如此真实,如此充满活力,如此热血沸腾,如此生机盎然。”无论现实中的里斯本沉闷、哀伤或者勃勃生机,佩索阿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隔绝。
宿命的碎片里,能看见一小片的你和我
最新出版的《不安之书》是由刘勇军翻译的,蓝色封面上隐约有佩索阿标志性的圆顶帽和圆框眼镜。这是佩索阿晚年的随笔集结,最先被韩少功翻译成《惶然录》。“不安”比“惶然”似乎更能表现佩索阿思考的深度,虽然他厌恶“思考”这个词汇。他喜欢感觉与观看。“我最爱之物一直是感觉——在我意识视图里记录下来的场景,被我敏锐双耳所捕捉到的印象”,研究者认为不安不是指代烦恼,而是无处不在的不安宁和不确定性。现在我们都是“薛定谔的猫”,正端坐在巨大的纸箱中,在叠加态中死或者活着。
佩索阿不去触摸任何的真实,是怕失去想象的空间,他一直犹豫在纸箱外。于是,才有无穷无尽的幻想可能。即使是对于写作,佩索阿借索阿雷斯表达出不同的感觉:许多时候,他陷入书写的烦闷中,觉得写作是一种自嘲,失去自我,正式的访问,是一种徒劳。不过,他也赞美词语是摸得着的身体,看得见的佳人,是肉体享乐。“我乐于遣词造句。”
佩索阿所发出的碎片化的呓语要几十年后才能以碎片化的密度击中未来的人们。而他的名字被更多人提起,则要等到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到来。这时,人们早已分裂成无数的碎片,在虚拟的网络中,我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设定自己。字节与数据之中,人们开始和佩索阿孤独的老灵魂击节而歌、同声相和。虚拟与想象都在现实的对面,芜杂而烦琐。佩索阿的解构与重组成为我们的镜子,刚好可以瞥见现代的虚无与荒诞。信息时代,人心已经比世界辽阔。
1985年,佩索阿的灵柩被迁入里斯本著名的热罗尼姆修道院。在这座整整修建了一个世纪的古老恢宏的教堂里,他和达伽马一同安息于巨大穹顶的星辉图案之下,而他们的灵魂超越于尘世。当然,生前的他们其实早已超越,只是所有人浑然不知。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