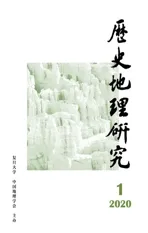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2020-05-30龚胜生石国宁李孜沫
龚胜生 石国宁 李孜沫
(1.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9;3.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
一、引 言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1)龚胜生 :《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疫灾频繁,张剑光(2)张剑光 :《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袁冬梅(3)袁冬梅 :《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袁冬梅 :《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成因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袁冬梅 :《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考证》,《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余新忠(4)余新忠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余新忠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余新忠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余新忠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余新忠 :《大疫探论: 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玉尚(5)李玉尚 :《环境与人: 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李玉尚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李玉尚 :《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从社会医疗史角度分别对唐代、宋代、清代和晚清民国江南地区的“疫病”情况进行了探讨,龚胜生团队则从历史医学地理学和灾害学角度对明代和清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进行了研究(6)龚胜生、王晓伟、张涛 :《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地理研究》2014年第8期;王晓伟、龚胜生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辑。,这里再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作一综合研究,请方家指正。
二、资 料 与 方 法
(一) 研究区域与时段
1.研究区域
“江南地区”在清代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八府一州之地。(7)李伯重 :《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民国时期该区域政区屡经变化,1927年前含江苏省金陵道、沪海道、苏常道和浙江省钱塘道所辖51县,1927年析江宁县城区置南京特别市,析上海县北部以及宝山、松江、青浦、南汇4县的各一小部分置上海特别市,析杭县城区置杭州市。1930年南京特别市和上海特别市改为南京市和上海市,直隶于行政院。1945年江宁县属汤水、麒麟、东流、古泉4乡镇划入南京市,宝山县属大场区划入上海市,1946年松江县、青浦县属七宝乡,松江县属莘庄乡划入上海市,两市辖境扩大。此外,1928年丹徒县更名为镇江县,且由于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江苏省会迁驻该县。江苏省还曾于1927年析无锡县城区置无锡市,1928年析吴县城区置苏州市,但1930年两市均裁入原县。(8)周振鹤主编,傅林祥、郑宝恒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169、507—510页;周振鹤主编 :《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至1948年底,江南地区共辖51县3市,土地总面积为48 942平方千米(图1)。
2.研究时段
文中所谓“民国时期”是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1912年1月1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历时近38年,共151季,即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第4季度(10月1日—12月31日)。

图1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行政区划图(1948年)资料来源: 参照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页)“中华民国时期全图(二)”,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海申报馆1934年版,第30页)图三十“人文详图 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政区图组“民国时期(三)”和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169、507—510页)江南地区的政区沿革编绘。图4—图6同。
(二) 数据来源
1.疫灾数据
文中所用疫灾史料全部采自《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第三卷《民国卷(上)》和第四卷《民国卷(下)》。(9)龚胜生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民国卷(上)》,齐鲁书社2019年版,第1317—2023页;龚胜生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民国卷(下)》,齐鲁书社2019年版,第2065—2758页。该汇编搜集了正史、方志、档案、实录、文集、医案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中国疫灾史料数据库。本文从中摘录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史料717条,这些史料共引用文献279种,其中地方志173种,卫生志22种,民国期刊64种,民国报纸5种,其他文献15种。对这些史料进行细致整理,编制疫情信息(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种)明确的疫灾序列,得到1912—1949年9月30日整个江南地区逐年分季的疫灾分布(表1)和各县在整个民国时期的疫灾年数(表2)。整理过程中,对个别年份、个别县份之疫时、疫种缺失的,参照同年相邻县份的确切记载加以补齐。

表1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县数的逐年分季一览表*
* 表中季节栏中的数字为该季节发生疫灾的县数 ,“ 疫灾县数”是全年疫灾波及的县数,一年之中无论发生多少次疫灾,一个县只计一次。
2.其他数据
疫灾面积和海拔数据通过ArcGIS 10.0软件在30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地图上提取。(10)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 //www.gscloud.cn。人口数据综合《江苏省志·人口志》(11)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苏省志·人口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上海通志》(12)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通志》第1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9—734页。《浙江省人口志》(13)徐八达、王嗣均主编 :《浙江省人口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4—250页。提供的20世纪30年代的数据估算得。水旱灾害数据系据江南地区各县市新编方志、《中国气象灾害大典》中的“江苏卷 ,“ 上海卷 ,“ 浙江卷”(14)卞光辉主编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江苏卷》,气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58、124—160页;徐一鸣主编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上海卷》,气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7、179—194页;席国耀、徐文宁主编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浙江卷》,气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5—161页。、《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公元751—1949年)》(15)火恩杰、刘昌森主编 :《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公元751—1949年)》,地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23页。、《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6)李文海、林敦奎、周源等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3—887页。、《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17)李文海、林敦奎、程等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4页。等综合整理得到。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各县市疫灾年数、平均海拔、人口密度、水旱灾害年数统计表*

续表
* 表中水旱灾害年数是水灾年数和旱灾年数的累加。
(三) 研究方法
1.疫灾序列编制
建立疫灾序列是进行历史疫灾地理研究的基础。从所建立的“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史料数据库”中,提取每次疫灾事件中的“疫时”(疫灾时间: 季节或月份)、“疫域”(疫灾范围: 县数或面积)、“疫因”(疫灾成因: 灾害链等)、“疫果”(疫灾后果: 发病与死亡情况)和“疫种”(疫灾种类: 致灾疫病)等基本疫情信息,以编年体方式建立1912—1949年江南地区逐年分季的疫灾序列。
2.疫灾计量指标
疫灾计量分析是进行疫灾时空规律探索的工具。根据我们已发表的历史疫灾地理系列论文(18)龚胜生 :《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龚胜生、刘杨、张涛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龚胜生、叶护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龚胜生、刘卉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辑;龚胜生、龚冲亚、王晓伟 :《南宋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辑;龚胜生、王晓伟、龚冲亚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文中采用以下五个疫灾计量指标:
(1) “疫灾年数”: 指某一时段内“疫灾之年”的累计个数,确定疫灾之年的方法是,不论疫灾流行的时间和强度,只要某年有一个县域或一支军队有疫灾流行,则确定该年为疫灾之年。如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年年都有一个以上县域发生疫灾,年年都是疫灾之年,其疫灾年数为38年。
(2) “疫灾频度”: 指某一时段内发生疫灾的年数与该时段历经年数的百分比,反映的是该时段的疫灾频繁程度。如民国时期历经近38年,江南地区年年都有疫灾流行,其疫灾频度为100%,在同一时段内比较,因为历经年数相同,比较疫灾年数多少与比较疫灾频率等效。
(3) “疫灾广度”: 指某年疫灾流行波及的县的个数或土地面积,反映疫灾流行的广泛程度。如1930年,江南地区54个县市中有39个发生疫灾,这39个县市的土地总面积为35 429平方千米,则1930年的疫灾广度为39县,或者35 429平方千米。疫灾广度也可用疫灾县数与区域总县数的百分比来表示,如1930年的疫灾广度为72.22%,即该年江南地区有72.22%的县域被疫灾覆盖。
(4) “疫灾厚度”: 指一定时段、一定区域内疫灾累计波及的土地面积与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值,反映整个区域的疫灾严重程度,如江南地区土地总面积为48 942平方千米,而民国时期38个疫灾之年累计波及的面积为817 073平方千米,后者与前者的比值为16.69,即疫灾厚度为16.69层,相当于平摊下来,江南地区在民国时期被疫灾席卷了近17次。
(5) “疫灾季发率”: 疫灾季节发生率的简称,指一定时段、一定区域内发生疫灾的季节与该时段总的疫灾季节数的百分比。如民国时期近38年间,总共有151个季节,其中有143个季节有疫灾发生,其疫灾季发率为94.70%。
3.疫灾空间分析
采用ArcGIS 10.0软件进行疫灾空间分析和地图表达,文中空间分析主要采用重心模型分析民国前、中、后期江南地区疫灾重心的变化,采用热点分析工具分析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冷点和热点。所有分析均在1948年江南地区分县数字化地图上进行,分析结果绘成地图,进行可视化表达。
4.疫灾相关分析
疫灾相关分析是探究疫灾环境机理的有效工具。文中采用SPSS 22.0软件对疫灾年数与海拔高度、人口密度、灾害年数进行线性相关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后,相关系数r>0,表示两者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0,表示两者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绝对值的大小,表示相关性的高低,用以粗略判断海拔、人口、灾害诸因子对疫灾流行的影响及其程度。
三、结 果 分 析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的时间变化
1.疫灾的季节变化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年年都有疫灾发生,疫灾频度为100%。总共151个季节中,143个季节有疫灾发生,疫灾季发率为94.70%,其中春季37个(25.874%),夏季37个(25.874%),秋季37个(25.874%),冬季32个(22.378%)。仅从疫灾频度看,季节性差异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江南地区的疫灾不发则已,一发则连绵不断,绵延数季。近38年间,一年四季都有疫灾发生的年份30个(78.95%);一年三季发生疫灾的年份7个(18.42%),一年两季发生疫灾的年份1个(2.63%),没有哪一年只有一个季节发生疫灾的。由于每次疫灾蔓延的范围有广有狭,分析疫灾的季节性还要考虑疫灾广度。如表1所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累计受灾1 267县次,其中春季324县次(25.57%)、夏季380县次(30.00%)、秋季435县次(34.33%)、冬季128县次(10.10%),这说明,从疫灾广度看,秋、夏季是江南地区疫灾最严重的季节,两季合占全年疫灾县数的四分之三;春季也不少,约占全年的四分之一;冬季最少,只占全年的十分之一。我们发现,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疫病流行,疫灾多发生于夏、秋季节,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也不例外,但与明清时期相比(19)龚胜生、王晓伟、张涛 :《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地理研究》2014年第8期;王晓伟、龚胜生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辑。,春、冬季节疫灾的比例明显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民国时期由脑膜炎、猩红热、天花、白喉所致的疫灾比明清时期明显增多,而这些疫病主要在冬、春季节流行。
2.疫灾的年际变化
民国时期,以年度论,剔除一年内重复发生的,江南地区的疫灾累计波及784县次,平均每年有近21县(市)受灾,疫灾广度平均达38.21%,即每年有近四成地方遭受疫灾的侵袭;累计疫灾厚度16.69,相当于整个江南被疫灾席卷了近17次。这是全时期的总体情况。在逐年变化上,如图2所示,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线性趋势线斜率为0.432 7。但波动特征明显,大的波峰有6个: 1919年为第1个疫灾高峰期,疫灾县(市)数达22个,疫灾面积达2.60万平方千米;1925—1926年为第2个疫灾高峰期,疫灾县(市)数每年都有24个,疫灾面积合计5.22万平方千米;1929—1932年为第3个疫灾高峰期,这是民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疫灾高峰期,其间疫灾县(市)数每年均在30个以上,年均34.75个,远高于全期均值(20.63个);1937—1938年为第4个疫灾高峰期,其间疫灾县(市)数每年都达26个,疫灾面积共5.44万平方千米;1942年为第5个疫灾高峰期,疫灾县(市)数达33个,疫灾面积3.39万平方千米;1946年为第6个疫灾高峰期,疫灾县(市)数高达42个,疫灾面积4.00万平方千米,这是整个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流行范围最广的一年。这6个高峰期之间的年份,疫灾广度相对较小,形成与之相间的疫灾低谷,整体来看,只有1915年的疫灾范围最小。

图2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逐年疫灾广度变化图
3.疫灾的长期变化
疫灾长期变化是长时间序列下疫灾的趋势性和周期性变化。结合我们前期对明代和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变化的研究,将明至民国时期(1368—1949年)江南地区逐年的疫灾广度变化情况制成图3。如图3所示,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里,江南地区的疫灾流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疫灾广度的线性趋势线斜率为0.016 5,但脉冲状波动特征很明显。其中,明代有5个脉冲高峰(1455、1509、1545、1588、1642年),清代有10个脉冲高峰(1680、1709、1733、1749、1756、1786、1821、1849、1862、1902年);民国则整个处于疫灾高峰期,有4个脉冲高峰(1919、1930、1942、1946年)。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地区疫灾的脉冲周期越来越短,明代为40—50年,清代为15—30年,民国为10年左右,这说明江南地区的疫灾是越来越频繁的。还有,明代277年,江南地区疫灾累计波及417县,年均1.51县;清代267年,江南地区疫灾累计波及726县,年均2.72县;民国近38年,江南地区疫灾累计波及784县,年均20.63县,这也证明,江南地区的疫灾是越来越严重的,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这其中可能有疫灾史料“远略近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江南地区人口增多导致人口密度不断加大、交通发展导致人口流动不断加强、环境恶化导致水旱灾害不断频繁、疫种增多导致瘟疫四季流行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图3 1368—1949年江南地区年度疫灾广度变化图
(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的空间变迁
1.疫灾空间分布的阶段特征
民国前期(1912—1927年),图4a显示,宁沪杭交通沿线诸县市疫灾最频繁(如江宁、丹徒、武进、常熟、吴县、上海、松江、杭县等),浙西山丘地区诸县疫灾最稀少(如安吉、孝丰、武康、於潜、临安、余杭、新登等)。此等疫灾分布差异的形成,主要与人口密度有关。宁沪杭交通沿线自古繁华,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大,故疫灾多发,而浙西山丘地区位置偏僻,人口稀疏,疫灾也较少见。
民国中期(1928—1937年),图4b显示,与民国前期相比,江南地区的疫灾分布出现了两个新变化: 一是疫灾高发区域明显扩大,除宁沪杭交通沿线诸县市外,滨太湖诸县疫灾也不少,太湖水患是重要致疫原因;二是致灾疫种越来越多,除霍乱、疟疾于夏、秋季节盛行外,天花、脑膜炎在冬、春季节也经常流行。如1929年春 ,“ 苏地盛行脑膜炎”(20)《脑膜炎盛行之可畏》,《申报》1929年4月6日,第9版。,上海“患喉痧及脑膜炎等病,日有所闻”(21)《患喉痧未满六小时而死》,《申报》1929年3月23日,第15版。,杭嘉湖三属“屡次发生剧烈之(脑膜炎)传染病”(22)邹跃如 :《浙江义乌县防治脑膜炎记》,《医药评论》1930年第35期,第34页。。此后,脑膜炎流行连年不断。1931年春,江南地区“死于脑膜炎者以千百计”,酿成“二十年来之大祸”(23)《浙疫惨闻》,《申报》1931年2月22日,第11版。,原来很少发生疫灾的浙西地区也成了脑膜炎重灾区。(24)毛咸 :《浙省近三年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统计概况》,《浙江民政月刊》1931年第39期。
民国后期(1938—1949年),如图4c所示,江南地区疫灾流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仅溧阳一县未见疫灾记载。与之前相比,该时期南京、镇江、杭州等城市不再是疫灾频繁区,代之而起的是上海市及其周边地区。台风、潮灾、战争,天灾与人祸叠加,以及天灾人祸导致的大批难民的麇集,是该阶段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疫灾高发的主要原因。抗战期间,上海“屋宇什九被毁,残垣败瓦,遍地皆是”(25)《南市闸北被毁区域粪溺横流,污秽堪虞》,《申报》1946年2月23日,第4版。,抗战结束后,由于“机关还都,义民还乡,日俘遣送,盟军换防,善后物资内运,学校工厂复业,来往频繁,强半必经上海”,以致上海人口激增,卫生条件恶化 ,“ 集聚垃圾,几遍全市,苍蝇孽殖,更使疾疫潜滋”(26)张维 :《概述: 上海市卅五年霍乱之发生》,《上海卫生》1947年第1期,第3页。,以致1946年发生的霍乱,其发病率比1932年的霍乱大流行还要高(27)范日新 :《上海市霍乱流行史及其周期性》,《上海卫生》1947年第1期,第4页。。

图4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空间分布变化图
2.疫灾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
就整个民国时期看,如图4d所示,江南地区疫灾主要分布于宁沪杭交通沿线及其以东至于江岸海滨的地区,太湖之西的地区疫灾相对稀少。如果切着太湖西边画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直线,将整个江南地区分为东北、西南两个部分,则疫灾主要分布在该线的东北部分。从疫灾分布重心看,无论是前期、中期、后期,还是整个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吴县境内,但略向西南迁移,说明江南地区的西南部分在民国中、后期的疫灾比民国前期要严重一些。
江南地区这种东西间的疫灾分布差异,可以通过冷热点分析看得更清楚。疫灾热点是疫灾年数的高值集聚区,相反,疫灾冷点为疫灾年数的低值集聚区。图5是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冷热点分布图。如图5所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存在两个疫灾热点区: 一是太湖下游之滨的吴县和无锡地区,即今苏州至无锡一带,这里人口稠密,交通发达,水患严重;二是长江三角洲顶端的环上海地区,这里商业繁荣、战乱严重、潮灾频发。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也存在两个疫灾冷点区: 一是江苏省溧阳县,二是浙江省安吉、孝丰、临安、於潜、新登诸县,这些地方都是位置偏僻的低山丘陵地区,人口稀少,且交通不便。

图5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热点冷点分布图
3.疫灾空间分布的一般特征
疫灾空间分布的一般特征是指疫灾分布的规律性特征。如图6所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分布具有四个方面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和我们以前对江南地区的其他时期以及历史时期的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
(1)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多发点。疫灾是一种“空间蔓延型”灾害,人口流动是影响疫灾流行的关键因素,而交通线恰是人口流动的载体,所以交通沿线疫灾多发。(28)龚胜生、李孜沫 :《清代山西地区疫灾时空分布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6期。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形成了以大运河和宁沪杭铁路为主干的水陆交通网,大运河沿线城市(嘉兴、吴江、吴县、无锡、武进、镇江)和宁沪杭铁路沿线城市(南京、上海、杭州、昆山、松江、嘉善、海宁)都是疫灾多发点。比如上海,水陆交通发达,沪宁间“火车一日往返,开行数次,来客云集”(29)《白门近事录》,《申报》1912年9月15日,第6版。,“ 每天出入旅客约五六万人”(30)戴芳渊、施毅轩 :《检疫》,《上海卫生》1947年第1期,第13页。,人口流动性最大,因此成为疫灾最为频繁的热点地区。相反,浙西山丘地区(安吉、孝丰、於潜、昌化、新登、於潜等)由于地处低山丘陵,位置偏僻,交通落后,因而疫灾较少,为疫灾冷点区(图6a)。
(2) 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虽然人口密度是动态变化的,但通过某一时期的人口密度与整个民国时期的疫灾年数做耦合分析,仍然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对疫灾分布的影响。图6a中的人口密度等值线系据20世纪30年代江南地区各县市人口数据绘制,图中显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最频繁的区域(疫灾年份23个以上,即疫灾频度60.53%以上)有13县市,其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千米200人以上,疫灾最为频繁的上海市、杭州市、上海县、无锡县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千米600人,疫灾最为稀少的孝丰、临安、於潜、昌化诸县的人口密度均不足每平方千米100人。经相关分析,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各县市的人口密度与疫灾年数呈显著中度正相关关系(r=0.432,P=0.01),说明越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疫灾流行越频繁。

图6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与交通、人口、灾害与地形高程耦合示意图
(3) 疫灾频繁区多为水旱灾害严重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自然灾害虽然不能直接导致瘟疫,但能改变病原体生境,可使病原体短期内大规模繁殖,并削弱受灾人群的抵抗力,从而诱发疫灾流行。(31)龚胜生 :《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水旱灾害频繁,水旱灾害发生后,往往诱发疫灾流行。如图6a所示,水旱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太湖平原的武进、无锡、常熟,杭嘉湖平原的海宁、杭州、杭县,黄浦江下游的上海,而这些地区疫灾流行都相当频繁。经相关分析,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年数与水旱灾害年数有显著的中度正相关关系(r=0.503,p=0.01),说明水旱灾害越频繁的地区,疫灾也越频繁。
(4) 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区。江南地区以太湖和大运河一线为界,以东的地区,海拔较低,地形平坦,河网广布,疫灾多发;以西地区,海拔较高,山丘延绵,交通落后,疫灾稀少。经相关分析,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年数与海拔高度存在显著的中度负相关性(r=-0.368,p=0.01),说明海拔越低的地区,疫灾流行越频繁(图6b)。
四、结 论 及 其 他
(一) 结论
(1)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频度为100%。疫灾季发率为94.70%,全年九成的疫灾县数发生在秋、夏、春三季,四分之三发生在秋、夏二季。逐年疫灾广度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其中,1919年、1925—1926年、1929—1932年、1937—1938年、1942年、1946年为疫灾高峰期,其余为疫灾低谷期。从江南地区整个历史时期看,民国时期的疫灾最频繁,也最严重。
(2)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主要分布于宁沪杭交通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太湖下游之滨苏州—无锡一带和长江三角洲顶端的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太湖以西地区疫灾相对稀少,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吴县(今苏州市)境内,但略向西南迁移,说明江南地区的西南部分疫灾渐趋严重。
(3)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特征是: 交通沿线城市为疫灾多发点;人口稠密区为疫灾频发区;水旱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疫灾。这与我们对江南地区的其他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其他地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二) 其他
民国时期,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疫灾史料的丰富,每次疫灾基本上都可以指实为具体的疫种。关于该时期各种疫病导致的疫灾分布情况,我们在《中国历史疫灾地理研究·民国卷》中有详细探讨,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这里只就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病种群稍加说明。民国时期的“法定传染病”,1916年为8种(霍乱、痢疾、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1928年扩展至9种(增加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44年扩展至12种(增加回归热、疟疾、黑热病)。这些疫病江南地区都有发生,除此之外,江南地区还见麻疹、血吸虫病、雅司病的流行,但以霍乱、脑膜炎、天花、白喉、猩红热最为常见。霍乱导致的疫灾累计波及529县次,每年平均13.92县有霍乱流行,即超过四分之一的地方受到霍乱侵袭;其次是脑膜炎,脑膜炎导致的疫灾累计波及230县次;再次是天花,天花导致的疫灾累计波及172县次;又次是白喉,白喉导致的疫灾累计波及97县次;猩红热导致的疫灾也不少,累计波及78县次。霍乱主要在夏、秋两季流行,脑膜炎、天花、白喉主要在冬、春两季流行。1919年、1925—1926年、1937—1938年、1942年的疫灾高峰主要由霍乱导致,1929—1932年、1946年的疫灾高峰由霍乱、脑膜炎、天花多种疫病复合流行所致,疫情更严重。霍乱疫灾主要分布于上海、吴县、无锡、武进、常熟等县市;脑膜炎疫灾主要分布于上海、南京、海宁、吴兴、杭州等县市;天花、白喉疫灾则集中分布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