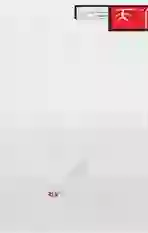巴什拜上山喽
2020-03-25沈念
一
一群羊密密匝匝地走在乡间公路上。
旅游车减速停下,耐心等待羊群让道。
羊的个头长得很接近,脑门白色.尾部肥大,毛色红棕,耳朵上方长出深深浅浅的两只羊角。也有些白羊混在队伍中.特别打眼,有的屁股上涂上了蓝色颜料,有的剪出一个大平头。那是牧民为了便于区分是谁家的羊。
骑在马上的一位“半克子”牧民挥动长鞭,像劈开一条河流,把羊群分成两半。羊一点也不慌张,迈着小碎步,呈人字形打开队伍的闸门。车重新发动,缓慢地从羊群中驶过,羊并不为身边经过的庞然大物所惊扰,互相摩挲着身体继续赶路。羊没有表情,抿着嘴,昂着头,看着前方。
我也从车窗外看到了,前方是连绵起伏的巴尔鲁克山。
第一次到新疆塔城,文学家茅盾说她是中国西北的最后一个城市,从地图上丈量,她是离海最远的地方,而蒙古语的意思是旱獭出没之地。我在塔城最先听人说起的不是山或那种消失不见的旱獭,而是这群羊——叫巴什拜的羊。半小时前,原籍甘肃后在山东长大却嫁到塔城来的年轻女导游正编排着它们:“头戴小白帽,身穿大红袍,尾巴分两半,好吃最难忘。”她描述的“难忘”前一天已经在餐桌上被我们咀嚼,我们用牙齿和舌头尝过它的鲜美味道。
“真不一样!”“好吃!”除了这两句抽象、空洞但也真切的感慨,初来乍到的我们似乎找不到更精准生动的新词来传递舌尖的感觉。巴什拜在新疆的闻名遐迩,也就在于它是北方牧场羊肉中的佳品,昧美肉嫩,营养丰富,无可替代。有时候,人就是靠昧觉的记忆对一个地方保存着长久的念想。
二
成群结队的巴什拜跟着主人,一个多月前转到了巴尔鲁克山北的这片夏牧场。
公路牧道旁的吐尔加辽牧场,像神的双手抖开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各种颜色的花藏身其间,像人海中美妙女子的回眸一笑。转场的路途遥远,劳顿跋涉,它们忘了眼前的风景。也许看了太多的风景,就没有风景能再让它们怦然心动。也许它们是用胃来记忆一个地方的,牧场风景美不美,是那里的草料好不好。
巴尔鲁克山在塔城之南,与人们熟悉的北边“界山”——塔尔巴合台山遥遥相对。从大比例地图上看,它像“雄鸡”顶端弯曲向下的那片漂亮羽翎。全长一百一十公里的巴尔鲁克山脉,西南宽,东北窄,宽窄比例达五倍之多,像一把大扫帚.把帚尾扫向西北偏北的中哈边境。
看到山,也就看到了边境线。塔城美术馆的中俄哈三国国际油画展的展厅里,一位新疆青年画家用笔下的“皑皑白雪”覆盖了起伏的山体和棕色丛林,那是我与巴尔鲁克山距离最近的一次遥远相遇。在另一位画家的作品里,巴尔鲁克山海拔三千两百多米的最高峰坤塔普汗峰,成了一位老牧民和几只巴什拜羊在阳光下眺望的清晰背景。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羊的眼睛都注视着你和你置身的世界。
也是巴什拜的世界。
三
“巴什拜!”羊群被甩在了车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漫游者,隔着玻璃欢快地唤着羊的名字。它们没有表情,也是用看不出情绪的表情和你告别。也许再次相见的时候,是在一张吵闹的餐桌上。食客不会记住一只具体的羊。
外面的阳光过于炫耀,它们心思涣散,或许听得不够真切——车的轰鸣像偶遇的蜂群嗡嗡嘤嘤,我们的呼唤掺杂其间,它们错以为是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没错,巴什拜也是那位在巴尔鲁克山区裕民县吉他克乡出生的受人尊敬的哈萨克族男子的名字。成年后拿着父亲分给他的一百多头羊和一群马,倚仗一次偶然发现的成功交配,他成了巴尔鲁克山区的人生赢家。
有人说,是山上那种一百多公斤重的野生盘羊误撞入了他家的羊圈,与哈萨克土羊交配后,生下的红棕色仙脸大尾羊。那些盘羊野性十足,抗御寒冻的能力特别强悍,即使零下四十度,照舊在雪地上自由行走觅食,杂交的后代也是骨骼强健、抵抗力强。也有人说,是勤快好学的巴什拜在草原上摸爬滚打,向老牧民谦虚求教,把从前苏联引进的叶德尔拜羊关进了羊圈。成功引进优良畜种的杂交科学实验,一次被写进草原史志的繁衍传说,是机缘还是必然,已无从考证。
大尾们的到来,让家圉的羊越来越多。他不得不雇佣牧民来放牧,也不得不一次次把羊圈的栅栏拔起,再建一个更大的羊圈。羊群是草原上财富的象征。巴什拜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牧主,富甲一方。他的羊群在牧场上出现,人们都要侧目注视。羊腆着圆滚滚的肚子走过的草地,来年又长出一片丰茂浓密的绿色。
如果只是拥有无以计数的羊,也许不足以让人记住这位草原上富有的大牧主。我听到人们津津乐道地叙说着,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巴什拜,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筹建了裕民县的第一座初级中学,又紧接着投资了塔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建起了塔城第一座电厂:民国三十一年(1941)请人修建了额敏河大桥,解决了裕民县通往塔城的人畜过河的困难,时任行政长官后来将这座桥改名巴什拜大桥航日战争期间,他给政府送了数百匹出征的马解放军进疆,他送去成吨的小麦和成群的牛羊慰问航美援朝的炮火在远方战场打响,他又捐献了一架飞机。当地史志上记载着,这架飞机折合四千头羊、一百匹马、一百头牛和百两黄金。这些并不是巴什拜的一己之力,帮他的是一群群不断繁衍的大尾羊。
那些穷苦的牧工,没有谁不认识巴什拜的羊。清早或傍晚出门,他们会羡慕地给认识的羊群让路:“这是巴什拜的羊!”对羊的尊敬也是对巴什拜本人的尊敬,巴什拜所做的每一件事值得他们敬重。他们自己或身边人多少得到过巴什拜的热情帮助。送钱物牲畜,买地盖房,愿意来当牧工的,人尽其能都可分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有一年秋天转场的时候,羊群闯进了一个汉族农民的马铃著地,主人急吼吼地驱赶着,牧工说,你看清楚了,这可是巴什拜的羊。农民立即噤声停止驱赶,脸红成一片天边的火烧云。回家后,牧工炫耀起途中遭遇,巴什拜听了却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了牧工,然后亲自登门道歉,还派人帮农民收割庄稼,赔偿了被羊踩踏后的损失。尽管如此,他的牧工依旧只惦念着他的好处和给他们的关心。巴什拜知道,放牧季节,牧工常常是孤身一人与大自然和羊群为伴。
“巴什拜刚离开这里。”人们心中的他慷慨大方、正直热诚,他的羊群转场走到哪里,就把他的声名带到哪里。备受拥戴的巴什拜,成了巴尔鲁克山区的知名人士,后来还担任了塔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成了一个符号,象征着财富、公正、热心、给予。不幸的是,六十四岁那年,身为塔城专署专员的巴什拜去杭州考察时病逝,后被专机运回家乡安葬。羊群经过墓园的时候,都会朝着墓碑的方向瞻望。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草原上出入每家每户的仙脸大尾命名为巴什拜羊。
这片看不到边际的原野上,巴什拜羊突然走到你眼前,又眨眼间走远:拐过一道弯,蹚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羊在行走,也是草原在流浪。
车驶过巴什拜大桥的时候,说是桥,跨过的却只是一条窄窄的河。河床裸露,杂草不生,河水来源于山间积雪,有大半年的时间积雪不化,河就一直瘦弱着。桥头名字闪过眼帘,让我又想起了落在身后很远的大尾羊。
巴什拜也曾经从这里走过去,草原上到处嗅得到羊群离开的气息。我们与羊在某个时空维度上有过多次的相遇,每一次相见,也许都是永别。
四
车停在吐尔加辽牧场旁的公路上。
从没见过这么蓝的天,朵朵白云悬挂在公路前方,仿佛你的速度再快一些就能追上她。
沿着窄石板路爬上高高的斜坡,穿过打开的一道铁丝网门,视野瞬间被推到一片无尽之中。羊群让人生发的草原想象,与实际所见相距太远。辽阔的定义被刷新。每一位外来者都无不为之震惊。远处的山,与向远处蔓延的草甸子、远处垂落的云层在看不见的地界相接。那个不知要走多久才能到达的草甸子尽头,就是积雪正极其缓慢融化的雪山。草甸子变成了一个看似很快走到却又永远抵达不了终点的球面。无法形容的美,多少双眼睛都根本装不下。这就是那一刻的心情。
迎着山谷吹来的风,花在摇曳,草原也在摇曳。“这是什么花?”耳畔的声音都是提出同一个问题,草原上盛开的是不同的答案。
紫色鼠尾草长着针状卯形的叶子,没过膝盖,遍地开放:杀虫治癣的翠雀花开得非常密集;根茎粗壮的红景天黄灿灿一片有棱糟的飞廉披着蛛丝状的毛,沿着茎下延展成翅:向阳坡面开着的是金盏菊伞状的寒地报春,有半年的花期,几乎匐着地面花托凸起的小甘菊锥状球形的模样远看像小菌菇:蔷薇科属的天山樱桃花叶同开,粉白相间麟茎圆锥形的贝母,倒悬生长的白花瓣上长着紫色斑点;瘦长的长蕊琉璃草,紫色的花冠微微弯曲像翘起的蝎尾……
“如果五月来,才是更好的花开季节……”女导游往前奔跑,突然匐倒在地,被草浪淹没,又爬起来继续跑,风把她那爽悦的笑声“捎话”我的耳边。她说,她是爱上在塔城相遇的他,也是爱上这片草原和看过一眼就忘不了的花。
我唯有闭上眼,想象那个更好的花开时节,漫山遍野,放肆盛开,也想象一个异乡女孩多年前爱上这里的心潮澎湃与细密欢喜。
五
羊在这片大地上经历过什么?
吐尔加辽是有名的夏牧场,它的汉语意思是贵族牧场。一个名字就划出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是谁家的羊都可以进入,过去如此,现在也是,护网围栏,非请莫入。从这里经过的巴什拜羊也许从来没吃过一片草叶。这些年月,巴尔鲁克山区的家家户户都在成功地养殖着巴什拜。草原上牧民的日常四季,夏天牧场丰茂放羊上山,秋天去集市卖掉多余的羊或把羊圈补满,冬天要照顾它们度过凛冬,春天等待羊羔出生。上山、下山、转场、牧养,人和羊群,与这片山地草原唇齿相依。
巴什拜羊像云朵般从牧道走过,嗅着空气中吐尔加辽的花草散发的诱惑芬芳,看了一眼围筑起来的铁丝隔栏网,就头也不回,决绝地走远了。它们丢下的是牧场,也是风景,是这一片最好的风景。
女导游跑得越来越远了。拍照的人们四处搜罗着风景和瞬间。我故意躺在草丛中,头脸朝上,四肢平展,蓝天白云,一尘不染,陽光透亮。闭上眼睛,有斑斓的五彩之光在眼里跃动,像一群金色的蜂蝶。没有云的地方,蓝得虚幻,像舞台打上的一块巨大布景,又像是天空浸在一个蓝色的世界中。侧身,目光从如密林般的花茎中穿越,披着光的花茎,每一根细微的毛蕊清晰。光让草原上的一切袒露,品格中的贵金属与世态中的低俗小说,碰撞出铮铮声响。
有两匹成年的马在草地上游荡,踢着蹄子,打着响鼻,与人合影,也在等待撒蹄奔跑。二十元十分钟,问完价钱,成交者踩着马蹬跨上马背,把牧场跑出震耳欲聋般的漂移感。人群早已四散,同行的一位大姐与我擦身而过,然后一个劲往前走,似乎是有多远就要走多远。我以为她是要离雪山更近,看得更仔细些。她的缀花纱衣随风飘动,她的背影变细变长,像是一株独立行走的花。转眼间她不见了.我有片刻的慌张,以为她突然掉进了深山峡谷或裂隙沟堑。我叫唤她的名字,她拱起纱衣后背,一只手挥动致意,身体却还是匐在草丛中。“我听见了鸟鸣!”她站起来,向我喜悦地叙说乌声从哪而来,又如何清丽鸣啭。但我耳朵里灌满唯一的风声,从山那边吹来的风,清爽、柔软,拂过面庞,穿越身体,精神和骨骼也为之发出簌簌响动。
天空洁净,悄无声息。看不到乌的影踪,也许乌藏身云层的枝权。有朵云,张开翅膀悬空,像是变成了一只巨乌,青背、羽斑、宽翅,投下万道斑影,时间的碎片被碾压成生活的粉齑,阳光照亮清澈的天体,也照亮巴什拜羊眼中的清澈。
清澈是这片土地上的标识。
山脉横卧绵延的地方是边境线,是羊热爱的夏牧场。积雪尚未完全融化,峰峦山谷间的白色点缀着褐色山体,背光处的雪终年不化。冬天裹风踏步而来的时候,又有新雪将过往覆盖。
无法覆盖的是人的足迹,牧民的、探访游客的、野外考察工作的、闲逛者的。我在塔城认识的一位摄影家朋友把我带到他的家中,墙上挂着他行走的“足迹”。这位痴迷于游牧文化的田野调查者,拍下了几乎所有塔城山林草原坡地上的千余种植物。三面环山的塔城,这里的中温带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被颜色深深浅浅的植物占领。
山麓西南的坤塔普汗峰南面陡,向北倾斜的落差有近两千米,生出一个大斜坡,种类繁多的草木花卉在气温的攀升里,从低谷向高山蔓延绽放。这一带有明确记载的野生植物就有百余种。这让我加深了对“巴尔鲁克”汉语释义的理解:丰饶、富足、无所不有。
过去这里也有山地放牧的习惯,虽然路途崎岖,但牧民还是会把羊群赶往牧草茂盛的山地。朋友拎出一根手指,沾着泼洒出来的酒,在桌上画出北高南低的塔城地貌,高山一浅山一丘陵一平原一湿地一高山,他的手指顺势往下,在讲述某个地貌时要停顿画出一个虚无的圆圈,他最终画出了一条被我记住的弧线,像极了一个倾斜的双手打开的U字。稍有地理或植物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阶梯状地形,必然的结果是多样性植物在这里富集.
“聚居成群的花,在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上都是孤独的存在。”摄影家朋友说起,他也拍过巴什拜,它的眼神有种清澈的孤独,另一种孤独,收纳了巴尔鲁克的丝丝毫毫的变化和馈赠。
六
我们从牧场上欢愉地下来,那群巴什拜羊拖着狭长的影子,从公路的拐弯处消失。“巴什拜刚离开这里。”我惊喜地指着它们离去的方向。它们是我见过的最缺少表情的羊。其实我也描述不清羊应该有的表情。
刚有那么片刻的恍惚,仿佛辽阔的草场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一只小个子乌啁啾一声刺入天际,看不到一只羊,只有那条蜿蜒的乡村公路和远处的村庄。没人知道这片土地上放牧的历史有多久远。
巴尔鲁克山南背风向阳,降雪量小一些,人畜越冬的很多冬牧场建在那里。冰雪从四月开始消融,黄色的大萼报春最先钻出冰雪覆盖的地面。融化的雪水从大地上的每一道缝隙汇聚河谷。
我是在塔斯特河谷终于看到的雪山水。到河谷的下坡山路有很多斜仄的弯道,我们换乘几辆越野车才顺利到达。水混浊,湍急流淌,山谷回声响亮。从巴尔鲁克山发源,有十六条大小河流穿过裕民县,奔赴名声更响的河流。山脚下的塔斯特河和布尔干河,分别从两个方向西流走出国界。另一条相邻的额敏河,自西向东经由库鲁斯台草原,最后流入咫尺之远却是国界之外的阿拉湖。发出蓝色幽光的阿拉湖,在瞭望中被打磨成一面镜子。山脊起伏,河谷狭远,在巴尔鲁克这个森林王国,看得到百万亩的原始次生林,十万亩的野生巴旦杏林,万亩野白杨林和千余种野生珍贵植物。季节变换,色彩缤纷,是生命的繁衍与共生镀铬着这片山水荒野的界线。
一群羊沿着塔斯提河往山上走,它们低头的模样,像是聆听着与河水一起流淌的属于光阴的故事。草原像一个展示的透明胃,吞吐着时间里的冰霜雨雪。
羊群爬上山头,在这里看得到牧场、院墙、堤坝、道路、河流、畜棚,以及由它们组合的风景。看风景的羊,也成了被看的风景。这片草原是他们的家,是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牧民对这里的爱,无人弃之远去,也无人驻留在外不再归来,那些远方,依然是远方。牧民赶着羊群回圉,像低矮的坡地上飘过一群云的影子。
草原上遇见的人都有一种朴素的诚实。我听他们说起一件往事,一个牧民在秋季买了一群羊,价格都是双方事先议定的,后来他去集市的交易会上发现他是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这些羊。他因此感到愧疚,而不是占了便宜后的窃喜,就主动找上卖主家送去补差价的钱。卖羊的牧民却坚持成交的生意不能再多要钱。草原上的牧民经常如此,把诚实守信的声誉和德行看作一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听说那个叫依洪达的买羊牧民第二年继续找上门,出了比市场高得多的价格。有人说,后来依洪达也总喜欢帮人排忧解难,一诺千金。也有人说,如果你有依洪达一半的品质,就是值得称赞的善人。
叫依洪达的维族老人,剩下最后几颗乌黄的牙齿,却依然可以啃光羊排上的肉。在女儿哈力旦的记忆中,一辈子牧羊的善良父亲,是草原上沉默的大多数人中极不显眼的一个。这般的人群,一辈子就活在勤劳谦卑者的草原上,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几乎不曾留下生活的纪录。草原上的历史就是小人物的历史。
七
天光灿烂,亮晃晃的。天要推迟三个小时才黑。天黑前,羊群归圈,身后的大山寂寥旷远,人们即将喝酒吃肉,大声歌唱。
从巴尔鲁克山返程,我们去了哈尔墩四道巷哈力旦家的小院。推开院门,长棚下的餐桌摆满了水果点心,几位当地手风琴演奏家、歌唱家欢愉地奏唱着草原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国》。前一天我在手风琴博物馆看到了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度的三百多台不同年代的手风琴,收藏它们的主人能讲述每一台手风琴背后的故事,也能将每一台手风琴奏出美妙旋律。我没有想到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手风琴乐器在这里如此风靡,每年的千人手风琴合奏还上了吉尼斯纪录。在这个“手风琴之城”,哈力旦记得小时候,父亲在牧场上拉响手风琴,成群的巴什拜羊都会安静地抬头聆听。她少女时代拥有的第一架红色32贝斯的百乐小手风琴,就是家里卖掉一只巴什拜后买的。父亲无数次说起,闭上眼,还记得那只羊的模样。
为了这顿晚餐,哈力旦和家人准备一个礼拜了。高大魁梧的丈夫大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去附近的牧民家中,杀了三只巴什拜羊。烤肉的火炉架设在红围墙下,看不见炭火的燃烧,但羊肉沾洒孜然的香味很快飘绕在农家小院和呼吸之间。食量厉害的人,可以吃掉一整只羊。哈力旦的弟弟皮肤黝黑,咋咋呼呼地炫耀那些饕餮者。
院子里支开了几张餐桌,上面摆放着六个民族的特色美食。这些美食来源于哈力旦的奇妙家庭组成。她的丈夫艾则孜哈比布拉是乌孜别克族,大姐嫁给了塔塔尔族,妹妹和哈萨克族组建了家庭,弟弟娶了一个蒙古族。从海边城市来的客人喝了两杯酒,就跑去题写“玫瑰庄园”书法匾额送给哈力旦。他把四个宇写得道劲有力,又生动活泼。喝彩者声响震动,哈力旦满脸笑容,她从厨房端着菜碟走在院子里,十几米的路上,每一步迈出的都是舞蹈。天生就是一个舞者。
她说在塔城歌舞团做过十多年的舞蹈演员,三十五岁那年离开舞台去了北京,带着女儿租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开始了陪读生活。喜欢小提琴的两个女儿先后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依洪达喜欢带着两个孩子在草原上拉琴,琴声跑得像风一样快,从浪流般的草尖上滚向远方。他凝视着孩子,涌上面庞的笑容,仿佛能把时光的褶皱抻平,又像是一潭安静的湖水,把所有经历的苦难溶解。
几年前,这位被称为巴尔鲁克山区最诚实勤劳的牧羊人,留下几百头羊走了,离世之际,他牵挂着哈力旦的“汉族弟弟”。站在餐桌旁,哈力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仿佛老人就坐在院子的另一角落里,怀里捧着手风琴,拉响草原上的歌。
贫穷小伙阿杜随乡友从山东济宁来到了塔城,找不到工作,无处落脚,囊中空空,依洪达知道后把他请来当了牧工,教会他牧羊。日久情深,依洪达非常喜欢阿杜,认他做了干儿子。哈力旦从此有了这么一位汉族弟弟。
依洪达对阿杜有一种奇怪的深厚感情。有一次阿杜骑马放牧,到傍晚巴什拜羊自个回了圈,人却不见了。他发动全家外出寻找,遇见后二话不说,就拉进医院急诊检查,说是担心他在外受了伤。其实阿杜是途中贪玩忘记了羊。他一路上胆怯地打听,路人故意逗这位年轻人:“巴什拜上山喽!”
那是在塔城牧羊生活的四年里阿杜唯一一次丢掉了羊。他把塔城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依洪达一家当成亲人。家乡接二连三的电报催促阿杜回家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依洪达有多纠结,他承诺过要给这个“儿子”盖房娶妻。依洪达舍不得他走。阿杜那些天早起把羊赶到草儿最肥的牧场,寸步不离地看着它们吃得肚子圆滚滚的。临别前,依洪达让妻子把家中全部存款一万七千块钱缝在了棉衣里层,叮嘱阿杜儿子回去后再拆开,拿着钱去盖房买地,娶妻生子。三十年前的阿杜不知道衣服里藏着一笔巨款。像一团暖融融的光,在他的心里再也没有熄灭过。2016年冬天他兴高采烈地再次回到塔城时,从没断过的牵挂思楚,却因老人离世成为一段孤独的回忆。
哈力旦去年带着家人去了趟济宁,阿杜的女儿结婚,婚礼上摆满了她带去的葡萄、拉条子、巴什拜羊肉串等新疆特产,两个女儿现场用小提琴拉起了明快悦耳的新疆音乐,宾客开心地欢歌载舞,像是办了一场新疆婚礼。
年过五旬的阿杜依稀记得当年放牧的那一群巴什拜羊,他给它们取过古怪的名字,虽然它们早就不在了,但还经常会走在他梦到的草原上。
八
都不知道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天空像在摇动一把小折扇,在晚风中收走最后一缕曦光。走出小院,我朝巴尔鲁克山望了望,朝塔尔巴合台山望了望。我朝绵长白昼望了望,也朝短暂黑夜望了望。仿佛还在草原上,看着属于塔城的风景,风吹过来,动人的歌唱和欢笑带你去往更远的远方。
“去喝奶茶吧!”有人突然在耳旁吆喝了一声。
又一个声音浮上來:“羊儿都上山喽!”
沈念,作家,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时间里的事物》、小说集《出离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