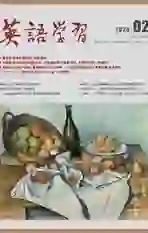跨越族裔的文化传承:专访华裔美国作家邝丽莎
2020-03-02迟浩男
摘 要:邝丽莎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具有商业影响力的一位作家。她凭借多部讲述华裔美国人历史的作品蜚声美国社会,其作品因关于人物细微情感的传神描写和对华裔美国人历史的细致爬梳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本篇采访稿以邝丽莎较出名的几部作品《雪花秘扇》《上海女孩》和《中国娃娃》为例,围绕创作动机、主题刻画、人物描写、华裔身份和文学批评五个维度对她进行采访,展示了邝丽莎作为拥有华裔血统的商业作家独特的创作理念与风格,也首度阐述了她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认识。
关键词:邝丽莎;华裔美国文学;族裔身份
本文是基于作者对华裔美国作家邝丽莎(Lisa See)的采访文稿整理而成。邝丽莎(1955—)是当代华裔美国女作家,她的曾祖父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邝泗(Fong See),又稱冯泗。因为美国移民官对于汉语的不了解,错将邝泗中的泗作为他的姓氏,因此邝泗的英文名以See为姓,由此代代相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一举打破美国主流文学对于亚裔文学的忽视,同时也成为华裔女性作家的时代最强音。稍晚于汤的谭恩美(Amy Tan)凭借她的《喜福会》(The Joy Lucky Club)取得巨大商业成功,与后来的李健孙(Gus Lee)、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和任璧莲(Gish Jen)被学术界常常并称为华裔作家“四人帮”。与谭不同,任璧莲更加关注少数族裔的身份流变性,她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和《莫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对这一主题均有反映。汤亭亭对于奠定华裔美国女性创作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意义,谭恩美的作品取得更多的社会反响,任璧莲首次尝试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去看待亚裔美国人的身份。与她们相比,邝丽莎的商业影响力在普通读者中则更大。
邝丽莎的成名作是《雪花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于2005年出版,后被华裔导演王颖改编成电影。该作品讲述的是始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一对结为“老同”关系的中国湘西地区女性的故事。“老同”是当时该地区同年出生的男生或女生之间结成的类似兄弟或姐妹的关系。小说描绘的是这样一对受到封建习俗压迫的女孩因为不同际遇而拥有了截然相反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两人之间形同姐妹的深情厚谊。这部小说之前,邝丽莎出版了中国侦探故事的三部曲:《花网》(Flower Net,1997),《内部》(The Interior,1999)和《龙骨》(The Dragon Bones,2003)。成名后,邝创作了以《牡丹亭》为背景的小说《恋爱中的牡丹》(The Peony in Love,2007),讲述两代华裔女性在美打拼的姊妹篇《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2009)和《乔伊的梦想》(Dreams of Joy,2011),以及依据亚裔美国女性群体在歌舞厅和影视业摸爬滚打的经历创作的《中国娃娃》(China Dolls,2014)。之后,邝的视角进一步深入到鲜为西方所知的东方故事,剖析历史对个体的影响。她的《蜂鸟道上的茶女》(The Tea Girl of Hummingbird Lane,2017)讲述一对母女因为种种原因失散了,一个在中国云南,一个在美国加州,借助于普洱茶而得以重新取得联系。邝的新作《海女之岛》(The Island of Sea Women,2019)追溯的是二战时期韩国济州岛海女的历史。本篇采访是作者在2017年4月完成的。彼时,邝丽莎创作完《蜂鸟道上的茶女》,正准备着手完成新作《海女之岛》。现整理此文,以期对国内研究邝丽莎的学者有所帮助。

(注:文中作者和邝丽莎将分别以迟和邝代替。)
迟:您好!我们对您创作的作品十分熟悉,您的很多作品都描写了女性角色。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您是否会比男作家在描写女性人物方面更具优势?这是您采用女性叙述视角的原因吗?
邝:是,我认为女作家确实更容易创作女性角色。不过,这不是我采用女性叙述视角的原因。我对被丢失、遗忘和故意掩盖起来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我们常透过诸如战争和将军总统等重要的历史时刻与人物了解历史。你可以说,他们是处在历史最前线的象征。可不妨退一步想想,谁在历史的后面?女人,孩子,老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部分,可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将这份采访稿翻译成中文。* 在英文中,历史的拼写潜在的意思是“他的历史”(history: his-story)。然而, 我对“她的历史” (her-history)更感兴趣。
迟:这种解读很有趣。我们来看您的作品,从《雪花秘扇》到《上海女孩》和《中国娃娃》,姐妹情谊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话题。您描写女性情谊的原因何在?
邝:女性占世界一半人口,我打心里同意女性能顶半边天。母性是特殊的,只有女人可以成为母亲。姐妹是独特的。事实上,所有的姐妹关系,特别是由于她们之间伴随一生的联系,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父母会先你离世,你长大后才能遇到你另一半。同样,你也会先你子女而去。所以,姐妹关系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相伴最为持久的一种联系,但也会因此变得十分复杂。女性间的关系与男性间的很不同。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私密的故事告诉她的女性朋友,但她不会选择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男朋友、丈夫以及孩子们。这会让女性间产生非常独特的一种亲密感。同时,这也让你非常容易暴露于背叛的危险中。我不是那种喜欢描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作家。相反,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更倾向于揭露女性关系黑暗一面的作家。
迟:为了创作《上海女孩》,您曾做过很多采访调查。有学者批评说这本书反映的其实是您的家族历史。您可以介绍下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吗?
邝:的确,我为此采访过很多人。我不认为你所说的批评家对我有批评的意味。我更愿意看成是一种表扬。我的家族来自广东,而非上海。当然,他们也不说吴语。不过,我也以某种方式通过这本书纪念我的家族。我们家族有过很多媒妁之言的婚姻。例如,我的曾祖父带着全家老小在1932年回到中国,为自己的九个儿子寻找合适的老婆。这些女子都是在14—21岁之间,在中国,她们都有自己的仆人。到了洛杉矶中国城,她们却过得像仆人。只有得到男人们的允许,她们才可以外出参加婚丧或满月酒席。我成长的过程中都见到过这些人,我希望写下她们的经历,纪念她们曾经历的磨难。
迟: 《上海女孩》中的珍珠与梅两姐妹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您这样描述是否有特定的原因,换句话说,您是否更喜欢其中一个角色?
邝:我当时需要为两姐妹确定她们的属相。当我确定珍珠为龙年生人,我就在考虑该给年纪更小的梅选一个出生年份。结果,我发现她更适合做一个羊年出生的角色。那么,我对她们有偏好吗?这个故事是从姐姐珍珠的视角来写的。还有,我自己是姐姐。所以我自然而然地相信,凡事都是姐姐对!
迟:在另外一部小说《中国娃娃》中,露比(Ruby)这位唯一的日裔主人公是个有雄心、做事灵活也很有斗志的人。她的存在是否象征着一种少数族裔自强拼搏的精神,或者仅是表现亚裔族群因为种族隔离而不得不抗争的故事?
邝:我认为露比是一个很能够在都市街头打拼的人,而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格蕾丝(Grace)在故事开头显得有些单纯。海伦(Helen)则兼有传统家庭庇护和一连串不幸的两种不同的人生阅历。我不认为露比因为是日裔,所以就显得更“有雄心、做事灵活,也很有斗志”。她其实本身就有这种特质。许多人遇到她这种情况时可能会低头屈服。我也要指出,这种特质不单单是露比个人的性格。当我创作她时,我在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日裔美国女人,我和自己的肤色背后的种族缺少依附与认同,我会喜欢同男孩打情骂俏,也憧憬着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电影里聪明俏皮的金发女主人公。这种人就因此化作了露比这个形象。
迟:在《中国娃娃》的前言里,您摘录了这样一句话“世上有三件东西无法被隐藏:太阳,月亮和真相 (献给佛祖)”。我想这句话是否也隐射文本中反映的种族问题终将需要面对和解决?您如何阐释这句话的意思?
邝:我其实没有考虑种族问题。我是在思考生活中的秘密,以及它不为人的主观意愿左右而被揭露的经过。我所关注的不仅是个体,还有政治家和政府的秘密被最终揭露的故事。露比、格蕾丝和海伦三人都有秘密。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更加积极灿烂一点。所有三位主人公尽享生活,总体上一帆风顺。第二部分颇为暗淡,以月亮为象征。第三部分,真相大白,最深层次最黑暗的秘密最终都暴露出来。
迟:您曾提到过自己的华裔美国家庭背景,您是否致力于表达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您认为自己对于读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邝:我生活在一个种族观点相当分裂的国家。一群人会将另一群人看作另类或者更低等的。我想为我的读者打开一扇窗。无论他们来自美国还是其他我的作品会出版的国家,我都想让他们体验另一种文化和时空。有时,这个场合设定在中国,有时是美国的唐人街。我想让读者理解,我们之间有更多的相同点,而非不同。有人用茶壶喝茶,有人用咖啡壶烧咖啡。有的人用平底煎锅做菜,有的人用炒锅做饭。这些都是不同文化的差异处,但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们都希望喝点热的暖和自己,都需要吃顿晚餐填饱肚子。这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象,而细节的差别并不影响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处。
在更广阔的角度,我想让读者认识到,我们拥有共通的人情关系和情绪表达途径。我们都会有父母的陪伴,这是普适性的关系。我们都渴望爱,我们都会经历痛与乐,困难与胜利,这也是普遍存在的事情。通过我的作品,我想讲述一个好的故事,让人们沉浸其中。不过,我也希望让读者思考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生活,领悟到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叫作人类的群体。
迟:谭恩美(Amy Tan)和赵健秀(Frank Chin)聚焦华裔美国人身份问题,您是怎样看待华裔美国人身份呢?
邝:这个标签首先不言而明。一个中国人的后代,因为出生或归化成为美国人,我们称他为华裔美国人。这与移民不同。华裔是很多代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也许看起来不再像中国人。比如我就是个例子!我看着压根不像中国人,不过我是在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式家庭里長大的。
多说一点,在我的新作《蜂鸟道上的茶女》里,我描述了一个在中国被遗弃的女孩,她后来被美国的养父母收养。我为此采访了不少类似境遇的18—22岁的年轻女生。她们也都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她们问自己,“我是谁?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华裔美国人?或者我是别的什么身份?”我在昨天的另一场采访里谈过这个问题。一个恰好是第三代华裔美国人的记者说,“喏,她们显然不是华裔美国人!”我深以为然,要知道,大多数这些被收养的女孩子,并没有在华裔美国家庭生活的经历。她们在白人家庭长大,与此同时,她们从未接触过中国传统文化,也未经历过华裔移民曾经历的种种打拼的艰辛和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她们只是所在家庭、社区、学校和教堂里面的一分子,一群拥有华人面孔的成员们而已。
迟: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赵健秀,他认为华裔美国作家关注女性主义问题,但忽略了华裔美国人经受的种族问题。您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邝:我非常仰慕赵和他的作品,但我很遗憾地说,他的看法是有纰漏的。读过汤亭亭作品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中国移民初来美国所经历的种族压迫呢?她的书《中国佬》(China Men) 详细描述了这点。当然谭恩美对历史和种族问题不太感兴趣,可是她为什么就要写这些问题呢?为什么谭不可以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至于我自己,会有人将我贴上“历史小说”的标签。我的第一本书《在金山上》确实是一本讲述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我其他的作品也都有涉猎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种族问题,比如《花网》《上海女孩》《中国娃娃》和现在的《蜂鸟道上的茶女》。我甚至会说身份问题是我所有作品的核心,不过主题的表现方式各异。在这里,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作家需要按照赵的希望去创作?让赵去写自己的书。他的计划是他的计划,他的关注点是他的关注点。作家就是作家,他们在创作时,需要从心所欲。他们有自由去表达自己想讲述的故事。赵或者其他任何人没有权利去告诉作者去创作什么。
之前,我也曾谈过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把赵关于谭和汤的错误评论放在一边 (也许他根本没读过后两位的作品?)我的问题是:如果每一个华裔美国作家都去写赵关注的书,人们如何能够理解不同个体经历的深度与广度?我现在回到之前谈到的观点,在美国,很多女性和家庭都经历过困难和歧视,我们需要聆听这些故事,但是我们也需要将自己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理解拓展和延伸。有人应该要去问问赵,为什么他不去同等看待华裔女性和家庭的故事与华裔男性小说?
后记:邝丽莎在这篇访谈里所展示出的观点,正是她一直所强调的女性叙事视角。不过,这并不等同于她将自己的关注点局限于女性问题,而是她通过性别问题折射美国社会在男女地位、种族问题和阶级差距上的不公。更为重要的是,她作为拥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在作品里传递中华传统文化,讲述美国亚裔群体故事。与此同时,她又在美国社会为少数族裔群体发声。不可否认的是,她对于族裔问题的看法有时候显得比较东方主义化,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看法可能不够全面,也会流于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模式化认识。但是,作为华裔美国作家,她做到了传承族裔传统,同时又以美国人的身份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社会平等包容的期待。最后,她也展现出对于世界主义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一个跨越族裔的文化传承者和创新者。
迟浩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英语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