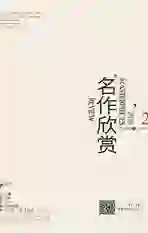审慎保存旧文明的精魂
2020-02-28夏成潘多灵
夏成 潘多灵
摘 要:受新文化运动权力话语影响,学界主流对胡先骕文化思想的评价近年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胡先骕执中守本的文化思想,紧执中正之道,力图重建古典美学法则;恪守汉字本位,塑造民族文化认同,其旨归在于“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的精魂”。胡先骕对传统的珍视和弘扬,在当下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胡先骕 文化思想 价值重估
胡先骕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植物学家、文化学者。他在植物学领域的成就早已得到学界公认,但其文化思想至今仍然受到严重的误解。本文尝试拨开新文化运动权力话语的遮蔽,在当下语境中探讨胡先骕文化思想的特质及其重要意义。
一、新文化话语权力场域中的胡先骕文化思想
初版于1987年,修订再版于1998年的钱理群、温儒敏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学界影响甚大。该书在评论以吴宓、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时,认为“吴宓、胡先骕虽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某些偏激的弊病不无中肯地批评,但是保守的立场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变革的趋势,其基本点是否定文化和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的,站到了时代主潮的对立面去了”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刊载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王富仁的文章《学识·史识·胆识(其一):胡适与学衡派》。文章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胡适和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均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但双方思想主张的来源决定了其主张的价值等级。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的新人文主义来自美国的一种学术传统,是他们的“学识”。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却非仅来自学术传统,而是在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不满中产生,并在改革中国社会文化的殷切希望中孕育并成熟的,所以具有一种“史识”的性质,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具体表现为一种个人的“胆识”。相较于胡适立足于中国现实,致力于改造社会的革新主张,胡先骕等人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学说,“既不存在直接的适用性,也不存在直接的对立性,所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立足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立场对胡适白话文改革主张的否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做的只是一些无用的文化功”b。钱理群和王富仁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名家,二人的观点一载于新时代之初,一刊于最近,但都崇胡适、贬胡先骕及学衡派,显示出学界主流对胡先骕及学衡派的评价在近几十年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至今,已有百年之余。百年来,新文化运动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路凯歌,锋芒过处,敌对者无不披靡。如果说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尤其表现在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自其肇始,便与新文学运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学以燎原烈火之势蔓延开来,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取代了传统文学的社会主导地位。新文学的巨大成功,形成了新文化的话语权力场域。布迪厄认为,“权力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是随着社会分化出现的一些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如科学场、艺术场等。c在布迪厄看来,每个场域都有其相对自主性,能够制定游戏规则并推及场域内的每个成员身上。文学活动作为一个话语生产场,处于场域中的人总是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制定规则,维护既有的文学等级秩序,因此艺术作品的变化原则取决于进入者在艺术场中的资源配置或力量关系的变化。
在特定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否定。自此之后,几乎凡是对新文化运动持有批评意见的学者,都被视为“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在这样一种武断、笼统的批评中,胡先骕文化思想的价值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当前对胡先骕文化思想的认识仍受到新文化运动权力话语的遮蔽,只有拨开新文化运动权力话语的遮蔽,回到胡先骕文化思想本身,才可能对胡先骕文化思想形成公正、客观的认识。
二、执中守本:胡先骕文化思想的品质特征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认为,“适倡革命,而光迪、先骕主存古,与适相持”,将胡先骕归为“存古”派。胡先骕一生酷爱古诗词,少年时期便得沈曾植指导,学习宋诗。即便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时,胡先骕也学诗、写诗不辍。终其一生,他写下舊体诗七百余首。钱锺书认为胡先骕的诗“转益多师,堂宇恢弘”,成就极高。但将胡先骕归为“存古”派,主要不在于胡先骕的旧体诗创作成就,而在于胡先骕的文化主张和思想倾向。
(一)紧执中正之道,重建古典美学法则
在《文学之标准》一文中,胡先骕说:“中外最佳之文学,皆极中正,可谓人生之师法,而不矜奇骇俗者也。”d在此,胡先骕将“中正”视为人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者的标准,可见“中正”思想在胡先骕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性。有人将胡先骕所说的“中正”理解为中庸、中和、中节e,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些歧义,不如将其理解为“平衡”,是形与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的平衡。在《文学之标准》的结尾处,胡先骕所引用的薛尔曼教授的一段话,最能体现胡先骕“中正”思想的精义:“如何以给予快乐而不堕落其心,给其智慧而不使之变为冷酷,如何以表现人类重大之感情,而不放纵其兽欲。如何以信仰达尔文学说,而同时信仰人类之尊严。……如何针砭之而不轻蔑之,如何讥笑其愚顽而不贱视之。……如何以回顾千百之失败,而仍坚持奋斗之希望。”胡先骕一生,多有不合时宜之事,早年他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反对新文化运动,因此被视为文化保守派,饱受批评;晚年他又顶住压力,批判苏联科学家李森科错误的植物学理论,因而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由胡先骕的言行来看,他所强调的“中正”丝毫没有传统中庸思想常有的“含混”及“和稀泥”色彩,而有着鲜明的原则性,是在对事物深刻洞见,对价值理想坚持守护的基础上达到的形与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从而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胡适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针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先骕写作并发表《评尝试集》,对胡适的文学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胡先骕的批评,集中体现出对胡适为追求白话尽弃传统文学形式的不满。他坚持认为,文学的“形”和“质”不可偏废。《文学改良刍议》斩钉截铁的语气和一系列的命令句式,在胡先骕看来,显然是武断的,但胡先骕也并没有完全反对胡适的写作尝试。在《评尝试集》结尾,胡先骕说:“是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创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胡先骕称胡适为开创者,而将完善的希望寄予后来者,对新文化运动虽多有批评,但是又怀抱希望,显现出他的中正立场。
胡先骕的中正文化思想更集中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与批评上。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胡先骕有着诸多批评。他认为浪漫主义者毁弃社会法则,不以理智为节制情欲之工具,而以冲动为本能之指南;竭力扩张自我,最终结果要么沦为尼采式的超人主义,要么沦为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两者皆欠缺节制和中正之要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者看似与浪漫主义相反,实为浪漫主义之变相,三者都否认人类固有的美德和自制能力。胡先骕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想多有偏见,究其原因,在于他以平衡为文学、社会和自身之规范,主张以理制情,以情节理,获得一种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古典美学法则。
(二)恪守汉字本位,塑造民族文化认同
改革汉字的思想产生于清末,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使国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挫败和文化焦虑。中国最早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汲取西方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在思索中国文化的病根。特别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人激愤愈烈,忧思愈深,对传统的批判更加严厉,乃至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许多中国人认为,从“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表音文字”是普遍性的文字演变规律;汉字还停留在象形和表意的阶段,是一种进化程度低、发展不充分的文字;汉字要追求时代的步伐,必须实现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使汉字“音”“形”同一。
黄遵宪说,“泰西论世,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与文字不相合者也”,“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f。在黄遵宪看来,汉字的历史悠久,正是汉字古老、落后的表现,使其成为中国人追求先进文化的最大障碍。裘廷梁着眼于西方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历史,认为“泰西人士,既悟斯义,始用埃及象形字,一变为罗马新字,再变为各国文言,尽译希腊、罗马之古籍,立于学官,列于科目。而新书新报之日出不穷者,无愚智皆读之。是以人才之盛,横绝地球。则泰西用白话之效”g,西方国家人才辈出、文化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语言文字随着时代不断进化,发展充分,便于学习。对此,钱玄同在1922年总结说:“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h要与西方争强图胜,必须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为此又必须以实现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废除汉字为先。
废除汉字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达到极盛,特别是“五四”之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高涨,“汉字革命”被更多地赋予了“进步性”和“科学性”,与之相左的观点则被视为“保守”和“落后”。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胡先骕却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挺身而出,护卫汉字和传统文化的地位,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勇气。
胡先骕对汉字的维护主要着眼于汉字在传承文化和民族认同方面的功用。胡先骕称汉字为“衍形文字”,衍形文字“音”“形”分离,在某些方面虽有所不便,却有自身独特的功用。
第一,汉字“音”“形”分离,“形”不随“音”变,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一般来说,字“音”更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拼音文字的“形”随“音”变,导致两个可能:其一,民族、地理的分割使一套文字系统中分化出多套来。胡先骕以西方文字做比较,认为查理曼大帝奠定欧洲统一大业时,拉丁语通行欧洲,其地位与今日汉字相仿。但是拼音文字“形”随“音”变,遂分裂出法、意、西班牙等各民族语。其二,时代的变化会使一民族语内部发生巨大变化。胡先骕说:“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过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以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英国的乔叟、斯宾塞,虽然距今不过五百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由于英语在时代发展中的巨大变化,二人的作品在今日即便是英国人阅读也颇有难度。而汉字作为“衍音文字”,“形”与“音”分离,“形”在时代变迁中基本上保持稳定,因此即便是两千年前的先秦典籍,依然让人觉得亲切。所以,胡先骕说:“周秦之文距今二三千年而尚易诵习,至唐宋之文,则无异时人所作。此正吾国所以能保数千年而不绝之故也。”
第二,汉字“音”“形”分离,“形”不随“音”变,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国地域广阔,由于河山的分割、生活习惯的差异,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各方言语音差异极大,相互之间难以交流。但是汉字“音”“形”分离,“形”不随“音”变的特点,却使各方言区共享一套汉字字形系统,各方言区的人民不会因为山河阻隔、方言迥异而产生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障碍。所以十五国风,不经移译,而能成书一册;二十四史,不经移译,而能成史一部。各地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便捷,与汉字是“衍形文字”关系密切。
第三,汉字“音”“形”分离,“形”不随“音”变,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兄弟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融合而成的。胡先骕认为,中华民族萌芽之初,“民族既殊,语言自异,百里之间,常须重译”,但是语言虽异,却共享汉字,千百年潜移默化,终于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民族融合的长期过程中,汉字的稳定性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基础。各兄弟民族和汉族共同生活,在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汉字。汉字的稳定性成为联系汉族和兄弟民族的一条无形而坚固的纽带,使民族间的紧密联系不会因历史离合而削弱,最终形成“东亚最伟大之民族国家”。
正是由于汉字在促进地区与民族间文化交流、传承和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巨大功用,胡先骕热情地赞扬汉字:“吾国既以创造衍形文字之故,而得形成四百兆之伟大民族,保持五千年不绝之文化。是吾文字与吾族无上之瑰宝也……”
三、审慎保存旧文明的精魂——胡先骕文化思想的指归
胡先骕认为,他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争论,不是进步与反动之争,而是“文明与野蛮之争”。胡先骕此处的区分非常耐人寻味。在胡先骕看来,胡适等人的改革雖有明显的现实功用,但这种现实功用是以对传统的毁坏为代价的,对此他不能赞同。在新文化运动者激烈否定传统时,胡先骕特别强调:“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相对于新文化运动者来说,胡先骕珍视的是文化的传统,所以他在许多方面与新文化运动者相左。针对新文学对西方作家的推崇,胡先骕泼冷水说:“非效法某种主义,便可称文学家也。文学极非一蹴可就之物。”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根基终究在于自身的传统,只有对传统认真内化,才可形成真正的创新。他说:“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在激进的社会变革中,中国文化最美好的部分能够得以保存。
的确,胡先骕文化思想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特别是他那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如针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平民立场,胡先骕批评说:“今日人类物质上精神之幸福,莫非根据于少数大智慧家之学说。历史上之往迹,亦随少数领袖人物为转移……若果一切文化迁就知识卑下之阶级,则浸成一退化之选择。”胡先骕文化思想中的那种将大众视为群氓的精英意识确实是让人不适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相对于肥皂剧集、网络神曲、美女直播、电视选秀,“旧文明之精魂”有着永远的价值和吸引力。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如今,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本质的改变,从而使得更为公允地审视传统成为可能。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在当下的语境,胡先骕“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的思想主张,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a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b 王富仁:《学识·史识·胆识(其一):胡适与学衡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
c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d 胡先骕:《胡先骕文存》,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罗惠缙:《论早期胡先骕的“古典”守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f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頁。
g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李春雨、杨志:《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胡先骕文化思想的价值重估”(ZGW17203);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项目(EEA140385)
作 者: 夏成,硕士,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潘多灵,硕士,豫章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讲师,研究方向:绘本艺术与文化。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