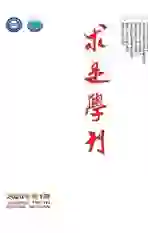波兰尼:意会现象学中的身体与意义
2020-02-26张一兵
张一兵
摘要:波兰尼提出的意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行为并非近代西方认识论所指认的线性反映论,而是一个复杂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场境整合过程。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与狄尔泰的解释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有着或多或少的逻辑关联。
关键词: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认识论;现象学
作者简介:張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23)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1.004
波兰尼①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在他所提出来的意会认知理论中,理性知识的言传自明性被无声的体知意会所替代;主-客二元认知构架中的线性反映论和观念赋型说,被复杂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场境整合所替代,生成了当代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在波兰尼1966年写下的《意会推论的逻辑》②一文中,他明确反对一切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并将在传统科学活动中发生的所有习以为常的东西通通悬置起来拷问,在方法论构境中,他明确赞同胡塞尔、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构式,即在每一个显相的呈现中发现其背后的隐密机制。在这里,波兰尼进一步指认出,如果意会认知是构成一切科学活动的真正基础,那么意会认知的发生就离不开身体。于是,在欧洲现象学构式中已经出现的身体的现象学分析,成了身体与外部双向意会的意义现象学。
一、理论构式上的反对和接近:关于科学知识的现象学和解释学
波兰尼指出,多年以前他就提出了以下观点:“对科学的探索在每一步上都是被无法确切指认的思想力量所决定的。”③这个无法确切指认的思想力量,过去是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得以自动运作的“神秘力量”,在这里当然就是波兰尼的意会认知。在他看来,这也会涉及一个“关于非明言的思想的理论”。在这里,波兰尼特别说明了自己的意会理论在思想史理论构式上的反对和接近。这是一种思想史定位。
首先,是意会认知理论所拒斥的传统科学观和形而上学理念。第一,波兰尼明确说,他的意会认知论,就是要反对在当下科学方法论上占上风的逻辑实证主义,因为,这种“根据感觉材料之间的明言联系来确立所有的知识”的哲学理念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实证主义高喊的“拒斥形而上学”就会是一个不可能现实的幻象。依波兰尼的观点,
我们只要认识到,意会认知是心灵的根本力量(fundamental power),它创造了明言认知,赋予它以意义并控制它的使用。意会认知的形式化(Formalisation),通过创造出关于精确思想的机器无限地增强着心灵的力量,但同时,它也开辟了通向直觉的新的路径;任何想要根据明言规则获得对思想的完全控制的企图都是自相矛盾的,都会带来系统性的误导和文化上的毁坏。对形式化的追求将会在意会的框架(tacit framework)中找到它真正的位置。①
这是波兰尼始终坚持的观点。意会认知是全部心灵存在背后的“根本力量”,被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科学逻辑基础的言明知识,恰恰是由可见“事实”之外的意会认知建构起来的,没有意会认知的内居存在,一切言明知识都无法真实地运转,没有形式化意会构式理解中的科学直观,一切可言明的科学发现和发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没有什么理由能把进行科学解释、科学发现、领会以及获得意义的途径分割开来。它们最终都要依赖于通过同一个关于理解的意会过程(tacit process)”。②这个断言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意会认知是重要的,但它并非真正在科学研究中成为“根本力量”,科学离不开内在意会直观,但科学活动和发展的真实基础是现实社会实践的构序水平,而不仅仅是意识活动中的意会认知。从历史的角度看,东方文化的本质是意会式的体知文化,但在这种意会构式中并没有生成现代实验科学的强力发展,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构序才创造了整个实验科学构式的基础和巨大需求,其中,言传式工具理性赋型当然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不是波兰尼所夸大的意会认知。我以为,说明意会认知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对的,但神化这一作用则是不必的。
第二,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也反对任何用对象化的控制论和行为主义方式对科学本质的误解,因为,科学活动不可能成为一种离开科学家个人心灵活动的外部客观对象运动。依波兰尼所见,科学本身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有目的的活动,它绝不会成为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③所声称的“非目的论的语言”表征下的自然实在。这是对的。内格尔正是波兰尼反对的当代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前者是从柯恩(Morris Raphael Cohen)那里接受了自然主义,又从他的研究生导师杜威那里接受了实用主义,最后以自然主义语境分析(contextualistic analysis)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主将。在内格尔科学自然主义构式中,科学面对的是离开人的生存的外部实在,在非目的论的理性逻辑语言情境中,先在于人的物质结构在科学中得以自然呈现。内格尔的这种自然主义观点遭到了波兰尼的坚决反对,因为在后者看来,一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没有目的的科学活动,也就是说,科学家个人的热情和价值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自然观察”中来;二是被假定为自然描述的理性逻辑,如果不能被科学家个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意会融贯,科学直觉的创造性就不可能突现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天文学中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不会是自然实在的自然呈现,而无不渗透着科学家自己对科学信仰的热情和个性化的知识特征。
其次,是意会认知理论在思想史逻辑构式上最接近的构序质点。这又有两个层面。第一,波兰尼认为,在现代欧洲哲学思想史的构境中,意会认知理论最接近的是现象学构境。说实话,现象学真的与科学哲学构式不在一个平行线上,所以,这是一个故作高深的构式逻辑伪链接。波兰尼说,对于意会认知理论而言,
你可以称这个理论——借用吉尔伯特·赖尔所创造的一个词——关于科学和知识的“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或者,你也可以参照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观点,将它称为关于科学和知识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这也恰当地将我的观点既与分析哲学相联系,也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相联系。①
在波兰尼这里,形式逻辑表征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言明知识构架,而他自己觉得意会认知理论内里的构式逻辑会是吉尔伯特·赖尔②所指认的非形式逻辑。这只是一个说法。而更重要的是,非言明的意会认知力量在哲学构式中更接近胡塞尔和梅洛-庞蒂③的现象学视域。我推测,波兰尼会以为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可以提供有别于实证主义逻辑的基本分析构架,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则更多地涉及以身体为视轴的知觉现象学④讨论。这是波兰尼下面要展开讨论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波兰尼在自己的全部讨论中并没有严格按照现象学构境的理路,只是直觉到自己的观点可以比喻为一种现象学的深层次探讨而已。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波兰尼进入不了现象学的构境。
第二,波兰尼认为,自己的意会认识论与狄尔泰的解释学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它们共同强调了某种理性知识内部发生的复杂作用机制。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波兰尼说,他的意会认知理论中“‘通过内居来认识的观点与狄尔泰的观点有着很明显的联系,但是我将这一观点扩展到自然科学,这一点显然又与狄尔泰的那些观点相对立”。⑤这可能是波兰尼自己并不准确的猜测了。因为,过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观点,狄尔泰区分了用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的解释说明和内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精神理解,波兰尼认为自己把狄尔泰的“精神理解”观点“扩展到自然科学”,但又拒绝了狄尔泰解释学中的上述分界,因为自然科学中的解释同样是以意会认知为基础的,所以,他比狄尔泰更高明一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先人们对狄尔泰的理解中就存在误认,因为,狄尔泰不仅指认了精神科学中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的不可通约性,也已经觉察到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及其观念,说到底,也是人类生命实在之内在体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影。所以,狄尔泰已经发现,我们不可能镜像式地面对自然对象、客观地经验和感知纯粹的外部规定性,自然科学也总已经在一定的人类本性的“存在的总体性(To? talit?t)”,即特定的历史生活关联与境中认识这个世界。在这个构境层中,面对外部自然对象的科学说明的本质还是人们的内在体验之上的理解!⑥所以,更加准确地说,波兰尼的观点与早先的狄尔泰的历史解释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波兰尼显然错怪了狄尔泰。
二、双向内化与内居:现象学构境中的身体意会
当然,波兰尼自认为,与意会认知理论最亲的思想观点是梅洛-庞蒂从身体出发的知觉现象学。这里,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梅洛-庞蒂的相关思想,以及波兰尼由此生发出来的意会认识论中的新观点。我们都知道,在梅洛-庞蒂那里,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特别是其后期的生活世界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梅洛-庞蒂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念推进到了身体现象学。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从身体开始”,由此,他开启了关于身体中的身-心复杂关系的现象学探索。在梅洛-庞蒂看来,身-心关系不是传统哲学中出现的主-客(我-它)分立和决定论构式中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你中有我的“模棱两可”的相互依存和转换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太极图倒是深刻地呈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逻辑构式。犹如我们每个人的左右手相握时发生的身体现象学事件:当我用自己的左手去感觉右手时,左手是认知主体,而右手是被认知的对象性客体,但这一主-客结构完全可以调换过来,即右手去感知左手,二者是处于一种奇妙的互为主-客的转换关系之中。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许多部分都是这种主-客边界模糊的相互依存状态。再比如,我觉得自己有些感冒,下意识地用我的手去摸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这个时候,手是认知主体,而前额成了对象客体,而同时,前额也会感觉到手的温度和其他触感,那一瞬间,两者都是主体和客体。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这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①这样,不同于传统心-身二元论的构式,复杂的身体存在就成为我们通向世界和世界走向我们的存在论基础。这也就是意味着,身体的现象学分析会解构传统认识论的基本构式。
波兰尼显然赞同梅洛-庞蒂的观点。不过在这里,身体的知觉现象学必定会被改写成身体意会的“现象学”。波兰尼指出,
我们的身体是唯一的关于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聚合体(ssembly)——这些东西为我们所知仅仅是通过:我们依靠对它们的觉知而关注到别的东西。我们身体的组成部件作为观察和操作(manipulating)外部对象的工具起作用。每当我们理解世界之时,我们都在依赖着我们对这个世界作用于我們身体的影响和我们的身体对这些影响的复杂回应(complex responses)的意会认识。这是我们的身体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②
波兰尼自己认为,他比梅洛-庞蒂的互为主-客的知觉现象学关系更深入的地方,是强调了在我们通向世界的身体知觉中,关键性的作用是身体本身作为工具所建构出来的意会认知,可是,这种身体工具发挥作用的意会机制却是无比复杂的。由此,身体才获得了我们在宇宙中存在的特殊位置。对此,波兰尼举过很多例子,比如我们通过眼睛经过一个复杂的眼部肌肉、视网膜运动和双眼间距自动调适等等一系列身体意会,瞬间突现出“看到世界”的视觉图像;再比如,我们通过探测工具觉识一个不可见的洞穴内部的情况,探针在洞穴内每一点细微的异质性触点,都会传递给手臂、大脑精神回路综合等复杂身体意会觉识,还原我们无法直接用眼睛看到的洞内状况。然而,波兰尼并没有觉察到,他是将梅洛-庞蒂在现象学意义上讨论的主-客依存的身体存在论重新变成认识论构式中的工具作用,虽然身体的意会功能被呈现出来。然而,波兰尼这一重要的逻辑误认却生出全新的理论构序。
首先,是身体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性的内化和双向内居。在波兰尼这里,不仅身体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复杂工具,而且作为工具的身体与作为自身延伸存在的外部工具之间,也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波兰尼说,
当我们使用导盲杖探索着走路时,我们的辅助觉知是怎样地将我们的身体向外延伸以将这个拐杖包含到(include)我们的身体之中。在讲、读、写中使用语言也是延伸我们的身体器官并使我们变成智能人类存在(intelligent human beings)。我们可以说,当我们学会使用语言或一个探针或一个工具并由此使得我们自己在意识到这些事物时如同意识到我们的身体一样,那么,我们就是将这些东西内化(interiorise)了并使得我们自己内居于(dwell in)它们之中。①
显然,这已经不是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构式,也不是上述波兰尼对身体存在的简单工具论定位,而是工具性的身体与作为我们身体外延存在的外部工具的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身体与工具之间的相互内化和双向内居。依我的看法,这也是波兰尼意会认识论中新出现的核心构序点。在波兰尼看来,我们使用导盲杖是将身体的触觉延伸出去,此时导盲杖不再是简单的外部工具,而是成为我们身体存在的一个内化机能。同理,作为交往工具的语言的使用,则像是把我们的大脑延伸出去,以生成一种智能性的存在,在这里,导盲杖和语言都是通过内居于我们身体存在而实现的。它们就已经是我们的身体存在。在这里,这种相互依存的存在论关联,证伪了传统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简单外部对立,而建构出一种新型的内居意会认识论。需要特别指认的是,这里的用具和语言内化为我们身体存在的一部分,并非传统认识论中的理性主义工具性义肢说,而是强调了用具内化为我们的身体存在,而我们则意会式地内居于它们之中。这是一种将用具(有机性的外部存在)内化于身体,再将我们的存在内居于用具的双向构序逻辑。然后,才有我们进一步利用内居其中的工具再内居于外部世界的意会图景。
其次,我们与世界相互内居和依存的意会存在论。当工具的内居性获得指认之后,波兰尼就更容易展开自己的意会形而上学了。他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哲学认识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将我们身体中的生命与我们对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认识连接起来”的逻辑关系(logical relation)。这已经不再是我们在传统认识论中熟悉的主体(我)与客体(对象性的它)的外部关系,而是一种我内居于它,它成为我的相互依存和双向构式的过程。这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阴阳鱼”太极图,②太极图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逻辑构式恰恰是深刻的关系存在论构序!
并且,波兰尼认为,这种独特双向构序逻辑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我们对整个存在的意会认识上。
当我们从一系列的细节关注到它们形成的整体时,我们在这些细节和那个整体之间建立起一个逻辑关系,这一关系类似于我们的身体与外在于它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理解一个整体的行为视为对它的组成部分的内化(interiorisation of its parts),正是这一内化使得我们内居(dwell in)于这些部分之中。可以说,我们居住在我们理解的细节中,正如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居住在我们使用的工具和探针中,居住在我们于其中被养育长大的文化之中。③
这就又回到波兰尼自己立基于意会逻辑的存在论构境上来了。无非是说,如同身体与工具(及语言)的双向内化意会关系,我们的现实生命在世界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双向意会构式。如果说,我此在在世之中的过程中,世界的内化是赋型予外部事物一种意会性的意义,由此,对象性的它成为我的部分,那么,我们将自己投入关系性的事物内部的意会式存在则是内居(indwelling),即我走向作为自身存在的非对象性的“它”(你)。我觉得,这里的内化-内居构式不仅是波兰尼意会认识论的关键,也会生成一种更深刻的意会存在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意义意会式地赋予周围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时,我们自己恰恰活在其中,波兰尼用dwell in或者更准确的indwelling(正内居于)来表达这种存在关系。
有趣的是,正是在这里,波兰尼在意会认识论中,提出了一个从“我-它”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过程。这是意会认识论的另一个重大进展。其实,波兰尼这一重要逻辑构式还包括他自己原创的第三构境层的“我-我”关系。波兰尼认为,
这样的内居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它使得我们充满感情地参与到我们理解的东西之中。某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困惑;而某种情况又可能会让我们振奋——当我们的理解移除了我们的困惑时,我们会感到释然。这样的智力胜利带给我们一种掌控感(feelings of comprehension),这种掌控感提升着我们的存在感。有关理解的这些感情蔓延地如此深入;在从大写的我-它关系(I-It relation)直到大写的我-你关系(I-Thou relation)的认知进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感情在深度上一直在增加。①
显然,这个从“我-它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受到了马丁·布伯②《我与你》一书的影响。在布伯那里,我-它关系是一种西方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对象性占有和利用的外部非本質关系,而我-你关系则是一种具有神性的本质关系。后者来源于布伯所理解的希伯来圣经,它摆脱了西方科学中那种利用知识和工具的中介式的对象性,而通过非中介的直接性和相互性达及存在的敬畏深处。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马斯洛也借用马丁·布伯的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的区分,将上述两种知识指认为大写的“我-它知识”(I-It knowledge)和“我-你知识”(I-Thou knowledge)。③在这一点上,马斯洛与波兰尼是同向前行的。在这里,如果说,大写的“我-它关系”是喻指绝对客观主义的旧科学观和传统认识论的构式逻辑,那么,大写的“我-你关系”,则代表了科学人本主义科学观和波兰尼的双向内化-内居意会认识论。在后者中,波兰尼意图凸显一种我们(科学家)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意会认知关系,即一切认知的本质都是一种“充满感情地参与到我们理解的东西之中”的活动:一方面,我们通过内化赋型予事物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内居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中。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波兰尼意会认识论的核心构式部分。实际上,这也是波兰尼早年《科学、信仰与社会》一书中科学家个人热情渗入说的进一步深化。
三、意会意义在内化与异化中的建构与解构
在波兰尼看来,意会认知的逻辑构式中存在着一个从(from)辅助意识到(to)焦点意识的转悟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从近侧项到远侧项的转悟过程。实际上,这个被波兰尼指认为“从-到”(from-to)的转悟,在真实的认知过程和意识活动中就是一个当下的意会意义的突现式场境,其中,总是发生着将辅助意识(近侧项)整合为一个指向被注意的焦点(远侧项)的意会意义。或者说,这个from-to不是物理时间上的先后,而是一个逻辑时间上的构式。并且,这一构序进程是不能逆转的,因为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辅助线索(近侧项)时,意会意义的突现(构境)瞬间解构。
当我们将注意力由那些事物所指向的意义转回到获得这一意义的那些事物上时,原本的“从-到”关系就会严重受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手指上,钢琴家会无法演奏;他手指的运动不再会对音乐演奏产生影响,它们失去了它们的意义。①
这是波兰尼反复强调过的问题。他认为,钢琴家的演奏是一个从近侧的手指弹奏到作品乐谱理解的远侧注意,一旦钢琴家将对作品的焦点注意力转回到辅助性手指的敲击时,则立刻会破坏音乐演奏。当然,波兰尼在此的讨论并不是重复意会认知的转悟结构,而是想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意会意义场境的当下建构与解构的复杂机制。这是过去传统认识论根本进入不了的构境层面。用我的话来表达,即场境意义的当下构境与破境问题。
首先,在波兰尼看来,一个事物的意义构序往往出现在它之外的意会整合,而当我们去直接关注这种整合本身时,意会意义场境却会消解。他说,
只要你在看着X(look at X),那么你就不是从X(from X)关注到某些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是它的意义。为了从X关注到它的意义,你就必须不再看着X,在你看着X时你就不再看到它的意义。诚然,意义是坚韧的(tenacious);它一旦建立起来,对它的解构(destruction)就不总是有效的,而且这种解构很少是彻底的,但是,一旦我们又再看着X,把它完全地作为一个对象,那么,这时对意义的解构将会是彻底的。②
这是一个十分抽象的说明。我们来举波兰尼经常用的一个例子。在骑自行车(X)时,我们的注意力焦点一定是放在骑行本身之外的观察路况上,但这一骑行行为的发生,一定是从复杂的行为惯性运动、目光、听力和高度精力集中诸种近侧项共同整合铸就起来的意会式意义构境。如果我们突然把注意力从路况观察转回到自己骑行(X)的手脚的运作操控上,意义构境就会立刻破境,人也会摔倒。这是发生在行为场境中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思想观念构境中的相近场境,我们在读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构式:一是直接关注文本中出现的“自然”“生产”“实践”“劳动”和“对象性活动”等一系列概念,将这一手稿直接判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献;二是将这些概念当作辅助的线索,而将思考焦点转移到青年马克思如何将这些概念整合起来的话语构式方法,从而捕捉到此时真正支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的隐性唯心主义构式。从波兰尼此处的分析看,第一种阅读方式已经是文本总体意义的解构了。当然,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反讽构境。
其次,意会意义的建构与解构背后的内化与异化关系。这里的异化,显然并不是德国古典哲学思想构境中的本真存在-异化沉沦的敌我性悖反,而是生物学、心理学中与同化对立的排异性外化构式。波兰尼认为,在一个意会认知过程里,行为和意识活动中意义的建构和解构是由更深层的原因构序的。
我们的注意力本是从(或者透过)一个事物直指它的意义,那么,当它转向关注这个事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从一个事物关注到它的意义,这就是使它内化(in? teriorise),而再将注意力转回去看着(look instead at)这个事物时,这就是将其外化或者将其异化(exteriorise or alienate)。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我们通过内化(interiorising)一个事物来赋予它以意义,通过异化(alienating)它来摧毁它的意义。③
波兰尼的这一点说明,比上面关于“X”的逻辑推论要通俗一些。这里,波兰尼用内化与异化的构序概念,以说明自己的意会意义场境的建构与解构,这也就是说,一切意义都并非凝固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当下构序起来和瞬间袪序的场境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文本中,波兰尼特意使用了表示事情正在发生的动名词interiorising和alienating。意义总是在特定的意会场境中发生和突现的,它的场境存在往往是透过一个事件或者现象而获得的意会总体,这是对一个事件或者现象的内化和透视;而当我们将思考点仅仅停留在事物或者现象本身时,总体的意义场境则会瓦解,这恰恰是这一事件和现象的外化认知和异化。马克思通过揭示经济拜物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批判,都是透过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物相,揭示出其劳动交换关系在市场中抽象而成的价值关系颠倒,从而超出资产阶级所停留其中的经济物相本身的幻象。用波兰尼的意会认知构式看,经济拜物教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化认知,而拜物教则是掉在物相中的迷雾性外化误认,或者“异化”误认。
请注意,波兰尼此处所指认的内化-异化意义构境,并非仅仅说明复杂意义的生成,它甚至包含了日常生活中随时发生的经验现象的呈现和获取。比如,我们面对的世界的视觉现象的发生。我们每一眼“看到”,其实都是意义的意会式内化发生,而非镜像式的外化(异化)反射。在他看来,视觉的发生是
从大量的线索——有些在我们的视野的边缘(edge of our vision),其它的一些在我们的身体内——关注到它们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将我们的身体体验转换成对外部事物的知觉,这看起来也是这样的过程的个例:我们将无意义的体验(meaningless experience)转换成远侧项上这些体验整合而成的意义。①
波兰尼是想告诉我们,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意会认知构式会复杂很多,甚至在传统反映论中最简单的经验现象的发生,都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意会意義的建构过程。比如,在传统认识论中,我们看见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球,红红的光亮,正在燃烧的木块,以及身体可以感到的热浪等,通常这就是康德先天构架自动觉识后的视觉经验的发生,可是波兰尼让我们注意,此刻,在瞬间的“看到”中,往往都会意会式地塑形生成“火堆”视像,并且依次延伸意会到非康德座架后的“可以取暖”(如果是冬天)、“靠近危险”(某次烫伤的经验)、“不能造成火灾”(电视看到的灾难)等复杂意义。显然。这些意义都不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直接结果,在这里,一大堆无意义的身体体验(比如木柴的可燃性、燃烧中的高温、冬天的寒冷、烧伤之痛、火灾等等),突现式地内化“转换成远侧项上这些体验整合而成的意义”。而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某一个经验现象的直接性外化体验上,整合的内化意义则不复存在。这就是意会认知理论与传统认识论的差异。
再次,意会认知与心物二元论(dualism)的构式悖反。在波兰尼看来,与传统认识论那种凝固化的实体主义观念不同,真实发生的认知结果既不是素朴实在论中的客观实像,也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理念,意会认知凸显了当下的特定主体性场境的发生,并且,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对笛卡儿心物二元论内省的新解。为此,波兰尼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假设一个生理学家已经完全地描绘出一个正看到某东西的人的眼中和脑中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他的观察结果不能使他看到他观察的这个人所看到的东西?这是因为,他是看着这些(即被观察者眼中和脑中所发生的一切)发生,而被观察者则是从这些或者透过这些关注到这些对他而言的意义。②
这更像是一个故事。我们假设,一个天文学家正通过射电光学望远镜观察复杂的星云,他所看到的天文现象并非是具象的简单视觉成像,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意会建构过程;而与此同时,另一位生理学家,通过一个复杂的仪器看到天文学家观察天象时正获得的视网膜和大脑皮层中发生的一切,可是,他并不能看到前者看到的星云显现。因为,后者没有前者通过无数专业知识和观察经验近侧项聚焦整合而成的意会构式中的意义场突现。如果说,前者是意会认知中的意义“心像”,而后者在前者的构境层中则是“物像”。更有趣的问题会是,这二者颠倒一下关系,心物二像性的构境也会完全颠倒,即天文学家去观察生理学家在仪器观测中直接看到的视网膜信息和脑电波成像时,也会是一头雾水。显然,这里的心物关系已经与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根本不同。不准确地说,这是波兰尼在认识论视域中无意捕捉到的意会整合构境与非构境物像之间的关系。这也可能涉及了意会认知的不同意义层级问题。
最后,意会意义建构的不同存在层级。波兰尼也非常明确,他认为,上述的对象性地看着(我-它关系)与意会式地内居关注(我-你关系),也表征了意会认知中的不同结构和存在层级。这似乎还隐喻着这样一种观点:“我-你关系”是意会式内化,而“我-它关系”则是意义场境解构的外化和异化。
看着(looking at)和从……关注到(attending from)的二元论与有机体的明显层级有关,这种独特层级的存在(existence of distinct level)为二元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意会认知的结构在有机体的运作中有它的对应结构,决定着某个有机体的稳定性和力量的那些法则在控制着这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对应结构。①
显然,波兰尼这里借用的“二元论”为假,因为它并非真的是两个基始性本原的并存,它至多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构式。实际上有意义的是,他这里提出了意会存在中的不同存在结构的层级问题,即一定的意会结构由一定的运作法则所支配。但在具体的讨论中,波兰尼的构式却是有问题的。对此,他列举了一只手表的例子。
我的手表为我指示时间。它能够不停地在走,这是因为它的主发条在游丝和摆轮的控制下进行绕旋反解;这能推动它的指针转动,指针能够指示时间。这是手表的工作原理,也正是这一原理规定了它的构造和运行(construction and working)。这个原理不能用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来说明。手表中没有哪一个组成部分是由物质的自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ation)来形成的。这些组成部分都是由人工塑形(artificially shaped)制造出来的,并且被灵敏地连接起来以发挥(perform)它们指示时间的功能。这就是它们的意义:“理解”一块手表,也就是理解它是做什么用的以及它是怎么工作的。②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故事。手表为我们指示时间,但手表能够标识时间,却是因为它的内部有一个我们并不能真正知晓其运行原理的极其复杂的精密运转着的机器。波兰尼告诉我们,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层级:“这一认知结构对应着由不同原则决定的两个层级。被直接关注的这些细节被无生命自然的法则所控制;而在这些细节在被联合起来以从它们关注到它们的联合功能时,它们是被机器的工作原理所控制。”③这是说,手表中每一个部件的物性存在细节是被自然法则控制的,但手表的整体功能却属于一个新的机器运作层级法则。这个解析显然是粗糙的。因为依我的看法,如果是在意会认知逻辑构式中,第一个层级根本不属于意会认知,第二个层级才是意会构式。如果再认真一些,这里的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它至少会出现两个以上的多重存在层级:一是手表的所有部件之物质承载者都属于自然物质存在;二是手表的所有部件的人工劳动塑形,早就已经超出了自然物质存在方式,它们的作用固然仍属于自然法则,但实际上已经是工业生产中人工重新构序的东西了;三是让这些部件以复杂的结构组装起来并以特定的机械运作功能精确指示时间的功能,这更不是自然界法则的作用,而是人构式起来的全新物质存在方式,它的运行机制是人的技术赋型的结果;四是我们透过手表的机械运转,意会式地知晓时间,这第四个层级也不属于人所利用和建构起来的机械运动法则,它是人的存在内化于对象,并意会式地内居于其中的意会认知法则。显然,也只有最后一个层级是意会认知发生作用的地方。波兰尼没有界划清楚的地方,并非意会认知本身的层级,而是不同存在构序中的层级。
波兰尼似乎对自己的这一新观点很是得意,他进一步总结到,“这展开了关于层级的整个序列的图景,這一序列一直通向担负责任的人类那一层级。这一序列将会形成一个关于运作的层级,每一个更高的层级控制着低一级的层级留下的不确定的空白”。①作为科学家,波兰尼的一个非专业哲学家的弱点是,喜欢简单放大自己理论构式的意义域。他认为自己关于意会层级论的观点可以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普适性话语。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我们自己直接建构的话语事件的层级结构。波兰尼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文艺作品的生产来展示这一结构,比如,以讲话为例。它包含五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也是最低一个层级,是发出声音;第二个层级是词语的表达(utterance);第三个层级是接合(joining)词成句;第四个层级,是句子的组合形成某种风格(style);第五个层级,也是最高的层级,是构成(composition)文本。②
然后,波兰尼煞有介事地解释道:“每一层级的法则都在邻近的更高一层级的法则的控制下运作。词汇表使得你所发出的声音成为词;既定的词汇表根据某种语法形成句子;句子被纳入某种风格,接着它被用以传达这篇文章的观点。”③当然,这五个层级是波兰尼硬分出来的,因为在我们日常的演讲中,它是一个意会发生的整体。比如,我在做一个关于波兰尼意会认识论的原创性的学术发言,讲话,这是一个物理声音的生理制造,其实,说出的话已经是被组成句子的词语,并且,它一定带有我的构境论风格,完整地表达则为有思想内容构境的话语文本。可是波兰尼没有注意的细节是,完全有可能一个演讲者的话语有词语没风格,且更没有原创意义上的思想性。粗一点说,即有前三个层级却没有后两个层级。比如一个照本宣科的老师的授课,他可以讲课,但这种讲课是谈不到风格的。更直接的例证是,在一个中国幼童背诵一首唐诗的他性境像复制中,没有上述这五个功能性结构层级,因为,除去物理发声,后四个话语生产层级都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意会认知并不在场。
①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著有《科学、信仰与社会》(Science,Faith,andSociety, 1946)、《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1959)、《超越虚无主义》(Beyond Nihilism , 1960)、《认知与存在》(Knowing and Being ,1961)、《意会向度》(The Tacit Dimension ,1966)、《意义》(Meaning ,1974)等。
②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 in Philosophy, Vol. 41, No. 155(Jan., 1966), pp. 1-18.
③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5页。
②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5页。
③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1901—1985):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193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短期执教于纽约市立学院,从1931年起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间只有1966年任职于洛克菲勒大学哲学系),1946年起升为教授,1955—1966年任约翰·杜威讲座教授,1966—1970年任校级教授,1970年退休。主要代表作为:《没有形而上学的逻辑》(1957)、《哥德尔的证明》(合著,1958年)、《科学的结构》(1961)、《对目的论的再考察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其他论文》(1978)等。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4页。
②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英國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起在牛津大学任教。1939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1945年退役后,回牛津大学任韦恩弗利特讲座形而上学哲学教授。1947年任《精神》杂志主编,1968年退休。赖尔早年倾向于E.胡塞尔的现象学,后来对逻辑原子论、逻辑经验主义感兴趣,最终转向日常语言哲学。代表论著有:《心的概念》(1949)、《两难论法》(1962)、《柏拉图的进展》(1966)、《论思想》(1979)等。
③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后来主持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席,与萨特一起主编过《现代》杂志。主要著作有:《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和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等。
④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4页。
⑥参见拙文:《关联与境:狄尔泰的历史哲学》,《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73—183页。
①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302页。
②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5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6页。
②太极图是我国古代文化中表达宇宙间阴阳力量关系交织、相互依存的重要哲学标识。所谓太极即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其中的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易经系辞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由于太极图形如阴阳两鱼互纠在一起,因而被称为“阴阳鱼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的思想渊源可上推到原始时代的阴阳观念,太极图早期也称作“先天图”。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纠合,正是阴阳对立统一、相互消长、互根互动理念的最佳图示。
③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6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6页。
②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奥地利著名哲学家。1878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1896年至1900年,先后在维也纳大学、来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与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艺术,醉心于狄尔泰和齐美尔的哲学。1924年至193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宗教哲学教授与伦理学教授。1938年,布伯移居到巴勒斯坦,任希伯来大学宗教社会学教授,而后又出任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是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的首届主席,1965年逝世于耶路撒冷。主要代表作有:《我与你》(1923)、《人与人之间》(1947)、《两种类型的信仰》(1950)、《善恶观念》(1952)等。
③马斯洛:《科学心理学》,林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3页。
②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3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 in Philosophy, Vol. 41, No. 155(Jan., 1966), pp.8-9。
③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3—124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4页。
②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24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1页。
②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1—132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Tacit Infer? ence”, in Philosophy, Vol. 41, No. 155(Jan., 1966), pp.15。
③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2页。
①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2页。
②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2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 in Philosophy, Vol. 41, No. 155(Jan., 1966), pp.16。
③波蘭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第133页。
Polanyi:BodyandMeaninginPhenomenologyof TacitCognition
ZHANG Yi-bing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acit cognitive theory by Polanyi, the cognitive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is not the linear reflection theory pointed out by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y, but a complex process of field integration of auxiliary consciousness and focus consciousness. Tacit cognitive theory by Polanyi is more or less logically related to hermeneutics by Dilthey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by Merleau-Ponty.
Key words: Polanyi, tacit cognitive theory, epistemology, phenome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