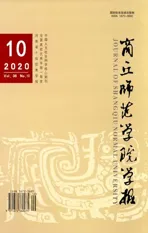东方视域下的过程存在论
——庄子的独特解读
2020-02-25德丝拉瓦达美诺娃
德丝拉瓦·达美诺娃
(保加利亚 圣索菲亚大学 汉学中心)
一、存在论与道家哲学引论
在中国古代思想背景下,哲学解释方法揭示了一个渴望结合东方传统价值和存在解析论的成就。道教文化遗产不仅通过它的镜像差异性,还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道合一的理念吸引着欧洲人。许多作者,包括诗人、作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科学家,都根据东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去认识存在论和解释论的区别。这样的预设成为与“远东精神”、东方人和东方传统有关的精妙理论、比较研究和政治理论的起点。
我们可能会问自己,将道家存在论的概述构建为一个想象整体是否正确,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合理。由于鄙视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和现在技术文化的人为性,道教和与广泛性有关的文化为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创造力来源。它揭示了生命中隐藏的无常,也揭示了宇宙或者社会中的基本问题必然不能通过哲学理论来展示,而只能体现在诗歌、寓言或意象思维的假设中。它执行着一种哲学批判,批判着这种思想——随着从认识论到存在论含义的转变,所谓的“常识”可能存在于知识的其他分支和语言方式中。
中国古代哲学不是研究认识论问题,而是真实的人通过智慧找到一种方法去解决真实的问题。在道的哲学假设过程中,一个普遍统一性本身就包含着一切,称之为“道”(道有两个主要含义:“道路”和“方法”)。儒家经典探索道的历史的真实性,而道家哲学(以自发性为主导)则排除任何传统的区别。道家注重无标准、无竞争的态度,甚至挑战了自身学说的合理性。
过程存在意味着在所有的人为性的意义之前,被称为“想象思维者”,是以无条件、不可还原的方式存在着,涵盖着无边无际并且反对任何自然话语的失真。作为一种终极的化身,言语诞生于“虚无”的头脑里,就像声音出现在寂静中一样,因此“遗忘词语”是任何认识的前提。庄子是第一个研究语言限制的中国哲学家,并且研究了道的语言是自发性生成的,具有潜在的丰富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庄子》是由战国中期的庄子及其后学撰写的。书中一些令人惊叹的故事,揭示了所谓思想狭隘的人的现实状态,与圣贤相比,他们徘徊在云层之上的日常生活中。庄子阐述了如何去施展想象力的方法,最关键的是用简单的思维方式,用新颖和原始的方法思考。庄子用幽默和严密的逻辑去抨击一些关于世界的独断的主张,特别是对什么是善和恶、对与错的判断学说。庄子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语言的使用有着非常规的思考,并且他的自发性想法消除了对纯粹工具理性的关注。
尽管他有着怀疑的态度,但庄子并不认为我们的处境是彻底绝望的,至少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变得更好。作为一种建设性行为,他的虚构模式遵循着至关重要的忍耐力思想和“精神期望”创造了分散策略。在无限中飞跃暗示着一种虚构的现实,其中的一切都既是暂时的而同时又是永恒的,超越了日常的任何活动。这种对于真实生活的思索,超越了常规和限制,造成了缺乏任何世俗眼界的“快乐生活”。在潜在的想象中,这个逍遥游的人自己沉浸在清醒和昏睡的边界中,这使他以一种高昂的姿态超越了任何动机和目的(这被称为非行动)。
让我们以过程存在论为视角分析庄子关于存在的三个原则。
二、庄子关于存在的三个原则
(一)将过程存在作为精神之旅(变化原则)
道的过程存在论是对美德、智慧和超越物质条件的渴望,是精神通过漫游转换的完整寓言。中国的叙事常常将思想的自由旅途与天、地、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思想结合起来。在这个概念里,我们短暂的存在只是一段航程、一条道路或是一段巡回。逍遥游被认为是打破常规的构想,进入想象现实中,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意识阶段和终极解放。在离开现实世界的这些人中,这位游者一直在这条路上,路上有多个开放的目的地,并且在这条路上他会经常改变自己的行程。最终,他唯一的目的地就是自己,这是非常光辉和超前的终点。
东方神一般的圣人超出日常生活活动的一般状态,即使他仍然生活在其他人群中。道人(行者)在两个世界中徘徊:一方面他实现了神潜在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像道家圣人一样神圣般的美德。在神仙和圣人之间徘徊的原因使我们进入到这种条件所附加的矛盾心理的核心——去漫游意味着要了解一切,同时现在我们一无所知。行者的每一次转弯可能会被赞扬为权威,或者被遗弃、被驳斥为流浪,甚至被贬低成一个乞丐。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漫游是偏离真理,还是走向真理的一种方式?漫游的基础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纯粹的自由。
行者可能会变成崇高的存在主义人物,一个能通过不断隐喻的运动从“彼岸”信息发现自身意义的人——飞入无边无际。庄子的漫游(逍遥游)关闭了生命中隐藏意义的无常,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一种存在主义的分析或者被称为“具体哲学”。漫游与人的生命统一代表着人的短暂存在,伴随着非常困难和突兀的转变。这种运动是离心式的——跨过了熟悉的边界去探寻遥远且近乎传奇的地方,用稳固单一的轨道去交换遥远未知的世界。或许这种运动是向心式的——渴望被视为古代中心的东西,包括返回到文化源头的神圣之地。
让我们探寻一下道家哲学把圣人解释为漫游者的影响。将行者从已知世界移除的目的还有更深的含义,据称在未知领域发生的运动并没有发生。那遥远的地方并不存在,并且没有人看到那些地方。在极端的形式下,无地点的漫游是重言式表达的——行者来自游子村,来自地球边缘的平原,等等。除了争取一个名声地位,自由地翱翔与墨守成规的官场作风是绝对对立的。真正的智者知道,他自己仍然是无知的;他从一个“没人看到过的地方”来,并且接纳一切、也不评判别人的行为。
当思想的运转被打断,意识就会转向无意识,圣人就会达到专注当下和超越当下行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他无法描绘出“无序”情形下发生了什么。这种方式(道)的特点是具体并且真实,但是通过预言和虚构思考它,就会把现实神话,从而幻想建立一个想象王国。作为行者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跟随道,不知何故,像做梦一样,甚至是无知,因为他说不出来;他“忘词了”,他的舌头打结了。智者的内心是空虚的,没有什么思想将他和现实联系起来,他能获取与道的直接感知。循着这个方向研究,道家的启蒙点可能就是对现实自成一体的批判。庄子发展了生命之梦的隐喻:从想象的视角,揭示了死亡和生命的新体验,也纠正了对存在真实意义的误解。
自然被看作是自发和改变的,而不是对人类活动和变迁无关紧要的基础。贯穿于存在的差异性和平等性之中的就是转换的原则。道的自我转换包含了多样的相对性等,人和蝴蝶联系在一起,生命和死亡也联系在一起。在云层上翱翔的人仅仅是超越了天空和大地,他们的思想状态依然不受任何运动的约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他塑造了一种新的个人、诗意和文化类型,并通过“无翼飞翔”的寓言来表达——打破无知的枷锁。精神之旅是由一种视觉的、非文本的、象征性的语言和所谓的“形象思维”来代表的,即把事物的画面和形象作为一种梦的隐喻。《庄子》中的蝴蝶梦说明了生命的短暂性和二元性。
(二)蝴蝶梦和生命的短暂(差异原则)
上面提到,庄子是中国最重要和最矛盾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神秘哲学中,现实被看作是由一种无限转换的表象所产生出的幻觉。他将自己的思想写成寓言故事,就是著名的“蝴蝶梦”。在叙述庄周梦蝶中,庄子从梦中醒来,他不确定自己是真的睡着并梦到一只蝴蝶,还是一只睡着的蝴蝶在做梦化为了自己。根据这位哲人的观点,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并且认为将“存在”作为一种与“不存在”完全不同的状态是错误的。相反,庄子认为,无行为是一种行为,人们对信以为真的事情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了解。
梦的内容不是现实中的经历,它是假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做梦,在梦中做各种奇怪的旅行,就好像这是真的一样。想象的力量,从伪深刻和迷人的思想展示出来。对庄周来说,他绝对不可能变成蝴蝶,但是这个梦的经历是真实的——在非反身的关键时刻它不是梦,是一种感知。这种感知引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生命是什么?仅是一个梦?或是梦拥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埃舍尔的黑白版画一样奇怪:两种隐喻和显像相互交织而存在。记忆和想象力包含了简单和复杂的形象,但是其目标是将记忆指向正在发生的客观形象——重新安排现实的经历,以及不存在的虚构故事。
事实上,《庄子》的模仿展示的不仅仅是讽刺才能——通过讽刺他发现了无限,不断的经历着知识的边界。幽默通过不相容的世界观碰撞产生,笑声像“重击”突然爆发,一个正常态度上的突破,迎接着不可接受。梦自身展示了“与现实相对的黑暗”——非结构性的、混乱的、持续运动的道的整体。自我修正的概念综合了道教哲学三个认知存在方面:价值论、认知论和心理技术,表明了正义和开明的圣人的生活方式——与宇宙转变期一致的人。
要从想象中逃离就意味着要走入一种坎坷的——这是一种对所有差异立即一视同仁的不断体验,或者说所有形式的表达绝对接近道的情况下重新定向。《庄子》讨论了大觉,克服了梦和醒的状态的对立。天籁作为讲话和沉默之间的过渡,真正的诚忘预示着知识和无知。正如《庄子》在二十六章所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道家大师们无休止地谈论着自己的道路,借着寓言他们更新了日常的启蒙,同时保持了完全的沉默。根据“不可言说的道”,主张无名就是自发的遗忘,顺其自然。我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忘记语言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和他说话了。庄子在其著作的上述章节中提出了矛盾的问题。道作为过程,是发生的可能性的增长,而不是发生的产生,所以在道的表达中,任何语言暴力显得过分并无用。中国的思维深入地探索了这种因果不确定性和不可言说性,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现实层面。
(三)事物和存在的普遍平等(平等原则)
“万物平等”是一种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是不竞争:平等要求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摒弃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将万物看作是自然现象,自满自足,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挑战了自我意识的合理性。哲学在生活方式中的作用体现在智者描述的故事中——不是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而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庄子的嬉闹和自由——在想象的世界中漫游——用“无目的漫游”来表达。
想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着自身的前提、结构和力量,并深刻地体现在庄子的文本中。通过观察大量的自然现象,如飘风、江海、声音、颜色、婴儿、狗等,庄子试图去传递一种“反道运动”,这是一种对自然虚构、讽喻性的模仿。在经验层面上,宇宙的对立并不会发生在漫游者的思想和行为中。竞争行为的叙述在文本中共存,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虚构和想象。想象在广义上是思想形成博学思维的回忆——用经验的某些元素复述故事,以便创造一个与经验现实更具针对性的对比。在狭义上,想象仅仅意味着思想不是一个物体的真实形象——我们可以开始想象无存在,例如《逍遥游》中的鱼鲲和鸟鹏,作为一个神话般旅程的例子。
在某种意义上,道家的世界观以及非笛卡尔哲学的逻辑,赞扬了生存的美德和自然的和谐——在西方似乎是一种潮流,但这其实不是一种新潮流,而是回归对自然生活的原始态度。由内在转化过程所产生出真诚的、真实的心境被称为“自我”。许多道家的思想家从我们生活的普通社会世界中区别出“自然”——当我们顺着我们的本性,其结果就是和平和繁荣;当我们反对本性,其结果就是混乱的。自然是自发和平和和谐系统的表达,所有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在道路上的位置。万物平等的道义要求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当看万物时,摒弃你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摆脱令人窒息的命令式的形式。
道家不仅努力去完善万物平等原则,而且还鼓励自我实现和个人表达的完整性。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所建议的那样,拒绝维持特权隐私并不意味着否定了人格现象,而是描述了相互存在模式下的基本主体间相关性。智慧和超脱并不重叠:道者在世俗中拖着他的包袱,因为他的使命是忠于他所命定的时间。人性的概念描述了一种内在的倾向,以回应道的召唤,重新发现一个在另一个(存在混合)作为实现固有的道的效力。
道虽然常年空无,但在道之外是不可能改变的;熟悉不断变化规律的人与伟大的终极(太极)和谐相处。聪明的人是冷静的、不受约束的、心胸宽广的,不像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他们不可能有存在主义的倾向。一个人对生产运作的开放性和预见性有着清晰的愿景,感知到有形转换背后的无形过程,以及表面坚持背后隐藏的多事世界。道圣完全明白,天、地、万有和他自己都是一体的,万物最终都各就其位,完整的恢复可以通过原始自然的纯净来实现。拥有真正智慧的人远远超出了事件的链条交替,而他无法控制自然的认识,使他更接近于与道自发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摆脱任何固执的过程中,应该抛弃实质性的语言——真正的大师知道如何探索所有人类可能的观点,探究关于道路真相的所有观点,同时对它们进行均衡和超越。说道时,运用各种功能形式的诗意来表达,如庄子的所谓的“杯状词”,在神圣平等的光芒下,无限地出现。天有开始,没有开始,没有无开始;有存在,有非存在,没有不存在。突然之间,就有了存在和非存在的区别。然而,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存在,什么是真正的非存在。
三、结论
沃尔法 (Wohlfart)教授的分析,涵盖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对早期道教寓言中道家语言艺术的简要概述 。关于“无”(不存在)与“有”(存在)在词源上的争论可以归纳如下:《道德经》中的充实和空虚并不表明纯粹的存在和不存在——“无”和“有”作为发生现象学结构的两个阶段,相互包含,超出纯粹的存在论的规定。对“无”(无被认为是中国原始逻辑中最早的人为抽象概念)表意读物示意地描述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1)用火来清除难以穿透的灌木丛——砍伐树木后,森林就消失了,但它重新生长的潜力被保留了下来。它的转变是一个从不存在到存在的转变,需要隐藏的潜力的逆转(储存的种子和茎发芽的基质)。(2)一种仪式上的萨满舞蹈,它的哑剧般的模拟动作唤起了人们想要的存在状态。圣人转向表象发作之前可用的象征性维度,这是其他事物奇迹般地转化为另一种事物或成为事物的开端。
在经验世界里,“无”和“有”是存在的基本模式,和转换形式一样(无就是没有),通过返回到原初的道来实现转换。反过来,存在“有”源于非存在“无”——显然,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出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它们之间的相对立。道家存在论体现的是在发生语境中普遍变成“出现”和“离开”。 “道”作为一个过程是由空虚和丰满统一所形成——轮子、罐子和房间通过它们内部的空,来达到它们的用途。它们依赖于作为阴阳统一的道来完成使用,不应该仅仅被描述为对象,而应该被看作功能过程。在道家哲学中,空作为意义的主要来源,在可得性模式中比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权:智者会回归到无的恒常性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