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丰村小说《美丽》的“道德试错”性
2020-01-25周文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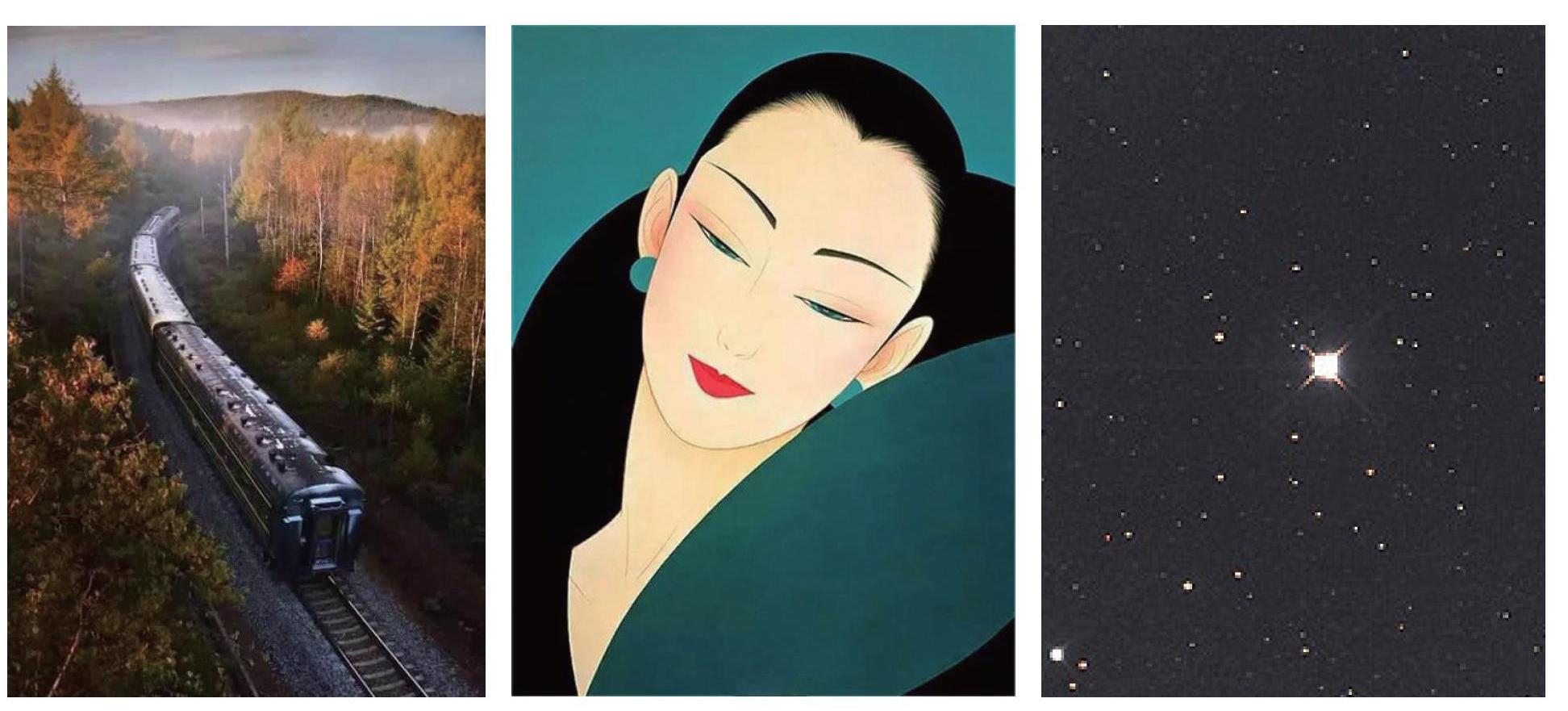
摘 要:丰村的《美丽》是一部以婚外恋为题材的小说,由于其所处特殊的时代性,使这篇小说成为“道德试错”的典型,具体体现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小我”成全“大我”的自我牺牲精神等方面,所依据的仍然是政治标准。这既有其特殊年代的局限性,也有作者主观上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态度。
关键词:道德试错;三角恋;“小我”与“大我”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文学界曾出现了一批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写人情”的作品。其中,尤以婚恋题材的小说受人关注。丰村的短篇小说《美丽》面世之初便受到极大争议,其后在反右运动中又被冠以“宣扬资产阶级个人爱情观点”之名定为“毒草”。直至1979年,才被作为“重放的鲜花”之一再次面世。而作为“鲜花”重新开放,所依据的更多是政治标准,在文学史上也多是以“突破题材的禁区”来概括这一文学现象,而孙先科先生则从文本出发,将《美丽》认定为“道德试错”的典型。 所谓“道德试错”便是“主人公由寻求一种新的感情关系开始,使旧的平衡遭受破坏,但“尝试”过后,经过自助或他助、自律或他律的修复过程,重新回到旧的感情状态。”[1]29-37本文將以此概念为基础,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人物设置,“小我”成全“大我”以及“道德试错”的实质来具体分析这篇小说的“道德试错”性。
一、“道德试错”的前提
——人物关系的设置
黑格尔认为人物关系设置对叙事具有整体的影响。人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情节形成的基础,更影响着故事的走向。小说《美丽》中的人物关系可分为两重——三角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而无论就其中的哪种关系来看,都是具有不伦性的,这也给人物的“道德试错”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季玉洁与首长。季玉洁作为首长的秘书,对工作尽职尽责而又严格苛刻,尤其对自己的上司从生活到工作照顾得可说是无微不至。在她的认知里,她的责任就是为首长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成为首长的“记事本”“眼睛”“耳朵”“脚和手”。在季玉洁的描述中,首长是一个完全称职且令人尊敬的领导形象,也是一个典型的“十七年”时期的干部形象:对下属理解、体贴、负责,但也相对严格。对首长的钦佩使这个刚步入社会的女大学生不愿意看到首长对自己工作的任何不满意,也就不自觉地扩大了她的工作范围:从首长的作风、习惯、兴趣到身体健康,无所不至。正是这种“过度”的工作热情与责任,使她产生了对首长超出上下级关系的男女之情。她会为了首长“青年干部应该有时间学习”的建议熬坏身体,也在病中期待又恐惧着首长的到来,以至“我不见他,我就担心,我希望看见他,而我一看见他的眼睛就会不安,接近他我也会心跳”。但这种理应受“道德谴责”的感情没有得到她本人认可而选择了压抑,即使在首长的妻子姚华去世后也未曾接受首长的求爱。姚华的仇视与临死前的不甘以及外界的议论让她无法对自己所爱的人敞开心扉,后来进京看望老首长,也因为家里多了个“不是什么生客”的女人而选择再一次启用道德力量来压抑自己的真实心迹。
(二)季玉洁与首长夫人。季玉洁和首长夫人姚华可以说是“亲近”的,但无形中她们也是“情敌”的竞争关系。在季玉洁的感情并未明显外露时,二人之间可说是互帮互助的姐妹关系,她们之间关系的转折则是因为姚华对季玉洁情感心理的察觉:“我们家像有一块吸铁石吸着你哩”,对季玉洁渐渐敌视。可以说姚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认为幸福应该体现在家庭,即使生病也不愿意离开家庭,但受过革命与战争锻炼的姚华似乎也缺乏着一份传统女性所特有的温柔与智慧,临死之际没有谱写托孤托夫的颂歌,而是竭力阻止季玉洁占有自己的丈夫与家庭。正是在姚华无情的“维权”的对比中,季玉洁的形象竟变得无辜可怜起来。在她察觉对首长的心意后,竭力压抑自己的情感流露,并向党支部书记寻求帮助,向组织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对于姚华,即使她对自己仇视憎恨,季玉洁也会提醒首长去看望重病的妻子,这种无私的行为背后,难说没有作为“第三者”的心虚与愧疚。无论如何,季玉洁与首长最终的无法结合,姚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首长与首长夫人。这是一对典型的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夫妻,二人在革命时期同生共死,感情的基础与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姚华作为妻子,深爱丈夫也懂得如何爱,在与季玉洁的关系恶化后,也尽量避免在丈夫面前表露,更不会将之归责丈夫而产生争吵。即使临死之际,也要宣布对丈夫的永久霸权,但却没有得到丈夫的最后一眼。生活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首长对于姚华,无疑是有爱情的,但终究因公而未能见妻子最后一面,是典型的“十七年”时期的英雄叙事。恰是出于这样的革命爱情,首长即使已经察觉季玉洁的心意却没有点破,也为季玉洁情感的不伦性增设了前提。
丰村便是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三角恋爱网。首长作为两个女性追逐爱恋的对象,在这段关系中是一个缺乏明确态度立场的主体,他的存在只是保证一个道德视角和道德主题的形成以及这段三角关系稳定性的保持。季玉洁作为“第三者”出现,实际上将两角的爱情关系转换为“三角”的道德关系,她在小说中承担的不仅是三角爱情关系中的一角,更是承担着一种“符号的,抽象的功能”——道德抉择。
与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不同,季玉洁作为“第三者”这一形象与其感情承受者——首长有着另一层身份关系——上下级。在季玉洁对首长妥善细心照顾的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人揣测的对象,“机关里的同志也不是没有意见呵”“但你对秘书长的态度,是不是有向上爬的思想呢?”这种上下级关系的严肃性使单纯的爱慕变成他人眼中向上爬的工具,如果季玉洁后来没有拒绝首长的求爱,那么不难预测这种结合势必会成为一部分人口中的“向上爬”。这种“办公室”恋情的身份设定也给本已“不正当性”的感情增添了一把道德的枷锁。
二、“道德试错”的实现
——“小我”成全“大我”
对于季玉洁和首长以及姚华的三角纠葛,丰村给出的解决方式便是“小我”成全“大我。诚如孙先科所言:“以牺牲爱情的立场解决“三角”冲突,以维护道德选择的合法性”[1]29-37。
那这种成全是如何实现的呢?当季玉洁意识到对首长感情的异样时,知道自己不能爱他,否则就会陷进错误的泥坑,所以宁愿自己承担痛苦也不愿破坏首长的家庭,这在道德上是值得歌颂的,也是很顺理自然的情感。但在姚华病逝之后,首长的求爱此时已經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毕竟“三角关系”这一道阻碍已消失。若此时季玉洁答应首长的求爱,在合理性上是无可指摘的。笔者认为,此时她依然顾虑着他人的话语评价以及姚华临死时的威示,使得道德上的“大我”依旧占上风,而无法遵从真实的人性自我。如果说第一次拒绝首长的求爱尚有这两件枷锁的阻隔,那么时过境迁之后,季玉洁再次见到首长并打算表明心迹时,她此时的退缩则是作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有意为之。究其原因,“作品为表彰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为他人、为工作),人为地将感情逻辑扭曲、复杂化了”[1]29-37,只是因为首长家里多了个“不是什么生客”的女人,就将自己再一次置于“第三者”的位置上,以道德的名义压抑自己的感情,而她的这种感情最终破灭的痛苦亦是作者为凸显她的道德性而强加的。为了强化季玉洁牺牲“小我”的崇高形象与合理性,作者给予她一种至高的褒奖:“北京的夜是多么好,在深夜里,你就会觉得与毛主席在一起哩。”在这失恋未眠的深夜,“大爱”战胜“小爱”的季玉洁,内心个人情感也完全被道德压榨殆尽,能给她以安慰的也只有自己所信仰的主流价值观。
作者在将“小爱”升华为“大爱”时使用的逻辑是非此即彼的,二者互相不见容于对方,有人认为这是将“大爱”与“小爱”根本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虚设。”[1]29-37这一点也可以从季玉洁与外科医生的爱情上体现出来。在与外科医生相处的过程中,由于工作原因,季玉洁多次爽约,将培养爱情的情人间正常的交往行为看成与工作所代表的具有崇高性的“大爱”相对立的一面。这种“小爱”与“大爱”根本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她发出反抗:“为了爱情,要我放弃工作,改变职业这是不可能的”。如此为了突出季玉洁崇高的“大我”形象而使她为工作事业做出情感的牺牲,在一定程度上是做作的,不自然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病态的“自虐”。
而作为人性之一部分的自然情感诉求遭到压抑,势必会对其本人造成一定的影响与改变。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失去“小我”情感的季玉洁并非像季大姐所说的那般幸福,这体现在季玉洁叙述这段感情经历时忧伤、愁苦的外部环境:“火车轰轰地飞奔,窗外的春天的黄沙仿佛雾气一样,紧跟着狂跑的火车流滚。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风在车窗外面的旷野上嘶叫着,有时也发狂地碰动着火车的窗户。”故事是在一个并不晴朗的环境中展开的,故事的主人公——季玉洁在回顾自己的爱情经历时始终有一种“别扭”的表情:“也许是由于心情的沉重和烦乱?皱了皱惯于思索的眉头,迟疑着坐在了我的身边,久久没有说话。”而季大姐作为故事的转述者,无论怎样给主人公的结局添加幸福的因子,小说中也始终弥漫着一种“苦涩情结”。
季玉洁选择压抑“小我”的人性私欲,除了失去爱情,还成为了“无爱”的女性。但作者毕竟带着“突破束缚”的文学写作使命,与当时正在出现的男性化的、缺乏个体情感的“铁姑娘”不同,有着人性情感的因素,融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于一体。但是,这样的人物形象,也显示出写作者面临的一个无法消除的悖论:既不愿意按流行模式写作又不能真正冲决模式,因而小说中的女性只能不断地清理、抛弃自己的自然属性(女儿性),不断加添自己的社会性因子,最终变得“无性”和“无情”。对于这种女性,作者仍是采取一种歌颂的态度,“一个事业上的胜利者,在生活上会是败北的吗?”作者通过抽空幸福的所指,将幸福与事业强行联系在一起。“她仿佛是企图说服我似的”“你看着,玉洁会是幸福的,她怎么会不幸福呢?”这里季大姐也即作者想要说服的不仅是听故事的“我”,更是听到这个故事的所有其他听众以及季大姐本人:季玉洁所作的牺牲是正确的,能够敢于牺牲“小我”的人必定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和有主张的人,也一定会因她的牺牲而成为一个更“幸福”的人。笔者认为,作者对季玉洁生活态度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存在的极左思潮对创作和个人生活及思维的影响。
三、“道德试错”的写作实质
——公共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抑
“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领域比较活跃,出现了一批突破了之前极左文学思想“禁区”的各种题材的作品,但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仍然是最重要的原则。丰村的小说《美丽》虽然以“婚外恋”题材写人性人情,与前期小说相比有所突破,但所触及的只是题材禁区,其内核仍是政治性道德小说,或者说这种“道德试错”小说是一种对政治与道德宏大主题的“深度模式”改写。
既然作为实质上的政治道德小说,季玉洁个人对爱情的自然情感诉求受到道德和政治的双重克制就在所必然。支部书记在小说中是政治力量的化身,她让季玉洁对党保证自己的思想动机,而她后来也基于对党和支部书记的保证,拒绝了首长的求爱,且最终与期待的爱情擦肩而过。作者加于季玉洁工作与爱情的冲突,虚设二者的绝对对立性,将情感的“小我”完全压抑,形成张扬夸张的“大我”形象。以至于如有的论者所说,“婚姻已经是高张道德的场所,正常的两性之间的情爱已经被异化。私欲之爱与道德训诫为指向上的大爱之间呈现为一种两分的矛盾和断裂,私欲之爱只是充当了一个供道德训诫进行否定和批判的不光彩角色。”[3]同时期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也是以婚恋为题材的同类型作品,我们也可以从小说中科长的话里找到这种压抑个性的爱情观:“我们这个杜会的人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不就是要这样的关心别人,关心集体么?对别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互相都把对方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说穿了,共产主义精神不就是这么个内核吗?
之所以如此,从写作者的因素来看,当然受着社会思潮的限定,而且丰村本人从抗日战争时期投身于革命事业,创作体现为政治服务也是必然。在自述中说,自己之所以会写这篇小说,是因为“1955年,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著名报告,启发、教育了我”,小说写的“仅仅是忠于党的事业,热爱工作,勇于生活的普通青年知识分子。小说里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件,只不过写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4]。可见作者的写作起点仍是为大时代代言。这就不难理解小说《美丽》既想张扬人性有所突破,却又使故事的发展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两种话语的冲突与矛盾性使小说作品“发出的声音难免含混不清”,在文学性上也有一定的缺陷。
虽然作为道德小说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涉及到对人性的分析与探究仍是一种文艺创新的好苗头。这篇小说在题材上将“三角恋”和“婚外恋”这种广受争议的男女关系引进小说,甚至让国家干部也成为关系中的一角,如此大胆的取材,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定的自觉性和文艺创新意识。而对人性的大胆描写——季玉洁对首长炙热而隐忍的爱,姚华临死之际对于爱情婚姻的霸权心态等,其中一些真实的人性因素的显现也成为这篇小说后来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
综上,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一定要回到它所在的历史现场。《美丽》虽然脱离不了其特殊的时代局限,但在文学创作上的突破——对人性的试图描写却是值得承认的。而在文学创作上,正如为了迎合主流话语而损害作品的文学性一样,当下不少文学作品也走向了反面极端——为了远离主流话语而对历史及其人物进行着颠覆性的改写,赋予其过多的“人性”而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本身所应具有的“史”的正面意义。因此,文学如何与主流话语保持一定的“产生美”的距离则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参考文献:
[1]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J].文艺理论研究,2004(1):29-37.
[2]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李松涛.欲言又止的秘密诉说———试论百花文学中爱情题材小说的声音多重奏[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9.
[4]丰村.丰村小说选·后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90.
作者简介:周文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