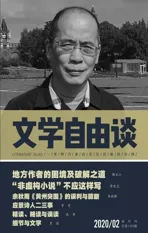应景诗人二三事
2020-01-02□李更
□李 更
报纸副刊的版面越来越少。我所编的文学副刊,从一周三版,到一周一版。编副刊的人数也是如此,当年,我们副刊编辑部有七个人,后来,只剩下我一个。虽然有基层作者在为我打气,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是我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从我的邮箱就可以看出。我以前是把邮箱印在版面上的,后来就不敢公开了。我们单位的局域网邮箱,几天不清理就会被挤爆,用“堆积如山”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经常是,等着见报的稿找不到,人家却是早就发给我了,其实是湮没在大量的投稿中,我必须“爬”无数层“楼”才能发现。
慢慢就没有多少自由来稿了。作者们也知道,僧多粥少。我们本地光是诗歌作者就有两百多人,这还是常规部队,还有许多网上诗人不在编的。他们自己也明白,一年能在报纸发表一次就不错了。
真正执着的,还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用笔写字的诗人。他们似乎在保持一种仪式感,或者,有人说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那么就一定得留下手迹。一个老友,诗歌发烧友,“老干体”,不折不扣的打油。自从漂亮女儿被领导包养又抛弃后,他便到处告状。后来,领导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就开始每个月给我寄打油诗,字迹潦草,都是五言绝句那种,后来干脆三句半,都是应景,或者叫应急。坚持十几年了,水平实在达不到发表的要求,但是,我知道这就是他的全部寄托。我不知道他换的新电话号码,托人带话给他: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为什么老写信呢?我请你吃饭。但他还是没有直接找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和他女儿都“神经”了。
真的有那种以文学养命的老人家,八九十岁了,在报纸上发表一首诗,马上奔走相告,翻来覆去把报纸读上几年。有的老人的孩子跟我说,老爷子发表一首诗,就能够又活一年。
我早已经想不起来我上一次用邮票是什么时候了。可是,现在仍然有人通过邮局寄稿,而且还是挂号。其中一位,不断变化花样,可能是怕我记不住他:先是平信,我十分吃惊,居然收得到;后来,他显然知道平信容易丢失,就寄挂号,寄快递。再后来,我开始不断收到邮局的催收条——这又是邮局的奇葩之处,你直接把邮件放到单位传达室不就得了?不行,要收上门费——我一问,是寄给副刊部的;副刊部就我一人,只有我去了。去一次还不行,人家邮局搬家了,于是再去。排队,就几个人还是排队,关键是,一个服务员在那里慢条斯理,可能是慢工出细活。两个钟头下来,终于拿到信。打开信封,直接血压高:还是那个老哥,还是五言绝句,还是应景。
应景也可以;很多应景诗人会不断改变造句用词,而他十几年没变过。元旦、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当然还有毛主席生日、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近年来还有平安夜、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光棍节……按照这些节,就写开了诗。其实我也跟他沟通了不少次,虽然我也不懂“老干体”,但起码知道怎么用词。
类似他这样的,至少十几人,纠缠我半辈子了。有脾气不好的,还经常去领导那里告我,甚至导致一个到文联混级别的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
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还真是称得上热爱文学。有的诗人只是因为干的行当和诗歌有关,就写诗了,属于干一行爱一行。我认识一个老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杂志做诗歌编辑,从此拿诗歌不得了,每天都要写一首,靠版面交换,到处发表诗歌,也不大不小得了某些奖。以前奖品都是什么镜框、搪瓷茶缸之类,后来老哥会混人脉,当上杂志主编了,人家给的奖品含金量暴涨,除了游山逛水,土特产都懒得往家拿,直接现金……直到把杂志玩儿完,他老人家退休。退休有一阵也抑郁,不能写诗了,因为写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找到发表的地方。不能发表,对于他而言也意味着写诗的终结。但是,这一天不写诗,他都想不出一个起床的理由。好在他以前帮助过的一个作者当公仆了,返聘他当一个杂志的执行主编。朋友们都说,街上一有事,老哥就写诗。这是他的生物钟,到点就闹,控制不住——体制内坐下的病,和武汉肺炎一样目前没有特效药——过节闹,过劫也闹,不闹不足以平民愤。他以前是著名的“节日诗人”,现在还可以叫著名的“灾难诗人”。
幸好像老哥这样没有什么才气的,虽然放眼望去,成千上万,互相雷同,相互撞车,但怎么闹也只是稿费多少润笔多少的问题。
但有的,喜欢炫技,显示才华,就不是老哥那样的简单追尾撞车,直接就是重大车祸,闹出事情了。
庚子春天,武汉爆发重大疫情。一些应景诗人以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也爆发性地创作了一大批诗歌。他们可能是想急切地炫才,也可能是为了痛刷存在感,泥沙俱下地把自己的作品涂抹在网络上,可以想象其中的平庸。于是,有的诗者为了突出重围,拿出了让湖北人武汉人非常痛恨的所谓诗歌。
其中两首,估计是可以按照他们愿望遗臭几年了。
《光明日报》已有评论了: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肆虐、全民群防群控顽强抗疫的节骨眼上,一些诸如《“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微信公号文章,却为了吸引关注,用非常不恰当的方式耍起了小聪明。“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勇往直前!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视死如归!”作者的“标题党”效果,不但没能引起读者任何的好感,反倒让广大网民感到愤怒。
抒情有很多种,但是没有一种是拿灾难拿国难抒情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认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十年,当时到处是文学“口炮”,我就喜欢和人进行抬杠式辩论。记得一次是讨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境界高低,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旁观心态,即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我认为鲁迅是个现场主义者,他的文学是积极参与现场的,他的文字是激情的;文学之于鲁迅的分量,就是大量的参与性的杂文。
再看林语堂,他在抗日烽火紧张之时,却还是一种纯粹文人的心态,每天就想着怎么做个文章以不叫自己闲过也,也许为了稿费,也许闲着也是闲着。比如他有一篇《胡桃云片》,便是“凭窗闲眺,想觅一个随感的题目”而憋出来的。他自己招认:“今天我对于展开在窗际的‘一·二八’战争的炮火的痕迹,不能兴起‘抗日救国’的愤慨,而独仰望天际的秋云,甜蜜地联想到松江的胡桃云片。”也就是说,家国兴亡,对于他这种文人来说,远不如自身的环境、感觉更有益于文章的灵感,所以,当人家在“愤慨”时,他却在“甜蜜”,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
不同的是,林语堂并不像某些文人那样要面子,“嘴上说抗日救国”,心里在为生计着急。他看来不紧不慢,“但虚伪还不如惭愧些吧”,便极其耐心地描写胡桃云片的款式、花色,细致于弘一法师的游闲之笔了。这算不算现在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起码,林语堂没有走到“冠状君”的地步,没有幸灾乐祸。他至少没有强迫自己去当应景作家。
2020年2月2日,“读一首好诗”公号推出陈衍强的诗歌《仰望天空》。这则写于2020年1月22日的诗共八行,如是写道:“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
这可比“冠状君”走得更远,直接开涮武汉人、湖北人。作者据说是云南什么作协什么杂志的负责人,可能是这种背景彻底惹恼了所有有正义感的文化人,遭到口诛笔伐在所难免,网络上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连云南省原作协副主席都恼火了,写文章讨伐:“ 陈衍强冒犯的不仅仅是湖北人、武汉人,而是中国的十四亿人!……像陈衍强这样不但不出手支持、声援,而是极尽损人利己之能事,借灾难为文谋取名利的,千古亦无几人!他已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人性,离禽兽已不太远!”
其实,如果在平时,文人之间的调侃也是无所谓的,口水诗也比那些“老干体”更方便应景,只是陈衍强选择的时间不对头。虽然湖北,尤其是武汉就是口水诗的重灾区,平常那里的诗人们也是到什么大街上、地铁里、围墙旁贴他们的口水诗,还经常搞像群众运动一样的口水诗歌朗诵会,互闻口臭,但是这个节点你不给点正能量,还借机会炒作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原谅。
当然,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好名坏名都是名,口水诗人、应景诗人的想法基本一致。
近些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所在的纸媒副刊版面逐渐缩减,甚至一周都保证不了一个。其实其他地区报纸副刊也基本上一样,还能出版的,也是不正常状态——有领导爱好文学的,会不定期出版副刊,可能主要为了满足领导的文学爱好。
我编了三十多年文学副刊,帮助的地区作者好几百人。副刊结束了,但是这些作者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破灭。为了继续他们的文学梦想,我开始放下自己的写作,到处找平台,因为他们中间的确还是有不少水平不低的作者,只是因为没有平台,而缺乏展示、交流的机会。我的一些老师、老友或多或少都在帮助这些体制外的作者。
当然,也有个别占有平台的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们可能认为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有一个诗歌月刊的主编,也是个应景诗人,以前主要在深圳一带活动,给当地文学掮客卖刊号,一直低三下四地周旋于老板、街道办主任之间。后来,有关部门对纯文学扶持力度加大,他马上摇身一变,从到处叫老师拜码头,变成鼻孔朝天。最近我试着给他推荐一位基层作者的作品,他几乎秒杀地给了我一个格式化回复,居高临下地告诉我:“你要多读经典,改变陈旧诗风。你这首诗要压缩,要重写,许多无效的词语表达要删去。”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打开我发的文件——我提交的是一组诗歌,他以为是一首诗,而且,估计他把我也当成和他一样写诗的了。我学习他当年低眉顺眼的口气问:“您能否具体指导一下,哪些属于无效词语?”他的回答是:“参!再参!”然后给我发了一份列有上百本书的书单,上面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资料性书目,大部分是他朋友的诗歌集。他暗示我去买来学习。
我告诉他,我不是诗人,发去的也不是我的作品;年纪大了,老花眼,你要求我读的书除了四十年前在大学读过的,其他的我都读不了啦,你留着自己卡拉OK吧。
我很好奇,上网查了一下他的动态。原来他好像爬到什么作协领导的位置了,搜索结果的大部分条目,是他和什么徽商在一起的活动。我问了一些了解他过去的作协、文联的朋友,他们都表示吃惊: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他们省的诗人告诉我,他只能靠自己编辑的刊物和别人交换发稿,是典型的应景诗人。
202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