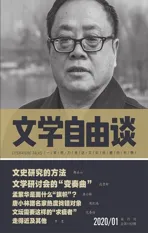诗歌真的病了吗?
2020-01-02牛学智
□牛学智
前不久,因为参加某个诗歌研讨会要发言,集中精力读了专门为该研讨会而出的一本文学期刊的诗歌专刊。该专刊有一百八十多页,诗人从60后到80后、90后共六十余人,刊诗二百一十首。从刊物栏目命名“60后:他们,黄金的刻度”“70后:他们,祭祀的青铜”“新生代:他们,黑铁的光芒”“她们,银子的歌唱”,亦可以看出,编辑是有意为着打破某种地域风格局限,在“诗意审美”层面,来展示当前的某种诗歌创作态势的。诗歌编辑成天埋头于诗歌阅读,他们当然了解诗歌运行轨迹。既如此,为了省点时间,一开始,我便把阅读定位在对“审美”和“审美形式”的体会与理解上,心想,兴许能有什么东西震撼到我。然而,通读完的感受是,我久已麻木的文学心灵的确被震撼了,不过,“振幅”好像不大,充其量是有“震感”。现在,我先把这些诗的审美形式大体归纳一下。
这些作品,可以先分为“面向社会的诗”“面向自我的诗”和“面向他人的诗”三个大的类型。面向社会的诗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欲言又止,植入批判,思想有张力。比如,王怀凌的《弯腰记》:“如果不弯下腰来/我就不可能看清堡子山周围深草中/若隐若现的坟冢/苗圃里擦汗的老人和地头上独自玩耍的孩子”,冯雄的《绽放》:“一朵花的绽放 也是这尘世/一点小小的幸福/当你把隐藏其中的苦难/呈示给一个失去理智的世界/谁在乎你的晨开晨落”,查文瑾的《石窟》:“佛在山洞里/原来他也怕风雨”,等等。尖锐的象征意义总是隐藏在常见事物和日常词语中,当然也因缺乏进一步具象化呈现,诗句并不完整,只是泛化的批判而不是具体的尖锐,因此表意仍然比较抽象。
另一种是戛然而止,重在现象描述,思想趋于收敛。如,马占祥的《轰隆隆的落日》:“现在,我在山里,只静静看着轰隆隆的落日/低下头,在一座寺庙后藏下余光”,杨建虎的《从解冻的河流开始》:“远走他乡。从解冻的河流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等待——/水落石出”,等等。这类面向社会的诗,经常留恋于一物一现象,是轻轻触摸现象,不是深度分析现象,弄不好极易写成废话。这两首诗最后两句话看似有什么味道,其实是典型的废话。由此可见,面向社会的诗,实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社会内容。
面向自我的诗,有三类表现形式:其一,穷究其源,以叙述为主,审美形式呈追述式。如,梦也的《在我早年的文章里》每一节打头一句都是同一句话“在我早年的文章里”,追述了早年的思想初衷,也叙述了为什么放下那些“危险”元素的原因,但诗突然又结束于“有一包被偷偷掩埋的炸药包/不知什么时候爆响?”延伸向社会的诗意神经被掐断,作者选择了否定早年的自我,在检讨中把自我思想中的冒失、莽撞烫贴得平平展展、顺顺溜溜了。
其二,反躬自问,以心灵辩难为主,审美形式呈反讽式。如,安奇的《向西》:“就好像继续向西我就可以亲手捏制一个陶罐/盛满为我续命的水 古河道已经干枯 而水滴还在”,刘乐牛的《做自己的陌生人》:“有多少伤痛,我就接受多少祝福/夕阳惨淡的黄昏,我以/自己为天涯,对苦难的每次挣脱/都蕴含无限希望”,等等。辩难既有自我的根本动力在于体验到了比自我更大的力量、视野,又不全是自我内心修养的,而是对原有自我的一种轻蔑。这预示了一种反讽,将指向自我的重构。
其三,抉心以自食,以自我颠覆为主,审美形式呈解构式。单永珍的《供词》比较典型:“在培训学习期间偷偷约会/在咖啡屋耍过酒疯/在游泳池看过姑娘的乳房/在理论学习笔记里抄过下半身诗歌/在东岳山上和一群屠夫结义”。自我解构不同于自我辩难,后者不会改变心灵的方向,前者却是彻底推倒;后者有扩充、重构,前者永远在颠覆的路上。论思想力量,在所有面向中,恐怕唯独解构主义最有力量,因为它以自我解剖为窗口,一直会追究到一切僵化的根源,只要靶心不变的话。这一类诗歌也是当前中国诗歌中最稀缺的一种气质。
面向他人的诗,至少有以下四类姿态:一是以飞翔的姿态张望,思想是超脱的。林一木的《交还》写的是父亲,起始于童年命名,终止于家族命运:“父亲,它讲述的是一个家族命运的/僭越者/以羞愧之石/交还你的权力的故事”。他人命运并未融入自我,他人遭际也就最终仍然是供人远距离张望的“故事”。二是以抚慰的姿态俯视,思想是融入的。李耀斌的《送别》,所送之对象不明确,但里面有揪心的疼痛:“粘在指间的一缕白发/携带着我的体温,一段岁月/几场风雨的一缕白发”。俯视不见得高于飞翔,但俯视不会把轻的东西写重,飞翔却能,这是本质区别。三是以邀约的姿态审视,思想是他者化的。陈燕的《花祭》:“我仔细观察过/小区所有的植物/想必栽树之人和我一样/都深情于纯粹//除了洋槐/剩下的全是玫瑰”。最令读者生厌的修辞,是以自我经验或干脆以自我心灵为尺度,但这诗中巧妙地把自我与他人身份进行了置换,淡化自我认知的同时,认同也就产生了。虽然认同可能是片面和粗暴的集体无意识,毕竟,它们均比自我宽阔。四是以拥抱的姿态进入,思想是同一化的。杨森君的《藏书石》:“一本完整的书/只配神在月夜下轻轻地取出来/翻看它”。敬畏而至于到神的高度,基本上接近跪拜了。这种俯身向下的姿态,也许充满人文情怀,但多数时候与对象在同一高度,这就取消了诗应有的独立价值。
既然是谈当前诗歌的审美和审美形式,以上所列恐怕多有遗漏,很可能还会往下分解出更多的形式出来。不过,仅这几种类型,窥斑见豹,足以说明今天的诗歌写作,即便是纯粹审美和审美形式分析,也是相当单薄的。单薄在哪里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话说的不错。夯实审美感受和审美形式的,仍是诗歌的主题与价值取向。
通读完近二百页的诗歌专刊,一个突出的体验是一个味儿。自问也罢,拷问也罢,疑问也罢,反问也罢,几乎都合拢在自我内心的安宁、享受、幸福和诗意上。这就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要么诗人眼里的他人、现实、社会、世界真那样,要么诗人在睁眼说瞎话;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前者,显然是伪命题,60后、70后、80后和女性诗人,看同一季节同一片落叶,怎么可能是同一感受?如果是后者,一定是某种受用的诗歌选用、评价标准导致的集体感知体验的模仿。
不信,我们可以同有独特体验的诗人诗作稍作对比,便一目了然。
比如,“出走”“云游”,王小妮看到的是“割稻的人”“捡破烂的人”。我读到的这些诗人,他们也走得很远,看到了很多陌生的事物,但最后只说明自己如何要清静下来修炼自己。这是转了一圈的唯一成果,实在太简单了。王小妮诗中的那两种人,其实在别的诗人笔下就一个称呼:底层者。单从事实描述上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然而,诗如果不重视语义,等于白写。显然,王小妮眼里有人,而我读到的这些诗人,眼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一点得失。比如,“喝酒”,李白诗里确有不少酒气,也弥漫着醉态。但我读到的喝酒诗,诗人好像喝了假酒似的,昏头胀脑、摇摇晃晃、不知所云。比如,“死”“坟茔”“天堂”“孤独”“灵魂”“悲悯”,昌耀诗一般不直接写这些大概念,但处处感觉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力量;可我们诗里的这些东西,基本是“僵尸”或者看到了“僵尸”而已,意义含混。再比如,“幸福”“快乐”“享受”“静心”,杜甫也写快乐,但快乐的前提是“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后的“俱欢颜”;被诗界严重误读的海子,当然更写有不少快乐的诗,可快乐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但是“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而且还能自由地做到“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我们这些诗人的快乐,只在或主要在欣赏一朵花的开放,聆听一支小夜曲产生的明亮幻觉,走在充满阳光、雾霾及风雨的人间,等等。总之,大家脑中没有什么尖锐的时代问题意识。更可怕的还在于,更年轻的诗作者,似乎更加灰暗,更加阴沉,或更加轻飘、更加轻佻,仿佛一出生就一副人生退场的架势,或者没开始写诗就一副老态龙钟的世故圆滑样儿。这是怎么了?诗歌真的病了吗?
行文至此,我也不知深层原因在哪里,只是直感告诉我,大家不约而同如此一个味道,首先与某种时代趣味有关。那么,我愿借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一书中的一个观点来结束本文。他批判的是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姿态、身段的人文知识分子,他说,在他们眼里,“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软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我读到的这些诗人诗作,也许还不止于此,但是他们异口同声的那种柔绵、哼哼唧唧乃至于少年强说愁的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实在与大英图书馆里的那帮中产阶级学生趣味,并无什么特别的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