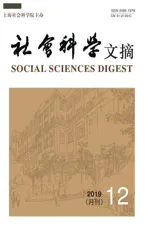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70年
2019-11-17孟繁华
文/孟繁华
“当代文学”的概念,按照洪子诚先生的看法,是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在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中确定的。但是,当代文学的“前史”早已展开。这个“前史”,不止是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具有中国当代文学“元理论”“元话语”性质的著作,同时也包括“当代”不同时期具体的关于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的评论;包括自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刘绶松、张毕来、丁易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表达的历史观和讲述方法,甚至也包括季莫菲耶夫的《文学理论原理》、毕达科夫斯基的《文艺学引论》等苏联文艺理论著作对我们文学观的深刻影响。这个“前史”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同时它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的依据和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个“前史”,当代文学史后来的研究和“问题”就是空穴来风。
当然,70年来,不同的历史语境,那些含有内在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以不同的方式控制或影响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因此,当代文学史在70年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用洪子诚先生的观点,“当代文学”的概念是“被构造出来”的,“当代文学史”当然也是被构造出来,任何一种历史都是“被构造”出来的。70年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历史语境的规约,当代文学史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形态,即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这三种文学史研究形态,都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一部分。当代文学史形态的变化,也恰恰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
文学史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
当代文学的“前史”,在“十七年”规约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向和要表达的具体内容。这个趋向和具体内容,在后来书写的各种当代文学史中有更加具体的表达。一方面是对文学“异端”的清场,一方面是对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树立和保卫。后来的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的归纳最有代表性。其中最典型的是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受到肯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他就成了“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他通过高产稻种增产丰收,证实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证实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梁生宝不是集合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和塑造。
但评论界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并不一致。不同的看法是,梁三老汉这个形象比梁生宝更有血肉、更生动和成功。1960年12月,邵荃麟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路线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说:“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邵荃麟的的观点不止是对一个具体人物和一部小说的评价,事实上他还是从维护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角度看待梁三老汉的。
这些材料尚未公开之前,严家炎对《创业史》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他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对作品的主要成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创业史》的成就主要是塑造了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这一观点与邵荃麟不谋而合。邵荃麟、严家炎从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考虑,认为作品真实地传达了普通农民在变革时期的矛盾、犹疑、彷徨甚至自发的反对变革。梁三老汉在艺术上的丰满以及他与中国传统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是这部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这一看法在当时是不能被接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需要那些犹豫彷徨的人物。梁三老汉符合人性和人物性格,但与当时建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因此,这一评价没有成为主流声音。
对《创业史》人物的争论,后来演化为文学界的一个重大文学事件。这就是“中间人物论”的肇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与文学史的“当代性”
1985年及其前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重要的年代。文学界经过“人道主义”“西方现代派”“寻根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的讨论,虽然乱花迷眼,却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野,无论参与者持有怎样的观点,有怎样不同的身份和背景,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界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那个给所有人以希望的大时代,预示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文学史观念的变化,离不开这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因此,对4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80年代是一个走向新的开始的年代。
1985年10月29日,唐弢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对于唐弢先生的看法除了少数支持者,反对者的声音更大,更言之凿凿。唐弢先生提出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固然是制约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方面。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可能从一个方面质疑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但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观点的正确。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限制,切近的历史很难把握在著史者的手中。每个人对切进历史的不同理解,使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免议论纷纷难成共识。虽然古代文学史也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但是,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古代文学史,无论怎样建构,它的基本作家作品、流派、现象等,大体没有歧义,其他的只是具体评价问题了。现、当代文学史的情况与古代文学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唐弢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但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未免周全。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樊骏先生的《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严家炎先生的《求实集·序》等,就知道在那个时代从事文学史写作是多么困难。时事政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风吹草动,甚至某个人的主观意志,都会干扰和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都会为文学史的写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唐弢先生后来曾经深刻检讨过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左翼作家联盟的评论,对在《新月》杂志上攥稿的作者以及某些所谓“第三种人”的评价,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徐志摩、钱锺书、杨绛等的评价。对周作人、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评价,他多有检讨并“深怀歉疚”。但是,唐弢先生是有自己写作现代文学史想法的,比如“论从史出”“以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和风格”等,但都无法实现。因此,唐弢先生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唐弢先生对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怀有偏见,他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实践,通过处理各种与文学史写作没有关系的各种问题才表达这一观点的。他是有切肤之痛的体会才说出这番话的。反对者很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或忽略了唐弢先生的初衷或苦衷。
与唐弢先生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同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文章一出反响巨大。文章认为,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在论述这些“进程”的时候,它涉及的问题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德特征;以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他们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文学评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说:“《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的同时,陈思和、王晓明等上海青年批评家也思考着同样问题。特别是陈思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的提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出一辙。他们在《上海文论》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是文学史研究的另一引人注目之举。这两个与文学史有关事件的思路不完全相同,《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是一个关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和思路;“重写文学史”更注重于具体的评价实践。
这两个文学史观念,在后来的研究者那里几乎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是,现在看来可能都被夸大了。黄子平后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当粗糙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更重要的是,自以为来到了一个新时期,才使构思文学史“新剧本”有了可能。
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与学术话语的建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国际语境已经形成,这个语境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冷战结束后,中国文学悄然地进入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文学家不仅相互沟通交流文学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认同也不断相互妥协的过程。比如文学弱势地区对本土性的强调和文学强势地区对文学普遍价值坚守的承诺,其中有相通的方面,因为本土性不构成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对立和挑战;但在强调文学本土性的表述里,显然潜隐着某种没有言说的意识形态诉求。但是,在“文学联合国”共同掌控和管理文学事务的时代,任何一种“单边要求”或对地缘、地域的特殊强调,都是难以成立的。这是文学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语境决定的。这种文学的国际语境,就是我们今天切实的文学大环境。因此,无论是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还是文学史的专业性——即学术话语,既有国内同行的对话,也包括同国外汉学家以及国外文学创作的比较和对话。
世纪之交,一批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集中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董建、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此间还有包括中国当代文学部分的、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形式出版的多种文学史著作以及不同的文体史,比如散文史、诗歌史、批评史,等等。这些文学史著作集中代表了这一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水平。
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史领域最高成就的,还是洪子诚先生。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于1999年8月出版后,不仅是国内高校使用最多的教材,而且已有英文、日文、俄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等译本,韩国文、意大利文正在翻译当中。洪子诚是一位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洪子诚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延续了他《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思路,但比后者更丰富,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没有从传统的1949年10月或7月写起,而是从“文学的‘转折’”写起,其中隐含的思路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社会历史事件,它的性质已经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开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和强化,并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文学规范和环境。这样,他叙述的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他的视野显然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而对“转折”的强调,则突出表现了洪子诚的学术眼光。或者说,过去作为诸种潮流之一种的文学选择,是如何演变为唯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学方向的,从而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比对具体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要得多。而对这“问题”的揭示,才真正显示了一位文学史家对“史实”的辨析能力。他对“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题材的分类和等级、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红色经典”的构造以及文学世界分裂的揭示等,是此前同类著作所不曾触及或较之更加深刻的。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同样也有各种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能是一部没有“问题”的文学史或“理想的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肯定存在某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他的“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不仅会理解他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的熟悉,更有他治文学史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坦诚。他的“犹豫不决”,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多的是他治当代文学史的切实感受。
所谓重写文学史,就是将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化。我们之所以要重写当代文学史,就是因为对此时的文学史不满意。重写,就是重新历史化,就是我们要不断应对新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化,有两个重要的参照,就是“时间”和“逻辑”。这两个参照的概念互为表里,与文学史家要描述和构建的文学史诉求有直接关系。时间的起点是描述性的,逻辑的起点是构建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我们在试图把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同时,其实就是不断地重写文学史。这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因此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探索之地。70年来,在这个领域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建构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连同它的问题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当代文学的面相。它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沉潜和稳健的领域,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领域。它取得的成就、不断整合的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整体地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