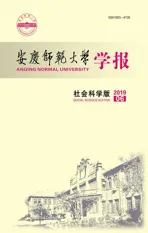1927—1937年国民政府省厅督导县政制度的施行及其弊端
2019-03-15梁华玮
梁华玮
(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淮南232038)
“省”之名称,虽自元代以来沿用至今,但“省”之统驭基层组织的监管功能则源于秦。自秦汉实行郡县制以来,秦汉之郡、唐代的道,宋代的州等皆形同于省之组织功能。至元代,“省”才正式形成一级组织,并一直延续至今。“县”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后逐渐成为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基层组织,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基层行政单位。自民国以来,近代中国的政局混乱不堪,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至1928年底才在形式上实现统一,但统一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增强中央权威,努力改进地方政治,整合中央与地方,以达真正的全国统一。国民政府依孙中山手订的《建国大纲》,在地方制度上实行省县两级制。省级主要设省政府和各厅,县级主要设县政府,具有官治和自治两重性,因此,相对应的省厅对县政实行监督和指导职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国民政府对地方建立一种严密的机制来进行督导和监察,而这种机制的主要部分就是省厅督导县政制度。目前学界对于县政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从省厅督导县政的角度的研究成果则较为缺乏,成果鲜有。①国民政府县政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翁有为:《国民政府县政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王先明、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自上而下、从省到县为视角,对省县制度设计、运作弊病和效果等方面略作探讨。
一、省厅督导县政的制度设计
整个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地方行政制度始终实行省县二级制。“国民政府肇建以来,地方制度采用两级制,县之地位,固与过去无何悬殊,县府仍为亲民之机关,职居荐任,对上则经过省府间接受中央之命令。”[1]11也就是说,县政成为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县为自治单位,载在政纲,是国政之泰否,即系乎县政之良窳。”[2]因此,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权威,必须治理和整合地方,而对县政的监督和指导主要依赖于省厅。
(一)宪法性质的法制
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代表其政权性质的宪法制度中,对省县的规定基本都有相同的内容。例如,国民政府在1931 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规定:“省置省政府,受中央之指挥,综理全省政务”,“县置县政府,受省政府之指挥,综理全县政务。”[3]95在1936 年5 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又有相同的规定:“省设省政府,执行中央法令及监督地方自治”,“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长办理县自治,并受省长之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办事项。”[3]116-117
(二)省级方面的法制
国民政府省制的主要依据是《省政府组织法》。总体来看,省厅督导县政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省设省政府,综理全省政务。省政府实行委员制,设委员若干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职权主要包括:在不抵触中央法令的范围内发布省令,制定省单行条例及规程;划分或变更省辖地方行政区域;全省官吏之任免等。也就是说,省政府作为县政的直接上司,具体负责监督指导;同时还对县官的奖惩、请假、考绩等进行监督。
第二,省政府内主要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各厅设厅长指挥监督所属职员及所辖机关,对主管事项得发厅令。各县事务均由各厅处分别负责办理,民政厅职掌为县行政官吏的提请任免,县地方自治及其经费,警察保卫、赈灾等。财政厅职掌为省税及省公债,预决算编制,省政府收支等。教育厅职掌为管理各级学校,社会教育及学术团体等。建设厅职掌为管理公路、铁路、河工等。换言之,各厅作为职能机构,主要负责的事务恰恰就是各县具体办理的主要事务。因此,各厅与县政的关系,就主要在于前者督催、监察和指导后者履行这些职责。
(三)县级方面的法制
国民政府颁行的《县组织法》,成为县制的主要依据。综合来看,县政必须接受省厅的督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县设县政府,在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事务、监督地方自治;在不抵触中央及省的法令范围内,可发布县令并制订县单行法规。各县政府所属各局之组织及权限,除法令别有规定外,由各省政府定之,并咨内政部备案。县政府于必要时,得呈请省政府设置卫生局、土地局、社会局等其他专管机构。如有缩小范围之必要时,得呈请省政府改局为科,附设县政府内。
第二,县政府按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财赋多寡分为三等,等级由省政府编定。县政府设科多少和科员数额,由省政府决定。县之废置及县区域之变更,由省政府咨内政部呈行政院,请国民政府核准公布。县内的区及乡镇区域之划定及变更,由县政府呈请省政府核准实行,并由省政府咨内政部备案等。
从上述制度设计来看,国民政府对县政的法制规定太过繁多和密集,以致对县政造成束缚和限制。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县政所处理的具体事务众多琐细,加上各区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又复杂各异,这就使得单靠教条僵硬的法制规定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对此,有人指出,“建国大纲虽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然训政时期约法八十一条之规定县政府受省政府之指挥,是县之无独立地位,一如往昔的情形。”甚至县的职权,“在县组织法中亦未加规定,此则纯为当时立法者之疏忽”。县政府所处地位之困难,“基于职权之混淆而生”。理论上,县政职权“有自由裁量及省令办理两种,前者为本身之职务,后者为代理省政府办理之职务。现因此两种职务并未区分,省中往往过分干涉县之行政,事实上县政府乃无独立之职权。县之行政自然不克发达。”[1]11-12换言之,省厅督导县政的制度设计已经显示其“异化”特征。
二、省厅督导县政的施行及其弊端
国民政府在统一时期主要精力放在军务上,无法集中关注县政。至统一全国后,国民政府才正式着手开始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重视省政和县政:一方面,在法制方面,推行修订的《省政府组织法》,颁行《县组织法》等。自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后,首次颁行《省政府组织法》以来,分别于1926 年11 月、1927 年7 月、1927 年10 月、1928 年4 月、1930 年2 月、1931 年3月进行了六次修正;自1928 年9 月国民政府首次公布《县组织法》以来,又分别于1929年6月、1930年7月修正公布,最终逐渐形成具有国民政府“特色”的省制和县制。另一方面,在行政区划方面将原先的府、道等地方一级裁撤,并加以重新划分和合并,全面实行省县二级制。例如,国民政府先于1928年6月将原来的京兆、直隶合为一个省,即河北省,不久新设青海省、宁夏省,后又将原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改成为四个省。到1929 年1 月,国民政府又将原奉天改称为辽宁省,以全面实行省县二级制。
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省厅督导县政制度却产生了诸多严重弊端。诚如时人所言:“从县政的立场上看,我们所需要于省的,只是监督,而不是宰割。”[4]7主要表现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省厅政出多头,造成县政无暇顾及和政务废弛。由于职责不同,不同上司对县政下发不同的命令。时人明确指出:“省政府有民财建教四厅,再加保安处,禁烟委员会等,起码有六七个机关,对县政府下命。各厅处咸以本厅处之立场为观点,认其主管之事件,为当前最要之急务,同时督责于县,限期执行。”于是各县便敷衍了事,“虽有许多想作事的县长,事实上亦逼迫得他不能作事”[5]17。对于此种弊病,蒋介石也相当清楚,指出:“各厅处骈肩而立,各成系统,各固范围,各私财用”,“同时督责于县,县长莫知所先,亦无法同时并举”,“吏治之坏,此种畸形制度,实为厉阶!”[6]358此类政出多头的弊端必然造成县政废弛。“政出多门,百务丛脞,结果一事未举,一利未兴,此实为今日各省之通病。”[7]5
第二,省厅不协调,造成县政纠纷不断。有学者批评说:“各厅举政,各不相通,有时甲厅认为必行之事,而乙厅则觉其可缓,有时乙厅通令废止之事,而丙厅方严催举行,于此纷纭错杂之下,县政府遂成为最困难而最繁复机关!”此种弊病较为普遍,“以中部各省为甚,而中部各省中,又以豫鄂皖为最。”[7]1例如,有的县“自缩减政费后,每县不过月支八九百元,仅可用秘书一人,科长二人,科员书记各一二人而已”,但是财政厅却令“各县设立财务委员会,以管理地税收支”,“调县政府职员兼充之”;同时,民政厅又令“各县设立清乡善后委员会,以办理地方善后事宜”,又要“调县政府职员兼充之”,实际上县政府自己“政务丛脞,事积如山,安有职员之可调?各厅明知之而不顾也。”[7]2
第三,省厅“朝令夕改”,造成县制时常变更。对此,有时人指出:省政府“对于各县的公事,朝令夕改,毫无定见,即所谓‘官样文章’,也弄不妥当。”[8]3例如,1932 年有监察员检举江西省政府擅自变更地方制度。“查现行地方制度,省与市县之间,并无第三种组织,亦无何种行政长官。”然而,江西省政府“不遵现行法令,亦不经中央核准,自由变更行政组织,自由制定与中央法令抵触之条例,划江西全省为十三行政区域,每区新设一行政长官,其违反法令,破坏行政系统之罪,虽有百口,亦莫能辞。”[9]111同时,省县变动频繁,以致县制没有连续性。当时有人指出:省县“频频更调,而旧去新来,又复各有主见,往往前事尚未举行,后事忽又变更,或前令限期完成,后又通令废止,遂致办法日多,而效率甚尠。”[7]5-6
第四,省厅乱发政令,严重干扰县政运作。省厅经常发布某些政令,严令各县推行某些政事,但不从实际出发,造成这类政令实难推行,反而阻碍了县政。有学者认为:“厅长对于各县实际情形,及农村状况,又太隔膜,遂致厅令与各县事实,往往背道而驰。”各省“所颁行法令规程,积之可成巨帙,对于察吏安民,防饥御匪,殆无一不备,惜皆成于学者幕僚之手,而非从农村实际考查得来,故常有窒碍难行之处。”[7]4这种随意性的政令必然造成县政的财政和精力耗费。“一县府之经费无多,一县长之精力有限,欲于同时期,对其层峰所嘱之事,百端悉举,兼筹并顾,匪特人事所难能,抑亦财力所未许。”[10]4
第五,省厅不作为,造成县政乱作为和不作为。时人注意到,省政府主席“终日忙于会客赴宴,迎送贵宾,除每星期例会主席外,实无暇与各厅长讨论政事。”各厅长“只知孜孜于部属员司之任免,求差谋事者之安插,更益以私人交际,公共宴会,亦殊无余暇以治其正业。甚至出现民政厅长“不知一省户口若干”,建设厅长“不知一省出产若干”,教育厅长“不知一省学校若干”,财政厅长“不知一省捐税若干”等怪象[7]1。省厅不作为必然造成县政乱作为和不作为。例如,江苏省“曾通令各县,依法编组正式保卫团,并限期训练完竣”,而实际上除少数县“稍著成绩外,大都皆属奉行故事,搪塞功令,乌合之众,何胜警卫,致剽刧之案时间,反动之迹潜滋,县政暗礁,莫此为甚。”[2]18有的县长不仅不作为,而且还贪污腐化,勒索压榨。1928年3月,安庆巿商民协会电蒋介石等人说:皖北一带,“各县巧立名义,苛捐重税,人民被其诬□为土豪劣绅,勒捐至数万以上者,尤不可胜计。”[11]
由上可知,这种省厅督导制度的实行产生了诸多令人无法预料的弊病。换言之,此制不可能实现原来之目的,已经产生了普遍性的“异化”现象。
三、省厅督导县政的效果及其原因
国民政府通过省厅督导县政制度,到底取得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是否达到原来的目的?其实,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这种制度的实行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反而产生严重的腐败。对于县政情况,时人明确指出:“我国目前县政之腐败,已成不可讳言之事实。”[12]1不仅如此,县自治事务及县政组织功能已呈现废弛状态。有曾任县长的官员指出:处于国民政府统治核心的江苏省,其县政实际上“不过等纸上之谈兵,各种自治之推进,亦仅具承转公文纸赘疣机关,殊鲜举办自治事务之成绩。”[2]17又如,1932 年,蒋介石在致安徽省政府主席电文中严厉批评安徽“县政又颓废不堪”,“一切善后工作迄无负责人员担任主持”[13]。再如,1934年,蒋介石又给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电文中批评道:“沿江各县如湖口、彭泽等城,一切腐败污秽如故,与前并无进步,此乃县长之不得其法,不知职守也,应注重督察。”[14]也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的县政已经造成漠视民众,与民众隔离。“中国近年政治,几无事不与民众隔离,主持政治者,又只知运用其上层理想,发为高论,而对于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八之农民生活状况,反多忽略不顾。于是中央大政方针,尝非各省所能实施,各省行政计划,又非各县所能通行,各县一切措施,更非民众所能承受。如此层层矛盾,事事分歧,政治如何能上轨道?人民如何能获政治利益?”[7]1
由于此制没有取得预期成绩,所以国民政府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例如,行政院下发明令,明确省厅与县政各自职责范围。1931 年4 月29 日,行政院核准《确定各省厅县局间指挥权限办法》,规定:省政府直接指挥、监督县政府;各厅对于主管事务,应秉承省政府,关于重大事务之处理及其政府职员之任免、惩戒,仍依现行法[令]规定办理,不得径自执行;县政府下设各局,专由县长指挥、监督,但各局长如无法定原因,不得随县长为进退;由县长遴选呈请核委之各局局长,除依法径呈省政府外,并应分呈各主管厅审核[6]330-331。1934 年7 月,国民政府公布《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将省府机构统一裁并为四厅两处,重新划定各厅处及其所辖机关职掌。并将所节余经费全部拨增各县政费,被裁人员应重行甄别,量其才能,以作充实县政人才备选之用等[6]346-348。同年11 月,内政部“通咨川、湘、赣、鲁、冀、绥、贵、桂、粤、浙、南京等各省市政府,于规定时间内一律实行合署办公。全国各省除河南、湖北、安徽、福建、宁夏、广西七省,均于民国二十三年内遵照办法规定实施外,其余如江苏、浙江、陕西、甘肃、四川、河北、察哈尔、湖南、山西等省及上海市等,均以此制确足矫正积弊增加效率,先后仿照实行。”[15]1934 年12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颁布《剿匪省份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1935 年1 月又颁布《剿匪省份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对县政进行改革,要求集中县政府权力责任,充实县政组织,增进县政效率,并将县政府所属公安、财政、教育、建设等局分别归并于各科,设科管理等[6]528-529。
尽管如此,但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国民政府仍未革除省厅督导县政的弊端,成绩鲜有。有人批评道:“省府合署办公实行后,省对县指挥太繁杂的毛病虽然去掉,但是监督太苛细的弊端,仍然存在。”[5]18对此,1935 年蒋介石也在政治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省县存在“上下隔阂”,各县“悉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然而,“县长遇有应须请示进行事项,亦复常苦省县远隔,不易秉承,以致为行政中心之县政,演成因循朦混之风气。”省与县间“均俨然形成两截,治官治民,遂均失脉络贯通臂指相使之效”[16]2。对于此类弊端,当时学者也有深刻揭露:“今之县政府除例行公事外,作任何大小事,必先呈省厅核准,然后始能进行,于县政之发展上,大有妨害。简直限制得县一事不能作,有临时之事件发生,若待省厅核准后再去作,或时过境迁,事情已不需要再作;或作亦较前多费人力财力。”[5]18
这种制度产生如此不良的效果,其原因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地方政治不良,“政治之积习未除”。“盖近年以来,地方吏治,虽不为国内贤者所注意,然争名于朝者,目光集注于中央政府,又值军事尚未结束,一切设施,亦未能归于正轨,于是有贪婪无识之徒,往往因缘或膺民牧之任,或居县长之尊,致使地方奸邪罔利之辈,乃得朋比为奸,相于推波助澜,剥削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酿成民怨沸腾,民痛加剧,而县政遂不堪问矣。”[12]1二是县政制度设计存在弊病,“县政制度之不良”。“县长职权太过分散,县以下各局长,由主管厅提出省府委任,每有不受县长节制,遇事径自向厅请示,县长有职无权,此亦为政治不能进步之一大原因。”“过去地方自治事业,户口调查等一无确实统计,致无可根据。”[16]还有学者分析指出:县政府没有多少权力,“因省政府之采用委员制,主席无集中统一之权力,事实上各厅等于各别独立之机关,均可对县政府直接下命令,是名义上虽祗受省府之指挥,然实际上县政府可有四五个上司。有人至谓县政府之地位,等于各厅之联合办事处,诚为实际上之情形。”[1]1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站在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实行省县二级制、省厅督导县政制度,其目的在于改善地方行政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中央政府权威旁落,地方军政势力膨胀,无法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整合。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后,在全国实行省县制度,通过省厅对县政实行督导制度,并进行了一定的制度改革,符合充实中央权威、实现国家统一的发展趋势,对于地方制度现代化的转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种督导制度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产生令人无法预料的严重弊端,造成县政的政务废弛、纠纷不断、乱作为和无能等,从而导致了原来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异化”。换言之,国民政府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督导,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解决省县政府运作机制的规范性和实效性问题。